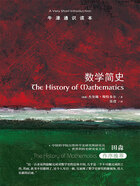
费马与他的定理
皮埃尔·德·费马生于1601年,在法国南部度过了他的一生。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律师,曾担任图卢兹议会的顾问,那是一个所辖范围很大的司法机构。费马利用所剩无几的业余时间从事数学研究,并且远离巴黎的知识分子活动圈,几乎完全是独自一人在做那些工作。17世纪30年代,他通过巴黎最小兄弟会的修士马兰·梅森与更远地方的数学家们进行交流。但在17世纪40年代,随着身上政治压力的增加,他抽身而出,再次独自进行数学研究。费马取得了17世纪早期数学领域内的一些最深刻的成果,不过对于其中的大部分,他只乐意用吊人胃口的方式提及一点点。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他的专题通讯员保证,如果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他会补充细节;可这种闲暇从来也没出现过。他有时会简单地陈述自己的发现,或者会发出挑战,直白地给出他正思考着的那些想法,却不透露他那些好不容易得来的结果。
他对大定理的第一次暗示便出现在这样的一次挑战中。1657年,他把信件寄给了英国数学家约翰·沃利斯和威廉·布龙克尔。他们没看出他在说些什么,并且认为若做出回应便失了身份而对此不予理会。费马过世后,其子塞缪尔在编辑他的一些笔记和论文时,该定理的完整陈述才为人所知。费马将它记在了他手上丢番图所著的《算术》一书的空白处。我们在适时回顾书中哪些内容启发了费马之前,需要简要地介绍一下费马大定理本身。
回想起上学时所学的数学,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的便是毕达哥拉斯定理。该定理指出,直角三角形最长一边(即斜边)的平方,等于两条短边(即两腰)的平方和。大多数人可能还记得,如果两条短边分别为3及4个单位长度,那么长边将为5个单位长度,因为32+42=52。这种三角形被称作“3—4—5三角形”。有了它,人们借助一根绳子就可方便地在地上画出直角;而教科书编著者也会用到这种三角形,他们想设置无须借助计算器便可解答的问题。
由三个整数构成而满足相同关系的集合还有许多,例如很容易验算52+122=132,再如82+152=172。这样的集合有时记作(3,4,5)、(5,12,13),等等。它们被称为“毕达哥拉斯三元组”,而且有无数个这样的三元组。就像数学家喜欢做的那样,现在假定我们稍微改变一下条件,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不是取每个数的平方,而是取它们的立方,又会怎么样?我们能否找到使a3+b3=c3成立的三元组(a,b,c)呢?或者我们能否更进一步来找寻一个三元组,使得a7+b7=c7甚至a101+b101=c101成立?费马得出的结论是尝试毫无意义:对于任何超过平方的幂运算,我们找不到使等式成立的三元组。不过,和往常一样,他把处理细节的工作留给了其他人。这一次,他的借口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空间不够:他说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证明,只是页边的空白处太小,写不下了。
丢番图的《算术》一书有个1621年的版本,是克洛德·加斯帕尔·巴谢所译。费马就在这样一个译本第八十五页的空白处记下了上述问题。自从1462年在威尼斯重新发现了一份希腊文手稿以来,《算术》一书就一直吸引着欧洲数学家。对于丢番图本人,人们过去一无所知,而现在所了解的就更少了。这份手稿称他为“亚历山大的丢番图”,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他在埃及北部那个讲希腊语的城市生活、工作,度过了人生中一段重要的时光。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埃及本地人还是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任何对他生活年代的估计不过是猜测。丢番图引用过许普西科勒斯(约公元前150年)的一条定义,而赛翁(约公元350年)则引用过丢番图的一条结论。这就将他的生平限制在五百年的跨度之内,但更小的范围我们就没法知道了。
与其他希腊数学领域的作者留下的几何文本相比,这本《算术》极不寻常。它的主题不是几何,也不是日常计账的算术。它其实是一组复杂的问题,要求整数或分数必须满足特定条件。例如,第二册的第八个问题要求读者“将一个正方形分为两个正方形”。出于眼下的目的,我们可以将上述问题转变为更现代的表述方式,从而能看出它与毕达哥拉斯三元组有关,即一个给定的正方形(如前所示,记作c2)可以分成或分解为两个较小的正方形(a2+b2)。当最大的那个正方形等于16的时候(这种情况下答案涉及分数),丢番图展示了一种聪明的方式来求解;之后他就转而去研究其他问题了。
然而,费马对此犹豫了,而且肯定问过自己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个方法可以扩展吗?人们能不能“将一个立方体分成两个”呢?这正是他在1657年向沃利斯和布龙克尔提出的问题(费马后来向他们通报说那是不可能的,随后沃利斯愤怒地反驳说这样的“负面”问题是荒谬的)。费马在页边空白处的提议实际上不仅适用于立方运算,也适用于任何更高次幂,这远远超出了丢番图所要求解的范围。
以上叙述中已经反复出现了另一个名字,所以让我们现在沿着历史的脚步从丢番图回溯到毕达哥拉斯,后者据信于公元前500年前后居住在希腊的萨摩斯岛上。尽管这一年代很早,但许多读者可能会觉得对毕达哥拉斯比对丢番图更加熟悉:作为数学史学家,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确实是“你会一路回溯到毕达哥拉斯吗?”毕达哥拉斯定理为人所知的确已有很长时间,令人失望的却是没有证据将其和毕达哥拉斯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几乎没有证据将任何东西同毕达哥拉斯联系起来。若说丢番图是个身世神秘的人物,那么毕达哥拉斯便被神话与传说所笼罩。我们没有出自毕达哥拉斯或其直接追随者之手的文本。关于他的生平,有幸保留下来的最早记载出自公元3世纪,也就是在他生活年代的大约八百年后,由作者们出于各自的哲学企图发掘而出。据说毕达哥拉斯在巴比伦或埃及学过几何;而这段出自推测的旅程,或许不过是那些作者虚构的,用来巩固他的地位与权威。至于他的追随者应该做过什么或者据信做了什么,这类故事可能有一定事实上的基础,但人们不可能确定其中的任何一个。总之,毕达哥拉斯简直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很多事都归在他的名下,可事实上人们对他并不了解。
毕达哥拉斯、丢番图、费马与怀尔斯,这四人的生活年代跨越了两千年的数学史。我们无疑可以追溯贯穿于每个故事中相似的数学思想,即使它们之间相隔了几个世纪。然后,我们就“完成”费马大定理由始至终的历史了吗?回答是“并没有”,而且原因还不少。第一个原因在于历史学家的一项任务便是将虚构从事实中剥离出来,并且让神话与历史脱钩。这并不是要低估小说或神话的价值:二者都体现了社会用来定义自身并理解自身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可能具有深刻而持久的价值。但是,历史学家一定不能让这些故事掩盖可能指向其他叙述的证据。在毕达哥拉斯这个例子中,比较容易看出貌似强有力的叙述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从最脆弱的话题中被编造出来;而就安德鲁·怀尔斯的例子来说,我们相信我们掌握了眼前的事实,也就更不易看出其中的问题。几乎所有故事的真相总是比我们最初想象的或是比作者有时想让我们相信的更为复杂,关于数学与数学家的故事也不例外。本章余下的部分便来探讨数学史上一些常见的神话和陷阱。为了方便起见,我将它们称作“‘象牙塔’版本的历史”、“‘垫脚石’版本的历史”以及“‘精英’版本的历史”。本书其余章节会接着给出另一些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