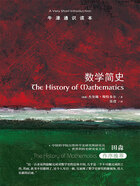
“象牙塔”版本的历史
怀尔斯的故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自己故意与世隔绝长达七年之久,这样他就可以在不受打扰或干涉的情况下研究如何证明费马大定理。费马显然也是个孤独的人。如果没有别的原因,那就是地理上的距离将他和那些或许已经能够理解并欣赏他工作的人隔开。我们已经谈到了丢番图与毕达哥拉斯,却也没有提及他们同时代的人。难道这四位真是开拓新途径的孤独天才吗?这对数学研究来说是恰当的或最优的方式吗?让我们回到“毕达哥拉斯”这个主题接着谈下去。
与毕达哥拉斯相关的故事一直声称他在身边建立或吸引了一个团体或兄弟会。他们分享了某些宗教与哲学观念,也许还分享了一些数学上的探索。不幸的是,那些故事还声称兄弟会必须严格保密,这自然给人们对其活动进行无休止的猜测留下了空间。但即便这样的故事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事实,毕达哥拉斯似乎也有足够的魅力吸引追随者。他的名字流传至今。这一事实的确表明他一生都受到尊重与敬仰,而且也表明他不是个隐士。
我们对确定丢番图的活动范围更有把握,他大概能在亚历山大享受与其他学者在一起的时光。几乎也可以肯定,他会有机会在庙宇或私人藏书中接触从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收集而来的图书。《算术》中的问题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发现;但也有可能是他从比如书面文本或口述等其他各种来源汇编而成的一个单本合集。这本书重复出现的主旨之一,是数学经口口相传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人,并如此反复。像任何具有数学创造力的人一样,几乎可以肯定丢番图同某位老师或自己的学生讨论过他提出的问题和相应解答。因此,我们不应把他想成一个私下著书并沉默寡言的人,而应将他看作一位重视学习与知识交流的城市公民。
费马即便受限于图卢兹的区域范围以及全职政务的苛刻要求,也并不像书中第一次出现时那样孤独。他早年在波尔多学习时有些朋友,其中一位叫艾蒂安·德·埃斯帕涅,此人的父亲是法国律师、数学家弗朗索瓦·韦达的朋友。韦达的作品原本并不多见,但由于这层关系,费马就有机会读到了。这注定会对他数学生涯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费马的另一位朋友是担任图卢兹顾问的同僚,叫皮埃尔·德·卡卡维。1636年,他移居巴黎时就随身带着关于费马及其发现的消息。费马经由卡卡维与马兰·梅森相熟;通过后者,他又与当时或许是巴黎顶尖数学家的罗贝瓦尔以及旅居荷兰的笛卡尔有了通信联系。后来,他同鲁昂的布莱士·帕斯卡及牛津的约翰·沃利斯交流了自己研究丢番图时的一些发现。因此,即便是远离重要研究中心的费马,也被连进了遍及欧洲的书信网络,这是一个虚拟的学者社区,后来被称为“文字共和国”。
说到怀尔斯,就更容易看到“孤独天才”故事中的裂痕:怀尔斯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后来在哈佛、波恩、普林斯顿及巴黎等地从事数学研究,在所有这些地方,他都是蓬勃兴盛的数学社区中的一员。最终使他对费马大定理产生兴趣的数学线索源自他与同在普林斯顿共事的一位数学家偶然的谈话;五年后,他需要新突破时便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来寻求该主题相关的最新思想;在证明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技术支持时他把秘密透露给了同事尼克·卡茨,并且把尚未解决的问题拿到了研究生讲座课中进行讨论,尽管最后除了卡茨外所有听众都走了;他在英国剑桥举行了三场讲座来公布整个证明,而在此之前的两周,他请同事巴里·梅热检查证明;最终的证明由另外六人检查;一个漏洞被发现后,怀尔斯邀请他以前的一位学生理查德·泰勒帮他一起进行修正。此外,在寻求证明定理的年月中,怀尔斯从未停止教学活动或缺席院系研讨会。简而言之,尽管他一人独处了那么长时间,但也融入了一个允许他如此行事的社区,并在他需要时提供帮助。
怀尔斯独处的岁月吸引了人们的想象力,不是因为这对一位在职的数学家来说是正常的,而正因为这不寻常。数学从根本上来说必然是各个层次的社交活动。世界上每个数学院系都设有公共空间,无论是凹室还是公共休息室,而且总配有某类书写板,以便数学家们在喝完茶或咖啡之后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语言或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很少合作撰写论文,也不会被鼓励这样做;但数学专业的学生经常富有成效地合作,而且还互教互学。尽管有现代技术的各种进步,但数学主要并不是从书本上学习,而仍然是通过讲座、研讨会及课堂来跟别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