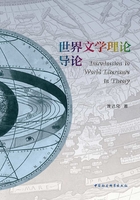
三 本雅明《译作者的任务》及其启发
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文化转向和各种“后学”理论的长足发展,而在这一股潮流当中有一篇文章影响较大——这便是本雅明的文章《译作者的任务》。[13]1923年,本雅明将波德莱尔[14]的诗集《巴黎风光》(Tableaux Parisiens)翻译成德文,并撰写了《译作者的任务》一文作为该书的导言。奇怪的是,此文却丝毫不曾提及波德莱尔及其诗集,因而完全可以抽出来当成一篇独立的文章。后来此文被追认为解构学派、文化研究派的翻译理论之代表作品。此后,与世界文学研究相关的许多论述都或多或少与这篇文章的相关观点若合符节。这篇文章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重新发现,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讨论,甚至是过度的阐释(在德里达那里便是)。这与当时的潮流相关:解构主义理论方兴未艾,伽达默尔、保罗·利科、德里达、保罗·德曼等阐释学或解构主义大师风行一时。[15]本雅明被“挖掘出土”,被重新发现,树立为一位翻译研究、文化批评理论和阐释学领域的先知。汉娜·阿伦特[16]、德曼、德里达等学者,一再回应他那些隐晦而深刻的观点。也因为后续研究者的进一步阐释,翻译研究被引入到阐释学研究之中,而阐释学也不得不面对《圣经》翻译的相关问题。
本雅明《译作者的任务》这一篇文章之所以极为重要,对作者而言则在于其直接讨论了翻译背后的终极问题:人类语言的神圣性的一面。本雅明生前最重要的好友之一舍勒姆[17]曾指出:本雅明借《译作者的任务》一文在语言哲学方面公开讨论起神学。因为其表述方式极为隐晦,充满了犹太哲学的神秘主义色彩。本雅明本人也极为重视这几页文字——因为这里面贯穿了某种相当于他座右铭的东西,或者说有一种信念寓含在里面。简言之,本雅明隐晦地赋予了译者以崇高的任务,即通过翻译找到多种语言的亲缘关系,弥合纯语言(德语“die Reine Sprache”,或译“元语言”,即英语“the pure language”)的碎片,重新找回失落的上帝语言。这无疑是一种类似于“返归巴别塔” 的隐喻。[18]
本雅明的论点有犹太哲学的神秘主义作为支撑点,所涉下面几点与我们讨论的世界文学理论密切相关,分别是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纯语言或语言的神圣性,可译性或不可译性。
(一)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与此平行对应的问题是:译者与作者的关系。本雅明认为,译作并不能帮助读者看见原作,因为阅读译文只能看出原作的基本信息,却无法传达最实质性的内容。文学作品的内容包括基本的陈述和信息(statement or information),而这并不是文学作品的本质,所以即使译作准确地向读者传递了原文所表达的基本信息,读者也无法了解原文的“本质”内容。而“本质”内容,本雅明将其解释为难以捕捉的、神秘的、“诗学”的内容,本身是无法传递的。本雅明认为,低劣的翻译传递的是文学作品中“非本质”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译者不应服务于读者”的观点,来源于本雅明对总体艺术的接受理论的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译文作为一种独立著作形式(而非原著的衍生品)的存在。
本雅明引入了“生命”与“来世”这两个历史性的概念来理解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以及可译性(或不可译性)的问题。他认为生命的长度不应以其自然生死为限度,而应以其“历史”为限度。[19]当一个生命的自然阶段结束后,其名声(或对外界的影响)将延续下去。本雅明将这种生命的延续比作“来世”。同样地,一部作品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其生命的终止,因为它的“来世”将作为其生命的延续而继续存在。由此可见,本雅明的“来世”并不是一个自然概念,不是真的“有生命”的,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才能理解的“对生命的显现”(manifestation)。这种观念在本雅明的思想中较为重要,因为实际上他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理解一切有生命的事物的历史。
在本雅明看来,译作者的任务是帮助原作在它的“来世”中获得一种永恒的、不断更新的生命形式——名声(fame)。本雅明将译作与原作的联系方式比作一种“生命线”(vital connection)。“翻译总是晚于原作,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定的译者,因而它们的译本标志着它们生命的延续。”[20]所以,译作对原作的显现不是对其生命(life)的显现,而是对其来世生命(afterlife)的显现。本雅明认为,“如果译作的终极本质仅仅是挣扎着向原作看齐,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译作。原作在它的来世里必须经历其生命的改变和更新,否则就不成其来世”[21]。这是原作与译作的区别,所以关键并不在于译作的“忠实”(fidelity)与否,换用本雅明在该文的后续篇幅中的强调“译作者的任务是在译作的语言里创造出原作的回声”[22]。这样强调差异,强调译作与原作平行对应但全然不同的观点,与传统翻译观念中追求信实的原则,可谓是背道而驰。
本雅明的讨论重心还在于重新解释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忠实”与“自由”(freedom)两个概念,并赋予其新的阐释路向。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忠实”与“自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是基于一种理念,即“译文与原文应当近似”。如前所述,本雅明认为译作的目的不是复原原作的意图,而是反映出对语言互补性的向往。传统翻译方法所遵循的忠实是对于原文语言的忠实,追求“复制”原文中词汇的所指意图。然而在本雅明看来,翻译永远也无法完全复制原文的意图,只能在意图上与原文的语言实现一种互补的关系。他使用了“花瓶的隐喻”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一个破碎了的花瓶,不一定有相似的碎片,但是应在细节上能够拼接在一起。语言同样是这样,语言之间呈现的是互补的关系,而非相似的关系。因此译作的语言应该更加“透明”,从而使 “纯语言”的表达得以实现。[23]
因此,本雅明认为,并不能简单地将译作看作对原作的复制。从翻译的意图上看,译者应当具备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寻找原作中的意图,而是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真理,即在一个更高的语言层面上译文要显示出与其他语言的互补关系。本雅明一再强调,译者并不亏负作者任何债务,也就是说,译者与作者之间并不是差等次序的关系。因为在纯语言的面前,两者是平等的,但又是互补的。格拉海姆(Joseph Graham)在重新理解德里达对本雅明这篇文章的分析时也已指出,“他们(指本雅明和德里达)都把翻译和阐释说成是语言的补充模式,即一个文本补充另一个文本的模式”[24]。以生命形态为喻,译本是原作的来世生命或延续的生命(continued life)。翻译是一种“特殊而高级的生命的形式”,译者的目的也不在于原作之中,而在于表达语言之间的互补关系(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s)。
(二)何谓“纯语言”?
为了解释译作与原作、译文语言与原文语言的互补性,本雅明特地解释了语言之间是“亲族关系”的理念,以便与传统翻译理论主张译作要与原作相近似的观点作区分。本雅明认为,语言之间的亲族关系,不体现在相似性上,而体现在一个整体目的之下的互补性上。“……在译作里,不同的语言本身却在各自的意指方式中相互补充、相互妥协,而最终臻于和谐。”[25]这种层次是最高的层次,即“纯语言”(或译“元语言”)的层次。
那么,何谓“纯语言”?下文我们便尽量以本雅明的思考来解释。[26]本雅明借犹太神学里“纯语言”的概念来论证语言起源的神圣性,或一般世俗语言背后所隐含的神圣语言。在作为整体的每一种语言中,所指的事物都是同一个,然而这同一个事物却不是单独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而只能借助语言间相互补充来显现总体的意图。纯语言,体现了语言与启示(或者说形式与意义)的即时统一。尽管现实的人类的语言已经变质,却仍蕴含着“纯语言的种子”。因此他指出“语言从来不可能提供纯粹、简单的符号”。在每种语言及其作品中,除了可传达的信息外,还有某些不可传达之物,那就是纯语言所承载的真理。不可传达之物,需要以直译的方式来暂时地完成其本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应当试着去理解本雅明的思想,即便是我们不认同其思想(假设或推断),但还是应当看到其思想对于理解世界文学和翻译研究之关系的种种启发。事实上,本雅明曾将语言划分为三种,即人类的语言、物的语言和纯语言。(1)纯语言,即为上帝(神)的语言,这种解释来自于犹太神秘主义哲学,但后来却影响了20世纪的阐释学理论。纯语言不是来自历史和现实,而是来自神学、信仰,有不可证的一面。基督教《圣经》中《新约·约翰福音》 第一句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这个汉译的“道”,便是“言”(Word),便是“logos”(逻各斯)。在本雅明或其他受犹太神学影响的学者那里,最深刻的精神,最高的、不可置疑的真理,无疑是来自上帝的语言。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是具有某种“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因为作品中所寄寓的那种普遍主义,便是来源于“上帝的记忆”。故而,译者的宗旨,绝不是为了读者,而是为了超越性的真理。(2)按照本雅明的思路看,人类的语言与上帝的语言有本质的区别。上帝的语言具有本质属性。如《圣经》所示,当上帝叫出某物时,便立即在给予其命名和定性的同时,赋予了其本质和连带的各种知识体系。所以,上帝的语言是一种“创造”,而人类的语言并不能“创造”,只能是认出或识别。人类仅能通过语言认出物和知识——这些都是上帝所创造的。(3)在纯语言和人类的语言之外,还有物的语言。本雅明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认出物,是因为物向人传达了其自身,凭借的是上帝创造万物时在物的身上遗留下的精神实质。这种残留下的精神实质,即是物的语言。本雅明的语言哲学观,虽然颇有神秘玄虚,无法验证,但其背后却有一种独特的历史哲学观念在支撑。
实际上,本雅明既没有精确地定义什么是“纯语言”,也没有确切地表明翻译工作真正能达到“纯语言”的层次。他的翻译观念便是建立在这种悖论之上。这正如他早已意识到翻译的不可能性(不可译性),却仍是必须要讨论其可能性(可译性)。为何如此?因为在他看来,语言若要在意图上完成一种持久的、终极的解决,这是超出人类能力范围的。因此,所有的翻译都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工作。尽管如此,翻译还是需要的,译作也仍然有其重要的价值。“在译作中,原作达到了一个更高、更纯净的语言境界。自然,译作既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境界里,也无法占有这个境界的全部。但它的确以一种绝无仅有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方式指示出走向这一境界的路径。在这个先验的、不可企及的境界里,语言获得了同自身的和解,从而完成了自己。”[27]换言之,译作有语言的“指向”但不能够“到达”“纯语言”的层次。这种悖论,便可用以理解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辩证关系。
(三)(不)可译性
本雅明的论述寓含了其神学观念,以及对语言的超越性理解,这一点正好体现在他对“(不)可译性”的思考上——而这也正恰恰反映出了他对于《圣经》“巴别塔叙事”的认同。概括地讲,他是这样认为的:人类的语言是不完整的、不自足的,在人的意图之上,总是存在着一种更高的整体性意图。换言之,本雅明的理论假设,与《圣经》中“巴别塔叙事”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他在《译作者的任务》一文的结语中,集中表现了这样的倾向:“在太初,语言和启示是一体的,两者间不存在紧张,因而译作与原作必然是以逐行对照的形式排列在一起,直译和翻译的自由是结合在一起的。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的潜在的译文;这在神圣的作品中具有最高的真实性。《圣经》不同文字的逐行对照本是所有译作的原型和理想。”[28]一般情况下,现代人(专门学者除外)阅读的《圣经》都是各个民族的现代语译文,因而可以说《圣经》及其译文一方面是讨论“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原型(prototype),另一方面《圣经》及其所有语言的译文也构成巴别塔在语言上的再现。犹太教、基督教都认为,《圣经》是上帝启示真理的语言,那么,人类的世俗语言便与这种神圣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内涵的张力,即“人言”与“圣言”之间是一种既统一又对立的悖论关系。实际上,《圣经》中所折射的语言问题,可以理解为同一问题的两个维度,即一方面,神圣语言需要被世俗地理解和表达,另一方面是这其中有一种困难:人类能否理解或翻译“上帝的语言”(超越性的真理)。一般情况下,宗教文本翻译的主要目的,便是让受众理解某种宗教,劝服他们接受教义。故而这一类文本充满了宣传和劝服的修辞。基督教是基于《圣经》文本的宗教,这就要求经文译者不得不肩负起既要追求语言之美,又要传播福音的双重任务。但这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之,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两者一体两面、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基督教《圣经》最独特之处。以上的论述,其实突出了关于翻译活动的三种认识:一是翻译这种工作对于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存在与传播过程所具备的重大意义;二是翻译所具备的“巴别塔”角色作用;三是《圣经》翻译中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俱存的问题。
在本雅明这里,影响可译性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在该作品的所有潜在译者中找到一个称职的译者,这是可能的吗?其二则更进一步:这部作品是否适合被翻译(有没有可以实现的潜能),是否在召唤翻译(一种意愿或目的的体现)?[29]很明显,第二个问题才是本雅明讨论的重点。他认为原文确实在召唤译者来翻译。原作的本质是原作的生命所在。把这种本质再次呈现出来,让其在历史中延续下去,则是原作生命的至高目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召唤翻译的原因。正如本雅明所说,“可译性是特定作品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作品必须被翻译;不如说,原作的某些内在的特殊意蕴通过可译性而彰显出来”[30]。在这种目的之下,译作者完成的正是这样的任务:译作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原作的来生,在历史中延续了其生命。
本雅明一再地重申语言之间的互补性,显露出他对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思考,以及对于终极目的——回归到纯粹语言的向往。[31]从一种超越的视角去观察“互补性”,则可发现:译作与原作一样,都是由一种语言组成的,都不能完全抓住隐藏在语言之下的意义的碎片。这暗示了人类语言的流动性和混乱性。“巴别”(babel)这一词汇,也正体现了这一点。从《圣经》的记述来看,“巴别”的本义就应该是“变乱”。上帝不希望人类有一样的语言,团结一心乃至因此无所不能成就,是以变乱人类的语言,使各言其言,无以沟通,这样人类也不至于有朝一日不知天高地厚,来同上帝一争高低。故而,核心问题正是语言的问题。
“巴别”(babel)一词,一方面是专有名词,不可译;但是另一方面它还充当着普通名词,意即“变乱”。然而,既然这个词是专有的、不可译的,将其译成“变乱”便造成一种语言的变乱。换言之,人类自以为有一种独特的语言可以把它转述,结果语言的变乱却已经发生。德里达指出“babel”一词,若以专有名词理解,则是一个纯粹能指对某一个个别事物的指涉,而作为普通名词则是关于某一类事物的泛指。然而,他援引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该词的考证,发现这个词有更多的含义。这里的“babel/变乱”至少有两重意义,其一是语言上的变乱,其二是塔造不下去时人类的不知所以状。伏尔泰从词源上考证出“babel”同时还有“父亲”的意思,代指“圣父上帝”。此外,babel/巴别,即希伯来语中的巴比伦,本意为“上帝之门”。巴别是混乱之城,也是圣父上帝之城。上帝以他的名字开辟了一个其他人无法沟通理解的公共空间。故而,若语言中只有专有名词,理解便没有可能;若没有专有名词,则理解同样没有可能。[32]这就是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一体两面的共生关系。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上帝,上帝给万物命名,他理所当然也就是原初语言(真理)的本原。语言本来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上帝以“巴别”为“变乱”,变乱了巴比伦城的语言,也变乱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所以在德里达看来,上帝是语言的本原,也是变乱的本原。
巴别塔的神话,解释了语言混乱的起源,也交代了各种族语言无以化约的多元性,以及翻译使命的必然性和不可能性。翻译从实际上看是势在必然,不可或缺,从终极上看则又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趣的是,德里达指出了一个我们容易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每每是在翻译之中读到这个巴别塔的故事。恰恰是翻译,使巴别塔的故事有了传播的可能。
巴别塔的坍塌和单一语言的解体,暗示着二者的重构是不可能实现的。对语言神话的颠覆从根本上消除了意义存在的可能性,也是对上帝存在的瓦解。这是对语言所做的哲学层面的阐释。正是借助翻译文本的多样性,德里达成功地拆散了语言意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并最终解构了西方哲学致力于通过语言获得真理的传统。难怪德里达会如此看重翻译,他甚至宣称:“哲学源于翻译,或者可译性这个论题。”[33]哲学人文学的最重要问题,便是翻译的问题,因为翻译就是阐释,反之亦然。翻译之必须,是阐释之必须,一如文字非经解读无以达诂。翻译之不可能,则一如一劳永逸的阐释之不可能。
在本雅明那里,翻译的终极目标在于重新拼凑出“纯语言”的花瓶,实现上帝的弥赛亚式回归。然而,这同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基于犹太神学的救赎观念而展开的论述,因而这种翻译观念是接近于神学的(在德里达那里是语言哲学)。在本雅明心中,原文和译文被理解为纯语言的花瓶被打碎之后的小碎片,而译文——尤其是众多彼此互有差异的译文,组合起来,才是人类得以窥探上帝语言(真理)的唯一途径。这一点体现了他的宗教神秘主义观念。
本雅明关于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辩证关系的讨论,以及对于纯语言的思考,在其他学者那里也能见到。在本雅明之前,德国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34]对这个话题曾有精辟的阐述。谭载喜总结道:“他(洪堡)一方面指出各种语言在精神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在结构上也是独特的,而且这些结构上的特殊性无法抹杀,因而翻译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任何语言中,甚至不十分为我们所了解的原始民族的语言中,任何东西,包括最高的、最低的、最强的、最弱的东西,都能加以表达。’……因而,语言结构差异和不同言语群体所产生的明显的不可译性,能够为潜在的可译性所抗衡。”[35]这很好地解释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关系以及翻译的纯语言追求。在本雅明之后,乔治·斯坦纳[36]也有相似的阐释。斯坦纳在其著《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考察的正是语言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从该书的题名就可以看出,作者采用的就是一种“巴别塔”诠释视角,本质上与本雅明的观念没有差别。正如任东升已经指出,“他(斯坦纳)把翻译看成是拯救人类的‘弥赛亚’(Messiah,意思是‘救世主’),认为因‘巴别塔’而变乱的人类语言最终要‘回归语言的统一’。‘人类分散语言之水注定要流归单一语言之海’。”[37]而且,这与德国犹太神学家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1886—1929)在翻译德语《旧约》时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每一次翻译,都是弥赛亚的拯救活动,逐步使救赎近在眼前。”[38]这一类的观点,尤其容易在德国犹太人学者的著作中看到。在他们看来,翻译是回归到巴别塔之前的努力,这是神学上的超越性思考。然而事实上,我们即便是剥除了其神学和神秘主义背景,这种思考或想象对阐释学而言,也有其益处。请记住,这是借用来思考的工具。正如斯坦纳在其书《巴别塔之后》中也借巴别的故事,详细地解释了“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因而翻译研究也使用阐释学的理论和方法。[39]
(四)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启示
翻译,可以看作一种诠释——这种论点,其实在20世纪上半叶也早已有许多学术论证,最重要的一种观点可能要数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论及的翻译的三种分类。
雅克布森曾将翻译分为三种:
(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或重新阐释;
(2)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如英语翻译为中文;
(3)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即跨符号系统之间的翻译。[40]
第一种是语内翻译,即同一种语言内部的解释,比如将古代汉语写成的诗词翻译成现代汉语。第二种是跨语际的翻译,即一般意义上所讲的翻译,是从一种语言符号到另一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比如从英语到汉语的翻译。第三种是符际之间的翻译,这是抽象而言的翻译,即以一种符号系统中的符号来解释另一种符号系统中符号的意义。比如,将一首诗翻译成一幅画或一段音乐,或者将一节文字翻译成一种表演艺术。雅克布森关于翻译的讨论有助于我们认识翻译的本质,即以一种符号虚拟地、假设地对等另一种符号语言。刘禾在其著《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之中讨论的各种案例,便是第二种翻译,即语际之间的翻译,以语际的词汇转换和合法化来看翻译背后的话语运作。[41]刘禾在后来另一本书《帝国的政治话语》(The Clash of Empires)中所讨论的超级符号(super-sign)“夷”的翻译则属于第三种。[42]刘禾这两本书都明显带有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解构主义倾向的意味。
本雅明的翻译理念在20世纪影响甚大,直接影响到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尤其是操控学派)、解构主义(德里达)、阐释学派(伽达默尔)等的发展。到20世纪末,翻译一跃而成世界文学研究的中心。当代的世界文学理论,大多是基于翻译的可译性理念而建构,例如达姆罗什的理论,便是强调世界文学文本的翻译、流通、再生产、再阐释的面向。然而,在近年来,世界文学研究的阵营内部也产生了各种反响,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纽约大学学者阿普特(Emily Apter)是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翻译研究理论的积极参与者。她对于世界文学理论中的“可译性”问题有其不同的看法。她认为,所谓企图通过翻译重建巴别塔,回到语言统一的状态,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神话。实际情况是,不可译性在现时代的全球文学流通中,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阿普特引起争议的专著《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的政治之维》(以下简称《反对世界文学》)一书,便是基于“不可译性”来重新讨论“世界文学”的理论和现实。[43]她指出,“近年来诸多复兴世界文学的努力都仰赖于可译性的假设。其后果是:文学阐释并未能将‘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或‘不可译性’充分考虑在内”[44]。故而,《反对世界文学》一书采用文学比较的方法,重新承认“非翻译”(non-translation)、误译、不可比较、不可译等情况的存在。“《反对世界文学》一书勘探的是这样的假设:翻译与不可译性,乃是文学的世界形式的组成部分(constitutive of world forms of literature)。”[45]阿普特认为,以往的翻译研究对本雅明谜一般的“纯语言”观念有许多讨论,却忽略了本雅明最为着迷的概念是“翻译的失败”,其中的误译、不可靠的翻译和曲解(法语“contresens”)都值得更深入地探讨。翻译的失败,在如下的两种情况下尤其明显。(1)面对不可说,不可理解、不可表达的超越性内容。比如基督教的上帝,中国《道德经》中的不可名状、无法解释的、玄之又玄的“道”。这是宗教的绝对主义(religious absolutism)。所有“神学上的不可译”(theological untranslatability),皆可归入此类。(2)有关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中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在本雅明看来,翻译不是将原文语言转换的工作,而是近似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工作。因此,面对不同文化传统的翻译研究,学者或读者必须持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这是因为在一个文化传统中正确的标准,在另一个文化传统中有可能便是错误的。故此,各文化和而不同,应当互相尊重。要之,阿普特从本雅明出发,挖掘出世界文学理论中被长久忽略的“不可译性”面向,有其独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