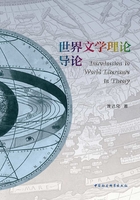
四 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文学?
翻译的视角,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世界文学”或“世界的文学”概念中包含的问题:全球化时代所谓“世界文学”,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文学?世界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前者看到了文化传统的差异性,而后者则看到了全球化经济市场带来的文化的同一性。实际上,文本(原著和译作)构成的世界,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世界”。这一个世界是由广义上的作者、译者和读者(包括批评家或学者等)围绕着文本(原作或译本)共同建构起来的,如韦努蒂所说的“翻译的共同体”或“文化的乌托邦”。
(一)什么样的世界?异质的想象共同体
韦努蒂借用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来思考世界文学和翻译的问题。[46]安德森把民族当成一种现代时期的“特殊的文化人造物”,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强调情感、意志、想象和感受在民族认同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安德森在论述现代民族想象得以成立的条件时,特别提到“印刷资本主义”时代下大规模印刷的小说和报纸所起的重大作用。比如,菲律宾作家黎萨(José Rizal,1861—1896)的小说《社会之癌》[47]构想了一个活动在同一时间(空洞的时间)和同一地点(殖民地、马尼拉)的、能够用共同语言交流的、超越各阶级、族群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接触。他们之所以能被当成一个共同体,有一大部分原因便是来自于文化想象,而报纸等新媒体在民族国家发轫期对这种共同体想象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报纸等新媒体让人们共享一种“同质的时间”。这是“民族”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一种“圣礼”。因此,这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但是是同质的想象共同体。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在认识论上借用了本雅明所使用的批评观念——一种“历史进步主义”的时间观念。在本雅明看来,历史进步主义建基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homogeneous,empty time)之上。“如果撇开处在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的进步概念不谈,人类的历史进步概念就无从谈起。对人类进步概念的任何批判,都必须以对前一种进步概念的批判为前提。”[48]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即各种因人因地之别而不同的时间标记内容都被淘空,变成由时钟一分一秒、逐年逐月地量化了的、一致的机械时间。唯有在这种同质的时间上,有着不同的情感体验的成员才有可能想象一个同质的共同体。
韦努蒂同时借用了“想象的共同体”和“同质的时间”这两种观念,但又有所改造、有所创新。他认为,翻译创造了一个个本土的兴趣共同体。翻译的本土铭写,产生了安德森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然而,一些对一个特定文本有浓烈兴趣的读者,尽管来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他们可以被当作一个读者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当中,各人对于这个特定文本的实际理解,可能相去甚远,甚至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49]因而这种共同体是异质的。读者的个人身份、情感认同和文化背景都不尽相同,甚至是其身处的时间节点,都不一定相同。这种情况,与安德森意义上的“想象共同体”中的成员具备的一种同质性(同时同调、同一种认同)完全不同。
韦努蒂总结道:“翻译活动中的本土铭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交流行为,不管多么间接或无常。它围绕译本创造了一个本土的兴趣共同体,能够理解译本并将其付诸各种应用的一个读者群。这种共享的兴趣,可能是在译本发表时自发产生的,吸引了来自翻译语言中早已存在的不同文化因素的读者。它也可能寓于某个体制之中,在那里,译文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学术的或宗教的、文化的或政治的、商业的或市政的功能。围绕着译文产生的任何共同体,在语言、身份或社会地位方面绝不是同质的。”[50]译作,正是连结本土和外国的可资想象的各种元素的一种载体。只要本土的和外国的读者对同一译作有了兴趣,不论其阶层和所属团体如何,这种兴趣都会使得一种新的“阅读”的共同体得以产生。然而,这种共同体是靠文化想象来维系的,读者们在现实中并无关系,甚至兴趣也不尽相同。这一共同体有时甚至会出人意料地焕发出巨大的文化政治能量。例如,韦努蒂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来解释这一点。他认为,严复《天演论》的译文所起的功能在于“构建了进步中国抵抗西方殖民者也就是抵抗英国的民族身份”,以至于译文中的“适者生存”在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之后变成人们广为接受的口号,对未来国族想象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51]因而,事实上这便是仰赖于民族市场中译本所发挥的“读者想象的异质共同体”所产生的力量。尽管这个读者共同体是异质的,成员也参差不齐,他们仍因为翻译文本而发生了种种联系,但是翻译文本包含归化与异化两种倾向(两个变量),因此翻译文本有可能会加强或者减少共同体的异质性。
关于这个以译文为中心的“想象共同体”的异质性问题,韦努蒂有其独特的观察。韦努蒂指出:“当以差异的这种伦理政治为动机的时候,译者就寻求建立与外来文化融合的一个共同体,分享并理解外来文化,进行基于这种理解的合作,进而允许外来文化改造和发展本土价值和体制。寻求某一种外国共同体的冲动本身就说明译者希望发展或完善某一特定的本土环境,在翻译的语言和文学中,在翻译的文化中,弥补某一缺陷。”[52]虽然韦努蒂认为异质性难以消除——不同语言环境之中的接受状况是无法等同的,但是异化的翻译可以通过质疑动摇一种语言环境中习以为常的主导价值和思维方式,从而使得读者的接受行为更加开放。因此,翻译就是为外语文本发明新的读者群——译者们明白他们对译本的兴趣是由国内外共同体读者所共享的,即使他们的兴趣并不对等。
韦努蒂在其著《译者的隐形》一书中指出,“翻译是这样的一种过程:译者根据解释的强度提供一系列的能指符号,用目标语中的能指链来替代源语文本中的能指链”[53]。翻译力图让人们相信它能够“透明”地传递异域文本,但它越是“透明”,则越是对异于本土语言文化的因素进行了压制和改写。人们从译本中看到了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或者自己已经习以为常的本土文化。韦努蒂认为有三种翻译情况使得译者隐形。三种情况如下:(1)当一个优秀的翻译者被认为应该是隐形的;(2)或一个优秀的译本被认为是在目标语中通顺流畅地再现原作者的意图;(3)又或者合格的翻译被认为能够为新的语言接受群体带来和原语言内的接受群体同样的感受。这三种情况,往往显示出翻译实践背后的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心态,或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故而韦努蒂主张一种异化的翻译(选择对目标语文化而言处于边缘地位的文本进行“不透明”的翻译,以在目标语文化中起到某种质疑既定意识形态的作用的实践),来替代翻译中的归化,因为后者是一种以目标语的文化价值观为中心的翻译实践,压抑了文化多元性的种种可能。
(二)“本土剩余物”: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韦努蒂认为翻译铭写着本土的价值观念,因而翻译活动是意识形态的,也是乌托邦式的。第一点不难理解,也已经被操控学派解释得非常清楚(前文已有论及)。韦努蒂则有这样的补充:“翻译活动总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翻译出某种‘本土的剩余物’,即与接受文化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地位相关的价值观、信仰和再现的一种铭写”[54]。第二点在此可重新梳理一遍。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翻译与世界文学的联系。我们一般所说的“意识形态”,即当下占据主导位置的价值观或信仰。“乌托邦”的概念,最早来自于托马斯·莫尔的同名著作《乌托邦》,意即“不存在的地方”[55]。韦努蒂这里借用的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56]的“文化乌托邦”(cultural utopia)的概念,意指一种尚未存在的存在,一种指向于未来人类可能的生存状态。
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原是指马克思主义之中的无阶级社会。在布洛赫看来,文化创造通过“剩余物”来实现,是一种立足于历史而指向未来的能动活动。历史或过去是作为文化遗产而存留至今的东西,而剩余物是撕扯开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坚固结合而隙漏下来的零星小点。这些零星小点是具有真正生命力的文化艺术杰作。剩余物使得精神生活成为可能,通过利用遗骸而创造出新的生命。“剩余物”是对当下意识形态的反叛,它指向一种乌托邦的可能性,而乌托邦理论往往具备了指引改造现实的力量。乌托邦具有批判现实的力量——这正如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所说,“一幅不包括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一瞥,因为它漏掉了一个人类永在那里上岸的国家。人类在那里登陆后,向外望去,看见了一个更好的国家,又扬帆起航。进步就是实现乌托邦”[57]。在韦努蒂那里,他把布洛赫的历史向度更换成翻译的向度,即翻译利用“本土残余物”(domestic remainder)铭写外语文本,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布洛赫意义上的“剩余物”。[58]剩余物是本土语言中的残骸。正是通过利用本土语言遗骸来铭写外语文本,这种翻译的行为才创造出了新的意义。
韦努蒂还指出:“本土铭写的意图就是要传达外国原文,因此充满了通过那个文本——尽管在翻译中——创造某一共同体的期待。残余物中存有一种希望——译文将创建一个本土读者群,分享外来兴趣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也可能是出版商眼中的市场。而且,只有通过残余物,只有用部分外国语境加以铭写时,译文才能在本土读者和外国读者之间创建一种共同的理解。在应用意识形态的解决办法时,译文投射出来的是一种尚未实现的乌托邦共同体。”[59]事实上,韦努蒂意义上的翻译的“共同体”和“乌托邦”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翻译的共同体是指同一译本的读者群体的构成,而其乌托邦则强调译文的文化功能,与上文提及的韦氏提倡差异性翻译密切相关。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作为两种与社会现实相关联的意识和精神范畴,具有相关也相区别的联系。[60]笼统而言,意识形态有凝聚人心的作用,但是其相关的思想观念较难产生一种改变社会现状的冲击力。乌托邦则是一种会对现实政治造成冲击、变革甚至颠覆性影响的意识和思想内容。其自产生开始,乌托邦便是作为一种政治讽寓(political allegory)而出现,具有强烈的现实的、社会的批判功能。[61]因此,韦努蒂所讲的由翻译产生的“乌托邦”,也可看作一种超越于现存秩序,并且可能会对它造成冲击、变革的思想。韦努蒂的这些思想观念对于我们讨论世界文学有这样的启示:或许差异性的翻译,才是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的合理做法,而翻译的功能便在于改变世界文学存在的状态,带来更加多元的文化,赋予改革的动力,最终开启未来的诸多可能。
让我们回到歌德和翻译的论题以结束这一章。歌德曾对其秘书爱克曼说,“我对《浮士德》的德文本已经看得不耐烦了,这部法译本却使全剧又显得新鲜隽永。”[62]这印证了上述的说法:译文让原作得到重生,是其继起的生命。事实上,歌德对于翻译有其自己独到的看法,也与我们上文的讨论稍有关系。
歌德曾在其著《理解西东合集评注》(1819)[63]中将翻译分成了三大种类,也是三个阶段,并提出了与其相涉的文体和功能。
(1)第一种翻译让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异国,散文式的翻译最好不过。[64]
(2)之后是第二个阶段:人们设身处地想象异国的情境,然而其实只获得了外文的意义,并力图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达。[65]
(3)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高的和最后的一个阶段,人们想要让译文与原文完全等同,这样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译文要与原文处于同一位置……至此,陌生与熟悉,已知与未知相互靠近的圆环终于合拢了。[66]
第一种即借助翻译来了解外国文化。歌德举的例子是他极为赞赏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将拉丁语《圣经》译成德语。在这里“散文式的”意指平白浅显的语言。这是初步的接触,在这一阶段歌德最为尊重本国读者,要求尽可以让读者读懂。第二阶段其实就是换用一种表达方式进行重写。在第二阶段,译者设想自己处身异国境地,“可实际上只是盗窃异国的思想观念,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思想加以表述”,歌德将其称为“模仿创作阶段”(十足的模仿创作)。[67]对照歌德的实践可以发现,歌德在阅读东方文学后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比如《西东诗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都隶属于他说的这个第二阶段。
歌德所说的第三阶段则较为难懂,但与我们上文讨论的纯语言密切相关。歌德认为“在这个阶段,译文寻求‘与原文完全一致’,以至达到译文就是原文、原文就是译文的程度。歌德把这样的文本称为第三种文本”[68]。曹明伦援引斯坦纳等人的思考并总结道:“荷尔德林认为,人类每一种具体语言都是同一基本语言或曰‘纯语言’的体现,翻译就是寻找构成这一基本语言的核心成分。不同的语言是从‘逻各斯’这个统一体中分裂出的一些飘忽的单元,翻译意味着融合不同单元的元素,意味着部分地回归逻各斯,由此可见,从歌德那里,本雅明受到的启发是‘第三种文本’,而他的‘纯语言’则来自荷尔德林。”[69]这其实能在本雅明的《译作者的任务》一文中找到附证,因为在该文的结尾部分本雅明一再地谈及荷尔德林逝前在翻译的两部索福克勒斯悲剧。“在荷尔德林的译文里,不同语言处于深深的和谐之中……”[70]然而,本雅明又指出大部分翻译如同荷尔德林所译的索福克勒斯作品一样,“在其中意义从一个深渊跌入另一个深渊,直到像是丢失在语言的无底的深度之中。不过有一个止境。”[71]这个止境,就是《圣经》“真正的语言”。
要之,我们看到在歌德那里,他强调一个民族通过学习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长年累积、潜移默化,最终将优秀的、先进的外国文化融合进民族性格当中。此外,歌德认为本国作家/读者,可以通过吸收翻译的作品,再使用本国语言、利用本国文化背景,重构原作,最终替代原作,这也即最终将翻译文学变成本国文学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这两者都可以看出歌德如何借助世界文学来壮大本国的民族文学。最后,歌德同时也看到翻译和语言的超越性面向,称其为“最高级的翻译”。歌德也承认,人类的第一种具体的语言都是同一种基本语言,即所谓的“纯语言”的体现,故而翻译便是寻找构成一个更贴近所有人类语言共有的东西,一个“文化和语言的中间地带”。这其实便接近于本雅明论及的“纯语言”,如果我们剥除其宗教的、神学的、神秘主义的外壳,那便是人类语言共同建立、并由此相互理解的基点——一种抽象的人性。所谓的抽象的、异质的想象共同体,除了如韦努蒂所说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之外,还必须以这种抽象的人性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建构成形。
[1] [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访谈代序》,第24—25页。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国哲学家,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马克思的幽灵》等作品。
[2] [爱尔兰]波斯奈特:《比较文学》,姚建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4页。
[3] [爱尔兰]波斯奈特:《比较文学》,姚建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4] [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28—134页。
[5] Emily Apter,The Translation Zone: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6] [美]艾米丽·阿普特:《一种新的比较文学》,载[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等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
[7] André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ledge,1992.
[8] André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ledge,1992.,p.xi.
[9] Susan Bassnett,“From the Cultural Turn to Translational Turn:A Translational Journey,” David Damrosch,ed.,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Chichester,West Sussex:Wiley Blackwell,2014,pp.234-246.[英]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载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303页。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琳:《翻译学文化转向的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 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剧作家、诗人,代表剧作有《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布莱希特热衷于先锋戏剧实验,并有其独特的戏剧理论作为支撑。他提出了戏剧“陌生化”(间离方法)的理论,在世界戏剧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产生了“布莱希特学派”。
[11] 本特利(Eric Bently,1916—2020)是20世纪中期地位崇高的戏剧批评家,同时也是剧作家、译者和大学教授。本特利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来曾出任哈佛大学诺顿讲座教授(Charles Eliot Norton Professor),在学术界地位也同样显赫,有很大的影响力。
[12] 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1995)中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alienation)这两种基本的翻译策略。归化,是指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译策略。使用归化策略的译者应尽可能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于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异化,则是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策略。使用异化策略的译者应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语言的表达方式。换言之,归化法要求译者向译语读者靠拢,采取译语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法则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在源语文本中所使用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London:Routledge,1995,p.19.
[13] 该文见[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1—94页。
[14] 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20世纪法国诗人,西方现代派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象征派诗歌的先驱,著有诗集《恶之花》和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等。其诗作极为精美,但主题和意象却是颓废的,故而可谓“颓废”是其作品的最主要标签。
[15]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20世纪德国哲学家,诠释学领域最重要学者之一,著有《真理与方法》(1960)等作品。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20世纪法国哲学家,诠释学领域重要学者,其重要功绩在于全面地论述了诠释学的现象学方法论基础,著有《历史与真理》《活生生的隐喻》等作品。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比利时人,196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康奈尔、哈佛、耶鲁、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任教,其重要功绩在于将法国和德国的解构思想引入美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著有《审美意识形态》《阅读的寓言》《浪漫主义的修辞》等作品。
[16]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国犹太人,后移居美国,是20世纪重要思想家、政治理论家,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反抗平庸之恶》等作品。
[17] 舍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1982),德国犹太人,生于柏林,1923年移民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今以色列),历史学家、犹太神学家、诗人。舍勒姆在20世纪是犹太教神学方面的最顶尖学者之一。他本人受到本雅明的语言哲学观念的影响,也一样认同人类的语言有其神圣的来源(divine origin)。
[18] 巴别塔,或译通天塔。巴别塔的隐喻,来自《圣经》中《创世纪》(11:1—9)中的巴别塔故事。其经文(和合本)如下:“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在这里,先民的语言是统一的语言,是最接近于纯语言的亚当语。巴别塔的隐喻极为重要,是关于人类语言和翻译的源头的一个隐喻,成为语言学、神学、哲学、美学、人种学等领域讨论的一个出发点。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s Traducteurs)的会刊便取名“Babel”。“斯坦纳干脆用‘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来隐喻人类的翻译行为及其对翻译理论的探索;翻译工作者则被喻为‘通天塔的建设者’,所以‘巴别塔的重建只能由翻译家们率领工匠去完成’。”任东升编:《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巴别塔隐喻与翻译研究关系,请参该书第15—19页。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Third Edition,New York: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1998.汉译见[英]斯坦纳(Steiner,G.)《通天塔 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编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
[19]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3页。
[20]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3页。
[21]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3页。
[22]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5页。
[23]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1页。本雅明如是说,“相反,由直译所保证的忠实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样的译作反映出对语言互补性的伟大向往。一部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会遮蔽原作,不会挡住原作的光芒,而是通过自身的媒介加强了原作,使纯粹语言更充分地在原作中体现出来”。
[24] [美]格拉海姆:《围绕巴别塔的争论》,载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格拉海姆将德里达的法文论文翻译成英语,并写了这一篇文章解读评论德里达的观点。格拉海姆英译德里达的文章,原文见Jacques Derrida,“Des Tours de Babel”,trans.by Joseph F.Graham,Jacques Derrida,Psyche,Inventions of the Other,Vol.1,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91-225.汉译见[法]德里达:《巴别塔》,载[德]阿多诺等《论瓦尔特·本雅明 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郭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72页。
[25]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9页。
[26] 本雅明关于“纯语言”的思考有着犹太神秘主义的影响,从这方面讲是借助前现代的理论来实现超越性的思考。此外,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试着从他的视角和思考路径出发,历史化地、语境化地、学术化地去理解他的思想,但对这种神秘主义思考应当具备一定的怀疑、警惕,甚至是批判的态度。
[27]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7页。
[28]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4页。
[29]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2页。
[30]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2页。
[31] 解构主义学者保罗·德曼则有反对的观点,即反对将本雅明的翻译理论理解为对纯粹语言的回归和向往。他认为,本雅明并不是想表达将破碎的花瓶(各种语言是这个比喻中的碎片)拼接恢复(glue together)的意思,也因而本雅明没有回归到太初(回归到巴别塔)之前的愿望,更谈不上所谓的“弥赛亚的回归”。在这里,德曼将本雅明理解为一个虚无主义者。这一点引来颇多争议。德曼的论文,请参[美]保罗·德·曼《“结论”:瓦尔特·本雅明的“译作者的任务”》,载[德]阿多诺等《论瓦尔特·本雅明 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郭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3—100页。
[32] 详细分析参见陆扬《德里达〈巴别塔〉的翻译思想》,《圣经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65页。
[33] Derrida,Jacques,The Ear of the Other:Texts and Discussions with Jaques Derrida,Christie McDonald ed.,Peggy Kamuf,tran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5,p.120.“The origin of philosophy is translation or the thesis of translatability.”
[34] 威廉·冯·洪堡,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也是著名的教育改革者、语言学者及外交官,是近代比较语言学创始人之一。
[35]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8页。
[36]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2020),生于法国巴黎,以德语、法语、英语为母语,先后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日内瓦大学等知名学府,教授比较文学课程,在翻译理论、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等领域影响颇大,著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何谓比较文学》等作品。
[37] 任东升编:《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38] 任东升编:《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39] 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Third Edition,New York: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1998.[美]斯坦纳(Steiner,G.):《通天塔 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编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
[40] Roman Jakobson,“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Lawrence 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2000,p.114.
[41] 刘禾:《跨语际实践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英文原著:Lydia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C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42]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 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其英文原著标题为“The Clash of Empires”(帝国的碰撞)。Lydia Liu,The Clash of 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43] Apter,Emily,Against World Literature: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New York:Verso,2013.达姆罗什在为该书所写的书评中提出了一些商榷的意见,尤其指出该书忽略了许多关于“世界文学”研究的著作,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David Damrosch,“Review of Emily Apter‘Against World Literature: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51,No.3,2014,pp.504-508.
[44] Emily Apter,Against World Literature: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New York:Verso,2013,p.3.
[45] Emily Apter,Against World Literature: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New York:Verso,2013,p.16.
[4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生于中国云南昆明,其祖父是英帝国的高级军官,其父亲生前任职于中国海关。安德森生前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在政治学、社会学、东南亚研究等领域颇有建树。其著《想象的共同体》影响极大,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必读书目之一。其弟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是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也是影响巨大的当代思想杂志《新左派评论》的主编之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晚年也参与过“世界文学”的讨论,参见Benedict Anderson,“The Rooster's Egg:Pioneering World Folklore in the Philippines,”Christopher Prendergast.,et.al.,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London:Verso,2004,pp.197-213。
[47] [英]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José Rizal,The Social Cancer,A Complete English Version of Noli Me Tangere from the Spanish,Translated by Charles Derbyshire,Manila:Philippine Education Company;New York:World Book Company,1912.身处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的作家黎萨(中国闽南人的后裔)用西班牙语写成了小说Noli Me Tangere(拉丁语,译为“不许犯我”)。1912年,该书被查尔斯·德比郡(Charles Derbyshire)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易名为《社会之癌》,这个英文译名在英语或中文学界更为读者所知。该书还有几个英译本,其中一个是由格列罗(Leon Ma.Guerrero)译成。格列罗是一名菲律宾的外交官,也是小说家和译者。1961年,格列罗出版了黎萨这部小说的英译本,易名为Lost Eden(《失落的伊甸》)。安德森在其英文著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初版本(1983)中,所征引的正是格列罗的英译本。安德森后来在《想象的共同体》第二版的序言(前引书,第2页)中承认自己“未经深思”便使用了格列罗的英译本,犯下了一种严重的错误,直到1990年“才发现格列罗的译本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错误百出”。安德森的错引劣质译本,也可看作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的一个有趣个案。此外,笔者认为,黎萨混杂多元的身份和民族主义书写,以及其小说的多种英译本,构成一个有趣的世界文学的世界。
[48] [德]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德]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李茂增等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49] [美]劳伦斯·韦努蒂:《翻译、共同体、乌托邦》,载[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等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50] [美]劳伦斯·韦努蒂:《翻译、共同体、乌托邦》,载[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等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51] [美]劳伦斯·韦努蒂:《翻译、共同体、乌托邦》,载[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等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52] [美]劳伦斯·韦努蒂:《翻译、共同体、乌托邦》,载[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等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53] 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New York:Taylor & Francis,1995,p.17.“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the chain of signifiers that constitutes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s replaced by a chain of signifier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which the translator provides on the strength of an interpretation.”
[54] [美]劳伦斯·韦努蒂:《翻译、共同体、乌托邦》,载[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等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55] Sir Thomas More,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More:Utopia,George M.Logan,ed.,Robert M.Adams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6]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德国哲学家,1949年后在民主德国,被聘为莱比锡大学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科学院院士等职,1961年访问联邦德国时,留居不归,在图宾根大学任教。著有《乌托邦精神》《本时代的遗产》《主体—客体》《希望的原理》《哲学基本问题》等作品。
[57] 王尔德的原文,“A map of the world that does not include Utopia is not worth even glancing at,for it leaves out the one country at which Humanity is always landing.And when Humanity lands there,it looks out,and,seeing a better country,sets sail.Progress is the realization of Utopias.”汉译见[英]王尔德:《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载[英]王尔德《王尔德全集4 评论随笔卷》,杨东霞、杨烈等译,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58] [美]劳伦斯·韦努蒂:《翻译、共同体、乌托邦》,载[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等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59] [美]劳伦斯·韦努蒂:《翻译、共同体、乌托邦》,载[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等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页。
[60]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德国犹太人,社会学家。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自由、权力与民主设计》《知识社会学论集》《社会学系统论》等作品。[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61] 具体分析请参张隆溪《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载张隆溪《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
[62] 转引自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63] Johann Wolfgang Goethe,Noten und Abhandlungen a bessere verständnis des West-östlichen Divans,Berliner Ausgabe,Kunsttheoretische Schriften und Übersetzungen [Band 17-22].Band.18. Berlin,1960.转引自孙瑜《歌德翻译思想评述》,蔡建平主编《外国语言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探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9页。
[64] 原文为“Die erste macht uns in unserem eigenen Sinne mit dem Auslande Bekannt;eine schlicht prossische ist hierzu die beste.”见孙瑜《歌德翻译思想评述》,蔡建平主编《外国语言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探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65] 原文为“Die erste macht uns in unserem eigenen Sinne mit dem Auslande Bekannt;eine schlicht prossische ist hierzu die beste.”见孙瑜《歌德翻译思想评述》,蔡建平主编《外国语言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探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原文为“Eine zweite Epoche folgt darauf,wo man sich in die zustande des auslandes zwar zu versetzen,aber eigentlich nur fremden Sinn sich anzueignen und mit eigmem Sinne wieder darzustellen bemuht ist.”
[66] 原文为“Die erste macht uns in unserem eigenen Sinne mit dem Auslande Bekannt;eine schlicht prossische ist hierzu die beste.”见孙瑜《歌德翻译思想评述》,蔡建平主编《外国语言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探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原文为“...den dritten Zeitraum,welcher der höchste und letzte zu nennen ist,derjenige nämlich,wo man die Übersetzung dem Original identisch machen möchte,so dass eins nicht anstatt des andern,sondern an der Stelle des andern gelten solle.[..]so ist denn zuletzt der ganze Zirkel abgeschlossen,in welchem sich die Annäherung des Fremden und Einheimischen,des Bekannten und Unbekannten bewegt.”
[67] 转引自曹明伦《翻译之道 理论与实践》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68] 转引自曹明伦《翻译之道 理论与实践》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69] 曹明伦《翻译之道 理论与实践》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
[70]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 93—94页。
[71] [德]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