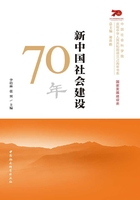
第二节 “三年困难时期”与随后的人口反弹(1958—1976年)
人口的增长与缩减轨迹,经常与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密切契合。1957年出现的“反右扩大化”运动以及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反右扩大化”运动结束时,共有55万人被划定为“右派分子”,其中就有主张节制生育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因此,有人认为是“错批马寅初”才“误增三亿人”。但中国人口的变迁过程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始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人口一直处于迅速降低的态势。当然,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的下降——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县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主要起源于“饥荒”的影响。“大跃进”运动和“大炼钢铁”抽离了农村劳动力,“大办公共食堂”很快吃完了粮食,又缺少灵活机动的粮食调拨机制,于是在一些比较激进的“大放卫星”和大刮“浮夸风”地区,出现了严重的“饿死人”的现象。再加上营养不良所造成的出生率的降低,使这几年的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主要是农村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从表1—2可以看出,在这几年,一方面是县的人口出生率趋低,另外一方面是县的死亡率趋升,导致了这几年的人口损失。尤其是在1960年,县的死亡率突破到28.58‰,而同年县的出生率才19.35‰,于是出现人口增长率-9.23‰的负增长。即使到1961年,经过逐渐地恢复,中国县的人口增长率也才达到2.41‰。
1962年是中国人口增长史上极其重要的转折年。在此之前,都是市镇的出生率和自增率高于县,但在此之后,则是县的出生率和自增率高于市镇。比如说,该年市镇的自增率为27.18‰,县的自增率为16.95‰。从1962年起,中国掀起了“饥荒”之后的新一轮补偿性生育高潮,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婴儿大爆炸”。但总体趋势是:全国人口出生率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自1963年的43.37‰一直下降到1976年的19.91‰——下降了23.46‰。所以,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到随后补偿性生育的冲高,再到人口出生率的逐步降低,中国这个第一人口大国完成了其历史性的人口转型过程。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转变,就没有以后发生的人口大转变。所以,既不能说“反右扩大化”带来了人口的“无计划”增长,也不能说“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国的计划生育。事实上,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71年国务院转发了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5]。可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为控制人口规模,解决人口快速增长与生活资源渐进增长之间的矛盾,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实行计划生育、晚婚晚育,倡导“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节制生育政策。
现在来看,这一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取决于人口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另一方面也由于实行了“赤脚医生”制度,控制了传染病的传播,大大延长了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中国人口的增长模式,逐渐转化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转变。
表1—2 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后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单位:‰

表1—2 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后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单位:‰续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这一时期人口增速得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基层组织的有效控制。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所有模式,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组织化,通过妇联主任上门“做政治工作”的模式,以及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语录》的学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强化等,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速。
第二,晚婚晚育政策的推行。“文化大革命”时期推行的“晚婚晚育”政策,打破了1950年《婚姻法》男20周岁、女18周岁的法定结婚年龄格局,倡导青年男女自觉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推迟结婚年龄,将精力主要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受政策的强制与半强制影响,当时的实际登记结婚年龄,主要在男25周岁、女23周岁左右。在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直辖市,甚至于比这个年龄还要迟一些。
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人口控制的目标。“四五”时期(1970—1975年)明确提出力争将城市人口自增率降低到10‰左右,将农村自增率降低到15‰左右——第一次在政府正式文件中提出了人口控制目标。1973年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并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了“晚、稀、少” (晚婚、间隔生育、少生)的生育政策。事实上,到1976年市镇的人口增长率降低到6.52‰,县的人口增长率降低到13.5‰,超计划完成了人口控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