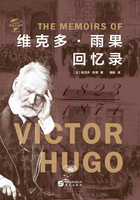
第1章 在兰斯(1823—1838)
1825年,在兰斯,经夏尔·诺迪埃介绍,我第一次听说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这时,正是查理十世加冕期间。
1825年,没有人很认真地谈论威廉·莎士比亚。伏尔泰对威廉·莎士比亚的嘲笑像律法限定着人们的思想一样。杰曼·德·斯塔尔夫人已经接受伊曼努尔·康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和路德维希·冯·贝多芬等伟大人物诞生的土地——德意志。让-弗朗索瓦·迪西正处于创作巅峰时期,在学术方面获得的荣誉可与雅克·德利尔比肩,在戏剧界获得的荣耀与雅克·德利尔不相上下。让-弗朗索瓦·迪西成功地翻译了威廉·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使它们能被人们接受。他吸取了威廉·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悲剧色彩”。人们认为他能从莫洛克 身上塑造出阿波罗。那时,伊阿古
身上塑造出阿波罗。那时,伊阿古 被称作“佩扎雷”,霍雷肖
被称作“佩扎雷”,霍雷肖 被称作“诺西斯特”,苔丝德蒙娜被称作“赫德尔蒙”。迪拉斯公爵夫人克莱尔迷人且机智。她常说:“苔丝德蒙娜,多难听的名字啊!呸!”丹麦王子扮演者穿着一件带毛皮的淡紫色绸缎短袍,常叫道:“滚开!可怕的幽灵!”事实上,只有在幕后,人们才能容忍这个可怜的幽灵。幽灵如果敢冒险露头,就会遭到埃瓦里斯特·迪穆兰的严厉责骂,某个叫热南或者别的什么人就会顺手抓起鹅卵石砸它-用尼古拉·布瓦洛的话说就是:精神绝对不会被不相信的东西撼动。在舞台上,幽灵被丹麦王子扮演者胳膊下夹着的“骨灰盒”取代。幽灵是荒谬的,“骨灰”就是这种风格!人们不是还在谈起拿破仑·波拿巴的“骨灰”吗?把棺材从圣赫勒拿岛转到荣军院难道不是暗指“骨灰归来”吗?《麦克白》中的女巫被严令禁止出现。法兰西剧院的看门人接到命令,但可能对接到的命令完全置之不理。不过,不能说我之前没听说过莎士比亚。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都听说过莎士比亚,只是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也嘲笑过他。我的童年,就像所有人的童年一样,从一开始就带着偏见。一个人的偏见在孩童时便已存在,在职业生涯中会被减弱,而常在年老时复归。
被称作“诺西斯特”,苔丝德蒙娜被称作“赫德尔蒙”。迪拉斯公爵夫人克莱尔迷人且机智。她常说:“苔丝德蒙娜,多难听的名字啊!呸!”丹麦王子扮演者穿着一件带毛皮的淡紫色绸缎短袍,常叫道:“滚开!可怕的幽灵!”事实上,只有在幕后,人们才能容忍这个可怜的幽灵。幽灵如果敢冒险露头,就会遭到埃瓦里斯特·迪穆兰的严厉责骂,某个叫热南或者别的什么人就会顺手抓起鹅卵石砸它-用尼古拉·布瓦洛的话说就是:精神绝对不会被不相信的东西撼动。在舞台上,幽灵被丹麦王子扮演者胳膊下夹着的“骨灰盒”取代。幽灵是荒谬的,“骨灰”就是这种风格!人们不是还在谈起拿破仑·波拿巴的“骨灰”吗?把棺材从圣赫勒拿岛转到荣军院难道不是暗指“骨灰归来”吗?《麦克白》中的女巫被严令禁止出现。法兰西剧院的看门人接到命令,但可能对接到的命令完全置之不理。不过,不能说我之前没听说过莎士比亚。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都听说过莎士比亚,只是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也嘲笑过他。我的童年,就像所有人的童年一样,从一开始就带着偏见。一个人的偏见在孩童时便已存在,在职业生涯中会被减弱,而常在年老时复归。

查理十世

杰曼·德·斯塔尔夫人

伏尔泰

伊曼努尔·康德

弗里德里希·席勒

让-弗朗索瓦·迪西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雅克·德利尔
1825年的这段旅程中,为了消磨时光,我和夏尔·诺迪埃相互讲述植根于兰斯的哥特式故事和传奇爱情故事。我们的记忆有时会结合想象。因此,我们讲的故事都带有传奇色彩。兰斯最可能出现传奇故事。异教徒的领主们曾经住在兰斯,其中有人把玻里斯提尼斯中被称为“阿喀琉斯的跑道”的小片狭长地带作为女儿的嫁妆。在故事集 中,吉耶纳公爵途经兰斯围攻巴比伦。巴比伦是海军上将戈迪修斯的首府,重要性与兰斯不相上下。正是在兰斯,由欧佐拉伊洛克里
中,吉耶纳公爵途经兰斯围攻巴比伦。巴比伦是海军上将戈迪修斯的首府,重要性与兰斯不相上下。正是在兰斯,由欧佐拉伊洛克里 派出的代表团,到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
派出的代表团,到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 的“贝洛娜大祭司”
的“贝洛娜大祭司” “登陆”。在讨论贝洛娜大祭司登陆时,我们就欧佐拉伊洛克里的问题进行了争论。据夏尔·诺迪埃说,因为欧佐拉伊洛克里人是没有完全进化的人,所以被称为“猫人”。不过,据我所知,这是因为他们住在福基斯沼泽地。我们在现场重新描述了圣雷米吉乌斯传说和他在仙女迷宫里的奇遇。香槟之乡有很多传说,几乎所有古老的高卢寓言都源自兰斯,兰斯是幻想之地。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国王们才在兰斯举行加冕仪式。
“登陆”。在讨论贝洛娜大祭司登陆时,我们就欧佐拉伊洛克里的问题进行了争论。据夏尔·诺迪埃说,因为欧佐拉伊洛克里人是没有完全进化的人,所以被称为“猫人”。不过,据我所知,这是因为他们住在福基斯沼泽地。我们在现场重新描述了圣雷米吉乌斯传说和他在仙女迷宫里的奇遇。香槟之乡有很多传说,几乎所有古老的高卢寓言都源自兰斯,兰斯是幻想之地。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国王们才在兰斯举行加冕仪式。

拿破仑的骨灰安放在荣军院

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
传奇故事以兰斯——一块幻想之地——为背景再自然不过,因此,查理十世加冕仪式的故事立即在兰斯萌芽。诺森伯兰公爵休·珀西代表英格兰参加加冕仪式。据说,他非常富有。他是富人,又是英格兰人,怎么可能不受欢迎呢?那时,英格兰人虽然不受普通民众的欢迎,但在法兰西上流社会很受欢迎。某些沙龙推崇英格兰人是因为最近的滑铁卢战役,而且极其推崇法语英语化。因此,诺森伯兰公爵休·珀西还没到兰斯,就已经被大家所知。兰斯传播着他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对兰斯来说,加冕典礼是天赐之福。大批富人如潮水般涌入兰斯,就像尼罗河河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入兰斯。房主们翘首以待,期盼着客人们的到来。
1825年,在一条通往广场街道拐角,有一栋很大的石头房子,房子有一个马车入口和一个按路易十四皇家风格砌成的阳台,阳台面朝大教堂。下面是关于这栋房子和诺森伯兰公爵休·珀西的故事:
1825年1月,房子的阳台上贴了启事“出售”。法兰西《环球箴言报》随即宣布查理十世的加冕典礼将于1825年春季在兰斯举行。城里的人们欢欣鼓舞,出租房间的启事随处可见。最差的房间租价每天至少也要六十法郎。有天早上,一个穿着考究的黑衣人打着白色领结,说着一口蹩脚法语,出现在这栋房子里。他是一个英格兰人。他看着房子的房主,房主仔细地打量着他。
英格兰人问道:“你想卖房子吗?”
“是的。”
“多少钱?”
“一万法郎。”
“不过,我不想买它。”
“那你想做什么?”
“只是想租用。”
“那就另当别论了。租一年吗?”
“六个月吗?”
“不是。我想租三天。”
“啊!”
“租金多少?”
“三万法郎。”
这个穿着考究的英格兰人就是诺森伯兰公爵休·珀西的管家。他正在为主人寻找参加加冕仪式的临时住所。房主察觉这个人是英格兰人,因此,猜到了他的主人便是诺森伯兰公爵休·珀西。管家对房子很满意,房主也坚持自己的要价。因为诺森伯兰公爵休·珀西是诺曼人后裔,所以他接受了房主的租金价格。诺森伯兰公爵休·珀西付了三万法郎,在房子里住了三天,每小时的租金为四百法郎。
我和夏尔·诺迪埃都是探险家。我们偶尔一起旅行时,会各自探索喜爱的东西。他会寻找珍藏本,我会寻找遗址废墟。他会因为得到一部完好的《钦巴龙丘》欣喜若狂,而我会为找到一个破损的门而狂喜。我们将对方比喻为魔鬼。他对我说:“你被恶魔奥吉夫附体了。”我回答:“你被恶魔埃尔策菲尔 控制了。”
控制了。”
在苏瓦松,我在探索圣让德威尼斯时,夏尔·诺迪埃在郊区遇到了一个拾荒者。虽然拾荒者的篮子里是破布片和废纸,但拾荒者是乞丐和哲学家的桥梁。夏尔·诺迪埃捐助乞讨者,有时候也捐助善于思考的人。这时,他进入拾荒者的家。拾荒者本是个书商,夏尔·诺迪埃从他的书堆中看到一本很厚的书。这本书大概有六百或八百页,是西班牙语版本,每页分两栏。这本书被严重虫蛀,底部的封面也缺失了。夏尔·诺迪埃问拾荒者这本书的价格。拾荒者颤抖着答道:“五法郎。”他唯恐遭到拒绝。夏尔·诺迪埃同样颤抖着付了五法郎,但内心充满喜悦。这本书是《歌谣集》全集。现在在市面上,这个版本的完整本只有三本。几年前,有一本售价七千五百法郎。这个版本仅存的三本正迅速被虫蛀。为贵族供应图书的人不愿花钱去印制新版本以保存人类智慧遗产。因此,就像《伊利亚特》一样,《歌谣集》未曾再版。
查理十世加冕的三天里,兰斯的街道上、大主教邸宅和沿韦德尔河的大道上都挤满了人。他们渴望一睹查理十世的尊容。我对夏尔·诺迪埃说:“我们去看看大教堂吧。”
兰斯以哥特式基督教艺术闻名于世。人们在谈论教堂时常说:“亚眠的中殿,沙特尔的钟楼,兰斯的教堂外观。”查理十世加冕前一个月,一群石匠爬上梯子,攀着绳子,花了一星期时间用锤子把教堂正面墙上雕像突出的地方敲了一遍,以免石头从浮雕上脱落砸在国王头上。敲下的碎片散落在人行道上,随后被扫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保有一个被敲下的基督头像。不过,1851年,头像被偷走了。这个头像很不幸,先是因为一个国王被打落,后来又在我流亡途中被弄丢。

诺森伯兰公爵休·珀西

路易十四

查理十世加冕
夏尔·诺迪埃是个令人敬佩的文物研究者。大教堂里面到处是脚手架、彩绘风景画和舞台侧灯。我们把整个教堂探索了一遍。中殿仅由石头砌成。石匠们用一大块硬纸板盖住中殿。毋庸置疑,这是因为纸板建筑与当时的君主制更加相似。为了查理十世的加冕仪式,他们把一座教堂变成一个剧院。从此,人们看到教堂就不由得想到了剧院。因此,刚到教堂门口,我就问当值的警卫:“我的包厢在哪里?”
兰斯大教堂是所有大教堂中最美的。在教堂正面,雕刻的是国王们,在半圆壁龛上,雕刻的是被刽子手施以酷刑的人们。教堂正面墙上的画像是不和谐的音符奏出的最惊人的交响乐之一。很久以来,人们梦想着一睹这个以宗教主题为主的教堂画面。从广场仰望,高度令人目眩。在两座塔的底部,有一排巨大的雕像代表着法兰西国王们。他们手里拿着权杖、宝剑、赦免权杖和地球仪,头上还戴着古色古香的、镶着耀眼宝石的冠冕。场景壮丽辉煌又阴森可怖。推开敲钟人的门,爬上蜿蜒的楼梯——“圣吉尔斯的螺旋楼梯”,来到塔楼上祷告的高台。往下看去,雕像就在下面。映入视野的是一排排国王,好像要冲进无底深渊,钟声的低语随空中微风的轻吻而颤动。
一天,我从塔顶透过教堂斜面窗洞往下面看,整个教堂映入眼帘。顺着教堂朝下看去,看到一个长长的石头支架。支架的形状模糊不清,看起来像是一个圆盆状的东西。雨水在那里聚集,在底部形成了一面狭窄的镜子,还有一簇开了花的小草和一个燕子搭的窝。在直径只有两英尺 的空间里,有一片湖、一个花园和一块栖息地——一个小鸟的天堂。我看着燕子给雏儿喂水。在盆地边上,有个地方看起来像枪眼,燕子就在那里筑巢。我仔细查看这些鸢尾状的垛口。石头支架像一尊雕像。这个快乐的小世界是一个老国王的石头王冠。如果有人问上帝:“这个叫洛塔里奥的、叫腓力的、叫查理的、叫路易的皇帝或国王有什么用?”上帝也许会答道:“他成就了这尊雕像,还为燕子提供了住处。”
的空间里,有一片湖、一个花园和一块栖息地——一个小鸟的天堂。我看着燕子给雏儿喂水。在盆地边上,有个地方看起来像枪眼,燕子就在那里筑巢。我仔细查看这些鸢尾状的垛口。石头支架像一尊雕像。这个快乐的小世界是一个老国王的石头王冠。如果有人问上帝:“这个叫洛塔里奥的、叫腓力的、叫查理的、叫路易的皇帝或国王有什么用?”上帝也许会答道:“他成就了这尊雕像,还为燕子提供了住处。”
查理十世的加冕仪式如期进行,此处不再赘述。对1825年5月29日加冕仪式的回忆已有人讲过,而且比我讲得更详细。

雅克·亚历山大·伯纳德·劳
我只想说这是个光芒四射的日子,上帝似乎赞成这场庆典。阳光透过透明的长窗——因为兰斯已经没有彩色玻璃窗——洒进教堂。阳光洒在大主教身上,祭坛上也洒满阳光。查理十世的内务大臣洛里斯东元帅雅克·亚历山大·伯纳德·劳为阳光欢欣鼓舞。他忙得不可开交,与建筑师让-弗朗索瓦-约瑟夫·勒库安特和雅克·伊尼亚斯·希托夫不时低声交谈。晴朗的早晨使人们有说“加冕的太阳”的机会,就像人们过去常说的“奥斯特利茨的太阳” 一样。在灿烂的阳光下,很多灯和蜡烛努力发出一束束光。
一样。在灿烂的阳光下,很多灯和蜡烛努力发出一束束光。

雅克·伊尼亚斯·希托夫
不一会儿,查理十世穿着一件樱桃色的、镶着金条纹的长袍,匍匐在大主教脚边。法兰西贵族站右边,身着绣着金线,用羽毛装饰的亨利四世风格的,由天鹅绒和白色鼬皮做成的长袍。代表们站在左边,穿着蓝色的礼服,领子上绣着银色鸢尾。

法兰西王储昂古莱姆公爵
教堂见证过各种情况:枢机主教们的教皇祝福,其中的一些主教见证过拿破仑·波拿巴的加冕仪式;元帅们的胜利;法兰西王储昂古莱姆公爵 的遗传特征;跛脚但能走动的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先生的满足;约瑟夫·德·维莱勒家族的兴衰;放飞的鸟儿带来的喜悦;四个信使扮演扑克牌中的大小王。
的遗传特征;跛脚但能走动的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先生的满足;约瑟夫·德·维莱勒家族的兴衰;放飞的鸟儿带来的喜悦;四个信使扮演扑克牌中的大小王。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
从大教堂一端到另一端的旧石板上铺着一条巨大的特制“加冕地毯”,地毯上绣着鸢尾,盖住了石板地面上的碑石。浓郁的香烟充斥在教堂中。放飞的鸟儿在这片烟云中飞来飞去。
查理十世换了六七次服装。奥尔良公爵路易·腓力——即后来的路易·腓力一世帮他更换服装。五岁的波尔多公爵亨利·达托瓦——即后来的香波伯爵亨利坐在查理十世旁边的座位上。
我和夏尔·诺迪埃与代表们坐在长椅上。当加冕仪式进行到一半,查理十世俯伏在大主教脚边时,一个来自杜省的代表——埃莫宁先生转向旁边的夏尔·诺迪埃。他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表示不想打扰大主教的祈祷,顺手把一本书塞到我朋友手里。夏尔·诺迪埃接过书并瞥了一眼。

奥尔良公爵路易·腓力
我低声问:“什么东西?”
他答道:“没什么珍贵的,只是一卷残缺不全的格拉斯哥版的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
教堂的一个挂毯就挂在我们对面,挂毯上的图案是约翰·雷克兰和腓力·奥古斯都的一次不太重要的会面。夏尔·诺迪埃翻了几分钟书,然后指着挂毯说:
“看到那个挂毯了吗?”
“看到了。”
“您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
“不知道。”
“约翰·雷克兰。”
“那又如何?”
“约翰·雷克兰也在这本书里。”
这本书由羊皮装订,书角已磨损。这是一本《约翰王》。
埃莫宁先生对夏尔·诺迪埃说:“买它时,我花了六苏。”
1825年5月29日晚,诺森伯兰公爵休·珀西举办了一场舞会。这是一场壮观的、童话般的舞会。这个《天方夜谭》的使者给兰斯带来了一个天方夜谭般的夜晚。每个参加舞会的女士都在自己的花束里发现了一颗钻石。
我不会跳舞。夏尔·诺迪埃自十六岁起就没跳过舞,因为当时有个老妇人看到他的舞蹈看得入迷,并且赞扬他:“你很迷人,跳舞就像旋转的车轮!……”因此,我们没参加诺森伯兰公爵休·珀西举办的舞会。
我问夏尔·诺迪埃:“我们今晚做什么?”
他举起那本残缺不全的书答道:
“我们读这本书吧。”
于是,我们当晚读了那本书。
换句话说,是夏尔·诺迪埃读了那本书。虽然我觉得他不会说英语,但他应该能读懂书中内容。他大声朗诵,边读边翻译。在他休息的间隙,我把从苏瓦松的拾荒者那里买的《歌谣集》拿出来读了几段。像夏尔·诺迪埃一样,我也边读边翻译。我们比较他那本书中的英语和我这本书的西班牙语并比较戏剧与史诗。夏尔·诺迪埃为威廉·莎士比亚辩护,因为他能用英语读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我为《歌谣集》辩护,因为我可以读西班牙语版的《歌谣集》。我们对比他书中的私生子福康布里琪和我书中的私生子穆达拉。我们一点一点地争论并说服对方。最终,夏尔·诺迪埃爱上了《歌谣集》,而我对威廉·莎士比亚敬佩有加。
接着,我们的听众来了。在加冕这天,即使不去参加舞会,在兰斯这个偏僻的小镇上也会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的小俱乐部很快成立了。首先,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罗歇先生来了;接着,来了一个文人——斐迪南·埃克斯坦先生;然后,我父亲的朋友、乡下的邻居马塞洛先生——总是拿我父亲的和我的保王主义思想开玩笑——参与进来;随后,好心的埃布维尔侯爵来了;最后,花了六苏买书的赠书者埃莫宁先生也来了。
罗歇惊呼道:“这钱花的不值!”
我们的交谈变成一场辩论。大家批判《约翰王》。马塞洛先生宣称行刺亚瑟是不可能的。有人向马塞洛先生指出这是史实,但他难以接受,因为对国王来说,自相残杀是不可能的事。马塞洛先生认为,把国王推向断头台始于1793年1月21日 ,弑君就等于1793年的断头台事件。杀死国王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只有“平民”才能做到。除了路易十六,没有国王曾被暴力处死。然而,马塞洛先生勉强承认查理一世被暴力处死。在查理一世的死亡中,马塞洛先生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其他的都是蛊惑人心的谎言和污蔑诽谤。
,弑君就等于1793年的断头台事件。杀死国王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只有“平民”才能做到。除了路易十六,没有国王曾被暴力处死。然而,马塞洛先生勉强承认查理一世被暴力处死。在查理一世的死亡中,马塞洛先生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其他的都是蛊惑人心的谎言和污蔑诽谤。
虽然马塞洛先生是个非常忠诚的保王党人,我还是冒昧地暗示他,16世纪已存在这种情况。那时,耶稣会士明确提出“让显贵流血”,也就是说国王应该被杀。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就取得了显著效果。两个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被刺死,一个耶稣会士——吉尼亚尔神父被绞死。
我们接着谈论剧本、环境、场景和人物等细节问题。夏尔·诺迪埃指出,马蒂厄·帕里斯 说福康布里琪和“狮心王”理查一世的私生子——法尔卡修斯·德·特伦特是同一个人。为了证明这一点,斐迪南·埃克斯坦提醒大家,据拉斐尔·霍林斯赫德
说福康布里琪和“狮心王”理查一世的私生子——法尔卡修斯·德·特伦特是同一个人。为了证明这一点,斐迪南·埃克斯坦提醒大家,据拉斐尔·霍林斯赫德 的说法,福康布里琪或法尔卡修斯·德·特伦特为了给父亲报仇,杀死了利摩日子爵艾马尔五世,因为“狮心王”理查一世在查卢兹的围困中受伤致死。查卢兹城堡是利摩日子爵艾马尔五世的财产。利摩日子爵艾马尔五世虽然不在,但对从城堡里射出的箭或掷出的石头落到国王头上这件事,必须用性命偿还。罗歇先生嘲笑剧本中描写的“奥地利利摩日”的叫喊声,嘲笑威廉·莎士比亚把利摩日子爵艾马尔五世和奥地利公爵混为一谈。罗歇先生在讨论中取胜,他的嘲笑解决了讨论的问题。
的说法,福康布里琪或法尔卡修斯·德·特伦特为了给父亲报仇,杀死了利摩日子爵艾马尔五世,因为“狮心王”理查一世在查卢兹的围困中受伤致死。查卢兹城堡是利摩日子爵艾马尔五世的财产。利摩日子爵艾马尔五世虽然不在,但对从城堡里射出的箭或掷出的石头落到国王头上这件事,必须用性命偿还。罗歇先生嘲笑剧本中描写的“奥地利利摩日”的叫喊声,嘲笑威廉·莎士比亚把利摩日子爵艾马尔五世和奥地利公爵混为一谈。罗歇先生在讨论中取胜,他的嘲笑解决了讨论的问题。

“狮心王”理查一世
因为谈论已改变方向,我没再多说什么。威廉·莎士比亚剧本的内容触动了我。他庄严的剧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约翰王》不是一部杰作,但有些情景崇高有力。在康斯坦丝的母性中,也呈现出许多极具天才的成分。
这两本书一直放在桌子上,被我们翻来覆去地阅读。我们大笑时会停止阅读。最后,夏尔·诺迪埃像我一样开始沉默。我们被打败了,他们大笑着。然后,他们离开了。我和夏尔·诺迪埃陷入沉思,想着那些未被赏识的伟大作品,为文明时代的人们,包括自己的文学欣赏水平的低下感到惊愕。
最后,夏尔·诺迪埃打破了沉默。现在,我能看到他的笑容了。他说:“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歌谣集》。”
我回答道:“他们还嘲笑威廉·莎士比亚!”
十三年后,机缘巧合,我再次来到兰斯。
那是1838年8月28日。接下来我要解释我为什么一直记得这个日期。我正要从武济耶回来,一看到远处兰斯的两座塔楼,就突然渴望再去参观大教堂。因此,我去了兰斯。
刚到大教堂广场,我就看到一门大炮架在大门附近,旁边的炮手们手里拿着点着的引信。1825年5月27日,我在广场上看到过炮兵部队。我原以为在广场上放一门大炮是惯例,就没怎么注意。我继续往前走,进入教堂。
一个外套袖子为紫色的、有点儿像牧师的人接待了我,带我参观教堂各处。教堂里的石头黑幽幽的,雕像很阴森,神坛看着很诡秘。教堂里没有点灯,阳光透过窗户,在地面阴森的石板上投射出窗户长长的暗影。在教堂其余部分的阴郁黑暗中,窗户的剪影就像躺在坟墓上的幽灵。教堂里没有人,没有低语声,也听不到脚步声。
这种孤独令人心酸,令人心醉神迷,给人一种被舍弃、被忽视、被遗忘、被流放和崇高的感觉。经历了1825年的喧嚣,教堂恢复了昔日的尊严和平静,不再有华丽的装饰,也不再有举行仪式的礼服,并且撤去了所有的装饰。现在的教堂是光秃秃的、没有任何修饰的教堂,但看起来很美。教堂高耸的穹顶上不再有国王的华盖。宫廷仪式不适合这些肃穆的地方。在这里举行加冕典礼只是教堂的宽容。人类创造这些高贵的圣地不是用来献媚的。要把国王的宝座从教堂中除掉,将加冕国王从神面前赶走。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教堂的威严,而路易十四曾遮盖耶和华的神像。
把教堂里的牧师撤走。在使教堂变得黯然失色的一切都被撤走后,可以直接看到白昼的光芒。祈祷、仪式、圣经和这个场合的惯用词等都会消解神圣的光芒。教义就像一个黑暗的密室。通过宗教,人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圣光,而非上帝本身。废旧的教堂反而显得更宏伟。当人类宗教从这座神秘且被精心守护的教堂中撤出时,神圣信仰进入其中。如果让幽静孤独统治教堂,就会在那里感受到天堂。一个被废弃的、在废墟中的圣所,像瑞米耶日修道院、圣贝尔坦修道院、维莱尔修道院、霍利鲁德修道院、蒙特罗斯修道院、帕埃斯图姆神殿群、底比斯山的古墓和神殿,几乎成了一种典型特点,具有稀树草原或者森林那种原始而神圣的壮美。在这样的废墟中,人们才能找到某种真正的存在。

帕埃斯图姆神殿群
教堂是真正神圣的地方。人们在教堂中冥想,与自己的心交流。冥想中寻得的真理得以留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伟大。于是,冥想者的心中几乎不再有任何声音。已经消失的教条甚至连灰烬都未留下。不过,过去的祈祷留下了芬芳。祈祷本身具有绝对意义。正因为这样,曾是犹太教堂、清真寺、佛塔的地方庄严且值得敬仰。冥思者从不嘲笑祈祷者跪拜的令人敬仰的石块。俯首敬仰上帝的人留下的遗迹总令人敬佩。
在大教堂里漫步时,我爬上了三层大殿,到拱形的扶手下,然后,爬上教堂顶部。教堂尖顶下的工艺令人钦佩,但不如亚眠的像“森林”一样密密麻麻的栗木尖顶那么精美。
大教堂的阁楼外观阴森凄凉。教堂阁楼内部就像一座迷宫,各种椽子、横木、横梁、托梁、桁架、柱顶过梁,大梁、厚橡木板盘根错节,让人很容易眼花缭乱。人们可能会想象自己置身于巴别塔的框架中。这个地方像顶楼一样光秃,像洞穴一样荒凉,风凄厉地呼啸而过,老鼠在这里安家。蜘蛛讨厌栗木的气味,因此,在教堂墙面与屋顶交界处的石头上安家,在幽暗的地方吐丝结网。蜘蛛网倒悬着,常被参观者迎面撞到。这里的神秘尘埃让人感觉吸口气就能体验到几个世纪的历史。和房屋里的灰尘不同,教堂里的灰尘会让人联想到坟墓里的骨灰。
大教堂巨大阁楼的地板上有裂缝。人们可以透过缝隙俯瞰无底洞般的教堂。无法看到的角落仿佛是一个个暗影。猛禽从一扇窗户飞入,又从另一扇窗户飞出。闪电时常光顾这些高而神秘的区域。有时,闪电靠得太近,会引起鲁昂、沙特尔或伦敦圣保罗教堂的大火。
教堂执事走在我前面。他看了看地板上的鸟粪,摇了摇头。根据鸟粪,他就能辨别出鸟的种类。他从齿缝中低声抱怨:
“这是乌鸦拉的;这是鹰拉的;这是猫头鹰拉的。”
我说:“你应该研究人心。”
一只受惊的蝙蝠从我们面前飞过。
我们几乎走在险境中。我们跟着这只蝙蝠,看着各种鸟粪,呼吸着灰尘,在充斥着蜘蛛网和奔跑的老鼠的昏暗中,来到一个黑暗角落。角落里有一辆大推车。我只能分辨出车上有一个用绳子拴着的长包裹,包裹看起来像一块卷起的布。
我问教堂执事:“那是什么?”
他回答:“那是查理十世加冕时用的毯子。”
我站在角落里凝视着这个包裹。这时,我真切地听到震耳欲聋的响声。响声听起来像雷声,但来自地面而非天空,它震动着教堂里的木制建筑结构并在教堂里不断回响。接着,我又听到了一声巨响,然后是第三声。响声隔一定时间发出。我知道那是大炮发出的声音。因此,我想到了在广场上看到的那门大炮。
我问教堂执事:“那是什么声音?”
“电报在传播消息,大炮开炮了。”
我继续问:“什么意思?”
教堂执事说:“也就是说,路易·腓力一世的一个孙子刚出生了。”
鸣炮宣告巴黎伯爵腓力亲王 的诞生。
的诞生。
以上就是我对兰斯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