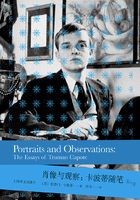
第8章 丹吉尔
(1950)
丹吉尔?从马赛乘船到此只需两天光景,这是一趟迷人的旅程,能够让你一路领略西班牙海岸。如果你正在逃脱警察的追捕,或者仅仅就是一个逃遁者,那么一定要来这里:群山围绕,面朝大海,它看上去像是一件白色斗篷披在非洲海岸上;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一年中有八个月气候怡人(大致是三月到十一月)。那里有迷人的海滩,一路延伸、像白糖一样松软的沙滩和浪花,实在是妙不可言;如果你对那种事情有兴致的话,这里的夜生活尽管既不特别简单质朴也不那般花样繁多,但却能从天黑玩到天亮;这儿的大多数人整个下午都在午睡,几乎没人会在十点到十一点前用餐,你琢磨一下,这其实也就再正常不过了。不过在丹吉尔,几乎其他所有事情都不正常。你来这儿之前,得做三件事:接种伤寒疫苗,到银行取出你的积蓄,和朋友道别——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苍天在上。这个建议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许多来此度短假的游客后来都定居于此了,任凭岁月流转,他们的数量让人触目惊心。因为丹吉尔就像一个盆子把你罩在里面,这里是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地方;时光的荏苒比瀑布溅起的白色浪花更让人不知不觉;我想修道院里的时间就是以这种方式溜走的,在不经意间,在穿着拖鞋行走间;就这一点而言,修道院与丹吉尔这两处地方还有一点共同之处:自我封闭。譬如说一个普通的阿拉伯人会认为欧洲和美国说的就是一回事儿,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不管那地方是在哪里——无论如何,都与他无关;而欧洲人也总是像被乌得琴和身边喧闹的戏剧施了催眠术一样,同样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
你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坐在“小索科”里,那里是一个酒馆遍布的广场,位于卡斯巴脚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它看起来就像是缩微版的那不勒斯的加雷利亚,但进一步了解以后,它会呈现出一种奇异的个性特质,你几乎无法将其与世界上其他的任何地方作比较。从早到晚,小索科无时无刻不处在人流涌动当中;百老汇,皮卡迪利大街,所有这些地方都有其消停的时候,然而小索科却是全天候地处在高度亢奋中。身处二十步之外,你就会被卡斯巴的迷雾所吞没;幽灵在迷雾中游荡漂浮,飘向索科那绞弦琴般的喧嚣声中,呈现一出生动的表演:这是妓女们展示的舞台,毒贩子的活动场所,密探的聚集之处;它同样也是一些更加质朴的平民喝着晚间开胃酒的地方。
索科有它本土的名人,不过这是个不牢靠的名头,你随时有可能从神坛跌落,瞬间失宠,因为索科的观众在见识过几乎所有的场面之后,都格外地反复无常。眼下,他们正追捧着埃斯特拉这颗明星,她人长得挺漂亮,走起路来像一根松开的绳子。她有一半的华裔血统和一半的黑人血统,目前在一家叫做黑猫的妓院。有传闻说她原本是巴黎的一个模特,是乘坐私人游艇到这儿来的,当然她原计划是以同样的方式离开的;不过看起来,这艘游艇的男主人已经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驶离了这里,把埃斯特拉滞留在此。有一阵子,毛米对她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索科人欣赏毛米的才华,他既会跳弗拉门戈舞,又善于交际:无论他坐在哪里,总会迸发出一阵大笑。唉,可怜的毛米,这个爱用一把花边扇子拂面纳凉的年轻外乡人,他有天晚上在酒吧被人捅了一刀,现在已经出局了。沃班克斯夫人跟她的两个随从虽没有那般为人知晓,却令我倍感神秘,这是个古怪的三人组,每天早晨都会在人行道旁的某张桌子前吃早餐:早餐也总是雷打不动——一碗炸章鱼和一瓶法国绿茴香酒。有知情人士说,如今已是万分落魄的沃班克斯夫人曾经被视作伦敦的头号美女;大概这是真的吧,她的容貌很精致,尽管把自己塞在一袭紧身的水手套装里,她还是具有一种独有的与生俱来的气质。不过她的品行却不尽然,她的随从也是如此。说说这两人吧:其中一个年轻人相貌英俊,忙忙碌碌,舌头像一个汤勺在丑闻的大锅里搅个不停——此人无所不知;另一个干练的西班牙女孩,一头油光可鉴的短发,一双皮革色的眼睛。她名叫桑妮,有人告诉我说,她得到沃班克斯夫人的资助,打算成为摩洛哥有组织的走私团伙中唯一的女性:在这个地方,走私是一个强有力的产业,雇用人数上百,而桑妮呢,似乎拥有一只小船和一伙船员,夜间穿行海峡前往西班牙。这三人彼此之间的确切关系并不完全明了;我们只需说,他们携起手来便囊括了所有已知的罪行。不过索科人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另一码事:沃班克斯夫人还有多久才会被谋杀,这两人当中谁会这么做,是这个年轻人还是桑妮?这个英国妇人很有钱,倘若是贪欲(显然就是贪欲)让她制约着她的同伙,那么潜在的谋杀也就显而易见了。所有人都在等待。而与此同时,沃班克斯夫人正无忧无虑地细嚼慢咽她的章鱼,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她的晨间绿茴香酒。
索科还带着一些时尚中心的气息,最新的潮流时尚均能在此地得到试炼。有一项革新迅速流行开来,那便是款式花哨的鞋,带着丝带花边,丝带向上一直缠到膝盖。它们看上去不怎么合脚,但还不及另一件东西更加让人遗憾,那就是在阿拉伯妇女当中兴起了一股戴墨镜的风潮,她们瞥人的时候,目光刚好越过面纱上沿,这模样总是带着一丝挑逗。如今,我们所能看见的就是这两大块黑色镜片镶嵌在里面,就像是两大块煤嵌在白布裹成的雪球里。
到了傍晚七点,索科迎来了高潮。这是人声鼎沸的开胃酒时刻,约有来自二十个国家的人在这片狭小的广场上摩肩接踵,他们发出的嗡嗡声就像是巨型蚊子一般嘈杂。有一次,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突然间就沉寂了下来:一个阿拉伯乐队欢快地吹着喇叭,沿着街道前行,路过喧闹的酒馆——这是我所听过的唯一欢快的摩尔式音乐,其他所有的听上去都是那种悲伤而破碎的哭号。但是死亡,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似乎算不上什么不愉快的事,因为这个乐队后经证实是一支送葬队伍的先行部队,随后到来的大部队都是兴高采烈地蜿蜒穿过人群。现在看到的这具尸体是一个打着赤膊的男子,躺在一个平台上,晃晃悠悠地被抬了过去,而一个戴着人造钻石的女士,靠在桌边,黯然神伤地举着一杯干雪利向他致意:过了一会儿,她就开怀大笑起来,露出一嘴金牙,讲着故事,聊着未来。小小的索科正是如此。
“如果你打算写点关于丹吉尔的什么东西的话,”我向一个人询问信息的时候,他这样说道,“那请你不要提及那帮乌合之众;我们这里的好人可多着呢,我们可受不了这个镇子遭受这等骂名。”
好吧,尽管我一点也不确定我们对于好人的定义是否吻合,但在我看来,这里至少有三个顶着光环的好人。譬如约翰妮·温纳。她是个温柔又可爱的女孩。她年纪很小,属于典型的美国人,看她那张乌云密布的惆怅脸庞,你永远也不会相信她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说真的,我不相信她能做到。尽管如此,她在这儿已经生活了两年,独自穿越摩洛哥和撒哈拉。约翰妮·温纳为何打算余生都在丹吉尔度过,这当然是她自己的事;显然她是爱着这里的:“可你不也喜欢这儿吗?醒来后知道你就在这里,也知道你永远都是你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不是你自己的那个人——永远拥有鲜花,永远看着窗外,看着小山变暗,看着港口的灯亮起来——你不也喜欢这儿吗?”另一方面,她和这个小镇总是格格不入;你不管什么时候见到她,她都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危机:“你听说了吗?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卡斯巴有个傻子把他家的房子刷成黄色的了,现在大家都这么做——我正准备看看能不能将此事打住。”
卡斯巴按照传统是蓝白相间的颜色,像是暮色中的雪,漆成黄色定会面目可憎,我希望约翰妮能得偿所愿——尽管我肯定她在另一场运动中没能成功地阻止当局清理大索科,这件令人心碎的事情害得她含泪在街头徘徊。大索科是一个雄伟的阿拉伯集市广场:柏柏尔人[27]带着他们的山羊皮和篮子下山,在树下蹲坐成一圈又一圈,听着别人讲故事,吹笛子,看着别人变魔术;篮子里装满了鲜花和水果;大麻发出的烟味和阿拉伯茶的薄荷香弥漫在空气中,浓烈的香料在阳光中烤炙。所有这一切都会移至别处,大概是为了给建公园腾地方吧,约翰妮双手扭在一块:“我为什么不该为此感到难过呢?我觉得丹吉尔就是我的家,如果有人闯进你的家里,把家具搬来搬去,你会怎么想?”
于是她走上街头,用四种语言来拯救索科——法语、西班牙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尽管她这几种语言都说得相当不错,她得到的最接近官方的同情来自于荷兰领事馆的门卫,她唯一真正意义上得到的情感支持来自于一个计程车司机,那人认定她一点也没疯,就免费送她到处游说。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接近傍晚,我们看到约翰妮正疲惫地在她挚爱却行将拆除的大索科广场上行走;她看上去真的是累坏了,还带着一只脏兮兮的小猫,皮肤也溃烂了。约翰妮有办法敞开心扉直接将她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她说道,“我刚才感觉我都活不下去了,然后我找到了曼罗。这就是曼罗”——她轻轻地拍了拍那只小猫——“是他让我觉得自惭形秽:他抱有对生活的兴趣,连他都能这样的话,我为什么就不能呢?”
看着他们——约翰妮和那只小猫——都是那样凌乱不堪和伤痕累累,你就明白了总有一样东西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如果不是常识,那便是他们对生活的兴趣。
弗里达·格琳就有着丰富的常识。当约翰妮跟她讲述大索科广场的现状时,格琳小姐说,“哦,亲爱的,你犯不着发愁。他们总说要拆索科,但从未真正成行;我记得1906年的时候,他们想把这里变成一个捕鲸加工中心:想想那恶臭吧!”
弗里达是丹吉尔著名的格琳三姐妹之一,另外两个是她的表姐杰西小姐和她的嫂子阿达·格琳夫人;很多时候她们两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让自己说了算。三个人都已年过古稀:阿达·格琳夫人以高雅入时闻名,杰西小姐以风趣著称,而最年长的弗里达则长于睿智。她已经有五十多年没回出生地英格兰了;即便如此,仔细观察一下她固定在头发上的草帽和拖在夹鼻眼镜后面的黑丝带,你便知道她会迎着正午的阳光出门,而且绝不会放弃五点钟的下午茶。在她生命中的每个礼拜五,都会举行一个叫做“面粉早晨”的仪式。她坐在自家花园的桌前,逐一审查那些前来申领面粉的阿拉伯人,然后将面粉定量配给给她们;这些人通常都是些年迈的妇女,属于领不到面粉就会饿死的那种:她们将面粉做成面糊,非得依靠这些面糊撑到下周五才行。很多人都拿这件事打趣说笑,因为这些阿拉伯人挺敬重弗里达女士的,这些老年妇女于我们其他人而言就像洗衣店里无人认领的衣服,而对弗里达女士来说,却是朋友,她在一个很大的记录本上分门别类地写下她们的性格特点。“法斯玛脾气虽坏,人却不坏,”她如此评述其中一个,然后又记录下另一个,“哈里玛这女孩儿不错,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而这,我猜想,正是你对弗里达女士想说的话吧。
* * *
凡是在丹吉尔待的时间超过一整夜的人,一定都听说过奈萨:听说过她快到十二岁那年是如何被一个澳大利亚人从街头带走的,这个澳大利亚人完全是按照卖花女的方式,把这个衣衫褴褛的阿拉伯孩童变成了一个优雅超凡的名人形象。据我所知,奈萨是丹吉尔唯一欧化的阿拉伯女子,奇怪的是,因为这件事没人会完全原谅她,欧洲人不会,阿拉伯人也不会,他们对她公然挖苦,由于她住在卡斯巴,所以这些人总有机会来对她发泄怨气:女人们让孩子在她的门上写一通污言秽语,男人们则是毫不犹豫地在街头对着她啐口水——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她犯下了最可怕的滔天大罪——成为基督教徒。这种境遇一定会催生苦涩的忿恨,可是奈萨,至少在表面看来,绝没有半点在意。她是一个平静而充满魅力的女孩,二十三岁;你只需安静地坐下,欣赏她的美貌、上翘的眼睛和如花的双手,便已乐在其中了。她见过的人并不是很多;如同故事书中的公主,她在墙的后面,在院子的阴凉处,读读书,和小猫嬉戏,还有一只白色的大美冠鹦鹉,无论她说什么,它都跟着学:有时这只鹦鹉会扑上前来亲亲她的嘴唇。那个澳大利亚人就和她住在一块儿;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找到了她,从那以后他俩就一刻也没有分开过;如果他有什么不测的话,那奈萨简直就是穷途末路了:她不可能再变回阿拉伯人,也不太可能完全融入到欧洲人的世界里。而这个澳大利亚人眼下已经年迈。那天我按下奈萨家的门铃;没人应声。门的上方有花格形的镂空图案;我凑过去瞟了一眼,透过帷幔一样的葡萄藤,看见她就站在院子的阴凉处。我又按了一遍门铃,她依然像雕像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神情没落。后来我才听说,前一天晚上,那个澳大利亚人中风了。
六月底,伴随着一轮新月,斋月拉开了帷幕。对阿拉伯人来说,斋月就是斋戒的一个月。夜幕降临,一条彩线划破长空,而当这条彩线变得无影无踪的时候,又响起了螺号声,那是阿拉伯人开始进食进水的信号,要知道,这些东西在白天的时候,他们是连碰都不能碰的。这种深夜的盛宴,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这种气氛会一直持续到天亮。远处的塔楼里传来了双簧管的声音,那是在祈祷开始前演奏的小夜曲;鼓声,虽然看不见,却能听得到,在紧闭的门后发出咚咚的响声,还有男子的声音,用一种声调念着《古兰经》,从清真寺里传到明月普照的狭窄街道上。即便是在耸现于丹吉尔城上方的高山上,你都能听到双簧管在深邃的夜色中发出的哀号,一段庄严肃穆的旋律悠然穿过非洲,从这里飘向麦加,再从麦加返回。
西迪卡塞姆是一片如同撒哈拉沙漠一般广袤无垠的海滩,周围是橄榄树林;在斋月接近尾声的时候,整个摩洛哥的阿拉伯人便会聚集在此,有的乘坐卡车,有的骑驴,还有的徒步行走:三天的时间,这里就出现了一座城市,一座精巧的梦幻之城,构成这座城的就是一盏盏彩灯和灯笼高挂的树下那一间间小酒馆。我们大约半夜的时候驾车来到这里;第一眼见到这座城市,就像是看到点着烛光的生日蛋糕在熄了灯的房间里闪闪发亮,而且它使你心中充满了那种同样令人兴奋的敬畏感:你知道你是没法把所有的蜡烛都吹灭的。不一会儿,我们就与同行的人走散了,在大股的人群中挤过来挤过去,要走在一起几乎不可能,在起初几次令人慌张的失散之后,我们干脆就不去找他们了;黑夜将我们攥在手中,我们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变成另一张戴着面具、欣喜若狂的面孔,在火炬的光焰下闪烁。到处都是小型乐队在演奏。甜美销魂的歌声,如同吸食毒品后的飘飘欲仙,伴着鼓声吟唱。在某处,我们穿过仿佛在银光下浮动的大树,蹒跚而行,在一群跳舞的人群中间几乎喘不过气:蓄着大胡子的老人围作一圈,打着拍子,中间那些舞者紧紧地挨在一起,密不容针,人群如涟漪一般起伏着,仿佛是风在吹动他们。按照阿拉伯的纪年方式,今年是1370年;看着丝质帐篷的影子,望着一家人在静静的篝火上烤着甜饼,随着跳舞的人群一起舞动,听着海滩上孤寂的笛子传来的颤音,这些不知不觉地让你相信你就生活在1370年,时光永远不会前行。
偶尔,我们要休息一番;橄榄树下有草席,如果你坐在其中一张上面,有人会给你递上一杯热薄荷茶。正是在喝茶的时候,我们看见一路纵队正匆匆忙忙从我们这边经过。他们身着漂亮的长袍,走在前面的那个人老得就像一根象牙,他端着一碗玫瑰花露,伴随着风笛声将露水洒向两边。我们起身跟着他们,他们带我们走出小树林,来到一片海滩。海滩上的沙月亮一般冰冷;沙丘朝水的方向缓缓移动,灯光的闪烁像流星一样在黑暗中迸发出光亮。最后,牧师和他的随从走进一座庙宇,而我们是不允许进入的,于是我们就沿着海滩漫步。J说,“看啊,有颗流星”;于是我们就开始数那些流星,许许多多的流星。风儿在沙滩上低吟,仿佛是大海的声音;橙色的月亮跪下了,一些凶狠的人影向着月光显形;海滩像雪地一样冰冷,可J却说道,“噢,我眼睛再也睁不开了。”
蓝色晨曦中,我们一觉醒来,发现我们正躺在一个高高的沙丘上,沙丘的下面所有的庆祝者们沿着海岸一字铺开,他们鲜艳的服装在清晨的微风中飘舞。太阳刚刚从地平线探出头来,突然传来了一声大吼,两个马夫骑在马背上,马背上并没有马鞍,他们沿着海滩疾驰而过,浪花四溅。就像是缓缓卷起的窗帘,太阳沿着沙滩向我们徐徐临近,我们震颤于它的到来,因为我们知道,当太阳的光芒照射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得回到自己的世纪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