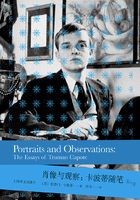
第9章 穿越西班牙之旅
(1950)
这辆列车的确是太过陈旧了。座位上的垫子凹陷下去,活像斗牛犬的面颊,窗子破了,全靠黏合剂将余下的部分粘在一起;走道当中,一只潜行的猫似乎是在捉老鼠,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断它的这次搜捕行动想必会有所斩获。
仿佛车头是套在一群上了年纪的苦力身上一般,慢慢地,我们终于爬出了格拉纳达。南方的天空像沙漠一样茫茫一片,热浪灼人;只有一片云彩,恍若移动的绿洲在空中飘浮。
我们要前往的地方是阿尔赫西拉斯[28],这是一座西班牙海港城市,面朝非洲海岸。我们所在的那节车厢里面有一个中年澳大利亚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亚麻色衣服,牙齿像烟草的颜色,指甲也不干净。没过多久他就告诉我们,他在一艘轮船上当医生。在这片天气干燥、岩石嶙峋的西班牙平原上,见到与大海有关联的人似乎的确是一件稀奇事。坐在他旁边的是两个女的,一对母女。母亲是一个圆滚滚的、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女人,一副无精打采、暗含不满的眼神,唇边还有薄薄的一层绒毛。她表达不满的对象总在变化;起初,她恶狠狠地瞪着我看——由于阳光愈加强烈,热浪透过破损的车窗滚滚袭来,所以我就把外套脱了——在她眼里,这是件失礼的事,她也许是对的。后来,她又将鄙夷的眼神投向一个年轻的士兵,他跟我们坐同一节车厢。这个当兵的和她有失检点的女儿看上去是在调情,彼此心照不宣。她的女儿体态丰满,脸长得像职业拳击手般好斗。每当那只游荡的小猫出现在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的女儿就会装出一副受惊吓的样子,而那个当兵的则会殷勤地将小猫嘘进过道:这样的一唱一和让他们经常有机会触碰到彼此的身体。
这个年轻的士兵是车上众多士兵当中的一个。他们神气地歪戴着穗边帽子在过道上闲逛,抽着润口的黑香烟,心照不宣地大笑。他们看起来是在自娱自乐,显然他们不该这么做,因为只要军官一出现,这些当兵的就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仿佛是看着泥石流、橄榄园和顽石山看得入神。他们的长官穿得像是要参加阅兵仪式的样子,满身的勋带,满身的徽章;有些还在肋下挂着明晃晃的、样式夸张的佩剑。他们并没有和士兵们混在一起,而是集体坐在头等车厢,看起来无所事事,更像是失业了的演员。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终于让他们有机会拔出佩剑了,我想这算得上是件好事儿。
就在我们前面的那节车厢被一家人给包了:一个瘦弱单薄却无比优雅的男子,袖子上缝着一道黑纱,和他一道的是六个热情似火的苗条女孩,大概是他的女儿吧。他们都很漂亮,这位父亲和他的孩子们,全是一种风格:头发乌黑亮泽,嘴唇像甜辣椒的颜色,眼睛像是雪利酒。那些当兵的会往这节车厢瞟上一眼,然后又转向别处,仿佛是眼睛直视了太阳一般。
每次列车停下来的时候,那男人最小的两个女儿就会走出她们所在的那节车厢,撑着太阳伞散一会儿步。她们喜欢看长长的人流,因为这趟列车在我们旅途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静止不动的。除了我以外,好像没人为此动怒。有些旅客似乎在每站都能遇见朋友,他们围坐在喷泉的周围,家长里短。一个老太太在十几个小镇的站台上都遇到了三五成群的熟人,每次遇到的人也都不同——每次相见过后,她都会泪如雨下,哭得那个澳大利亚医生不由得紧张起来:噢,别担心,老太太说,他也帮不上忙,她只是因为见到了所有的亲戚,所以高兴坏了。
每到一站,打着赤脚的妇女和几乎光着身子的孩子就会如旋风般在列车旁奔跑,把陶器里的水溅得到处都是,然后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声:水!水![29]你只需两个比塞塔就能买到一整篮子的深色无花果,果皮上还沾着水珠,还有一盘盘奇特的糖果炸面圈,外面裹着一层白色的糖,看上去像是只有穿着圣服的年轻女子才能品尝一样。到了正午,我们弄到了一壶酒、一条面包、一根香肠和一块奶酪,准备吃午餐。跟我们一节车厢的同伴们也饿了。包装纸打开了,酒瓶也开盖了,不一会儿,车厢里就呈现出一派惬意、近乎于优雅的节日气氛。那个当兵的和那个女孩分吃着石榴,那个澳大利亚人讲着好笑的故事,那个眼睛像女巫的母亲把鱼从她的胸脯中间的包裹纸里取了出来,吃的时候闷闷不乐,却也有滋有味。
后来大家都困了;那个医生睡得太沉,张着大嘴,连在他面前盘旋的苍蝇都没有惊扰到他。寂静一下子就让整节列车失去了知觉;邻近的那节车厢里,那些可爱的女孩慵懒地倚靠着,就像六株疲倦的天竺葵;即便是那只猫也停止了觅食,趴在过道里,做着美梦。我们爬到了更高的地方,火车徐徐驶过一片黄色麦浪中的高原,然后又在花岗岩的深谷间穿行,大风从谷中吹来,在一片奇异的荆棘树丛中发出瑟瑟的声音。曾经一度,透过树丛的空隙,我看到了我一直想要看的东西:一座山上的城堡,高踞在那里像是一顶皇冠。
这是一片属于强盗的风景。就在这个初夏,我认识的一个英国人(倒不如说是听说过的)驱车穿越西班牙的这片土地,就在这时,在人烟稀少的那面山坡上,他的车被一帮皮肤黝黑的匪徒给包围了。他们先是抢了他的东西,然后又将他绑在树上,用刀刃在他的喉咙上撩拨。我正陷入一片遐思之中,这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一排猛烈的子弹向这片令人昏昏欲睡的沉寂扫射过来。
那是机关枪的声音。子弹如疾风暴雨般射向树林,就像是响板发出哒哒哒的声音,这列火车就像是受了伤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缓缓地停了下来。一时间,除了机关枪的咆哮声,就再没了别的声音。然后,“有强盗!”我扯着令人恐惧的大嗓门喊道。
“有强盗!”那个女孩也尖叫了起来。
“有强盗!”母亲同样喊道,这个可怕的字眼席卷了整列火车,就像是有东西敲击着手鼓。结果却是虚惊一场。我们瘫倒在地,手脚都在瑟瑟发抖。只有那个母亲看上去还头脑清醒;她站了起来,有条不紊地把她的宝贝一件件藏起来。她把一枚戒指塞进圆发髻里,还掀起裙子,把镶有珍珠的梳子塞进她的灯笼裤里,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旁边的那节车厢里那群迷人的女孩们发出轻盈的唧啾声,犹如暮色中鸟儿的啼鸣。过道里的军官们跌跌撞撞地四处发号施令,结果互相撞作一团。
突然间,一片沉寂。车窗外传来了风吹树叶的低吟。压在我身上的医生全身的重量对我来说已经不堪重负,正在这时,我们车厢的门突然开了,有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他看起来不像强盗那么精明。
“喂,车上有医生吗?[30]”他微笑着说。
那个澳大利亚人把他的胳膊肘从我的肚子上面拿开,站了起来。“我就是医生,”他坦言,一边掸去身上的尘土。“有人受伤了吗?”
“有啊,长官。有个老人头部受了伤,”那个西班牙人说道。他不是什么强盗:哎,只不过是又一个乘客。我们又坐回到位子上,听着刚才发生的一切,因为尴尬而显得面无表情。貌似就在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有个老人一直攀在火车的尾部搭乘顺风车。方才他的手松了,一个当兵的看见他摔了下去,于是就用机枪扫射,权当是信号,好让火车司机停车。
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没人记得是谁第一个喊的“有强盗”。看起来他们的确是不记得了。那个医生找我要了一件干净衬衫,用作绷带,然后下车走到那个受伤的人跟前,而那个母亲转过身去,一副假正经的酸腐模样,把那把珍珠梳子掏了出来。她女儿还有那个当兵的跟着我们一起下车到树下散步,还有许多的乘客也聚集在那里,谈论着刚才那起突如其来的意外。
两名士兵架着这个老人出现了。我的衬衣绑在他的头上。他们把老人架到树下,所有的女人都聚集在一起,争先恐后地为他念玫瑰经;有人带了一瓶酒,这比玫瑰经更让他高兴。他看起来很开心,哼哼个不停。那几个先前还在火车上的孩子围着他咯咯笑。
我们来到一片散发着橘子香味的小树林。有一条小径,通往一片阴凉的海岬;在这里,你可以纵览整个山谷:灼热的阳光下,一片金色的草地泛起微澜,仿佛地球都在颤抖。那姐妹六人正在欣赏山谷的美景,还有群山上光与影的变化,陪着她们的是那个优雅的父亲,她们坐在遮阳伞下,就像(十八世纪法国盛行的)田园宴会上的宾客。那些当兵的就在她们周围转悠,那架势既躲躲闪闪,又心有不甘;他们不敢靠得太近,不过还是有个胆大的冒失鬼凑到遮阳伞的边上喊了一声,“我好爱你[31]。”清晰的回声从山谷传来,像空灵的音乐一般,那群姐妹面露羞涩,朝着山谷更为深邃的地方望去。
一团云,像山岩一样阴沉,在天空中聚拢,而下面的草地就像暴风雨将至的大海一样波澜起伏。有人说估计会下雨。但是没人想离开这里:那个受伤的人正悠然自得地喝着第二瓶酒,他不想离开,而孩子们也不想离开,他们发现了回声的奥秘,正站在山谷前欢快地唱着歌。这就像是场聚会,大家都慢吞吞地回到了火车上,似乎都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这里的人。而那个老人,头上缠着我的衬衫,看着就像个穆斯林;他被安置去了头等车厢,还安排了几个殷勤的女士来伺候他。
就在我们那节车厢里,那个皮肤黝黑、灰头土脸的母亲依然坐着,坐姿同我们刚才离开她时一模一样。她看来是不适合加入到这场聚会当中的。她长时间地盯着我看。“强盗,”她用暴躁且中气十足的口吻说道,语势强得毫无必要。
列车开动了,开得是那样的慢——蝴蝶从窗户里飞进飞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