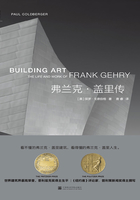
第7章 成为建筑师
1950年春季的一天,在多伦多贝弗利街15号自家的房子里,弗兰克的外祖母利亚被发现倒在了电话桌旁边的地板上。她突发中风,几天之后就去世了。得知消息的弗兰克伤心欲绝。对他来说,利亚不仅是一位智慧的长辈,同时也是全家最能理解他的困惑,最能体谅他那尚不成熟的内心世界的人。“我很爱她[138]。对我来说她就像生命一样重要。可以说是她成就了我。回首童年往事,她是唯一对我说过‘你会有出息的’的人。”他甚至觉得,比起母亲,是利亚真正地发掘了他富有创造力的一面。
但是,尽管弗兰克同外祖母感情深厚,他还是没有能够赶回加拿大去参加她的葬礼。那个时候,欧文的脾气已经越来越暴躁,常常失控——多琳至今记得[139],有一次他冲她发火,竟然抄起手边的一台收音机就朝她扔了过来。那些年里,西尔玛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欧文,住手!”显然,以欧文这种状况,他是无法回加拿大去吊唁岳母了。而西尔玛则无论如何也得回去。于是,留在家里照看着父亲的任务就只得落在了弗兰克的肩上。西尔玛从学校接回了12岁的多琳,带着她一起回了多伦多,参加利亚·卡普兰的葬礼。
母女俩的这趟旅程比预计持续了更长的时间,也比犹太人传统上的七天服丧期(shivah)要长了不少。由于没有美国护照,西尔玛在加拿大滞留了好几周,一直无法重新入境美国。因为证件上显示的出生地是波兰,她在美国的边境官员那里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弗兰克和欧文很担心西尔玛会再也回不来了,情急之下他们联系了他们当地的女议员海伦·嘉哈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我们可以说是病急乱投医[140],稀里糊涂地找上了她,指望着得到一点帮助。”弗兰克回忆道,“之前我们互相根本就不认识,我记得我们去了她的办公室,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她很真诚,说会帮助我们,而她真的这么做了。多亏了她,我母亲才能够回家。”[141]1950年6月20日,利亚去世后的大概第六个星期,欧文收到了一封来自移民归化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的信函,信中确认了西尔玛返回美国所需的签证。
西尔玛和多琳从加拿大回来后,戈德堡家的日子也渐渐地开始有了起色。西尔玛在百老汇商场纺织品销售部的工作很出色[142],被提拔成为部门的领班。顾客和同事们都很喜欢她,亲切地称呼她为“戈尔迪”(Goldie),或者更正式一点,“戈尔迪太太”。后来,她再次获得晋升,被调到了设计部门,负责商场为顾客提供的室内设计服务。弗兰克记得,有一次她接到了艺人小萨米·戴维斯(Sammy Davis Jr)家的室内装饰任务,这让她兴奋极了。西尔玛不是那种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但是,她一直保持着一种端庄而得体的风度,她相信一个人的外在能够影响内心修养。哈特利·盖洛德还记得,西尔玛常常带着他去比弗利山(Beverly Hills)的朋友家参加音乐晚会。“二十五到三十人,围坐成一圈[143],有人站起来到钢琴旁唱歌……这是一种相当优雅的聚会。西尔玛希望我们能常去,而我们也确实去了很多次。她真的是个很有意思的、很棒的人。”
到了1950年下半年,随着西尔玛在百老汇商场越干越好,戈德堡家终于可以搬出他们在第九街和伯灵顿街交口租住的公寓了,这间公寓,与其说象征着他们初到加州时对未来满怀的希望,倒不如说是见证了他们过去三年来艰辛的生活。和许多打算改善居住条件的洛杉矶人一样,他们也是往西搬。他们的新家位于奇里地区(Miracle Mile district),费尔法克斯大街(Fairfax Avenue)的农夫市场(Farmers Market)以南,橘子街(Orange Street)6333½号,是一座由四套公寓组成的无电梯住宅楼,他们的在二楼。这套公寓,虽然和比弗利山上的那些豪宅肯定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和之前第九街的房子比起来,无论是周边的环境还是室内的空间,都已经是改善了太多。新家里有两间卧室、一间独立的饭厅,后面还有个阳台。
虽然搬到了新家,但是作为最小的孩子,多琳还是得继续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公寓里的两间卧室,一间是西尔玛和欧文住,另一间则给了弗兰克,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学习建筑,需要一定的工作空间。每天,弗兰克都要在房里画大量的草图和素描,所以对于西尔玛来说,要保持他房间的清洁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母亲过去常说[144]弗兰克简直就像是在屋里挖煤,因为他用铅笔画图。我母亲很讨厌去打扫他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铅笔芯和铅笔屑。”
然而,即使在搬了新家以后,欧文糟糕的健康以及情绪的状况也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善。欧文那时的工作是[145]在标准咖啡公司(Standard Coffee Company)做一名上门推销员,不过他也只是个零工。1952年,这份工作总共给他带来了2036.80美元的收入。和西尔玛一样,欧文也一直十分注意保持自己外表的体面,但是,就连这点体面,对他来说都已经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在朋友和相熟的亲戚面前,他可以表现得开朗而热情[146]——哈特利·盖洛德记得欧文那会儿经常到他家去串门,他愉快地和他们聊天,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严重的健康问题。但是,回到橘子街的家,他却几乎连二楼的楼梯都爬不上去。因此,在那个时候,即便是那份兼职的推销员工作,对他来说都已经是个不小的挑战了。多琳记得她总是见到父亲艰难地爬上楼梯,然后在家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就是坐在那里愣神,几乎什么事都不做。对年轻的多琳来说,“家里真的是非常压抑[147]。那时的我讨厌回家”。
欧文的心脏越来越虚弱,而他五年前确诊的糖尿病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这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差,也导致了他更为频繁的情绪失控。多琳回忆起她的父亲“每天要打三针胰岛素[148],但是他每天还要喝一打可乐。我记得弗兰克和我曾经哭着求他不要再这样了。但他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父亲的精神状况让弗兰克感到很灰心都到县医院去看病,他曾带父亲去看过精神科医生,但是仅仅一次治疗之后,医生就告诉他欧文的情况已经无法治愈了。“这样说对他显得很不公平[149],但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别的表达方式了。”弗兰克回忆道。
弗兰克和多琳需要经常带着父亲到洛杉矶县医院(Los Angeles County Hospital)去看病。他们家支付不起私立医院高昂的费用,只能去这种专为穷人治病的地方,无法去那些洛杉矶最好的医疗机构,这也让他们对父亲的病情更加的不放心。“他每次都到县医院去看病[150]。那里有点类似于是某种福利机构。”多琳说。她还记得在父亲的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她陪着父亲在县医院的走廊里苦等床位的经历。西尔玛曾经求助于欧文住在东部的妹妹罗茜,希望她能帮忙分担一些她哥哥的医疗费。但罗茜拒绝了她。戈德堡一家再没有什么其他的门路了,因此,在这之后每当身体出现状况,欧文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县医院,和众多的病人一起在走廊里排队,等待着护士叫到他的名字。
* * *
弗兰克在1949—1950学年入学南加州大学,成为美术系的一名本科生,这一年里他所选修的大部分课程都是与建筑相关的。1950年春季,在格伦·卢肯斯的进一步鼓励下,他终于正式被建筑学院录取。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录取。弗兰克和另外三个同样修满了足够的基础课,并且成绩出色的学生,被建筑学院允许跳过一年级的课程,而直接成为建筑系二年级的学生。这是“第一次有人肯定了我”[151],谈到那封让他跳级进入建筑系的推荐信,弗兰克至今还显得很激动。这四名学生和另外十一人共同组成了南加大建筑学院的那一级学生,在五年本科生涯余下的时光里,他们将共同度过,并最终拿到建筑学学士的学位。
当时,洛杉矶地区主要的大学里只有南加州大学拥有完备的、能够授予学位的建筑系。十四年后,南加大在洛杉矶地区主要的竞争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才建立了自己的建筑和规划学院,这之后又过了九年,著名的独立建筑学院——南加州建筑学院(SCI-Arc,the 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才宣告成立。在1950年,南加大建筑系是洛杉矶唯一的建筑系,这座城市里许多重要的建筑师都在那里教书。而即使是那些不教书的建筑师,也会经常到学院里去转转,因为那里是战后初期,洛杉矶地区有限的建筑学术与文化中心。由大量活跃于设计界的职业建筑师组成的教师团队,使得这座学院极为推崇现代建筑。南加大建筑系与多伦多大学的建筑系,至少与弗兰克多年前在布鲁尔学院图书馆里的介绍材料上所读到的,那个只教学生设计漂亮的英式小木屋的多伦多大学建筑系,是截然不同的。在南加大,学生们所学习到的设计,更多的是诸如拉斐尔·索里亚诺(1934年毕业于南加大)那种严整的现代结构体系;或者是威廉·佩雷拉(William Pereira)的那种暴躁的现代主义建筑体形——佩雷拉的事务所是战后洛杉矶建筑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再或者是像约翰·劳特纳(John Lautner)的那些对当时的年轻建筑师们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形式极富视觉张力的未来主义住宅设计。上述的这一系列迥异的设计风格,后来被人们通称为“20世纪中叶的现代主义”(midcentury modern),它们都植根于洛杉矶这座城市,也都把南加大视为精神家园。在南加大建筑学院,大量教职人员都是活跃于洛杉矶当地的建筑师,他们在教书的同时,也都在这座城市里不断地进行着他们的设计实践,他们各式各样的作品,共同塑造了战后洛杉矶的城市风貌。
这些建筑师里,有不少弗兰克早就已经认识了。通过阿诺德·施里尔和朱利叶斯·舒尔曼,弗兰克已经早早地建立起了自己在建筑界的关系网络,其中也包括洛杉矶其他的一些现代主义建筑师,比如同样在南加大教书的哈韦尔·汉密尔顿·哈里斯(Harwell Hamilton Harris)和卡尔·斯特劳布(Cal Straub)。他欣赏并且敬仰这些建筑师,但某种程度上他还是觉得自己是这个圈子的局外人。弗兰克其实并不是那种热衷于小圈子的人,他被洛杉矶众多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优秀作品所感染,渴望能够向他们学习,同时他也梦想着未来,能够有自己的一番成就,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加入他们的圈子。他也想要被人欣赏和敬仰,不过那时的他,还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明确方向或方法。他仍在学习,在他有能力确定自己的方向,明了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建筑之前,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是当时的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的东西,而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前辈的作品。
弗兰克在建筑学院的第一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二个学期,他的设计课老师名叫比尔·舍恩菲尔德(Bill Schoenfeld),是个刚刚从南加大毕业没多久的建筑师。后来,他去了威廉·佩雷拉的事务所工作,之后还承担了洛杉矶国际机场项目的规划和设计工作。不过在1951年春季,舍恩菲尔德还只是个负责低年级课程的年轻讲师,而且,他对于弗兰克的作业似乎并不满意。“他们让我们设计一些小房子[152],很基础,并不十分复杂。”弗兰克回忆起当时的设计作业。但舍恩菲尔德专门给弗兰克打了电话,告诉弗兰克他觉得他根本不适合当建筑师,还说他应该“离开建筑”,弗兰克回忆道。舍恩菲尔德这样说,原因可能是出于他个人的对于弗兰克的不喜欢:从舍恩菲尔德后来的事业发展来看,他十分偏爱“国际式”(corporate style)的建筑风格,而弗兰克,很可能在他面前表现出了对于这种建筑的反感。那个时候弗兰克所仰慕的建筑师,如辛德勒和索里亚诺,无论从他们本人的个性上,还是作品的风格上,可以说与千人一面的所谓“国际式”都相去甚远。
弗兰克后来觉得,舍恩菲尔德之所以给他提出这种奇怪的建议,让他“离开建筑”,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无法明说的动因。“可能是反犹太主义[153],因为我曾经历过反犹太主义者的歧视和欺负,所以我能够感觉得到。而当时社会上的反犹太主义确实有所抬头。”虽然洛杉矶是一座日新月异的新兴城市,在许多领域里开了先河,但是在当时,洛杉矶的建筑行业,很大程度上还是与美国其他地方一样,仍然是由英裔新教徒群体(WASP)所主宰的一种绅士的职业。建筑业界的犹太人数量相对较少,而女性则更是几乎没有,许多著名的建筑师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是保守派,他们更关注的是建筑商业的一面,而不是艺术的一面。即便是一些现代主义建筑师,似乎也仅仅是把兴趣局限于美学领域的创新。他们的设计,在形式上常常是一些“打破传统”的优雅的玻璃盒子,但是在他们的建筑里面,女人仍旧承担全部的家务,掌握决定权的依旧是男人。事实上,对于那个时期的许多建筑师来说,这便是他们的理想和目标了。他们并不追求通过建筑去改变世界的运行规则,能够改变世界的外观,在他们看来就已经足够了。
弗兰克的观点和他们不同。在他的成长经历中,身边有不少强势的女性,比如他的外祖母和母亲。他知道在他们搬到洛杉矶后,是母亲坚强地支撑起了这个家。另外,从女友安妮塔身上,弗兰克也看到了另一个坚强的、有志向的女性,他认同安妮塔关于父亲应该更多地支持她去接受教育的信念,而这一点显然也促进了他们的关系。欧文和西尔玛在政治上一直都是左派自由主义,多年来艰难的生活挣扎,更加强化了他们的这种立场。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平等地获得机会,虽然经历了种种挫折,但他们的这一信念并没有磨灭,并且还传递给了他们的两个孩子。
不过,且不论弗兰克与比尔·舍恩菲尔德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弗兰克这个学期的设计课成绩,其实还算说得过去,得了个B,比他上个学期的C要高。尽管上个学期的老师并没有像舍恩菲尔德一样,对于他是否适合学建筑表示怀疑。虽然弗兰克与舍恩菲尔德之间的矛盾仅限于个人层面,但是,这对他日后对于建筑的理解,抑或是对于他自身的理解,还是产生了一些长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回忆,在弗兰克的印象中所贴上的标签,首先是一次可能的反犹太主义事件,而非是一次单纯的对于他能力的质疑。
南加大建筑学院对于现代主义的偏好,导致了他们对于建筑史,尤其是欧洲建筑史,相对来说缺少兴趣。学院里仅有一门关于建筑史的课程,内容有限而且乏味,在弗兰克的记忆里竟是些“无趣的大教堂图片之类的东西”[154],对于学生们的要求基本上就是动笔临摹,几乎从来不会有什么分析和讨论。直到很多年以后,弗兰克才真正得以体验到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古典建筑传统,以及20世纪的欧洲现代建筑,并且体会到其重要性。来自欧洲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对于洛杉矶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辛德勒和诺伊特拉都出生于欧洲,而且,除却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作品——尤其是诺伊特拉的——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包豪斯(Bauhaus)的影响。然而,与欧洲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在南加大却鲜被提及,他们更倾向于把洛杉矶的现代主义建筑视为是一种独立的,从美国西部被凭空创生出来的建筑思潮。即使是密斯·凡·德罗在美国的作品,对于南加大的师生来说,似乎也好像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一般难以接受。比如密斯在弗兰克还在建筑学院求学期间,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普莱诺(Plano,Illinois)建成的范斯沃斯住宅(Farnsworth House)。“我那时候痛恨范斯沃斯住宅。”[155]弗兰克回忆道,“我并不讨厌密斯。我只是无法想象如何在那样的建筑中生活。那简直是一种军事化的生活,住在那里你甚至不能随手把衣服搭在椅子上。”
南加大对于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的建筑总体上来说都缺乏重视,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建筑。自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以降,日本建筑被很多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师所欣赏,因为其简单的线条,纯粹的空间,以及那种亲近和简约的优雅融合。“那时唯一的人文主义的东西就是日本的影响。[156]当年,门德尔松来过南加大讲座,弗兰克说他当时‘根本无法产生共鸣[157],因为我那时仍处在崇拜日本的时期。那一时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有些至今仍然存在。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我的DNA里,无法除去了。至于欧洲建筑师(如门德尔松),我虽然也知道他很重要,但我还是觉得和他有距离。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也是一样。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一样。柯布西耶,一样’”。
不过,弗兰克始终保持着对洛杉矶当地现代建筑的浓厚兴趣,尽管他对其源流和历史不太关心。他依旧热衷在城里到处逛到处看,有时是与朱丽叶斯·舒尔曼和阿诺德·施里尔一起,有时则是和他建筑学院的新同学们一起。最常和他一起出去逛的,是个高高瘦瘦,有点羞涩的男生,名叫格里高利·沃尔什(Gregory Walsh)。格里高利在加州的帕萨迪纳(Pasadena)长大,起初就读于帕萨迪纳城市学院(Pasadena City College),后来转学来到了南加大。和弗兰克一样,格里高利·沃尔什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个“外来者”。他也来自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不过,他家是个保守的天主教徒家庭,而不是左派自由主义的犹太人家庭。弗兰克还记得,他曾经隐约察觉,格里高利的父母并不支持儿子和他这个犹太人交朋友。有一次,他们俩还真的差点绝交,因为沃尔什告诉他,不必担心他父母的反犹太主义,因为他们已经决定把弗兰克归入为“犹太人里那部分好人中的一员[158]”。
沃尔什和弗兰克一样,酷爱音乐、艺术和文学,他觉得自己比其他的同学要成熟一些。而且,与弗兰克很类似的是,他对于建筑的兴趣也不是通过对工程、结构或者地产行业的兴趣发展起来的,也是通过对于艺术的喜爱。他很早就放弃了成为艺术家的想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父亲认为他当艺术家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不光是艺术,其实老沃尔什认为建筑设计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他的儿子一开始学的是建筑工程。但是仅仅一个学期之后,格里高利就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是做工程师的材料,他不想再假装成一个听话的好儿子了,他真正想要做的是建筑设计师。此后,经过帕萨迪纳城市学院两年的学习,他觉得自己有了足够的把握,于是便申请转学,来到了南加大建筑系,不过南加大拒绝认证他此前学过的所有建筑课程,最后只把他插班进了二年级,而不是他本来期望的三年级。这个当时看来的小小的挫折,却意外地成全了沃尔什的好运,进入当时的二年级,使得他因此而成为了另一位和他一样有着不同于其他同学的背景的学生——弗兰克·戈德堡的同班同学。
格里高利虽然刚刚进入南加大就认识了弗兰克,但是,直到1951年秋季,他们上三年级时,两个人才真正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格里高利回忆,弗兰克“实际上是我唯一[159]能谈得来的同学……其他同学大多数是笨蛋”。但弗兰克“一直都很聪明……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事物的方式”。
“格雷格(Greg,格里高利的昵称)和我成为了铁哥们[160]。我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有点像当年我和罗斯的友谊。”弗兰克回忆道,“格雷格是个古典音乐的专家……他还是个关于日本的专家,正是因为受了他的影响,我才开始阅读日本的文学作品,研究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作品有联系的日本建筑,我记住了每座寺庙的形制和样式,提笔就能画出来。”格雷格常带着弗兰克——有时是弗兰克和安妮塔两人——一起去听古典音乐会。弗兰克还记得他和格雷格一起去听了[161]罗莎琳·杜蕾克(Rosalyn Tureck)演奏的《戈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
弗兰克和格雷格都拥有着超越建筑本身的,对于广泛的文化艺术的兴趣,而单就建筑方面来说,他们的建筑学习也都不只是囿于南加大的课堂上。和弗兰克一样,格雷格·沃尔什也热爱建筑考察,他们经常结伴而行。“我经常去考察[162]诺伊特拉、赖特和辛德勒的建筑作品。班上的其他人都没有这种爱好,除了格雷格以外。”弗兰克说,“因此那时候基本上每到星期天,我们俩就会相约一起出门探险。施里尔和安妮塔也常常和我们一起去。每次考察我们都会有不小的收获。”弗兰克说,见到感兴趣的建筑,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直接上去敲门,请求进到内部去看看。[163]
“格雷格能够理解我。”[164]弗兰克回忆道,“我热爱古典音乐,而格雷格恰好是个钢琴家,对于古典音乐有着很深的造诣。那会儿班上的同学很少有像他一样富有文化修养的。安妮塔也非常喜爱文化艺术。所以我们之间交流起来就很容易,没什么障碍。”弗兰克、安妮塔和格雷格成为了很要好的伙伴,他们不分你我,不光是在学校里,格雷格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弗兰克家庭的一员,以至于在多琳的记忆中,“格雷格就像是我的另一个哥哥”[165]。
弗兰克和格雷格一直自认为他们与班里的其他同学有点不同,这种不同也被他们三年级的一门课程作业所证实了,他们俩完成这项作业的方式和态度确实是独特的。作业的内容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位当代建筑师,分析他的一座建筑作品。“弗兰克选择的是特立独行的辛德勒[166],他所分析的作品是辛德勒在影视城(Studio City)设计的凯里斯住宅(Kallis House)。我的选择,约翰·劳特纳,也是个离经叛道的建筑师。我研究了他当时的几件重要作品之一,一座有着只用三根柱子支撑的六边形屋顶的住宅。”格雷格回忆道。他们两个人的选择,从很多方面上来说,都是与众不同的。辛德勒和劳特纳的职业生涯都是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事务所起步的,后来,他们又都离开赖特独立发展,各自进行自己高度原创性的建筑实践。辛德勒1887年出生于维也纳,弗兰克认识他时,已经是他职业生涯的晚期了——他于1953年去世——但是他依旧有着旺盛的创造力。那时,弗兰克研究分析的凯里斯住宅刚刚建成三年,这个作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弗兰克发展和创造出的属于他自己的建筑语言和手法。开敞的方盒子体量,倾斜的墙壁和屋顶,梯形的窗子,粗野的未完成感,以及随处可见的尖利的锐角,凯里斯住宅几乎可以说是三十年后弗兰克在圣莫尼卡的那座自宅的原始版本。[167]
劳特纳和辛德勒差不多,对于当时现代建筑流行的简单方盒子并不感冒。虽然他的作品富有他自己的独创性,但是,他很大程度上也沿袭了赖特,从他对于基本几何形体,如圆和六边形的偏好就可以看出。而后期他所致力于的对各种曲线和未来主义的形体的运用,也与赖特晚年所喜好的建筑形式颇为相似,甚至比赖特要更为夸张。劳特纳从年龄上比辛德勒要年轻一些,他的作品比辛德勒的显得更为优雅,而且他似乎总是要追求一种华丽的效果,这对于高傲的辛德勒来说无疑是他所不屑的,一种做作甚至于是廉价的风格。在格雷格·沃尔什选择他的作品进行研究那会儿,劳特纳还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中期,此后他又继续创作出了许多重要的作品,职业生涯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与弗兰克有所交集。尽管辛德勒与劳特纳在建筑形式和个人性格上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这两位建筑师最为知名的项目都是一些私人住宅。他们两个人都无法很顺畅地与那些大的公司客户或者商业地产开发商合作,因此,他们的建筑实践在数量和类型的多样性上都比较局限。不过在1951年,对于弗兰克和格雷格这样的建筑学生来说,辛德勒和劳特纳都是能够带给他们无数启迪和灵感的榜样建筑师。
南加大的建筑学院里,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可以激发他们创作热情的建筑师。弗兰克和格雷格都认为加尔文·斯特劳布(Calvin Straub)就是这样的一位卓越的建筑师和建筑教师——用格雷格的话讲加尔文就是他们的“指路明灯”[168],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教给了他们从街区和城市的尺度上来思考设计,而不是只盯着一座建筑。“加尔文·斯特劳布是我三年级时的教授[169],他从刚开学起就很喜欢我……他是第一个让我感到被关怀和被重视的老师,因为你要知道,我上一个学期的老师(比尔·舍恩菲尔德)压根就觉得我不适合干这行。”弗兰克回忆道,“上了三年级后,我才下定决心,绝不会放弃建筑,我才不会去管那个白痴说我什么,到那时候我才开始有了一点自信。斯特劳布的设计课让我学会思考建筑与街区的关系。”在弗兰克的记忆里他的课程内容都是“一种很理想主义的东西。在第一个学期里,我们做了许多关于理想化的城市的分析图解,我在政治上很左倾,所以这些东西很对我胃口。他的课真的很棒。他也很喜欢我,第一个学期他给了我很高的分数”。在格雷格的回忆中,斯特劳布的课堂上充满了“一种理想化的,类似于花园城市理论(Garden City)的那种东西”[170],而且他对于如何图解一座城市有着严格而具体的标准和要求。斯特劳布对于城市设计有着一些近乎吹毛求疵的规矩,弗兰克很可能也曾经因此而抓狂过,但是,弗兰克十分珍惜这种能够设计一个完整社区的机会,他耐着性子,按照斯特劳布对于分析图和平面图纸的要求完成了这个作业。学生们总是在喜欢自己的老师的课上表现得更好,弗兰克也是一样。“有一天他给我打来电话[171],告诉我,我已经遥遥领先于班里的其他同学了。我可是刚刚被(舍恩菲尔德)说过应该趁早离开建筑的!”弗兰克回忆说。
“我觉得在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172],对于斯特劳布的课程,我们每个同学都感到了有一些手足无措。”格雷格在一本关于他和盖里学生时代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他的这项名为‘美好生活’(good life)的设计课程,是一次关于一种理想化但可实施的社区模式的尝试,这是一种5000人左右规模的社区单元,在社区中,住宅、学校、购物和办公等功能被组织在步行尺度以内,人行和车行的流线被安全地加以分流。这种城市设计理念与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和克拉伦斯·斯坦因(Clarence Stein)的理论,以及‘绿带’(Greenbelt)等关于新城规划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对于三年级的我们来说,这些无疑都是十分陌生的。这门课的作业,要求进行大量的功能分析和研究,大部分是图表化的,而非‘真实的建筑’,很多同学对此都有怨言。但弗兰克和我没有抱怨,正是在认真钻研和探讨这门课的过程之中,我们成为朋友。”
不过,尽管弗兰克和格雷格都很欣赏斯特劳布的教学理念,认为得到了他启发,使自己能够在更广阔的、城市的尺度上思考问题。但是,他们两个人都不能认同斯特劳布过于模式化的设计方法,无论在建筑还是城市尺度上都是如此。斯特劳布十分热衷于一种简单的、模式化的建筑,从梁柱结构的跨度到平屋顶的尺寸,甚至是平面布局和立面划分都要基于几何模数。“我记得我们两个讨论过[173]这种设计方法,提出了这种方法所带来的一种潜在的消极影响:过度依赖模数,容易造成对于视觉效果的忽视。”格雷格写道,“这次对话所谈到的这些东西,后来也成为我们两个人的建筑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弗兰克和格雷格由此从斯特劳布的条条框框中跳脱出来,他们认为应该从造型审美以及功能使用的角度上去综合判断一个建筑作品的好坏,而不是去关注建筑如何巧妙地应用了模数——对他们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一课,只不过讽刺的是,他们最喜欢的老师却成了这一课上的反面典型。
弗兰克和格雷格从另一位老师——哈里·伯奇(Harry Burge)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伯奇没有斯特劳布那样的社会理想主义,他崇尚的是实用主义,这也是弗兰克和格雷格两个人共同的一种美学倾向。格雷格记得,伯奇总是穿着一件黄褐色的工作服,他的课也总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他要求每个学生选取自己之前的一个设计作业,“将其转化成[174]‘能够’实施的工程图纸,图纸要有精确的比例。把自己的建筑创作转化成可以建造的施工图是个很痛苦的过程……实际建造中的种种要求和限制,会淡化方案阶段纯粹的设计概念。”格雷格写道,“弗兰克后来告诉我,相比于学校中的其他课程,他从伯奇的课堂上所学到的,这种直观而严肃的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方式,最为直接地影响了他日后的建筑实践。”
在弗兰克的印象中,伯奇“无关诗意[175],更无关艺术。他就是个‘实用主义先生’……他曾说他觉得我会有很好的前途,因此他告诫我说:‘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今后,每当你完成一个新项目,无论多大或多小的项目,它都应该是你到那个时候为止最出色的作品。一定要记住这个,因为这就是人们评价你的标准。’”
在南加大学习的几年中,对弗兰克影响最为深远的老师,当数盖瑞特·埃克博(Garrett Eckbo)了。埃克博是一位景观建筑师,出生于加利福尼亚,曾在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at Harvard)求学,他与丹·基利(Dan Kiley)一同被公认为是美国当代景观设计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但是和基利相比,埃克博的设计理念更加倾向于以社会议题为导向。相对于一味追求美学效果的极少主义的植物布置方式,他更感兴趣的东西,是景观设计与更大尺度上的城市规划问题之间的关系。埃克博在他出版于1950年的著作《为生活的景观》(Landscape for Living)中提出,现代的建筑与景观设计应该被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一生都在主张把景观设计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因,弗兰克非常认同他的这种主张。后来,弗兰克还成为了埃克博在南加大的助教。
弗兰克记得,埃克博“成为了我最为亲密的朋友和家人[176]。甚至于在政治立场上,我们两个人也异常投缘……他也是个左派”。
埃克博的政治立场非常左倾,弗兰克记得他曾经因此而遭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骚扰”[177]。在一堂课上,埃克博表达了他对于罗森堡夫妇案(Ethel and Julius Rosenberg case)死刑判决的强烈愤慨,随后他便遭到了该组织的调查。[178]那堂课弗兰克也在场,他记得埃克博是在回答一个学生的提问时,谈起了他关于罗森堡夫妇所受到的不公正判决的看法的。后来经证实,那名提问的学生,是联邦调查局(FBI)安插在南加大的一名专门负责调查校园内左翼活动的探员,他故意用提问的方式,诱使埃克博在课堂上发表了上述政治言论。
联邦调查局的这种构陷行为,更加让埃克博成了弗兰克心目中的英雄。他与其他几个思想上左倾的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名叫“建筑小组”(Architecture Panel)的松散的小组织,旨在探索建筑的社会性,增强建筑设计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小组与一个名为全国艺术、科学和专业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Arts,Sciences and Professions)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组织有一些联系,这种联系虽然并不太密切,但还是引起了建筑学院当时的院长亚瑟·盖伦(Arthur Galleon)的注意。他把弗兰克和同是这个小组成员的格雷格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们说:“弗兰克,当你站在山顶上时[179],山的两侧你都能看得到。所以,站在山顶就好,不要滑向山的任何一边。”
弗兰克并没有听从院长的建议。从那之后,他依旧是“建筑小组”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参与组织了每周五晚间的一系列关于建筑设计与社会责任的座谈活动,并且鼓励小组成员参与到社会公共议题中去。当时,靠近洛杉矶中心城区的一项政府主导的公共住宅项目,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他们的小组就积极地参与到了讨论之中。这个项目位于洛杉矶的查韦斯·拉温(Charvez Ravine)地区,原本是一个主要由低收入的墨西哥裔家庭组成的社区。市政府买下了这块土地,打算在这里兴建一片名为“乐土公园高地”(Elysian Park Heights)的巨大的公共住宅项目,由理查德·诺伊特拉和罗伯特·E.亚历山大(Robert E.Alexander)主持设计。整个项目包含24座13层的塔楼和163座联排住宅,建成后能够提供大约3600套廉价公寓,将成为当时洛杉矶最为庞大的公共住宅项目。这样的项目,让弗兰克激动不已,在他的想象中,这能够展现一个建筑师针对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的看法。总体上说,这个项目在洛杉矶这座城市并不怎么受欢迎。人们反对“乐土公园高地”项目的最主要的原因,甚至并不是出于对当地被迫搬迁的贫困居民的保护(要等到一代人之后,这个理由才成了人们抗议大型建设项目时最常用的说法),而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由政府牵头,兴建如此大规模住宅项目的做法,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政策,它不应该在这座城市发生。尽管这种观念的产生,部分源于《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推波助澜,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加州地区的政治气候基本上也确实如此。这种思潮事实上也清晰地标示出了洛杉矶这座城市的底色,虽然城中遍布的快速路,以及快速扩张、蔓延不绝的广阔市郊地带,并且它们一直以来都象征着这座新兴城市的进步性和独特性。但是归根结底,洛杉矶是一座保守的城市。那些从美国中西部及南方移居过来的居民,来到洛杉矶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以及更舒适的气候,并不是来追求一个更为进步的社会的。通过对这个项目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判,“乐土公园高地”的反对者们成功地推迟了这个项目,并且最终阻止了它的实施。这种批判,尽管并不能全然令人信服,但还是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洛杉矶房管局(Los Angeles Housing Authority)的副主任弗兰克·威尔金森(Frank Wilkinson)也因此收到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传票。[180]最终,这块在项目取消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居民搬迁的,总面积254英亩(约合1平方千米)的用地,被卖给了洛杉矶道奇队(Dodgers),成为新的道奇体育场(Dodger Stadium)的所在地。
弗兰克的政治情感源于对底层的同情。一直以来,他也把自己视为是一个从未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外来者,这一想法,在他被南加大的建筑系兄弟会拒之门外后,变得更加强烈。弗兰克与他的哈特利表哥不同,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热衷于这类校园兄弟会组织的人,虽然他也曾一度加入过哈特利所在的阿尔法·厄普西隆·派兄弟会(AEPi),但是这主要是因为他很喜欢和哈特利在一起,愿意跟着他,而不是因为他自己主观上特别想要找一个兄弟会加入。而且,弗兰克后来还被开除出了[181]阿尔法·厄普西隆·派,因为他试图保荐他的一个黑人同学加入这个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兄弟会。然而,在弗兰克心里,被逐出那个阿尔法·厄普西隆·派兄弟会,其实并不算什么。但是被建筑系的兄弟会阿尔法·若·西(Alpha Rho Chi)拒绝,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弗兰克的这种心理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心理学上的“格鲁秋·马克斯效应”(Groucho Marx),对于一个欢迎他,愿意接纳他的组织,弗兰克并不会感到十分珍惜。他甚至乐于通过某种介乎于恶作剧和抗议行动之间的方式,退出这个组织。但是,如若他不是作为提出退出的那一方,而是被拒绝的一方,他就会感到非常的不高兴。被阿尔法·若·西兄弟会排除在外,让弗兰克感到出离愤怒,因为他的同学,包括格雷格·沃尔什和其他的几个朋友,都是这个兄弟会的成员。他认为这一定又是反犹太主义的驱使。“我明白他们想要干什么。”[182]他说,这样的经历让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在弗兰克心中更为根深蒂固。“这更刺激了我心中的左派自由主义信仰,使其变得愈加强烈了。”
* * *
与此同时,弗兰克与安妮塔的恋爱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和稳定。两个人都是初次恋爱,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与他们所共有的一种渴望逃离家庭和父母的叛逆本能密不可分的。但是,他们在这段感情中,彼此给予对方的绝不仅仅是家庭之外的一个避风港而已。他们觉得彼此有相同的世界观和相同的政治立场。安妮塔对于弗兰克在建筑和社会方面的工作和努力都十分认同,而弗兰克也相信安妮塔一定能够实现她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的理想。精神上的认同,毫无疑问,让他们十分享受这份亲密关系。而彼此之间身体上的吸引,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
戈德堡家与斯奈德家也逐渐熟络起来,两家人那时都觉得,孩子们结为夫妻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理查德·斯奈德还记得,那段时间欧文和西尔玛常常到北好莱坞他的家里来拜访,而斯奈德一家也会到橘子街上的戈德堡家去回访。“西尔玛总是表现得精神饱满[183],兴高采烈。而欧文则显得非常非常虚弱,但他也总是西服革履,穿得很正式。”——这表明,欧文和西尔玛都觉得,与斯奈德家的关系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这不是普通的亲戚朋友关系,随着孩子的婚姻,两个家庭即将成为一家人。
1952年冬季,两家人的大日子终于到来。2月2日,弗兰克与安妮塔在山谷犹太人社区中心(Valley Jewish Community Center)正式结为夫妻。那会儿距离弗兰克23岁的生日还有三个半星期,他的新娘则才只有18岁。西尔玛和欧文勒紧开支,省出钱来为弗兰克置办了一身新西装。贝拉·斯奈德也给安妮塔做了一件新连衣裙。婚礼的排场相当小,大多数的来宾都是弗兰克这边的、戈德堡家的亲戚们。不过当时弗兰克最好的朋友,也是已和安妮塔很熟识了的格雷格·沃尔什并没有到场。在婚礼的最后,弗兰克依照传统犹太婚礼的结束方式,踩碎一只高脚杯。随后,宾客们从社区中心转场来到运动员小屋(Sportsman's Lodge),参加由斯奈德家招待的宴会。运动员小屋位于文图拉大道(Ventura Boulevard),是一家奇特的旧好莱坞风格旅店,以其伪乡村式的装潢和养着鳟鱼的池塘而闻名。
在婚礼之前,弗兰克和安妮塔就在克伦肖大道(Crenshaw Boulevard)上租好了一间公寓,离南加大校园很近。他们花了点时间,用类似纸灯笼、豆袋椅之类的小东西,还有他们的艺术家朋友们赠送的画作,将公寓布置了起来。理查德·斯奈德还记得他在他们的公寓里见到的,一个鱼形的日本纸灯笼——“他一直都很喜欢鱼”[184]。整间公寓的布置,有着一种青春和随性的简约,给人感觉所有的元素都是即兴发挥的。这种轻松的、不拘小节的居住环境,是与弗兰克成长中所住过的那些公寓和房屋完全不同的。一开始,他和安妮塔似乎更多地把这间公寓当成了他们的一个设计项目来对待,而不仅仅是生活的地方,婚礼之前他们也从未在那里住过一夜。婚礼结束后的那天晚上,走出运动员小屋的弗兰克有点紧张,他要第一次和安妮塔一起回他们自己的家了。在婚礼招待会的间隙,哈特利表哥悄悄地在他兜里塞上了几个安全套,不过这份小礼物也并没能完全打消他的紧张,虽然他十分开心终于能和安妮塔成婚了,但他其实还并不太清楚晚上在床上该做些什么。他和他的新娘还都是处子之身。
在那间小公寓里度过了新婚之夜后,弗兰克与安妮塔便踏上了去往沙漠温泉村(Desert Hot Springs)的蜜月之旅。他们所住的沙漠温泉村汽车旅馆[185](Desert Hot Springs Motel)是由约翰·劳特纳设计的,弗兰克选择这家旅馆投宿,一定有部分原因是这个。[186]这趟旅行很轻松,沙漠温泉村离洛杉矶并不太远。无论从时间还是金钱上,当时的弗兰克也都负担不起其他更远一些的目的地了。很快,他和安妮塔就结束旅程,回到了克伦肖大道的家中。弗兰克需要继续他的学业,而安妮塔则开始打工赚钱,以支持丈夫完成学业,拿到学位。小两口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就必须自己承担挣钱养家的责任了。
婚后回到南加大,弗兰克又遇到了几位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老师,其中就包括学院里的另外一位政治左倾的教员——建筑师格里高利·艾因(Gregory Ain)。和其他一些弗兰克认识的,在那段反共情绪高涨的时期里遭到调查的建筑师一样,艾因——用格雷格·沃尔什的话讲——也是“愤世嫉俗并且虚无主义”[187]的,格雷格因此而觉得他很难相处。然而弗兰克却非常喜欢艾因的教学方式,尽管艾因对学生的态度一贯很冷淡。“我从来不清楚[188]他到底喜不喜欢我,或者喜不喜欢我的作业。”弗兰克说。但他喜欢上艾因的课,因为他觉得艾因在智识上胜过学院里的任何一位建筑教授。“他会在课堂上谈论艾略特(T.S.Eliot)的《大教堂凶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还会在课堂上朗读诗歌,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谈论建筑。”弗兰克回忆道。弗兰克觉得艾因把建筑作为文化艺术的一部分进行探讨的方式十分吸引他,认为艾因给他指明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虽然格雷格和弗兰克一样,在兴趣上也更倾向于建筑的智力性和非技术性的一面,但是他还是接受不了艾因的冷漠态度。而格雷格和弗兰克后来都有些失望地发现,艾因在思想上的开放,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广泛地接受多样化的建筑设计方法。用格雷格的话说:“他那种严密的、强逻辑性的设计方式[189],似乎是有局限性的。”
弗兰克另外一位重要的老师是埃德加多·康提尼(Edgardo Contini),康提尼是洛杉矶一家庞大的建筑和规划设计机构——格伦联合事务所[(Gruen Associates)下文简称格伦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家事务所因设计了美国最早期的一批购物中心而知名。1952年暑假,建筑学院的盖伦院长帮弗兰克在那里找了一份暑期实习,而他意外地发现自己与这家事务所非常合拍,于是,那之后的几个暑假,弗兰克都会回到那里工作。虽然格伦联合事务所并不是以弗兰克最感兴趣的公共住宅项目而著称,但是,他们在城市规划领域的活跃性十分吸引弗兰克。而且,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出生于奥地利的建筑师维克多·格伦(Victor Gruen)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对于战后城市形态的发展和演进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入的思考。所以,格伦事务所对于社会和城市的公共问题是有一定的关注的。无论如何,弗兰克很喜欢这份实习工作,也很喜欢这家事务所的氛围。1953年暑假,他还参与了后来成为格伦事务所最为著名的项目之一的,美国第一家封闭式购物中心——南谷购物中心(Southdale)项目,这个项目于1956年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城外落成。(作为暑期实习生,弗兰克并没有机会参与到实际的设计之中,只是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模型制作。)后来,弗兰克在南加大成为了埃德加多·康提尼的学生,他也因此对康提尼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康提尼的设计课上,弗兰克设计了一座由混凝土板搭起来的房子,他有意学习了鲁道夫·辛德勒当时的一个新作品。康提尼很喜欢弗兰克的这个作业,不仅给了他A的成绩,而且还力劝他考虑毕业后到格伦事务所正式工作。
弗兰克对公共住宅项目的兴趣,引起了他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同学雷内·佩斯凯拉(Rene Pesqueira)的注意。佩斯凯拉找到弗兰克,询问他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做一个城市规划的实际项目,项目位于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Baja California)。佩斯凯拉的家里与当地的州长布拉乌利奥·马尔多纳多·桑德斯(Braulio Maldonado Sández)相熟,所以才得到了这个机会,州长希望新的规划能够有效地带动这一地区的发展。对于一个还没毕业的建筑学生来说,这个项目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贵机会,弗兰克立刻就答应了下来。他和雷内一同被邀请到下加利福尼亚进行了基地调研,还得到了一笔可观的项目资金。回到洛杉矶,他们便在拉·贝瑞阿大街(La Brea Avenue)租下了一间小办公室,又从南加大雇来了几个同学,他们的“协作专业城市规划小组”(Collaborative Professional Planning Group)就这样有模有样地运营起来了。
在弗兰克和雷内所做的规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一座横跨加利福尼亚湾,将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与墨西哥本土联结起来的跨海大桥,他们希望这座桥能够发挥纽带的作用,刺激下加利福尼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我记得我们为这个想法感到兴奋不已[190]。下加州的桑德斯州长也被我们说服了,他答应我们会尽力争取这座大桥的实施。不过我们毕竟还都只是孩子,在我们眼里可能没什么事是做不成的。”弗兰克回忆道。加利福尼亚湾,最窄的地方也有30英里(约合48千米)宽,要在这里建设一座跨海大桥,且不论结构上是否可行,单从经济角度看,这个想法也实在是太过激进了。最终,这座大桥,乃至于他们所做的这份规划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付诸实施,而这个规划项目,也连同“协作专业城市规划小组”一起,不了了之了。
不过,参与这个项目,弗兰克也不是一无所获。他的毕业设计选题就是来自于这个项目。他和雷内·佩斯凯拉一起,在下加州规划项目的用地范围里选了一块地,设计了一个公共住宅综合体。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下加州规划项目还没有最终搁浅,尚在进行之中。因此,弗兰克设计的住宅综合体,看起来就像是真的要建设的实际项目一样。很长一段时间里,弗兰克都觉得自己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在毕业设计中实践了自己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观,并且还凭借这样的设计获得了报酬。他记得当时在南加大教授五年级设计课的建筑师威廉·佩雷拉[191],对于他和雷内的这种自主创业的精神和追求赞赏有加。
虽然选择了雷内作为毕业设计的搭档,但弗兰克与格雷格的关系也依旧亲密无间。格雷格的毕业设计题目比较常规——为丰塔纳市[Fontana,离圣伯纳迪诺(San Bernardino)不远]设计一座市民中心。毕业设计期间,他、弗兰克和雷内三个人,把弗兰克与安妮塔的公寓当作了他们的绘图室,在那里一起工作。因为南加大的建筑系实在是太挤了,画图和做模型的空间远远不够。他们把几块木头门板支在锯木架上,摆在客厅中央充当绘图桌,就这样工作了整整一个月,用百利金(Pelican)的黑墨水,画完了他们三个人的两个毕业设计项目的全部图纸。
安妮塔很喜欢格雷格,几乎把他也视为是家里的一员了。弗兰克和格雷格曾经一起用榻榻米垫子、纸糊墙和吊得很低的天花板,把他们克伦肖大街的那间小公寓装修成了日式风格,在那里为弗兰克的妹妹多琳举办了她十六岁生日的惊喜派对。“他和格雷格一定为此忙活了几个星期。”[192]多琳至今还对这场派对记忆犹新,虽然她同时也记得,来参加派对的,她费尔法克斯高中(Fairfax High School)的朋友们,普遍觉得他哥哥的这个主意有点奇怪——在一间装扮成日式风格的公寓里举行的一场“甜蜜十六岁”派对(sweet-sixteen party)。
在弗兰克和他的两位同学,把公寓改造成临时建筑工作室,为了毕业设计埋头工作的那段时间,安妮塔已经怀有了身孕,这也使得那间本就不大,并且客厅里还挤着三个建筑学生的小公寓显得更加局促了。不过,这还不是让安妮塔最头疼的。除了这间狭小的公寓,即将生下自己第一个孩子的安妮塔,还有一件更为烦恼的事情——她不喜欢戈德堡这个姓氏,不愿意被人称作安妮塔·戈德堡。嫁给这个名叫弗兰克·戈德堡的建筑师后,安妮塔的心里对丈夫的姓氏一直不满意。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跟着这个姓。安妮塔自小一直使用斯奈德这个无种族色彩的姓氏,因此她很难接受一个如此明确地标示出她犹太人身份的姓氏。况且,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社会上的反犹太主义还依旧甚嚣尘上,很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因为不愿意雇用一个姓戈德堡的建筑师而去另找别处,由此带来的潜在的经济损失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弗兰克从主观上是不愿意掩饰他的犹太人身份的,对于那些仅仅因为姓氏听起来是犹太人就拒绝一个建筑师的客户,他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之中,他也清晰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很容易被认出身份的犹太人,生活中确实会多出不少的麻烦。在南加大读书的几年,他已经感受到了洛杉矶无处不在的反犹太主义。压垮安妮塔,让她下决心改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部著名的广播和电视剧《戈德堡一家》(The Goldbergs),主演格特鲁德·伯格(Gertrude Berg)在剧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带有明显的种族刻板偏见的犹太母亲形象。这个角色的出现,让安妮塔再也不愿意继续背负着这个,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带着讽刺意味的喜剧形象的姓氏了,同时她也打定了主意,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随这个姓。
安妮塔的想法与西尔玛不谋而合。其实,改掉犹太姓氏在戈德堡家的亲戚中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欧文的哥哥和嫂子,就把姓氏从戈德堡改成了盖洛德,还给儿子取名为哈特利·默文·盖洛德三世(尽管这个新改出来的盖洛德家族里面,从来就没有过哈特利·默文·盖洛德一世和二世)。西尔玛虽然没有盖洛德夫妇那种锲而不舍提升社会地位的雄心壮志,但她也一直觉得戈德堡这个姓与她对于社会地位的期望不太相称。她已经忍受这个姓氏很久了,一直期待着有机会改掉它。不过欧文却并不认同女人们的想法。姓戈德堡没什么不好[193],他说,并且宣布要把这个姓刻在自己的墓碑上。[194]至于弗兰克,尽管在建筑学院的兄弟会和其他很多场合,他也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身为犹太人所遭遇的种种歧视,但是,他觉得改姓只能算是一种逃避,是对反犹太主义的妥协,而非抗争。“我并不想改姓[195]。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左倾,是个绝对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他说。盖瑞特·埃克博也觉得弗兰克完全没有理由改姓。埃克博的意见,以及欧文的反对,都让弗兰克觉得改姓不是个好主意。因此,他反复地劝说安妮塔放弃这个想法。
但是安妮塔丝毫不让步。“她无比坚决。[196],你就知道我不得不同意她的要求。没有办法。我已经被逼到墙角了。”弗兰克说,安妮塔是个“强硬的实干派”。他还说,改姓这件事,后来成为了他在婚姻生活中的一种行为模式,他“不停地安抚安妮塔[197]。为了让她高兴,我只得勉强地顺从她,我讨厌这样。我同意了让她改姓。但是我心里对此感到非常不舒服。”[198]这件事也成为一个预兆,在以后的日子里,弗兰克感到安妮塔变得越来越难以取悦。“好像我永远也无法满足她。当我拿回薪水支票,她会嫌钱太少。我和朋友出去玩,她也觉得不好。”但是弗兰克还是同意了改姓,为了维系他们的婚姻,这其实也不算是个太高的代价,他觉得。
在改姓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后,新的问题——改成什么姓,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弗兰克坚决表示他不想改变姓氏的首字母,而已经赢得了这场改姓大战的安妮塔,在这种小问题上也不想再计较了,于是,新姓氏定下来仍要以字母G来开头。安妮塔和她母亲提出了吉尔里(Geary)这个名字,或者是它的一些变体,正是在这个名字的基础上,弗兰克琢磨出了把拼写变为G-E-H-R-Y的主意。他创造出这个拼写方式所依据的原理,是只有建筑师或平面设计师才能想得到的。弗兰克想要让他的新姓氏在外形轮廓上,看起来和戈德堡(Goldberg)这个单词尽量相似。戈德堡(Goldberg)这个单词,在中部有升起来的字母l、d和b,收尾则是降下去的字母g。而在盖里(Gehry)的拼写中,字母h就起到了l、d和b的作用,让单词的中部升起来,结尾的字母y则和戈德堡结尾的字母g一样,让单词的尾部降下去。通过这种与设计相结合的拼写推敲,改姓这件事,对弗兰克来说,似乎变得稍稍容易接受了一些。
弗兰克后来对改姓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尽管在1954年5月6日,他就已正式改姓[199],但此后的很多年里,当他以“弗兰克·盖里”来自我介绍时,总是要在后面补上一句“以前叫戈德堡”,仿佛这样可以减轻一些改姓给他带来的,持续多年的不安和尴尬。他常常和格雷格·沃尔什开玩笑,把沃尔什最喜欢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名曲《戈德堡变奏曲》故意说成是《盖里变奏曲》(Gehry Variations)。但是,这种自嘲式的幽默,丝毫不会减轻他对于改姓这个决定的本质上的难以接受。弗兰克的父亲欧文,对于他们的改姓也大为光火——“他对我大发雷霆[200]。”弗兰克回忆说——但是因为身体太虚弱,他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自己也被改了姓这个事实。欧文、弗兰克、安妮塔、西尔玛和多琳,从此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了盖里家,然而在欧文的余生中,他依旧固执地把自己称为欧文·戈德堡。
改姓的时候,弗兰克就快从南加大毕业了,这一决定弄糊涂了他的很多同学,他们所认识的那个弗兰克·戈德堡,莫名其妙地就从班级的花名册上消失了。很多年以后,弗兰克才发觉,他的一些多年不曾联系的南加大时期同学,可能不会把那些与他的新名字“盖里”相关的新闻和信息与他们所认识的弗兰克·戈德堡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对于他后来的人生一无所知。“因为改姓,有一群人就这样从我的人生中消失掉了[201],而我甚至对此毫无察觉。”他说。因为已经确定了要使用弗兰克·盖里这个名字,他的学位证书也是以新名字签发的。在1954年6月南加大的毕业典礼上,弗兰克在正式被授予建筑学学士学位的时候,对他过去的人生致以了最后的敬礼——他要求在颁发学位之前的点名中,仍以“弗兰克·戈德堡”来宣读他的名字。
1954年剩余的时间里,弗兰克和他们的“协作专业城市规划小组”仍继续推进着下加利福尼亚规划项目的工作,尽管那个时候这个项目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那年春季,弗兰克在“建筑小组”结识的年轻建筑师阿尔·伯克(Al Boeke),鼓励他试试申请到理查德·诺伊特拉事务所的工作,伯克曾在诺伊特拉那里参与过乐土公园高地的公共住房项目。虽然对于诺伊特拉那种极端克制的国际式(International Style)的设计审美并无太多好感,但是弗兰克很欣赏诺伊特拉对于公共住房项目的投入和支持,因此他还是接受了阿尔·伯克的建议,申请了诺伊特拉事务所。面试那天,弗兰克带着他的毕业设计——墨西哥的住宅综合体项目的图纸,来到了这位著名建筑师位于银湖(Silver Lake)的办公室。看过弗兰克的作品,诺伊特拉觉得很满意,他对弗兰克说他下周一就可以来上班了。“说完他就起身准备离开,[202]我说:‘那我应该去找谁谈我的薪酬问题呢?’”弗兰克回忆说,“而诺伊特拉却说:‘哦,不是这样的,下周一等你来了,你会见到某某人,他会告诉你在这里工作你需要支付给我们多少钱。’”弗兰克从来不曾想象过,一个如诺伊特拉这般杰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会在自己的事务所里搞这种类似于学徒制的东西,让年轻的建筑师付钱来换取在大师身边工作的机会。他知道自己是肯定付不起这份钱的,即便是能付得起,对于这样的一份“工作”,他也压根没有一点兴趣。弗兰克感到自己被深深羞辱了,结束了和诺伊特拉的面试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的事务所,此后便再也没回去过。他甚至都没有打电话回去,告知他们他不再想去那里工作了。
经历了在诺伊特拉事务所的不愉快后,弗兰克又回到了格伦事务所,那个他曾经愉快地工作了两个暑假的地方。然而,这一次在格伦事务所,他也并没能待上多久,就又不得不离开了,离开的原因不是格伦事务所不好或者弗兰克不喜欢那里的建筑风格,与这些都没关系。在格伦事务所只工作了几个月,弗兰克就被迫地以一种让他自己都感到十分惊讶和不悦的方式离职——他被征召入伍了。
在南加大读书时,弗兰克就已经是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Air Force 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Corps)的一员了。1950年,在他年满21周岁,选择成为美国公民后,他就加入了这一组织。(因为欧文是美国公民,弗兰克可以选择美国或加拿大的国籍。西尔玛也选择了加入美国籍,在1952年1月通过了入籍考试后,她正式宣誓入籍。)在20世纪50年代,所有身体符合条件的男性公民必须入伍服役,因此,弗兰克选择加入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选择。弗兰克觉得,参加空军,可以让他延续从跟随表姐夫亚瑟学习飞行开始就一直保有的,对于飞行的兴趣。加入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让他在毕业后有机会参加空军飞行训练,这种服役方式,比一般的兵役要显得更有意思些。格雷格参加的是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Naval ROTC),从南加大毕业后不久,他就被派往了日本。
弗兰克就没有格雷格那么幸运了。虽然大学的四年里他参加了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全部课程和训练,但是就在毕业前夕,他却忽然被告知,被从训练团除名了,原因是南加大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负责指挥官发现了他左膝上的那个小肉瘤,认为这个小肉瘤会让他无法通过飞行训练前的身体测试。“‘我们犯了个严重的错误。’”[203]弗兰克记得那位指挥官对他说,“‘因为你膝盖的,你无法从训练团毕业。’”“而我说:‘我的膝盖从加入训练团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而且你们都知道。’他说:‘这是我们的失误,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很抱歉。’我那些年全部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了。我当时真应该起诉他们。”后来,弗兰克认为[204],与他之前在南加大遭遇过的一些事情一样,如此随意地把他从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开除,很可能也是一种反犹太主义驱使下的行为。
唯一让弗兰克略感安慰的,就是他觉得他应该可以获得免予兵役的待遇了(那时候很多学生甚至用延期毕业的方式来逃避兵役),因为如果他的膝盖被认定为无法参加空军训练,那他就理所应当的不再满足参军入伍所要求的身体条件了。但是,坏运气还是没放过他。毕业后,符合了征兵条件的弗兰克被通知去参加征兵体检,给他检查的是位跛脚的军医。“他看了看我的腿然后说[205]:‘哥们,和我这腿比起来你那根本就不算什么毛病。他们既然能在军队里给我找到事干,就肯定也能给你找到点儿事干。’”这位军医拒绝把弗兰克的身体条件认定为4-F级,这意味着弗兰克必须去服役了。于是,弗兰克只得暂时搁置他几乎还没怎么开始的建筑事业了,他那时甚至还没有真正地参与设计过一个建筑。1955年1月,从南加大建筑学院毕业仅仅六个月的弗兰克,就被正式征召加入了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