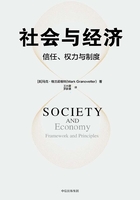
序二
大师的淡定
2018年12月的一天,忙里偷闲的家德兄,到我办公室小叙。一落座,闲扯了几句时事,话题自然落到格兰诺维特教授的这部《社会与经济》大书上。
家德是教授的弟子,深得真传,这点在一年前他出版的著作《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家德并未就此止步,他将教授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理论,很自然地移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用“圈子”、“关系”来透彻解读强连接、弱连接,以及网络中的机会与社会资本,当然他最为关注的是“自组织”。
教授的新著《社会与经济》,据家德介绍,是一部打磨了十几年的著作,很多章节的内容,家德都事先读到过,特别涉及东方文化的有关内容,教授都多次与家德仔细研讨。家德带来这部书(上卷)的打印稿,嘱我做一小序,虽力有不逮,然盛情难却,便应承下来。
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啃教授的这部大著,自然费力很多。更具有挑战的是,我对这部铺陈宏大、论梳细密的著作中所提到的诸多文献史料,并不完全了解。虽然蒙家德兄信任和鼓励,依然觉得难以做出更多有价值的评价。只能老老实实,放平心态,用一个“门外汉”的视角,对这部大著略谈几点读后感吧。
我读格兰诺维特教授的著作,一个机缘是2011年在北大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上一门“互联网前沿思想”的课程。课中有一个章节,介绍“社会网络”的理论。适时业界流行“社会计算”、“复杂网络”和“推荐算法”,格兰诺维特教授在《镶嵌:社会网络与经济行为》中的思想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将经济行为纳入社会网络来审视,在技术专家看来,是非常自然的。美国学者巴拉巴西1999年的“随机网络中标度的涌现”和瓦茨、斯托加茨1998年的“小世界网络的群体动力学”两篇著名论文,开启了互联网结构与动力机制研究的新疆域。应用专家有了理论依托,技术工程师有了研究方向和工具,产生了一大批成果。
教授的弱连接、强连接、镶嵌思想,也迅速被公式化、代码化,纳入各种分析模型,为网络结构分析、节点动力机制分析,提供着丰富的理论营养。但以我之陋见,这似乎并非是格兰诺维特思想的全部。
格兰诺维特教授这部用力甚多的《社会与经济》,似乎意在“纠正”这种“埋头应用”的偏差。他试图让众人的目光,重新回到他数十年前提出的这个“元问题”上来。这个元问题就是“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
承认“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似乎从直觉上并不难,难的是教授的这一论断,需要冲破既有范式的重重障碍,冲破业已固化成型的“经济学—社会学”关系的认知模式。这一认知模式渐渐被过去200年来的社会学、经济学的学者大师们用汗牛充栋的论著、阐释、演讲挤压成型,变成有关人性、组织、生产要素、生产关系、信任、权力、制度、文化,以及理性、道德、正义、财富、公平、分配等词语的“接插件”,用理论、流派、范式、模型,以及某某主义等封装好的“标签”,作为探究活生生现实问题的工具。
教授从“低度社会化”、“过度社会化”开始,不厌其烦地像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一样,用探铲、手镐、毛刷在岩石断层或者整齐的探方中,仔细辨认着结构功能学派、有限理性学派、文化决定论的主干和枝枝蔓蔓的支流——我心想,真难为教授了啊!
以我这个门外汉的眼光看,教授之所以这么做——据家德介绍,他这部著作的下卷,是众多的案例和实证分析——是为了让自己在三四十年前的理论创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教授就像一位孤傲的绅士,宁愿一再延宕著作的出版,也要将穿缀而成的思想框架奠基在扎扎实实、经得起检验的文献疏证的基础上。
这是学术,是卡里斯玛(Charisma)。
“卡里斯玛”是教授多次引用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概念,从早期基督神学引入政治学、社会学,并首次在1922年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中,用来形容那种超凡脱俗的领袖气度,以及令人景仰的非凡魅力所形成的威权统治。这种卡里斯玛在文艺复兴以降的500年间一路下滑,伴随“理性精神”、“自由解放”的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异军突起,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文艺复兴之后,学术卡里斯玛所面对的圣像,发生了180°的转弯。从宗教意义的上帝,转移到“斯宾诺莎的上帝”。
但是,教授所面对的,却恰恰是这种“卡里斯玛”的精髓部分:诚如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坚称的,罗马的衰败并非基督教所致,而恰恰是对基督精神的背离。对超凡脱俗魅力的景仰和向往,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托勒密传统中,热切追寻的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物至理,也是绵延上千年的中世纪炼金术士口中的至尊咒语和秘方。
“斯宾诺莎的上帝”,依然有“上帝”的余晖。
所以,教授需要用同样的耐心、同样的方法,暂时放下建构理论的冲动,克制宏大叙事的诱惑,逐一指认在他看来把理解世界的逻辑“弄拧了”的前人的工作。教授是认真负责的,也是富有卡里斯玛情怀的。
插一个不算八卦的话,家德兄跟我闲聊间,不经意谈及与教授同一时期的学者,甚至是合作的学者如威廉姆森、阿姆斯特朗都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云云,诸多同行纷纷议论说,教授是“离诺奖最近的人”。家德所转述的教授的淡定与洒脱,或许可以对这一绅士般的卡里斯玛情怀,做一点小小的脚注。
“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在我看来绝不是某种灵光一闪的观点,这是大智慧。尽管教授字里行间处处谦逊地回避各种建构范式的“嫌疑”,耐心地梳理数十年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思想演进,但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倒一个个儿”,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也需要游刃有余的功力。
从200年前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开始,社会学家就产生一个自觉不自觉的参照系,就是将社会学理论弄得跟物理学理论一样漂亮、坚实。经济学在我看来也有这股子劲儿(甚至更过分)。数量经济学就是如此,如果没法弄得特别靠近物理学,那就弄得特别像数学。
这股子劲儿,训练、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产生了一堆又一堆厚厚的文本,堆积成一座又一座山峰,就像炼钢炉旁边堆积的钢渣山一样,冷却下来后坚硬无比。教授面前的,就是这样的山峰。
经济学作为基础,就像一个插线板,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就像插头一样,奠基和依赖于经济学,这大致是旧的、宗教的卡里斯玛消退之后,普鲁士教育革命奠定的近现代大学范式中新的学术卡里斯玛。格兰诺维特教授和其他教授们都明白,这套卡里斯玛是用论文、数据、公式、影响因子说话的。
但是,互联网来了,情况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9年,世界网民和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越了自然人口的一半,信息已经成为毫无争议的新的生产要素,“斜杠青年”和自由职业者已经重新定义了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分法在信息经济面前已经了无新意,甚至这两个词语听上去都是“脏词儿”(携带着浓厚的工业文明的味道),新物种层出不穷——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旧的理论框架左支右拙,漏洞百出。
格兰诺维特教授关于“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的论断,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学术假设,而是一个事实,一个绕不开的事实。
说实话,在拜读教授大作的同时,我多次掩卷长叹:除了向教授表达敬意,我私下里觉得教授其实可以更“洒脱”一点,用德鲁克畅论“21世纪的管理”、“后资本主义社会”时的快意文字,痛快淋漓地宣读一份对旧学术卡里斯玛的起诉书。教授其实可以撇开这么多厚厚的参考文献,直截了当地摆出自己的洞见和思想的言说,率性地做一次“没有参考文献的著述”。
当然,话说回来,教授所做的一切,其实也正是这个艰难旅程的一部分。顺便说一下,教授的弟子——家德兄,正是他思想精髓的拥趸,也是身体力行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家德几年前将教授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圈子”“关系”“韬略”“亲缘结构”结合在一起,用“自组织”、“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重新审视的时候,我从他兴奋的神情中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欣悦之情。也许教授想畅快表达的思想,弟子们已经在做了吧!
点滴杂感,不成文字,聊以为序。
段永朝
2019年元旦改定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