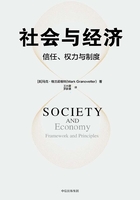
序一
人们期盼已久的格兰诺维特积数十年思考的大作——《社会与经济》终于出版了。格兰诺维特早年的博士生,现在于清华大学任职的罗家德教授,是格兰诺维特的“忠粉”,他和王水雄夜以继日地把格兰诺维特的这本大作翻译成中文,即将在中国出版。家德嘱我为该书作序,我诚惶诚恐。我虽钟爱经济社会学,但就“社会与经济”这个大题目来说,颇感力不从心。所谓作序,也只能是从我的角度,谈谈对这本书的理解。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他是一位跨界的奇才,可以说是当代社会学界最具有经济头脑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界最注重非经济因素影响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学家。他一生都在试图完成一项似乎难以完成的理论工作,就是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人类行为动态复杂系统,使该系统既能解释个人对集体行动的建构,也能解释集体和制度对个人选择的约束。
格兰诺维特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在全世界享有盛名。虽然他作品数量不多,但一出手就是经典之作。他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领域都很有影响,并多次获得引文桂冠奖。他提出的“弱关系”(weak ties)、“嵌入”(embeddedness)等学术概念,甚至成为引领学术流派的一个符号。几乎他的所有作品,包括《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等,都已译成中文并出版,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中国是一个注重“关系”的社会,在格兰诺维特理论中,最为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成果,就是他的“弱关系”理论。格兰诺维特发现并证明,在现代社会,亲朋好友之间交往频率高的“强关系”,在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交往频率低的“弱关系”帮助大。他对这个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很新颖的解释,因为“强关系”传递的只是同质的信息,而“弱关系”才更可能传递有用的新信息。同样也是格兰诺维特“忠粉”的边燕杰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证明在中国还是“强关系”起的作用大,因为所谓“关系”,只是传递的渠道而已,有的可能传递的主要是信息,有的可能更多传递的是权力、地位、金钱、人情的影响。
我早年就读过格兰诺维特的作品,并深受启发。我在提出社会结构转型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时,就借鉴了他关于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并把它和经济学中企业组织对市场具有替代作用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分析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对“羊城村”的研究中,《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是我重要的参考著作。格兰诺维特强调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嵌入在社会境况之中,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构成。这些论述激励我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寻找“经济生活的社会规则”。
在这本书中,格兰诺维特引述了大量的实证成果,不仅有他自己的成果,也穷尽了几乎所有的当代相关实证成果,用以论证他一生追求的宏大的命题,即“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格兰诺维特是那种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入手的大家,他“烹饪”出一桌无所不包的理论大餐,每一道“菜”都做得那么精细、那么别致、那么有味道。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格兰诺维特多年研究的总结和升华,必定会成为传世之作和新经济社会学前行中的一座丰碑。
从社会学思想史上来看,格兰诺维特通常被认为是经验社会学的高手,他身上并没有那些理论社会学大家的光环,特别是在今天“一切都要证明”的美国社会学的氛围中,人们通常认为,他与那些酷爱思想演绎、经验归纳稍逊的社会学理论大家不是一个套路。但恰恰又是他,颠覆了重大的理论问题。
由于我的知识范围有限,我只能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他的“颠覆”,或者说得婉转一些,谈谈他的贡献和创新。
一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学理论大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有一本名为“经济与社会”的巨著,他们都在书名中把“经济”放在“社会”前面,他们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是强调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影响,这在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似乎也一再被历史所佐证。但也有一些不同凡响的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如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把这种推论称为经济思想的“殖民”,即以市场逻辑支配和主导社会领域,把经济规则视为一切社会行动的标准。我觉得格兰诺维特的新经济社会学,从两个方面体现了“新”:一方面他重提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嵌入”,要为经济学“找回”(bring back)社会,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新命题;另一方面他未停留在从理论上“找回”,而是通过扎实的可验证的实证研究来“找回”,这是以前的理论大家都未能做到的。
二是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正如一句调侃的话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学家眼里,只有约束没有选择,而在经济学家眼里,只有选择没有约束。社会学的主流往往更加强调,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被制度、环境和观念体系所制约。经济学的主流则通常被认为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偏好和理性选择的决定作用。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Blau)、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经济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人都曾试图在制度和行为之间发展出一种具有分析力度的理论。在这条学术积累的脉络上,格兰诺维特别具匠心,在批判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理论倾向后,提出了社会网络理论,从而在制度决定论和理性选择决定论之间找到了一个具有分析能力的理论框架,为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成功地架起了一座连接的桥梁。
三是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同时还非常罕见地授予了女性经济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以表彰他们在治理领域的卓越贡献。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通过对交易成本的分析把企业的科层制组织治理和市场网络治理连接起来,找到经济治理模式选择的解释;而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在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之外,发现了第三种治理模式——自组织治理,解决了如何管理公共财产的问题。格兰诺维特则另辟蹊径,提出社会网络是第三种治理模式,发展了威廉姆森“中间型组织”的论述。也正因为此,很多人认为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强有力的潜在竞争者。
四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从学科发展史来看,经济学与社会学一直经历着文人相轻的漠视、理论假定的纷争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大概是经济学家中最注重社会问题研究的,他对诸如犯罪、教育、家庭等问题的研究和观点都独树一帜,让人眼前一亮。但他用经济学理性选择法则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被格兰诺维特在这本《社会与经济》的开篇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立论的靶子。为应对这种“经济学的侵入”,格兰诺维特高举新经济社会学大旗,以社会学的原理,深入触及经济活动的“硬核”(hard core),如生产、分配、消费和信息网络等,类似一种“后殖民主义社会学”的呐喊。但不管怎样,这种“对话”,不是学者的意气之争,而是有学派才有学术。
这本书应是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巨著的上册,我们期待着下册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以上杂谈,权作序。
李培林
2018年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