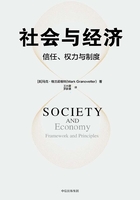
译者序
先谈一个有趣的现象,知道格兰诺维特的人一定都会觉得他是一位博学深思的理论家,他提出了“弱连带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理论和“嵌入理论”,在社会学引文中排名数一数二,对经济社会学的推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确实,受教于格兰诺维特教授五年半,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都是理论,但很奇怪的是,从他第一个学生伍迪·鲍威尔(Woody Powell)到和我同时在学的布莱恩·乌西(Brian Uzzi),以及之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加上我本人及很多师兄、师弟,却都在做大数据和动态系统模型,就好像我们的老师教的是方法、数理以及计算机一样。一个纯粹只教社会学理论的老师为什么会教出一群做数理模型的学生?
其实从这本书中就可以找到端倪。进一步说,这本书在推动一个新理论的发展方向,也为新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首先,本书第一章高举反化约主义大旗,提出用复杂思维分析经济社会现象。格兰诺维特的知名批判就是左批以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学派为代表的“低度社会化”观点,右批以文化决定论为代表的“过度社会化”观点,以下面这个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图1为例,化约主义用集体的因素,诸如人口分布、社会结构、文化、集体心理等,解释集体的经济行动或行动的经济结果(economic outcomes),也就是图中“4”的过程;用个体的因素,诸如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价值观、态度、行为动机等,解释个体的经济行动或行动的经济结果,也就是图中“2”的过程。在用集体因素解释个体行动时,如图中“1”的过程,就是“过度社会化”观点,个人是没有能动性的,被集体的制度与文化所决定,只有牢笼中十分有限的自主权;而在用个体因素解释集体行动时,如图中“3”的过程,就是“低度社会化”观点,个体完全自主决策,集体只是个体行为的加总而已。
格兰诺维特在第一章阐明了这样的化约主义解释是不完整的,而且一位“低度社会化”观点的学者一旦接受了文化对个人也有影响的论点时,就会常常使用“过度社会化”观点。低度、过度两极论点融于一篇论文之中,之所以作者也不觉得违和,正是因为两者都是化约主义,而没采用复杂思维。

图1 个体与集体研究的示意图
那么什么才是复杂的解释呢?一方面,个人受集体制度与文化影响,这在书中第二章将有所探讨,个人的行为绝对不是基于个人的自利与算计就自主行动的。其实,规则与价值形塑出来的心智结构也深深影响着个人的决策,但这个影响又不是决定性的,个人对利益的考量依然会带来能动性的需求,会通过关系、圈子与人际网等社会网结构获得自主决策的空间,甚至改变集体的制度与文化。另一方面,集体的制度与文化也通过一个人身边的社会网潜移默化地形塑个人的心智结构,这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就探讨了两种最重要的关系——信任与权力,从而展开了社会网作用在图1中“1”与“3”过程中的讨论。
每一章中格兰诺维特都展现了如何利用这样复杂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并以多个案例加以说明。比如第四章中讨论权力,尤其以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和其子孙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的权力运作为例,化约主义研究者总会将权力归因个人,如占有关键资源让别人依赖,或取得传统或科层组织的权威位置,或有个人的魅力。当然这些都对,但我们却要问,权力是嵌入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结构中的,有权力掌握者就有权力屈从者,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与网络如何展现?所以格兰诺维特探讨了结构洞的概念,即不管个人拥有怎样的权力特质,都是一种权力的结构性表现,也就是两群人之间的中介者拥有了信息垄断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利益。其权力成立的前提包括以下几项:两个分立的圈子各自拥有足堪权力剥削的资源,两个圈子有沟通的需要,而且依赖中介者的沟通。不仅如此,中介者还能操控两个圈子的分分合合:合了,“桥”就不需要了;分了,圈子各自孤立,“桥”就断了。不管这两种情况出现哪种,中介者的权力都不复存在。这就是一个较小的社会网结构中权力的运作案例。
从小社群中权力运作扩大到较大的复杂网,两个“圈子”可能就是两个阶级,因而中介者的权力变得极大,以美第奇为例,他们一方面靠婚姻关系打入并拉拢贵族权力阶级,另一方面靠生意与交友结交商业新富阶级。前者基本上瞧不起后者而不愿与之为伍,却又需要后者的财富为其权力服务,所以美第奇就稳稳地掌握着作为中介者带来的权力。而这样的分析又不能独立于集体的制度与文化分析之外,如果不是新富阶级崛起的历史背景,让我们看到时代文化、经济新兴势力的交叉踫撞,我们就很难理解美第奇取得的中介位置为什么这么重要。
反过来,我们又要问,一个集体中作为两个大社群的中介而取得权力的人有很多,处在历史机遇期和关键位置上的人也不少,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带来了集体制度与文化的改变?我们不得不考察美第奇在取得能动性的结构位置后,如何变成改革的代理人(change agent),如何动员利益相关方投入改变的社会运动中,又如何在改变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维持良好的复杂网结构,以传播改革,并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反作用力,从而维护改革,最终“涌现”出新的商业制度以及文艺复兴的新文化。
这样的案例在本书中还有很多。于是我们看到,在个人的权力因素之上,还要探讨权力关系的形成、小社群中权力的运作,以及复杂网结构的分析。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集体制度与文化通过社会网对行动者心智结构的影响,以及对其行为的限制与造就,另一方面又能看到,个人通过关系、社群以及复杂网络位置带来的能动性,进而如何带动改变,涌现出新制度与文化。个人行动、关系、社群、复杂网以及集体的制度与文化在一个动态互动过程中形塑了我们要观察的经济现象。
本书是格兰诺维特一生的力作。记得1994年时,他就开始把其中的章节拿给我看,还就其中的部分内容,尤其是牵涉到中国的内容与我讨论,1994年,出版社就迫不及待地对外宣布本书即将出版,一些图书馆还列上了书库目录,但没想到格兰诺维特精益求精,一遍又一遍地改写,直到23年后才出版,还只是上册,也就是本书。这本书提出的理论观点,不但在经济分析视角上不同,而且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也建立了新典范。虽说社会科学理论应该价值中立,但实际上重要的大理论(grand theory)都会有其价值取向,理性选择视角下的经济分析强调的是个人利益驱动、算计、竞争与效率,社会网视角下的经济分析则看重社会因素驱动、积极心理以及合作与可持续性发展。其实人性之中,两者兼备,这本书正是想以复杂思维融于一炉而冶之。
方法论上的新典范则要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吊诡现象:为什么一位几乎只做社会学理论也只教社会学理论的老师却培养了一群做大数据与系统动态模型的学生?在不同理论的范式竞争中,理论的推理、定性分析固然重要,但不同理论社群寻找共同认可的“事实” ,为“事实”找到操作性定义,并验证这个理论的解释效力高,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与已经完全数理模型化的经济学对话,更要“硬踫硬”地提出定量证据,并做理论比较。这就是为什么格兰诺维特的学生,乃至新经济社会学的学者会自学统计、建模、计算机等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理论体系变得完备。
,为“事实”找到操作性定义,并验证这个理论的解释效力高,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与已经完全数理模型化的经济学对话,更要“硬踫硬”地提出定量证据,并做理论比较。这就是为什么格兰诺维特的学生,乃至新经济社会学的学者会自学统计、建模、计算机等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理论体系变得完备。
大数据的出现使这套理论思维得到高速发展,如上所述,反化约主义的复杂思维为理论体系注入了复杂网与系统动态的元素,过去这类定量资料很难收集,尤其是复杂动态网的资料收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大数据自动地在大范围、长时段中积累着这类资料,其中脸书、推特、微信与QQ这样的社交网络资料更提供了复杂动态网分析的可能性。从而,个人行动、关系、社群、复杂网以及集体制度与文化的动态互动过程分析就成为可能。在这个范式里,理论与“实证” ,大理论、中层理论与理论模型,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构化数据与大数据同时并用,缺一不可,所以研究者往往会组成一个庞大的研究团队,集社会学、经济学、经济管理学、计算机、物理学、统计学等领域的不同学者或学生在一起,类似一个理工科的“实验室”,而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往往是“实验室”的“领头羊”。
,大理论、中层理论与理论模型,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构化数据与大数据同时并用,缺一不可,所以研究者往往会组成一个庞大的研究团队,集社会学、经济学、经济管理学、计算机、物理学、统计学等领域的不同学者或学生在一起,类似一个理工科的“实验室”,而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往往是“实验室”的“领头羊”。
新范式在既有理论之上往往带入了很多过去很难深入研究的议题,如复杂网结构的演化,动态系统的自适应过程,复杂系统中的“涌现”现象——例如制度变革、社会运动爆发、引爆思潮、重大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革命,还有系统的非常态变化、系统转型等。在方法上则在因果模型之上加入了系统模型,在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之上加入了动态分析,在结构化数据之上加入了大数据。新方法与新理论范式为过去一些很难分析的社会现象与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
这本书虽然是一本纯粹的新经济社会学理论的著作,但为研究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开辟了一片蓝海。
罗家德
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