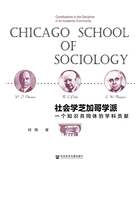
第1节 芝加哥学派的学科意义
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学系,尤其在美国,社会学更是一个新的事物,但并不是说芝加哥大学就是在一片荒芜之中创建了社会学系,其实,在前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就已经在美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早在19世纪中后期,面对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劳工阶层生活条件恶化、严重的贫富分化、官僚腐败、社会道德沦丧等经济社会危机,一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展了一些初级形态的社会学调查和社会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就是第一批美国社会学者,也对后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一 前芝加哥学派美国社会学
在非严格的意义上,第一批美国社会学家主要包括莱斯特·沃德(Lester F. Ward)、威廉·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爱德华德·罗斯(Edward A Ross)、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埃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 Small)等人,不过,他们大都穷其一生也未能在社会学领域中发展出具有可持续性的思想或体系。在这些人中,库利的知识遗产可能是影响最大的,此外,萨姆纳和罗斯的著作也可能还有人阅读。
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不同程度地在美国大学中创设了制度化的社会学机构。继他们6人之后(当然,吉丁斯可以被排除在外,他并未建立社会学的组织化遗产)(Oberschall, 1972: 224-225),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学研究中心。1892年,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授予学士学位与研究生学位的社会学专业。与之相比,其他5人无论是在组建社会学系的思想上,还是在院系的组织结构上都缺乏决定性的影响。要记得,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后来芝加哥学派的辉煌成就至关重要。
沃德(1841~1913),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1883年的《动态社会学》(Dynamic Sociology)。沃德的正式职业是政府的古植物学家,故,他把大量生物学术语引入社会学著作,借用生物学概念解释社会,强调社会变迁中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沃德向第一代社会学家灌输了进化论基调(Hinkle, 1980: 68 -72),为了使之适用于人类社会,其也对进化论进行了修正。1910年之前,沃德的社会学著作还是相当有影响的,但是,由于并非在大学系统中,沃德无法通过教学来影响学生,也无法培养出思想上的学术接班人。
萨姆纳(1840~1910),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第二任主席。虽然并非一个理论家,但他是一个有活力的、受欢迎的教师,他使得社会学进入了数以千计学生的视野。萨姆纳是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的拥趸,他在社会理论中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社会选择、适者生存,这是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基调。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出身于劳工家庭的萨姆纳在政治上却走向了自己阶级立场的反面,成为主张个人主义、不干涉主义,反对公共福利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萨姆纳最重要的著作是1907年的《民俗》(Folkways),广泛使用各种公开可见的人类学、民族志文献资料来分析道德模式与社会习俗的起源。此外,从未学习过社会学的他却组织了美洲大陆第一个“社会学班”,成为美国社会学教育的开创者。萨姆纳的学术影响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其一,当时,耶鲁大学是一个本科教学型大学,萨姆纳也从未指望进行学术性研究或者试图吸引研究生参与他的研究;其二,其极端自由放任的立场一度引起了包括斯莫尔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严厉批判(Christakes, 1978: 53 -54);此外,与萨姆纳持相同立场的为数不多的其他学者也倾向于把自己区隔开来,自成一统。萨姆纳引起的争议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评价说:“除孔德之外,还没有哪一个社会学家像萨姆纳那样在这门学科中受到这样的颂扬或诅咒。”(Barnes, et al.,1948: 155-172)
吉丁斯(1855~1931),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第三任会长,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但是,他过于期望在他的学生中扩大社会学影响。吉丁斯曾编辑过杂志,1893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社会学,直至20世纪20年代晚期退休。不同于沃德与萨姆纳,吉丁斯培养了一些学生,后来相继成为美国第二代社会学的领军人物,包括威廉·奥格本、霍华德·奥多姆以及斯塔德·查宾。和其他同期社会学家不同的是,吉丁斯对量化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量化技术可以使得社会学研究更加科学。尽管在这个领域的著作乏善可陈,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但是,对待量化研究的态度却对他的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间接地为社会学研究“科学化”做出巨大贡献(Oberschall, 1972: 215 -232)。他的理论体系集中表现在“类型意识”(consciousness of kind)上。但是,受其个性与偏见的影响,吉丁斯在方法论与理论上的思想未能发扬光大,也阻碍了哥伦比亚大学未能像芝加哥大学那样创建出一流的社会学院系。
罗斯(1866~1951),斯莫尔的朋友,接受的是经济学教育,对早期的《美国社会学杂志》助益甚大。在1901年曾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长期领导着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1914~1916年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没有哪个美国社会学家像罗斯一样拥有多姿多彩的一生,当然,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罗斯对社会学缺乏持久的影响。虽然他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教师、多产的作家,但是,“罗斯作为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改革家的身份并不逊色于作为职业社会学家的身份”(Barnes, et al.,1948: 818-819)。由于批判哈佛大学创始人的劳工政策,1900年被(哈佛大学)校方解雇(Furner, 1975)。数年之后,来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直至1937年退休。但是,罗斯未能把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研究型学术中心。罗斯缺乏指导学生的耐心,也没有实地研究的兴趣。他的大量活动都在校园之外,时常到海外旅行,更像一个民粹主义者、丑闻揭发者和社会改革家。罗斯反对社会学的专业化,缺乏参与学者间学术性活动的兴趣。然而,他本身的学者身份是确定无疑的,《社会控制》一直是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学著作。
库利(1864~1929),和罗斯一样,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开展学术研究,但很快转到社会学研究上来,几乎在密歇根大学度过了一生。库利性格孤僻,几乎是个不问世事的隐遁者,也一直遭受疾病的折磨,不喜欢行政工作,不爱做大规模的研究,也不想把社会学系搞大。库利并未推动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的繁盛,不过,他的学术声誉依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特别是他的著作对社会学家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包括192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库利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强调个体与社会的互补。“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概念,加上米德的一些概念对人类个体的社会压力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他还提出了“首属群体”与“次属群体”两个重要概念。
概言之,包括斯莫尔在内的美国第一代社会家们,都想发展出一般性社会学理论,使之成为学科的奠基性理论。虽然在唯物论与唯心论、决定论与意志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立场不同,但他们都致力于把社会实在视为一个独立与自治的研究领域。除了萨姆纳与吉丁斯之外(他们从事的是图书馆式研究),斯莫尔力促社会学应该具有更多的经验取向,强调实地研究和直接观察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出意义重大的经验研究贡献。这6位早期社会学家无论是在个性上还是在政治与专业化定位上都差异显著。在个体特征上,库利和吉丁斯有着严重的身体残疾,妨碍了他们成为学术领袖。尽管方式不同,但是罗斯与萨姆纳的政治、哲学立场阻碍了他们作为第一代社会学家产生影响。沃德边缘性的学术位置抑制了其对美国社会学制度化发展可能产生的贡献。只有斯莫尔凭借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位深远地影响了未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
到19世纪末期已经有多所美国大学提供社会学课程,但是,只有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专门的组织化的社会学院系,承担起定义学科研究领域、界定学科研究方法的历史使命:不仅要从那些老的社会科学学科中争取社会学的研究领地,而且还要设法使之与当时的社会改革运动区分出来,避免社会学研究沦为道德化的或者宗教式的社会调查,此外,也需要把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区别开来(Cavan, 1983: 407-420)。第一阶段美国社会学的终结以1918~1920年5卷本的《波兰农民》的出版为标志,同时,托马斯离开芝加哥大学也宣告了黄金时期芝加哥学派的来临。
二 芝加哥学派的学科意义
1.集体性事业的知识共同体
对不同的社会学家来说,学科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意义也迥然有异。有些人会详述社会思想中最早的先驱者,如孟德斯鸠、黑格尔或者圣西门;另外一些人聚焦于19世纪的思想家,如托克维尔、孔德、马克思以及斯宾塞等人;还有人则可能把迪尔凯姆与韦伯置于万神殿的中央。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对诸如齐美尔、滕尼斯、豪布豪斯(L. T. Hobhouse)、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o Michiels)、托马斯、帕克、曼海姆等早期学院社会学家更感兴趣。此外,在19世纪,像阿道夫·奎特赖特(Adolph Quetelet)、弗雷德里克·普雷(Frederic Le Play)、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和斯布欧姆·罗恩特瑞(Seebohm Rowntree)等人都对经验社会学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在关于社会学学科使命与基本概念上的见解并不相同,彼此研究的领域也相差甚大。直到19世纪晚期,大部分早期社会学学科的拓荒者还处于学院之外,依靠个人财产开展社会学研究。除了迪尔凯姆创建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和帕克领衔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以知识共同体的集体面目从事社会学研究之外,在20世纪之前,绝大部分社会学家几乎都是孤立地、按照自身兴趣进行个体化的社会学研究,甚至即使拥有相似的知识关注,彼此之间也不会进行交流与合作。当然,这受制于当时的交通与通信制约,对他们来说,能够做到的就是书信往来、面对面的接触以及与具有同样兴趣的学者进行交流,但是,最典型的工作模式仍然是孤独的。在早期社会学发展史上,只有以迪尔凯姆为中心的年鉴学派和以帕克为中心的芝加哥学派从事的才是一种一体化的集体性知识事业。
为什么192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会成为一个创造性的中心,催生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呢?从1915年到1935年“黄金时代”的芝加哥学派又是如何、为何能够在芝加哥大学繁荣昌盛呢?针对当时城市里的各种社会问题,芝加哥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开展了密集的、一体化的、高度协调的在地式研究。作为世界社会学的领导中心,芝加哥学派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特点鲜明,而且以城市为天然实验室集体性地对城市社会问题开展广泛而极富成效的研究。
在社会科学中,可以把一个“学派”看作类似于艺术史上的一群同类人:他们共享某种风格、技巧,或者一套符号象征,并在一定的时间或空间上具有较高水平的互动,如印象派作家、鲍豪斯建筑学派,等等。此外还可以利用一些理想类型特征来判别社会科学中的学派:不仅有一个奠基者、学派领袖,而且还有一个学术群体围绕着他(她)、跟随着他(她),人数可以在10~30人。学派领袖应该具有主导性的人格魅力,不仅有一套理念、信仰、标准化的分工来联结、凝聚学术共同体,而且有一个与学科内流行范式明显不同的范式,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学派追求的是学科的现代化或者再革新(Bul mer, et al.,1984: 2-3)。或者如特亚齐亚恩所言:“一个科学共同体应该围绕着一个知识上的克里斯玛型领袖组成一个整体,拥有调查研究经验现实的一套范式。范式的核心是由共同体的奠基者、领袖提供的,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范式典型地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由奠基领袖与其核心跟随者共同塑造。”(Tiryakian, 1990: 218-219)
学派的繁荣昌盛在于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制度性联系,拥有一个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良好的活动场所。此外,为了与更大范围内的学术公众抑或阅听人进行联系,还需要有一个杂志、评论或者其他形式的定期出版物,以之整合学派成员们分散的研究活动。相对于个体化学者,科学事业中的学派共同体能够通过领袖人物对共同体成员具体、局部的学术活动进行有效整合进而以集体智慧的形式来推动学科的发展。
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中,托马斯与帕克就是这样的两个领袖型人物,他们不仅自身知识渊博、成就斐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推动了社会学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质变。无论是托马斯还是帕克,都信奉经验研究,认为要想具有宽阔广博的学术视野,就必须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把研究关注深深地根植于当代世界的现实问题之中。这也正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主要特征,即糅合第一手的经验资料与一般社会变迁理念,把调查研究与理论探究共同作为一个研究项目的有机整体。芝加哥学派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学学科研究的经验化取向,但是,并非像经常被人们刻画的那样沉迷于经验研究。事实上,从托马斯的《波兰农民》到帕克与伯吉斯带领下的博士生们对城市社区开展的在地化研究,同样为社会学学科贡献了类似于默顿所说的“中层理论”,产生了所谓的“芝加哥学派的方法与理论”,可以说,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不仅在经验研究上成就斐然,其在理论贡献上亦同样卓著。
此外,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是一个致力于追求当代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最佳境界的知识共同体,对各种研究方法持一种开放性态度,即只要有助于经验研究,任何方法都可以作为研究手段。把芝加哥学派简单地等同于城市社会学、社会病理学、社会心理学或者米德的著作,甚至符号互动论的早期胚芽都是一种历史学理解错误。芝加哥学派对社会学学科的定位是多元的、折中主义的,这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192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没有一种学说以 ‘主义’结尾,这也正是人们努力避免的情形。新创造出来的知识远非要加入某种学说或者被赋予任何类似的标签。”(Faris,1980: xiv.)或者说,这也正是本书的主要目标,即刻画、解释芝加哥学派的多样性,探究在托马斯与帕克灵感的刺激下,各种创造性知识是如何在芝加哥学派手中滋生、孕育直至蔚然壮大的。
2.芝加哥学派的学术成就
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像出版于1918年到1920年的《波兰农民》那样,标志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已经进入到美国与世界社会学的领导者行列(Thomas and Znaniecki, 1918 -1920)。这是一部经验资料与一般理论相结合的经典著作,也是芝加哥学派系列调查研究中的第一部,集中体现了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特征,不仅揭开了芝加哥学派的历史帷幕,而且其提出的理论也成为学派经验研究的思想根基,个人生活史研究方法则成为学派后来者效仿的样板。继托马斯之后,直到1922年学派才出现下一部经验研究著作,即查尔斯·约翰逊在芝加哥种族关系委员会委托下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报告——《芝加哥黑人》。无论是在理论倾向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可以说这项在帕克直接指导下的研究打上了托马斯知识灵感的烙印。自此,芝加哥学派面向城市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相关研究成果除了发表在学派主办的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上,更主要的是以“社会学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现。帕克与伯吉斯是丛书的编委,负责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挑选出他们认可的优秀作品,交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23年尼尔斯·安德森的《流浪汉》成为社会学系列丛书的开篇之作。此后,丛书囊括了对芝加哥城市多个层面社会现象的研究,包括1927年恩斯特·R.莫尔的《家庭解组》、弗雷德里克·斯拉谢尔的《帮会》、1928年露丝·凯文的《自杀》、路易斯·沃斯的《犹太人区》、1929年哈维·乔鲍福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1931年富兰克林·弗雷泽的《芝加哥黑人家庭》、1932年保罗·克雷西的《的士舞厅》以及1933年沃尔特·雷克莱斯的《芝加哥的罪恶》。
另外,1920年代伯吉斯领导下的“青少年研究所”也发表了大量有重要影响的犯罪学研究报告和专著,包括1929年克利福德·肖、亨利·麦克凯、哈维·乔鲍福以及里昂纳德·科特雷尔等人从事的社会生态学研究著作《违法区域》, 1929年约翰·兰德斯科的《芝加哥的组织化犯罪》, 1931年由肖主编的两部生活史《拦路抢劫者》以及《违法职业自然史》,此外,还包括1931年肖和麦克凯关于不良行为原因的传世经典著作《青少年越轨的社会因素》,这是受维克夏姆犯罪委员会委托而开展的一项研究。除了关于城市研究的主题外,社会学系列丛书还涵括了许多其他主题的研究专著,如李福特·爱德华兹的《革命通史》、E.希勒的《罢工》和波林·扬的《俄国城的朝圣者》。
与托马斯作为学派思想渊源与仿效样板的《波兰农民》不同,帕克与伯吉斯对芝加哥学派的主要贡献是向博士生们提供开展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1915年,帕克首先提出要把城市作为研究客体。1925年他把伯吉斯、麦肯齐等人和自己的城市研究文章合编为《城市》(Park, 1915: 577-612),为学生们从事经验研究提供具体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此外,伯吉斯主编的《城市社区》(The Urban Community, 1927)与《个性与社会群体》(Personality and the Social Group, 1929)也成为学生们开展城市研究的参考书。帕克和伯吉斯最著名的著作就是以“绿色圣经”著称的《社会学科学导论》。这是黄金时代芝加哥学派的教科书,也是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主要大学社会学系标准版本的教科书。 虽然帕克或者伯吉斯没有具体的经验研究著作,但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学丛书、专著,无论与芝加哥城市相关与否,大都包含了一个或者帕克或者伯吉斯提供的导论,向人们介绍相关研究的学科意义与社会价值。
虽然帕克或者伯吉斯没有具体的经验研究著作,但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学丛书、专著,无论与芝加哥城市相关与否,大都包含了一个或者帕克或者伯吉斯提供的导论,向人们介绍相关研究的学科意义与社会价值。
早在1927年来到芝加哥之前,威廉·奥格本就出版了一部理论性著作《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Ogburn, 1922)。1920年代晚期,奥格本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在胡佛(Hoover)总统“近期社会趋势”委员会中的研究,以《近期社会趋势》(Recent Social Trends, 1933)著作结尾,并于同年围绕《美国社会学杂志》年度问题,提交了一项社会发展的统计研究。其二,与其助手致力于诸如投票、出生率、婚姻与家庭等现象的生态统计学研究。另外,在芝加哥学派黄金时代值得一提的是瑟斯顿(L. L. Thurstone)设计的用于态度测量的量表,意味着人们能够用量化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人类行为的主观方面。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主要成员从事的经验研究对其他学科的经验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刺激了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发展。在社会学万神殿的诸多大家中,像托克维尔、马克思、普雷、迪尔凯姆等人都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经验资料,他们或者通过观察获得第一手资料,如托克维尔与普雷,或者以访谈的方式来收集材料。然而,在20世纪之前,社会学主导性的研究方式是图书馆式的,研究者们的学术兴趣或者是哲学的,或者是理论的或者是历史学的。人们认为,对于社会学来说,对当代世界的第一手资料,甚至是第二手资料的认知并非必要的。大量的经验社会研究——无论是政治算术学、人口普查或者早期的社会调查——和社会学的联系是微弱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1915~1935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们以强有力的城市经验研究面目横空出世,对社会学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型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即从抽象的、历史性的、总体性的、哲学思辨式的社会学研究向具象的、局部的、现实的、经验性的研究范式转型。
3.以科学为志业的芝加哥学派
作为黄金时代芝加哥学派的精神领袖,帕克最初是一名记者,直至年近半百之时才在托马斯的邀请之下加入了成就其不朽一生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他看来,社会学并非一种道德哲学或者可以用于社会改革的调查工具,而是一种科学事业。正是把社会学研究工作视为一项科学事业,才使得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与在社会改革精神支配下开展的社会调查运动显著区别开来。为了让人们能够以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帕克和伯吉斯撰写了经典社会学教科书《社会学科学导论》。对他们来说,社会学研究要更加严格、更加科学地检验各种正在发展中的社会科学命题,基于此,他们大力鼓吹由托马斯开创的面向现实问题的经验研究,尤为注重收集第一手经验资料。当然,以科学方式来研究社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人并未提供可以借鉴的方法。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在社会学科学化的过程中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已经在学科科学化上取得重大进展的两门学科,即生物科学与心理科学,尤其是这两门学科注重系统化的经验调查给芝加哥学派的精神领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Shils, 1981: 264)。芝加哥学派的基本贡献就是把孔德提出、斯宾塞等人发展但尚未实现的社会学科学化变为现实,并开创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传统,即由理论社会学向经验社会学转向。
在社会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必须解决什么样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如何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等基本问题。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芝加哥学派开展的经验研究介于20世纪早期以社会改革为主要目标的社会调查运动和193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以科学为旗号的量化社会调查运动之间,或者可以这样讲,在前芝加哥学派时期,主导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运动,而在后芝加哥学派时期(经典芝加哥学派之后),主导社会学研究的是各种量表式的、以数理统计为目标的社会调查运动。可以看出,无论是早期的社会调查运动还是1930年代中后期的量表式社会调查,与黄金时代芝加哥学派以个人生活史、参与式观察、文献资料、社会地图以及生态学分析等典型的研究方法相比,尽管三者在时间序列上是前后相继的,但是,它们之间几无共通之处。另一种常见的错误是把芝加哥学派简单地等同于质化研究,认为帕克与伯吉斯的芝加哥学派是一种“柔性”的民族志式的质化研究,并将其与拉扎斯菲尔德、默顿所在的哥伦比亚学派的“刚性”量表调查研究对立起来。对于芝加哥学派来说,量化方法同样重要。学派承认各类优秀研究成果,而非排他性地偏好某种特定方法论类型的研究。或者说,芝加哥学派仅在学科发展的初期以质化研究为主,到了1930年代以后在奥格本等人的推动下,量化研究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
三 学术研究制度化的起航
优秀的学者与出色的思想是产生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但是要想成功地维系一个持久的学术传统则需要创立一个适当的学术机构。制度化学术机构的建立不仅为学者之间的互动创造了条件,而且也推动了知识活动向常态化、规则化方向发展。正如爱德华德·希尔斯所言:“在一个拥有边界、持久性的组织机构中,互动是结构性的。互动强度越大,结构为学者提供的空间就越多,而这对相关评估、认可、提升与配置又是决定性的。这种权力反过来又设置了特定传统的选择准则,并在教学与质询过程中得到强化。高水平的制度化学术活动机构能够为它的教学与调研活动提供规则的、预定的和系统化的管理组织。通过资格审查,组织机构可以调控人员的进出,为成员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可以在各种学术活动之间合理配置设备、机会以及报酬,如研究、教学、调研、出版、邀请等;也可以承担各种资源如金钱和物资保障上的义务与责任,如某种活动需要获得外部机构的支持;还可以跨越机构间的障碍,通过出版社公开出版来传播各种学术成果,使得相关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为公众所了解。”(Shils, 1981: 264)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组织化学术机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具备现代社会科学院系的基本特征,如投入大规模研究经费、积极使用辅助人员、购买相关仪器设备、通过研究项目和课题培养研究生、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学讨论会、关注研究方法论,以及强调及时出版研究成果,等等。社会科学专业化就这样一步步地向前推进(Haskell, 1977)。20世纪早期,以单一学者辅之以若干名研究生与一到两名研究助手、借助于图书馆文献资料的研究模式依然存在,但是,黄金时代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研究取向标志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型,即社会科学研究逐渐大型化、团队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出现跨学科研究;各门社会科学呈现日益强烈的经验特征,基于第一手经验资料的研究大量涌现。
黄金时代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是美国大学社会学院中第一个成功地整合了大规模研究的典型。在前芝加哥学派,各类社会学研究主要局限于大学教师个人实施的各种小范围社会调查,或者教师指导研究生进行类似调查。但是,在192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们不仅集体性地从事项目研究,而且还创造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和组织来整合各人的研究项目。重要的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的研究模式也得到了各种基金会的认可,进而为研究争取到大量外部资金的支持,如卡内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财政支持,预示着一种新的学术化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起航。
由于人们认为基金会的赞助对研究的客观性、公正性会产生影响,所以,这种赞助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与影响了1920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与政治科学的研究方向至今尚无定论。当然,基金会之所以乐于支持社会科学研究,原因在于,他们相信这类研究具有潜在的用途,不仅可以客观地反映民情社会,而且还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通过学术化的社会科学向社会提供有用的知识准备已经一切就绪(Shils, 1981: 155-172)。虽然基金会对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项目产生影响,但是,此时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们开展的各类社会调查与早期的社会调查运动已经表现出根本性差异:社会调查运动关注的是通过发现事实以重塑道德,但是,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们对社会科学与社会行动的关系有着更为成熟的看法,他们持有类似于韦伯的“价值中立”立场,即学术效用的价值在于揭示客观现实,而不是为某种政治的或者道德的或者宗教的目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