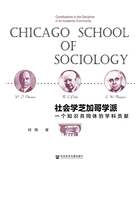
第2节 城市与大学的血脉相连
要想理解继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之后,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新发展,就必须要深入思考芝加哥城市的发展历史与芝加哥大学的独特性格,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科学的历史情境。一个典型的社会科学“学派”应该有一个共享的方法论与一组共同的问题,而这可以通过学派领袖予以体现。芝加哥学派的特征在于:对芝加哥城市进行经验研究,集中聚焦种族与种族混合区,涵盖社会问题、城市形态与地区共同体。所有的这些研究都被置于社会变迁的理论架构之中(以托马斯为代表),都有一个细致的概念框架与社会过程理论(以帕克为代表)。不同于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他们以对芝加哥城市的集中研究与关注研究的经验性质而独树一帜。可以说,芝加哥城市发展的历史与1892年新建立的芝加哥大学的独特性格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释了芝加哥学派与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分野的缘由所在。
一 边疆城市芝加哥的野性魅力
认识芝加哥,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是“年轻”。在19世纪中早期,芝加哥仅是美国文明中的一个边缘村落,位于新大陆的西部边疆。没有东部海岸城市那样漫长的历史,也并非处于区域大都市的地缘中心,除了亚伯拉罕·林肯、马克·吐温和路易斯·沙利文在生命中的不同阶段曾在此度过外,就从书本中也看不出芝加哥有任何引人注目的突出特征。此时盛行于中西部地区的主流文化并非书卷气的,人们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来承继社会传统(Duncan, 1965: 45)。更为重要的是,直到19世纪初才有较大规模的人口来此定居。1800年,现在的伊利诺伊州仅有数千美国人,直到1818年才建立伊利诺伊州。席卷19世纪以开发边疆为目的的西进运动和19世纪中期兴起的淘金热催生了美国西部大开发热潮,作为一个新兴城市,芝加哥是西进运动的直接产物(Burgess & Newcomb, et al.,1931:1-6)。 在《宅地法》公布之后,大量东部地区的普通民众纷纷来此寻找土地。伴随着乡村定居,城市逐渐发展起来,公共与商业活动中心也逐渐形成(Duncan, 1965: 3-13)。
在《宅地法》公布之后,大量东部地区的普通民众纷纷来此寻找土地。伴随着乡村定居,城市逐渐发展起来,公共与商业活动中心也逐渐形成(Duncan, 1965: 3-13)。
作为一个晚近发展起来的定居点,芝加哥是一座新城。表2-1显示了芝加哥城市人口的变化情况。1840年,芝加哥并不显眼,人口还不到5000人,但是,10年过后,已经成长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自1850年到1890年前40年是芝加哥城市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一个小城镇发展为一个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大都市,相继超越了23座老牌大城市,成为全美仅次于纽约的第2大城市。继1890年之后的下一个40年,虽然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开始减缓,但是,城市人口规模还是超过了1890年的两倍,达到了337万余人(Burgess & Newcomb, et al.,1931: 1-6)。
表2-1 芝加哥人口在1840~1930年的变化情况

在1892年芝加哥大学建立之前的40年里,芝加哥城市已经彻底地旧貌换新颜。在此阶段,只有1871年的大火(Great Fire)曾阻碍了这一进程,不过,虽然大火彻底毁灭了芝加哥木结构的旧城,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代表美国工业文明最新成就的钢筋水泥结构新城。芝加哥城市的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当时的铁路建设。1860年,芝加哥已经成为美国铁路网络的中心节点之一,美国西部的跳板与中西部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与之相关的物流、证券及工业生产急剧发展。城市吸引力也水涨船高,中西部农业地区的农民带着对知识,尤其是宗教的虔诚来到了这里;商业与知识阶层随之而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与城市扩张,国内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芝加哥工业化与城市化对劳工的庞大需求,大量的外国移民带着梦想与希望纷纷云集于此: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犹太人、捷克人、立陶宛人和克罗地亚人,等等,芝加哥城市变成了一个世界民族大熔炉。据统计,1900年170万城市人口中的一半人口出生于国外。20世纪初,黑人大规模涌入芝加哥,1910年仅占城市人口的2%,但是,到1930年已经上升到城市人口的7%(Spear, 1969)。
到1890年,芝加哥依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城市,一座沸腾的、喧闹的、工业化大都市。它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但是,却几乎没有时间来吸收知识。芝加哥有着自身的阴暗面,工业化导致了工业冲突,其中最激烈的冲突是1886年的“草市骚乱”和1894年的“普尔曼大罢工”。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曾写道:“无处不在的暴力、深不见底的肮脏;喧哗,无法无天,毫无爱心,气味恶臭;发育过度的乡村傻子,不计其数的城市恶棍;犯罪行径随处可见;商业欺诈厚颜无耻;毫无思想的社会伤痕累累。”(Commager, 1960: x)或者正如1879年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中对芝加哥的倾诉:
我们开垦新的田地,我们挖掘新的矿山,我们发现新的城市;
我们赶走了印第安人,灭绝了美洲野牛;
我们环绕大地兴建了钢铁大道,穿过天空架设了电报线路;
我们新增一个又一个知识,推出一个又一个发明;我们建设了学校,创建了大学;
然而,芸芸众生的谋生却并没有变得更为容易,相反,却日益艰难。
有钱的人变得更加有钱,而没钱的人依赖性变得更强;
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鸿沟也变得日益宽大;
社会对照的反差变得日益尖锐;
伴随着制服马车出现的是光着脚板的孩子们。(George, 1926: 390-391)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芝加哥也是一座崇尚知识与文化的城市。在中西部地区,深受新教信仰影响的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为这座城市培养了尊重知识的传统。芝加哥大学对学术的严肃认真在相当程度上就受惠于这一传统。在早期阶段,芝加哥的商业精英就以得到西奥多·托马斯的支持与1891年建立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音乐传统而自豪。自1893年开始,建立于1879年的艺术学院占用了一幢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这是芝加哥城市中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到19世纪末,艺术学院的核心是收藏古典主义与印象主义绘画(Maxon, 1971)。值得一提的是,建筑学的芝加哥学派不仅为美国的城市文明贡献了摩天大楼,而且也为美国首次创造了本土化的连绵型城市建筑风格(McCarthy, 1982: 75-96)。在诗人卡尔·桑德博格(Carl Sandburg)与小说家西奥多·德雷塞(Theodore Dreiser)、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弗兰克·诺瑞斯(Frank Norris)与罗伯特·亨瑞克(Robert Herrick)等人的颂扬下,城市图书馆在芝加哥获得了牢固的声誉。
二 校长哈珀的芝加哥大学信仰
1.芝加哥大学的创立
借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400周年,1893年芝加哥成功地举办了世界博览会,象征着芝加哥城市的文化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Duncan, 1965: 385-386)。当时,大多数东部地区的社会精英们一直怀疑芝加哥是否能成功地举办规模巨大的世界博览会,甚至认为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不可能比“密歇根湖岸家畜展览会”更好,但是,一些有思想、有远见的人如波士顿的威廉·詹姆斯、亨利·亚当姆斯、查尔斯·诺顿等人却从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中认识到,美国文化的创造力中心已经由波士顿和纽约开始转向芝加哥。因此,芝加哥大学的建立并非一个在暗无边际的商业大海中孤立的文化事件。蒙肯(H. L. Mencken)曾把芝加哥描绘为“美国最开化的城市……美国味最浓的城市”。 1/4世纪之后,对帕克来说,芝加哥:“远非某些个人与社会设施的聚集体……亦非单纯的制度与机构的集聚群。城市更是一种心智状态,是一个传统与习俗的载体……还是大自然与人化自然的产物。”
1/4世纪之后,对帕克来说,芝加哥:“远非某些个人与社会设施的聚集体……亦非单纯的制度与机构的集聚群。城市更是一种心智状态,是一个传统与习俗的载体……还是大自然与人化自然的产物。”
正是在这样的时空环境中,1890年芝加哥大学诞生了,两年之后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 芝加哥大学的建立剧烈地冲击了美国高校的学术体系。第一个研究型大学的荣誉属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者克拉克大学,但是,1892年洛克菲勒捐助下的芝加哥大学给其他学院和大学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它们不得不面临这所全新的、极富进取精神的大学的竞争。正如斯莫尔在回忆中的叙述:“一句话,所有其他大学立马陷于防御之中……一种神乎其神的说法立刻传播开来,即这个暴发户不仅有意图而且也有支持这种意图的资源对那些老牌大学展开竞争,就像标准石油系统曾对它的大量竞争对手所做的那样……令人怀疑的是,在此之前,美国高等教育是否还有过像芝加哥大学成立这样一个单独事件所带来的如此巨大的刺激。”
芝加哥大学的建立剧烈地冲击了美国高校的学术体系。第一个研究型大学的荣誉属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者克拉克大学,但是,1892年洛克菲勒捐助下的芝加哥大学给其他学院和大学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它们不得不面临这所全新的、极富进取精神的大学的竞争。正如斯莫尔在回忆中的叙述:“一句话,所有其他大学立马陷于防御之中……一种神乎其神的说法立刻传播开来,即这个暴发户不仅有意图而且也有支持这种意图的资源对那些老牌大学展开竞争,就像标准石油系统曾对它的大量竞争对手所做的那样……令人怀疑的是,在此之前,美国高等教育是否还有过像芝加哥大学成立这样一个单独事件所带来的如此巨大的刺激。”
2.校长哈珀的大学信仰
(1)哈珀:浸信会教育家
芝加哥大学的奠基人和首任校长是威廉·雷恩·哈珀。在年仅19岁之时,就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古典语言文学的博士学位。此后,相继在俄亥俄州格兰威尔丹尼森大学“浸信会协会神学院”和耶鲁大学任教。当他还是一名教师的时候,哈珀就展现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建立了一个古典语言文学研究所;此外,还担任“市民文化讲习所”的高级管理职位。 1890年在浸信会教友洛克菲勒捐赠的芝加哥大学建立之时,哈珀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为卓越的浸信会教育家,也成为理事会推荐的芝加哥大学校长的不二人选(Goodspeed, 1928: 1-66)。
1890年在浸信会教友洛克菲勒捐赠的芝加哥大学建立之时,哈珀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为卓越的浸信会教育家,也成为理事会推荐的芝加哥大学校长的不二人选(Goodspeed, 1928: 1-66)。
哈珀卓越的组织才能还典型地体现在他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系上。芝加哥大学之所以能够早早地进入美国大学的领袖行列,学校实际捐赠人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功不可没。在20年的时间里,洛克菲勒向芝加哥大学捐赠了3500万美元以满足学校发展的费用需求。在1910年决定结束捐赠之时又一次性向芝加哥大学捐赠了1000万美元,这段历史再次展现了哈珀非凡的游说能力与无往不前的进取心(Gates, 1977: 189 -198)。在洛克菲勒财团的支持下,芝加哥大学巧妙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财政赤字困难,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登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
作为同时代人中最富有成效的大学校长之一,哈珀不仅创建了芝加哥大学,把它提高到大学系统的最前列,而且确保芝加哥大学长盛不衰(Storr, 1966: 367 -368)。他的视野、精力、才气与热情,再加上他坚定的宗教信仰与对自身研究工作意义的永恒执着,使之在芝加哥大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赋予芝加哥大学独一无二的品质,这些品质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也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正如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哈珀拟订的芝加哥大学发展计划如同他为该计划所付出的努力一样意义非凡。人们创建了大学,罗伯特·亨瑞克说,如同他们曾经盲目地创建神殿一样,并未想好这个他们为之献身的神殿的最终样子,但是,这是他们精神信仰的内在要求。这种品性同样体现在哈珀对芝加哥大学的管理史上。”(Storr, 1966: 367-368)
(2)以研究为大学使命
作为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计划,即把这所大学建设为美国西部地区的教育中心。他认为,芝加哥大学应该成为人们求知深造的中心与从事高级研究的中心,不但要开展本科生教育,而且还要提供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同时,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知识与行动方案,进而助益社会。在芝加哥城市精英的大力支持下,哈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芝加哥大学建设成为全美最重要的大学之一。哈珀认为,芝加哥大学应该把研究与调查作为中心任务,使之与美国的本科教学型院校,甚至和建立于1879年、明确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区别开来(Goodspeed, 1916: 129 -130)。在芝加哥大学,资深教授都要在研究生院讲授通识课程。面向实践的研究生教育是芝加哥大学的主要目标,哈珀主张,“不是要向学生的大脑输灌限定领域的已知知识,而是要训练学生们借助于新的调查方法自己去探求新的知识”(Goodspeed, 1916:129-130)。哈珀是一位拥有巨大精力、激情与远见的人,他决心创造条件以实现自己的大学信仰。
对于许多高级人才来说,芝加哥大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提供的研究自由与教育创新。这种学术氛围始自芝加哥大学建立之初,一直延续到黄金时代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哈珀极力鼓励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开展学术研究,而这是同时代其他美国大学尚未做到的事情。在哈珀看来,“一个人只有自己从事调查才能教别人调查。如果教师没有这种精神,不以身作则,那么,也就永远无法引导学生进行这样的调查。另外,如果教师的教学负担过重,那么,他也将既无时间也无精力从事调查。无后顾之忧、专心科研与自由思考是实现上述调查活动的基本条件……人们希望,教授和其他教师能够每隔一段时间完全放下教学工作,以便于能够全身心地进行调查工作。尽管无法忽视教学的重要性,但是,将来院系中年轻教师的提拔将更大程度地依赖于他们的调查工作成果。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下,进行调查研究是首要的,而指导学生的教学工作将是次要的。”(Goodspeed, 1916: 145-146)
哈珀不仅鼓励教授们把研究与出版放在中心位置,而且还设法为教师们创造各种出版的途径,甚至在芝加哥大学招收第一届学生之前,哈珀就已经创建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有机部分”(Shugg, 1966: 6 -7)。借助于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在全世界扩大与传播其影响。哈珀鼓励每一个院系都创办杂志或者丛书,出版教师的研究成果。
芝加哥大学并不是第一所强调以研究为中心的大学,但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始人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克拉克大学创始人G.斯坦利·豪(G. Stanley Hall)和哈珀三位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创始人中,他是最有效率和最有耐心的研究型大学创始人。
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可能是西半球知识史上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单一事件”(Shils, 1978: 171),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即结束了美国移民到德国接受更高教育的历史(Veysey, 1965: 125),同时,也形成了美国高等教育本土化的研究传统。德国的高等教育对美国具有重大影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许多教师都具有德国留学经历,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实验室与高层次研究的定位并不十分适合美国土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两个显著特征:对自由的推崇与对成就的认可。在那里几乎没有任何宗教仪式与庆典活动,工作艰苦、压力巨大,教师不得不持续地与同事进行比较,并自我加压。正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巨大压力,使得斯莫尔和杜威先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1888~1889年,斯莫尔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而杜威则于1883~1885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并获得哲学与心理学博士学位。约西亚·罗伊斯曾这样总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的学习压力:“人们不能仅仅是一个听众,他更应该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实践者。”(Royce, 1892: 383)
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的下一个研究型大学是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首任校长豪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系任教。这所创建于1889年的大学在建校之初就做出如下定位:创建一个全研究型环境,致力于纯科学研究。学校招聘了大批才华横溢的教师,取得科研成就的前景看起来非常光明。但是,由于捐赠者乔纳斯·克拉克的缘故,克拉克大学很快就遭遇了大麻烦。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捐赠者已经过世不同,克拉克先生仍然健在,并生活在学校所在城市——伍斯特市;也不同于芝加哥大学的捐赠者洛克菲勒先生,虽然后者向芝加哥大学提供了巨额捐赠,但是,洛克菲勒既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挂在大学上,也不愿意卷入大学的运营事务中,始终与芝加哥大学保持相当大的距离。克拉克先生几乎要干预“他的”这所大学的日常运营的每一件事,这导致他很快就与校长豪发生了冲突。当校长豪拒绝把克拉克大学建设成一个本科教学型院校时,1892年年底,克拉克先生撤回了他对学校财政的支持。学校管理者与实际捐赠人之间的冲突波及了大部分院系的教师,但是,这对芝加哥大学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哈珀乘机网罗了一大批人才。后来,豪曾抱怨说,哈珀“偷袭”了他的大学,而邀请他来芝加哥大学当校长则是对他的侮辱。但是1892年4月发生的事件表明,克拉克大学已经走上了下坡路(Veysey, 1965: 166-170.)。
芝加哥大学是19世纪末第三个把学术研究作为首要任务的新建大学,也是持续最久的大学。到了20世纪早期,由于预算危机和学校领导层的平庸,外加上东部老牌大学的竞争,在学术研究上曾独领风骚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经辉煌不再(Veysey, 1965: 166-170)。曾经的大学理想也逐渐褪色,人们不再把大学的首要功能视为既存知识的保管者与承继者,现在,人们仅仅把大学看作发现新知识的商业活动。到了1890年,哈佛大学建立了艺术与科学研究院;而哥伦比亚大学则在1880年就在约翰·伯吉斯(John W. Burgess)的努力下建立了政治科学研究院。从教的使命感并未显著减弱,但是,这种发展趋势无论是对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还是对受教于其中的学生来说都是决定性的(Shils, 1978: 171 -172)。哈珀最初的计划是整合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与教师的学术研究以及其他相关职能,使得各个部门都能认同自己的工作并为之自豪。虽然强调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哈珀还是设法在教学与研究之间一直保持“微妙的平衡”,而不是过于厚此薄彼(Shils, 1978:171-172)。
(3)创新大学教育模式
持续创新对芝加哥大学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之前,大学教师的首要职责是教学,只有在完成教学之后才能进行学术研究。大多数美国高校既不鼓励学术研究,也不会提拔那些在学术研究上有所贡献的人。“在1870年代,学术研究没有丝毫重要性。”(Veysey, 1965: 172 -174)解决此问题的一个方案就是从大学中分离出独立学院使之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在美国,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种情形并未出现。实际上,由于直到19世纪晚期,许多新教背景的美国学者都曾在德国大学求学,这使得美国大学打上了德国大学模式的烙印,在一个单纯的学院里把研究与教学合二为一。在此背景下,哈珀掌舵的芝加哥大学对学术研究新模式的探索就显得极为重要,哈珀引领了在美国大学中设立独立研究学院的潮流。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的某些大学,如芝加哥大学,人们都认为,现在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关键时期,都强调高级研究会与研究生院的重要性。人们认为,各种严肃的科学研究都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因此,高级研讨会(seminar)式的教学尤为重要,至少,在自然科学中非常必要。在社会科学中借助于实验室研究人类行为的是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建立的心理实验室。然而,在那些无法采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中,如政治科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应该怎么办呢?主要的方法不外乎图书馆、书房、文献室中各种印刷材料与未公开出版的资料。尽管并非全无,但是,第一手的实地调查尚不常见。
研究生研讨会的内容多样。学生们可以报告他们的研究项目、评论相关文献、讨论某篇文章或者某部专著、阅读长篇论文或者集体深入研讨档案卷宗。具体干什么主要取决于指导老师的兴趣偏好。某些特别的人,像哥伦比亚大学的吉丁斯、耶鲁大学的萨姆纳、克拉克大学的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与豪等人,鼓励他们的学生关注忠诚与献身等问题。1917年之后,由芝加哥大学的帕克与伯吉斯组织的学生研讨会最为出色、卓有成效,并成为在社会科学中召开研究生研讨会的样板,曾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被诸多大学的效仿。在社会科学的早期阶段,几乎没有人从事精英式的学术研究,但是,1888~1889年身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斯莫尔以自身的经历敏锐地抓住了研讨会的潜在意义。一群来自不同社会科学院系的30名学生每周有五天早晨围坐在一个又脏又旧的长桌旁,“首先是一位历史系的学生发言,然后是经济学系,接着是政治科学系或者社会学系或者法学系的学生发言。当研讨会讨论的是关于华盛顿、费城或者纽约某个领域的问题或者某种实际社会事务时,师生们都会分享他们各自的观点。为了对问题有更全面的认识,来自不同学科的每一种观点都会在此争鸣”(Small, 1910: 35-36)。
高年级学生只有通过高级研讨的研究型学习才能取得学位的博士生制度是此次转型的核心所在。进入1890年代,成为大学教师的门槛大幅提高,研究生与博士生学位成为获得德国大学永久性教职的必要条件,甚至对于那些不需要学位学生的教学人员也是如此。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相当多的学者重新回到大学进入研究生院学习,如斯莫尔1888年34岁的时候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1893年30岁的托马斯来到芝加哥大学学习。
美国大学高级讨论会的主要目标是训练合格的学术人才。对研究生的指导主要取决于教授们的课题情况与学术精力,每个老师都可以拥有培养职业研究人员的独特体系。从1892年开始,芝加哥大学就强调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鼓励研究生和教师发表研究成果、出版研究专著。实现研究理想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斯莫尔召唤人们积极地达成自己的研究目标。1905年,芝加哥大学研究院院长(他一直担任此职直至1924年退休)在致辞中不无夸张地表达了这样的情绪:“对研究院来说,更大的荣耀是激发人们开放心智以真诚的态度审视传统的观念,而非仅仅通过重复老生常谈的知识来获得毕业。研究院遵循的首要宗旨是:牢记研究理想,并视之为神圣事业!”(Storr, 1966: 158-159)
拉丁文教授威廉·黑尔认为,接受研究型学术训练的学生必须要有“天赋与激情”。当然,这也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而非一名仅仅能博得他人好感的绅士。教师本身必须具备学术创造力,是一名能够带领自己学生的大师,能够站在该领域的国际最前沿(Storr, 1966: 158-159)。
正是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推动了芝加哥大学站在了美国高校的最前沿。不同于官僚制、科层化结构的德国大学,也不同于同期的英国大学,1860~1920年美国大学系统尚未最终成形,也缺乏学术权威。各种不同类型的大学形式彼此竞争。这种去中心化与竞争性的大学体系不仅导致了各个大学的知识饥渴,希望借助于学术研究增长知识,而且美国大学体系的扩张也反过来满足了这种饥渴。
在创始之初,芝加哥大学就致力于成为全美,甚至是世界顶尖水准的大学。这是其建设研究型大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而,如果把教师们限定在教学上的话,那么,他们的视野可能仅仅是地方性的,而且会局限在他们曾经教过的人身上(像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其师资都是知识精英群体,这使得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大学声誉从来都无法独立于研究人员的声誉;人们会根据研究人员获得的成就大小来评价其所在的大学优劣。”(Shils, 1978: 186 -187)正是在教授们的不懈努力下,芝加哥大学早早地把自己建设为全美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具有高起点的研究型大学定位有助于芝加哥大学成为全美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但是,1890年后与之有着相似发展定位的克拉克大学的命运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衰颓预示着芝加哥大学取得今天的地位还受更多因素的影响。这种结果远非用一个前瞻性的大学定位就可以解释的。解释早期芝加哥大学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比较复杂,但是,这是理解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繁盛最为基本的缘由。
把大学按照院系而非师资进行组织管理的模式能够给予学者从事创造性学术研究更多的灵活性机会,有助于新的思想与观念的诞生。教师们拥有一定的自由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与教学,这是促进学科知识发展的理想模型(Diner, 1975:513-514)。芝加哥大学创建的以研究为中心的院系组织对大学学科的学术化发展贡献极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就是芝加哥大学独特的院系设置的结果。早在19世纪美国就已经出现了以社会学观点来看待世界的传统,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社会学调查和社会学理论家,但是,只有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之后,才巩固了社会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性活动的地位。
3.哈珀的人才兴校战略
一流的学术师资是建设研究型大学的首要条件,为此,哈珀要为芝加哥大学网罗“全美最优秀的人才”。虽然在他试图招揽的对象中有很多人怀疑在粗野的中西部地区新诞生的芝加哥大学能有多大作为,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接受他的邀请来到芝加哥大学,由此芝加哥大学的师资队伍日益壮大。哈珀是一个非常看重学者的个人才华与天赋的人。如果某个人能够打动他,即使当时芝加哥大学没有合适的院系,那么,他也会为之在某个院系安置一个临时性的教职,或者直接为之创制一个全新的院系(Diner, 1975: 513-514)。
哈珀的决断力最明显地体现在芝加哥大学初创之时的师资招募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曼校长是在几乎没有半点竞争对手的情势下搜罗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优秀师资的,但是,到了1890年,对优秀师资的竞争日益激烈。虽然并未能把心仪的每一位优秀人才都吸引到芝加哥大学,但是,总的来说,哈珀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芝加哥大学招募了一批强大的高水平教师,包括8名前大学或学院的校长或院长。其中,最著名人物包括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拉丁文教授黑尔、经济学家拉夫林(Lawrence Laughlin),威斯康星大学前校长地理学家托马斯·张伯苓(Thomas C. Chamberlin),佛雷博格大学的历史学家赫尔曼·霍斯特(Hermann von Holst),以及科尔比学院院长兼社会学家斯莫尔。此外,克拉克大学的校长在与捐赠人发生冲突时,哈珀挖来15名一流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埃尔伯特·米歇尔森(Albert A. Michelson)。1894年,密歇根大学的哲学家杜威也来到芝加哥大学。1892年芝加哥大学已经拥有77名一流的教师与教授,14人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其中5人来自莱比锡), 21人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其中9人来自耶鲁大学)(Storr, 1966: 75-76)。
作为一个私立大学,芝加哥大学的资金主要来自慈善家的捐助,这意味着较之于中西部地区其他州立大学,其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研究重心,而它的竞争对手们则不得不按照立法机构的要求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尽管这种自由常会带来某种不确定性和饥一顿饱一顿的生存境遇,但是,它也给芝加哥大学带来毋庸置疑的优势。作为私立机构,芝加哥大学的领导者在设立研究生院与专门研究院等问题上更容易达成一致,还能够抵制本科生扩招的要求。只有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条件下,才能培育出大学独立的品性与革新能力(Driver, 1971: 57 -58)。年轻的芝加哥大学还缺乏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那样的自负,但是,人们同样对学校的未来充满信心,高度认同学校在学术上的优势。此外,虽然芝加哥大学是在浸信会教友基金会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是,学校并没有强烈的宗教教派色彩,相反,在信仰上相当自由开放,如建校之初就实行男女同校,而且也向黑人学生敞开大门(Deegan, Burger,1978: 11-32)。
三 城市与大学血脉相连
1.以科学助益社会
与纽约和波士顿相比,芝加哥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平民气质,以至于教师们很难理解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一切事情(Duncan, 1965: 211-212)。1893~1894年世界博览会结束后,留下了大量无人居住的房子与关闭了的旅馆,环绕在芝加哥大学周围。芝加哥大学如同漂浮在“点缀着若干擦拭一新的橡树的沼泽地带中的一块粗糙的沙地,每当夜深人静时在声声蛙鸣中入眠……显得那么荒凉、黯淡”。世界博览会如同城市的惊鸿一瞥,在给芝加哥带来荣光的同时很快就匆匆而去,取而代之的景观是“除了大量无人居住的建筑、沉睡的监狱和市民大礼堂外,就是城市的贫困,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垃圾堆中奔波。1894年从芝加哥大学研究生大礼堂的窗户外可以看到,弥漫于城市北区的失业大军正在寻找安身之所与果腹之物。”(Lovett, 1948: 54)越来越多的自由派教师们像城市精英中的自由派改革家建设安居房并试图寻找有效的方法来减轻城市化与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城市痛苦的简·亚当姆斯与格拉汉姆·泰勒一样,开始关心芝加哥城市社会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校长哈珀对社会学的期望嵌在其固有信念中,即社会学要能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斯莫尔坚定地相信,社会学必然对社会进步助益良多。正如莫里斯·詹诺维兹曾指出的那样,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家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嵌在这样一种传统之中,即深信“只有清晰地理解社会现实,才能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提供准确的方向,客观有效的社会学分析在本质上可以为社会集体性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Janowitz, 1974: xv)。稍后,在托马斯与帕克影响下的芝加哥学派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归功于人们对社会改革问题具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其时,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家们已经觉得自己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不可分割了。斯蒂芬·迪纳曾详尽地描绘了芝加哥大学校内外的社会改革家是如何协作共同推动城市改革运动的(Diner, 1980)。
较之与其他美国城市,芝加哥城市社会环境特征更加鲜明。1904年,在参观完芝加哥城市后,马克斯·韦伯觉得像在看一个剥掉了皮肤、肠子裸露在外蠕动的人(Weber, 1975: 286)。一种道德情感上的压力要求人们关心芝加哥城市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自由派新教徒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日益寄希望于社会学能够提供一个“科学”的拯救路径为芝加哥城市社会带来福音。这也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积极回应,如查尔斯·亨德森就非常活跃地参与了芝加哥一个关注社会改革的组织,直至1915年逝世(Diner, 1975: 524-526)。
2.参与社会改革运动
早期对经验社会的研究是人们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及其改革可能性的主要结果之一。19世纪晚期,美国城市的社会环境在新闻媒体的揭丑运动中不断被暴露出来。最著名的揭丑成果是纽约雅各布·里耶斯(Jacob Riis)的两部专著,即《另一半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1890)和《向贫民窟宣战》(Battle with the Slums, 1892)。简·亚当姆斯是芝加哥社会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她所在的赫尔-豪斯中心不再仅仅是一个独立机构,而且是社会改革家、政治家与学者们深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中心(Addams, 1919)。芝加哥最早的社会调查是由安居房运动的成员们完成的,许多人都是中产阶级女大学生,从事社会福利是社会认可她们的极少数工作之一。早期的社会调查成果主要有:在亚当姆斯指导下完成的《赫尔-豪斯地图与论文集》(Hull House Maps and Papers, 1895)、罗伯特·伍兹(Robert A. Woods)的《城市荒野》(The City Wilderness, 1898)、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的《芝加哥租房户境况》(Tenement Conditions in Chicago, 1901),等等。
与同时期绝大多数其他美国大中城市相比,芝加哥大学改革派教师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改革运动:“最重要的是,芝加哥的活跃阶层如改革家、商人、牧师、新闻记者、律师以及社会工作者等纷纷来到芝加哥大学,寻求一切形式的可能的帮助。改革者们深信无论是关于客观社会的科学知识,还是进行改革所需的智慧与勇气都是必不可少之物,芝加哥大学就是为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知识支援的启蒙机构。”(Diner, 1975: 550)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家们陆续在各个社会团体中积极行动起来。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成立于1903年的联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和城市俱乐部(City Club),其吸纳了芝加哥最优秀的学者与商人。很多人早就开展了以改革为取向的社会调查活动,如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恩斯特·佛雷昂德(Ernst Freund)、哲学系的詹姆斯·塔夫慈(James Hayden Tufts)和乔治·米德(Diner, 1980: 57, 69-70)。以米德为例,其在40年的学术生涯中基本上是一名纯粹的哲学家,但是,他也在大学之外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活动。最初,他在杜威的实验学校里做的是关于教育方面的调查研究,亲自指导了一系列的城市调查研究。1910~1916年,他参加了一项在芝加哥实施的类似于1906~1909年在匹兹堡实施的研究项目;1910~1912年,和一个10人团队进行了一项历时两年的牲畜围栏调查研究。在1912年,米德提议建立中央统计调查局以巩固、调整和采集各个地区的社会情况数据资料,为制定社会行动规划与政府公共政策奠定科学基础(Deegan &Burger, 1978: 362-373)。
3.早期经验研究的局限
早期社会改革行动并没有发挥人们所期待的那样重大影响。面临的城市问题是如此之繁、如此之大,以至于仅靠慈善家们来解决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对城市面貌做出重大改观。在某些地区实施的社会改良政策不仅用处不大,而且效率低下。不过,这些行动不论是对民意还是对某些政治家或者政府官员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此阶段,从事经验研究的标准并不是特别严格。很多研究经常出现概念不当、理论缺失以及过于道德化等问题。像亨德森、祖柏林以及其他芝加哥大学教师都缺乏科学探索的激情,与托马斯以及后来的帕克在城市研究中的科学严谨态度迥然不同。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学术环境的改变,要不是当时那种学术环境,也许后者的研究就可能是另一种面貌。例如,托马斯极可能继续以萨姆纳的方式从事民族志研究。出于对地方事务的巨大兴趣,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第一次那么紧密地联系起来。积极介入地方事务的传统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壤滋润着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在大学与城市之间建立了一种迥异于纽约与波士顿的紧密关系。
大学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机构,变化非常缓慢。作为一个新来者,芝加哥大学没有美国老牌大学那么多学术规矩的限制,有意愿也有能力开创一个全新的大学发展模式。一旦确立了这种模式,大学就将沿着既定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时至今日,芝加哥大学建立之初确立起来的那些品性继续保持下来。1905年49岁的哈珀死于癌症,他的继任者贾德森一直掌舵到1920年代。学校建校之初招募的那些教授也继续留在芝加哥大学,包括第三任校长恩斯特·伯顿和社会学系的斯莫尔。最重要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基本原则,包括强调研究生培养、调查研究、论著出版以及国内外学术精英招募的传统都延续下来。芝加哥大学依然珍视与芝加哥城市的紧密联系,积极介入芝加哥的城市发展,努力为芝加哥的社会改革运动提供调查研究。为了理解黄金时代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昌盛,应该将其置于独特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情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