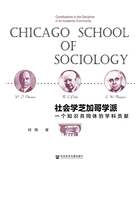
第3节 社会学的诞生及其早期成就
作为社会科学渐进制度化的一部分,1892年芝加哥大学成立后,社会学也在缓慢地发展。1915年之后在托马斯与帕克的领导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最终走向繁盛,其根基相当宽广,离不开芝加哥大学充满生机的学术氛围以及其他思想流派的影响,也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的滋养下,最终才成就了黄金时代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的相互联系非常紧密,这部分源自他们共同参与了当时的市民文化讲习运动。在这些场合里,芝加哥大学的年轻学人不仅可以从资深学者如凡伯伦、米德等人那里受益良多,而且通过这样的活动,学者之间也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形成一个兴趣与学术共同体。 哈珀创建的亲密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在发育之中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后续发展意义非凡。
哈珀创建的亲密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在发育之中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后续发展意义非凡。
一 源自实用主义哲学的传统
1.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哲学是芝加哥大学第一个“学派”。1903年著名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如是评价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成就:“在杜威的领导下,芝加哥大学(哲学系)仅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通常需要10年时间才能实现的从诞生到硕果累累的使命。成果是辉煌的——一个 ‘真正的学派’和一种‘真正的思想’。同样,也是极为重要的思想!除此之外,你还听到过曾出现的另外一个这样的城市或者这样的大学吗?在这里(哈佛大学)我们有思想,但是没有学派;耶鲁大学有学派,但是没有思想。只有芝加哥大学既有思想又有学派。”![这是1903年10月29日,詹姆斯写给亨利·惠特曼(Henry Whitman)夫人信中的一段话。可参见《威廉·詹姆斯通信录》[The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2(Bost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1920): 201-202]。此外,大约在相同的时间詹姆斯曾公开地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只不过未提及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的名字。“芝加哥大学之外的人们将会愉悦地评估芝加哥人的遗产,即 ‘尽管芝加哥大学缺乏文化底蕴,但是,当她开始冲刺时,她将在文化上光芒万丈’。芝加哥大学正以令人眩目的方式来实现这样的愿景。芝加哥有思想的学派!完全可以预见她未来的前景,未来的25年内芝加哥学派将被载入史册。”参见William James, “The Chicago Schoo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 January 1904): 1。历史表明,詹姆斯对杜威领导下的这个跨度25年的芝加哥哲学学派的预测几乎丝毫不差。](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52D39/11228660603640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53006-Kf7gHb8p5gOVQKQ0mWFFu09r6glron5H-0-62de5104c1041ca07b920feb085c83fc)
实用主义哲学家群体的主要成员形成于1890年代,但是,杜威不仅仅影响了实用主义哲学生机盎然的头10年,事实上,还影响了随后的1/4个世纪直至1930年代罗伯特·哈特金斯(Robert Hutchins)分裂重新组建的哲学系(Rucker, 1969: 25-27)。1894年,杜威从密歇根大学来到了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系的首席教授;1904年,由于和哈珀在建设实验学校问题上意见不合而投奔哥伦比亚大学。杜威仅在芝加哥大学度过10年时光,而杜威的哲学系同事仍然留在芝加哥大学(Storr, 1966: 296-302,339-341)。1894年和他一起来的米德依然留守于芝加哥大学;1895年加盟杜威领导的哲学系的安格尔于1904~1920年出任心理学系主任一职;同年,帕克最亲密的朋友——爱德华德·埃莫斯(Edward Scribner Ames)获得了博士学位。1894年从康奈尔大学来到芝加哥学习实用主义哲学的爱迪生·莫尔(Addison Webster Moore)同样执教于此(Rucker, 1969: 4-6)。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了一代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家,奠定了社会科学的实用主义研究基调,也为科学调查研究设置了一个总体性定位。1920年代米德、塔夫慈、埃莫斯和莫尔等人依然活跃在芝加哥大学。 因此,必须在更为广泛的视域中检视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对经验调查研究历史的影响。
因此,必须在更为广泛的视域中检视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对经验调查研究历史的影响。
2.中心概念:活动性
实用主义思想的中心概念是活动性(activity),一个同样运用于生物学、心理学以及伦理学的概念,通常与组织进化中的功能思想有关。活动性由一个有意识的主体(agent)执行,该主体有独立的情感与情绪;活动性存在目的或者目标指向;活动性与另外三个要素(主体、目标或目的、情感或情绪)之间交互联系。生物进化并非仅仅是机械性的,作为活动性主体的人类也并非观念的简单传递者,相反,目标是临时性的,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调整。
以“活动性”概念为基础,人们就可以定义行动(actions)概念。实用主义哲学家关注那些影响人类与客体变迁的过程。正是面向问题的实用主义倾向使得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如塔夫慈和米德等,都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改革运动中。在米德的著作中,其尤为强调行动的社会场所(social location):意识并非由封闭性的个体自我产生,而是在不计其数的个体成员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相对于开展行动的环境,目标是可以看见的,而且也非固定不变的。
实用主义经常陷入意识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已知与未知等范畴的二元论困境。这可以追溯到杜威早期的学术训练经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时,杜威主要受到黑格尔哲学影响。黑格尔哲学并不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而是认为主体与客体在动态过程中形成了同一性。人类关于社会世界的思想也不过是一种伪装起来的自我知识。但是,黑格尔哲学的唯心论与其他哲学学派之间存在的根本分歧,妨碍了对杜威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影响,特别是在杜威日益关注现代科学后,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更加微弱(Coughlan, 1975: 18-53)。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期间,杜威还曾师从斯坦利·豪(Stanley Hall)学习心理学。在豪那里,杜威了解到科学研究方法和实验主义的严格性(Coughlan, 1975: 37 -68)。1887年杜威明确指出,他的教科书——《心理学》(Psychology)的主要目标是调和生理学与哲学的关系,由此奠定了实用主义哲学的社会心理学基础。黑格尔学说认为,个体复制集体意识有助于摆脱这样一种认知,即人类可以借助于意识来战胜作为客体的物质世界。杜威相信:“能够超越生物学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唯一可能的心理学,就是社会心理学。”(Coughlan, 1975:67)杜威还发现了科学中的真理判断与观念、信仰中的真理判断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对应关系:“观念中的真理是一种能够发挥作用的力量……(基于此)梅塞斯·杜威(Messrs Dewey)、希勒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达成了对一切真理的总体性概念,而这只不过是重复了地理学家、生物学家、语言学家的观点。”(James,1955: 24)实用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之间的联系在刺激实践活动上意义重大,特别是对经验社会调查活动的刺激,体现在杜威的教育工作实践中,特别体现在他主办的“实验学校”中。1902年杜威出任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896年建立一所初等学校以之作为教学方法的实验室,检验哲学上提出的各种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施行于教学实践(Storr, 1966: 296 -302)。杜威(此外还有米德和塔夫慈)把教育视为民主教育,试图以此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个人的潜力。“实验学校”赋予了芝加哥大学在真理层面上从事调查研究的意义。行动哲学一定是积极性(非消极性)哲学。杜威认为,在青年期,教育可以显著地影响人们的态度与习惯,必须把教育视为哲学运动的一部分(Rucker, 1969: 83-106)。
3.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对其他社会科学产生的影响即使不是完全支配性的,也肯定是深远的。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通过米德(其深受杜威影响)在社会学系上的研究生课程来实现的。符号互动论的源头亦可以追溯到米德在研究生班上的教学。当然,多年以后,米德已经不再被视为一名哲学家,而成为“社会学家中的社会心理学家”(Strauss, 1991: xii)。1914年受教于杜威、米德和安格尔的埃斯沃斯·法里斯在此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在1918年托马斯离开社会学系之后,其接替了斯莫尔的系主任职位。稍后,法里斯对本能理论的攻击反映了他对杜威关于人类先天才能观念的批判,后者坚持认为,人类在生理与文化层次上存在显著差异(Dewey, 1917: 266-277)。
托马斯曾把杜威比喻为现代美国的“内科医生”(Janowitz, 1978: 1282)。人们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杜威的强烈影响,特别是他的社会过程概念具有鲜明的杜威烙印。托马斯提出的从社会组织化(social organization)、解组(disorganization)到重组(reorganization)的社会过程与杜威之前提出的挫折历程概念遥相呼应:先是“动机遇挫”(frustration of impulse),接着是进入“拟想行动”(play of imagination),最后是“行动重组”(reorganization of conduct)。不同的是,解组是托马斯社会过程概念的逻辑起点,而挫折则是杜威挫折历程概念的逻辑起点(Baker, 1973: 245)。
除了托马斯之外,在帕克的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作为詹姆斯的前弟子,帕克相当认同埃莫斯哲学观点(Matthews, 1977: 87 -87)。埃莫斯曾为学生讲授神学,其也是海德公园教堂救世宗信徒的牧师,向人们传输自由派宗教思想。埃莫斯是帕克的一位密友,因此,后者也经常到教堂去,甚至会短期地给礼拜天学校上课。帕克也经常在家中招待神学院的朋友们。故,不能忽视芝加哥大学哲学、神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互影响。
在一般意义上,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于:其一,助推人们发展出一套社会调查的方法路径,而这和上一代学者们致力于建构高度抽象化的学术体系显著不同。其二,鼓励人们通过亲自调查对社会进行直接的经验研究。较之于老牌大学中更加书卷气的学者,实用主义哲学培育了人们对经验研究的兴趣。例如,在经济学界,杜威对制度经济学家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的影响极大,后者致力于在哥伦比亚大学推动经济学测量工具的不断改善(Mitchell, 1953: 84-89)。
经过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家们几十年的努力,到了1930年以塔夫慈、米德、莫尔和埃莫斯文集的出版为标志,实用主义哲学达到了巅峰。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几乎所有的投稿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经验主义者,热衷于假设—(实验)检验……都认为,只有公理、原理、演绎、概念和设想才有价值,因为这些能够通过实验来予以验证,并在验证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与改进……每个人都表现出是终极知识的质询者而非解释者;他们一致地对自己的结论充满自信,这也表明,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研究看作终极决定性的。”(Rucker, 1969:166-167)
二 社会学学科的组织化建制
1.哈珀:为社会学系招兵买马
在开展基础研究、提供高级培训以及以知识助益社会(通过“科学”来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的理念下,哈珀做出了建立社会学系的决定并付诸实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校长们在确定人事安排上的权力非常大,可以决定新的应聘者应该被安排到哪个院系。这意味着对某些新兴学科来说,可以打破传统组织结构,创建一种革新的组织类型。在招募社会学学科人才时,哈珀走的是“大腕”路线,极力寻求那些成就斐然的学者,而没有太多地考虑这样的学者是否适合学科发展、能否满足学科建设需要。如果学校暂时没有“对口”的院系来接纳这些大腕,那么,哈珀或者把自己心仪的这些大腕安排在其他院系临时过渡,或者直接就为他创建一个全新的院系。略微特殊的是社会学系,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院系,哈珀并非在物色到理想学科掌门人之后为之创建一个院系,而是在决定创建社会学系之后再来物色合适人选。当然,哈珀本人也并不清楚社会学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更没有想到他所创立的这门全新学科会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第一批教师大都是由哈珀而非斯莫尔挑选过来的,对哈珀来说,他就是要为新的院系选择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人员。
(1)社会学家斯莫尔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是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哈珀个人兴趣的产物,而非刻意精心建设的结果。要是当时哈珀成功地得到了他想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个人——历史学家亚当姆斯(Herbert Baxter Adams)和政治经济学家艾礼(Richard T. Ely)——的话,那么就连社会学系的出现都是非常困难的。1890年秋,哈珀一直和他们联络,但是,两人都想当系主任,或者是社会科学系主任或者是历史学系主任。此外,艾礼还要求哈珀提供更高的薪水,有权自由地选择院系的其他教师。正是第二个条件妨碍了哈珀与他达成一项令双方满意的协议。哈珀不可能满足艾礼的条件,特别是让自己只是简单地应允他推荐的教师人选。
在和艾礼、亚当姆斯谈判的过程中,哈珀也联系了缅因州沃特维尔市一所小型的浸信会学院——科尔比学院的院长艾尔比恩·斯莫尔。斯莫尔对这个将由他出任系主任的社会学系相当清楚:“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那么,余生我从事的学术工作将是组织一个据我所知还尚不存在的社会学系。它应该包括历史学与经济学内容……就历史学方面而言,包括一个三年期的课程:不仅要学习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史,还要学习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史;就经济学方面而言,要熟悉各种可以称为当代经济学学说的知识,理解美国经济问题的实际状况以及这些问题之间存在的具体关系,而非仅知道某些抽象的学说;就社会学方面而言,第一年的课程是讲解历史哲学,最后一年要讲授适当的社会学课程——对各种社会哲学的综合,包括辅助的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等,用归纳法来替代形而上的历史哲学,此外,还要对特定的社会发展进行实际的诊断分析……我并不期望把社会学当作人类的一个显微镜,但是,我认为,借助于社会学这个显微镜能够发现社会的整体法则。”(Diner, 1975: 517)
较之于艾礼,斯莫尔相当谦逊而且要求也相对较少;还是一名获得了执业资格的浸信会牧师,要知道,芝加哥大学可是浸信会信徒洛克菲勒捐赠建立的大学。斯莫尔也从未要求社会学系人事安排的最终决定权,因此其和哈珀的商谈非常融洽,于是1892年在斯莫尔38岁的时候,哈珀任命他为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系(当时并未命名为社会学系)主任。自此,全身心地把社会学系打造为一门“以科学知识来增益社会”的学科成为他的终生使命。可见,芝加哥大学建立社会学系以及其后的知识进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校长哈珀任命特定人员政策的结果。假如是艾礼出任了“社会科学首席教授”之职,那么,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将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按照艾礼的设想,社会学应该是“政治科学系”或者“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系”下属的一个学科,几乎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发展,而且他本人也缺乏对社会学的兴趣,不可能像斯莫尔那样,热情友善地包容那些很有学术天分的年轻人的多样化学术取向(Diner, 1975: 517)。
在社会学系发展史上,斯莫尔主要是以其组织能力而非学术能力名垂青史。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嫉贤妒能、独断专行的吉丁斯不同,斯莫尔对同事的个人研究兴趣极为宽容,如斯塔的人类学兴趣、亨德森的社会工作取向,以及塔尔波特的家政学爱好等,都迥然不同。也正是斯莫尔的宽容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多样性学术性格的基础。同样重要的是,斯莫尔和校长哈珀及其继任者贾德森的关系都非常好。在他的努力下,学校为社会学系提供了初期发展至关重要的财政支持,如哈珀在财政上大力支持他创刊并担任主编至1925年退休的《美国社会学杂志》。
(2)人类学家斯塔
在斯莫尔接受这一教职不久之后,哈珀就又为筹建中的社会学系挑中了一位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斯塔(Frederick Starr)。斯塔是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文化学方面的主任,也是哈珀在“市民文化讲习所”的同事。他同意到斯莫尔所在的社会学系任教,但是,要求人们理解“他的工作是一个独立的工作,而且他可以把人类学扩建为一个完全的系或者学院”,并坚持“斯莫尔教授在人类学方面并不比我出色,而且人类学也绝不是社会学的一个下属学科”(Diner, 1975: 518)。对此,斯莫尔并没有提出异议,他建议斯塔可以开设三个方面的课程:“历史社会学”“当代社会学”和“建设性社会学”。由此,“社会科学系”改名为“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系”。直到37年之后,即1929年人类学才从社会学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院系。
(3)浸信会牧师亨德森
和斯莫尔一样,查尔斯·亨德森(Charles R. Henderson, 1848~1915)也是一名浸信会牧师,1848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卡文顿市,在芝加哥一家小型的浸信会学院中接受了教育(该机构后来由于缺乏资金而关闭)。亨德森曾在特雷豪特和底特律做过牧师,一直是数个慈善机构的领导人,曾积极参与了1870年代和1880年代美国的社会改革运动。在底特律期间,由于成功地做出了对电车工人罢工的判决而成为一位知名的公众人物。
通过浸信会渠道,哈珀联系上了亨德森。在和他讨论了芝加哥大学发展愿景的设想后,1892年6月哈珀正式任命后者为芝加哥大学教师。亨德森清楚地向哈珀表达了非常乐意来到芝加哥大学,但是,前提是要能够继续在浸信会做牧师工作,而且可以以大学牧师的身份从事教学与研究活动。在和亨德森谈妥了一切事宜后,哈珀才询问斯莫尔是否愿意接受亨德森到社会学系。像往常一样,斯莫尔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评论说:“社会学事实的全部主题和组织化基督教的可能性应该由一位知识广博且兼具实际牧师经历的人来处理。”此后,在社会学系亨德森成为仅次于斯莫尔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加盟使得社会学系可以开设福利工作组织方面的课程,而且也可以加强芝加哥大学与基督徒之间的联系。
亨德森以经验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如慈善组织、劳工问题、社会保险和“各种依赖性的、有缺陷的、行为不良的阶层”等,这根植于他那坚定的宗教信仰。他曾写道:“援助我们适应新的环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依靠主的保佑,上帝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科学,并让它们为我们所用。”(Henderson, 1899: 281)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对他的这种道德主义感到厌烦。然而,无论如何,围绕社会福利问题,亨德森强化了芝加哥大学与所在城市芝加哥的联系;在此过程中,还成功地培养了一些年轻学者如托马斯和伯吉斯等人对城市生活的兴趣与好奇心(Diner, 1975: 523-525)。
(4)家政学先驱塔尔波特
马里恩·塔尔波特(Marion Talbot)是哈珀为社会科学系物色的最后一位教师。哈珀试图招募韦尔兹利学院的前院长爱丽丝·帕尔默(Alice Freeman Palmer)来担任芝加哥大学女生部主任和历史学教授。但是,帕尔默坚持要带上她的朋友兼学生塔尔波特,并任命她为女生部主任助理。塔尔波特希望除了兼任助理主任外,还能够参与教学工作。哈珀同意了这一要求,让斯莫尔安排塔尔波特在社会学系教授“卫生科学”课程(Talbot, 1936: 2-5)。由此,“社会科学系”再次扩编为“社会科学、人类学和卫生科学系”。不管是对斯莫尔来说还是对塔尔波特来说,在社会学系开设“卫生科学”都是不合理的事情。直到1904年,芝加哥大学才为塔尔波特创建了一个独立的“家政管理系”。然而,一旦进入社会学系后,塔尔波特就努力证明这种安排是合理的。她在189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卫生条件和社会进步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卫生学必须和社会学携手共同致力于改善种族状况。”(Diner, 1975: 519)
至此,哈珀初步搭建了社会学系的人员架构。当1892年10月1日芝加哥大学正式开学时,社会科学系共有四名教师,分别是斯莫尔、亨德森、斯塔和塔尔波特。此外,还有少量研究生也会承担一些教学任务。这四人都是哈珀一手任命的,但是,无论是塔尔波特还是斯塔都没有兴趣把社会学建设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此外,无论是塔尔波特还是亨德森,在任命之初都没有学术性期冀。只有斯莫尔对社会学这门新的学科有一些正式的想法,当然,这些想法通常也是比较含糊朦胧的,包括:①社会学必须要研究当代社会;②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不仅要借助于文献资料,而且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指导;③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应该集中在实际问题上;④社会学必须是一门严肃的学术性学科,能够抽象出可以理解的理论,在物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使用科学严格的研究方法。当时,斯莫尔研究的主要是进化论社会学理论以及其中包含的达尔文式的变量。
2.斯莫尔:确立学科的领先地位
(1)沟通欧美学界的桥梁
社会学系是校长哈珀一个大胆的全新的实验,即创建一个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新学科。为此,必须要物色到一位称职的主任:不仅具有良好的管理技巧,而且要在社会学领域中拥有广泛阅历以及尊重同事。符合条件的人选非缅因州科尔比学院院长埃尔比恩·斯莫尔(1854~1926,主席1892~1925)莫属,没有人比他更能胜任这一职位了。 斯莫尔对促进社会学成为一门“现代科学”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对社会学领域中的技术发展趋势有着独到的见解。
斯莫尔对促进社会学成为一门“现代科学”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对社会学领域中的技术发展趋势有着独到的见解。
斯莫尔毕业于科尔比学院,曾在政府部门工作一段时间。1879年,他只身来到柏林和莱比锡学习社会心理学;在此期间,受到了社会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和古斯塔夫·西莫勒的熏陶,这形成了影响他一生的对社会科学伦理学意义的认知,即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Christakes, 1978)。1881年,学成回国后的斯莫尔重返母校科尔比学院执教历史学与政治经济学,但是,老教师们对他那些主题新颖的课程并不认可,使得他的教学任务很轻,进而有大量时间来广泛阅读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其后,其于1888~1889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尤为重要的是该校开设的新型高级研究生培养课程体系给斯莫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889年被任命为科尔比学院院长后,他不再讲授前院长主讲的道德哲学课程,而是代之以新的社会学课程,为此还撰写并印刷了一本小册子,即《社会的科学之导论》(Small, 1890)。
对德国哲学传统及其现代表现的熟稔,辅以和美国社会学界已经建立起来的稳固的联系,使得斯莫尔处于一个架通德国与美国两种方法论的独一无二的桥梁式位置。当时,美国的社会学充满了激情、狂热,而且也是学术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德国社会学则是一个更为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系统化的科学。斯莫尔的历史使命就是整合这两种风格迥异的社会学,为美国社会学开拓新的发展方向,重要的是,他具备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能力。
(2)对芝加哥学派的贡献
自1892年起,斯莫尔就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至1924年70岁退休。正是这32年时间里不懈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社会学系在1920年代辉煌成就的组织基础,确立了社会学系在全美的卓越地位。
其一,创建《美国社会学杂志》。这是1895年哈珀校长对斯莫尔提出的一个建议的结果。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之初,哈珀校长就设法建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建议斯莫尔创建一种社会学杂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基金会为之提供办刊经费(Dibble, 1975: 163 -168)。于是,第一期《美国社会学杂志》在同年出版发行,斯莫尔是杂志的创刊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芝加哥大学出版的《美国社会学杂志》对美国社会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1921年《社会学与社会研究》(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和1922年《社会的力量》(Social Forces)两本杂志发行才结束了美国社会学界只有《美国社会学杂志》一种专业期刊的历史。
其二,组建美国社会学协会。斯莫尔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创办了《美国社会学杂志》。无论是在芝加哥大学还是在发展中的社会学专业领域里,他都是一个特别能干和精力充沛的管理者。早些年,他出任过芝加哥大学文科主任;1904~1924年,担任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1905年创建了美国社会学协会,并且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协会的日常运作事务,编辑了美国社会学协会早期阶段的绝大部分文章。在他的主政下,美国社会学协会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紧密联系一直贯穿于芝加哥学派的黄金时代,这也是社会学影响力遍及全美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三,主办1904年的圣路易斯艺术与科学大会,出任大会副主席。早年在欧洲留学期间,斯莫尔花费了大量时间在欧洲各地游历,非常了解欧洲当时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通过此次大会,他相继把这些欧洲学者,如马克斯·韦伯、古斯塔夫·冯·拉兹恩胡福等人的思想引介到美国。可以说,没有斯莫尔优秀的管理与组织才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也不会成为全美社会学系的领头羊(Christakes, 1978: 20-23, 54-57)。
其四,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知识贡献。社会学是一门深度探索社会的学科,目的不在于社会改革或者人道主义,而是科学地理解人类行为。与他的组织与管理才能相比,斯莫尔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知识贡献要相去甚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斯莫尔开创了一个新的环境与风气,引导了其他学者积极进行调研与教学”(Diner, 1975: 523)。此外,他还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来界定社会学的范围,在和乔治·文森特(George Vincent)合作的教科书中试图描绘出社会学教学的目的所在(Small & Vincent, 1894)。斯莫尔坚信,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已经从一门散漫的学科变成了一门根植于经验研究的客观性学科,也是一门规范性、理论性特色不断积累的学科(Hinkle, 1980)。他非常认同经验研究,曾评论说,那些对中世纪城市与集镇特征的研究对社会学的意义还不如观察校园里孩子们的价值大。
在斯莫尔看来,社会学也是一门伦理学科,社会科学家应该在社会改革中扮演鲜明角色。由于不代表任何一个阶级或者利益集团,社会学者的专业才能与责任使命能够让他们有能力介入社会改革。在斯莫尔身上,科学主义与道德主义得到了完美结合。这种观念的逻辑是,虽然社会学能够提供因果解释,但是,这些解释并非完全机械论的或者决定论的。在社会行动中,还存在着人类的意志与愿望。斯莫尔还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整体性学科,其并非致力于研究特定的次要领域,而是要为社会进程提供一个概览性视角,为社会结构提供一个通则化的整体性说明。此外,他还赞同192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系中出现风起云涌的跨学科研究(Small, 1910)。
3.托马斯:开展社会学经验研究
在早期社会学系中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学教师只有斯莫尔一人,故,要想把社会学学科发展壮大必须增添专业的师资力量。但是,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对斯莫尔来说,合适的人员并不多。为此,他把目光投向了本系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身上。迫于师资紧张,在未取得博士学位之前文森特和托马斯就相继加入社会学系的师资队伍。至此,早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四巨头(Big Four)正式登场,即斯莫尔、亨德森、文森特和托马斯(Burgess, & Bougue, et al.,1964: 3)。文森特是芝加哥市民文化讲习所创始人兼主席的儿子,曾和斯莫尔合编了“绿色圣经”《社会学科学导论》出现之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使用的教科书《导论:通向社会的研究》(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ety)。但是,文森特的兴趣并不在学术,他渐渐地转向行政管理工作,并表现出色。1911年,出任明尼苏达大学校长;1917年,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系的桥梁(Diner, 1975: 526)。
与文森特在行政管理上的成就相比,托马斯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贡献更直接,铸就了芝加哥学派根本性的学术品质。1886年托马斯在田纳西大学获得了文学和古典文学博士学位,但是,在阅读了斯宾塞的著作后转向社会学。1893年在年届30岁之时,来到芝加哥大学作为研究生继续学习,并于1895年加入到社会学系的师资队伍中直至1918年。在此期间,他把全部的时间与精力都花在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的教书育人上,并于1910年成为正教授。托马斯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个通过外部大额资助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是早期社会学系教师中最多产、最杰出的一位学者。在斯莫尔鼓励经验研究的推动下,托马斯进行了深入的扎根研究,他的著作成功地把理论和经验结合起来。正如莫里斯·詹诺维茨看到的那样,他是“芝加哥学派知识分子根本性特征的缩影”(Janowitz, et al., 1966: viii)。
在1904年之前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托马斯对种族问题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他把种族差异从粗暴的生物学解释中解放出来,对种族差异的社会学解释做出了贡献。《社会起源资料汇编》是一部人种学的材料合集(Thomas, 1912),主要关心的是对人种差异的社会学解释以及如何将理论与经验材料结合(George, 1968: 260-264)。随着时间的推移,托马斯的观点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毋庸置疑,他仍然是社会学学科领域中最为杰出的创始人之一,正是他促使社会学者开始独立自主地研究人类差异的社会影响,使之从生物学或者遗传学的假定中解放出来(Cravens, 1978: 145 -147, 180-182)。和亨德森不同,托马斯并非致力于社会改革取向,而是更加独立地、科学地发展出能够解释社会组织不同形态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社会个体的理论。托马斯回避了道德主义和诊治药方,而是以冷静的方式分析那些在道德上争论极为激烈的问题,如性行为和卖淫问题,追求的是以人类学的方式来理解这些行为,而非对这些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或者改革这些行为。
4.帕克:加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与斯莫尔提拔托马斯作为社会学系教师一样,托马斯也为未来的芝加哥学派贡献了一个人才,即毕业于密歇根大学、曾师从杜威的罗伯特·帕克。在毕业后的头10年时间里,帕克是一名新闻记者,此后来到哈佛大学师从威廉·詹姆斯。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帕克又到德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在回国做了黑人活动家布克尔·华盛顿的七年秘书后,曾一度加入刚果改革协会。1912年在托斯开奇的一次会议上托马斯和帕克首次相识。1913年,托马斯成功地游说了时年49岁的帕克作为客座教授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一门黑人问题课程。至此,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干将托马斯和帕克都已经登上了学术舞台。虽然由于托马斯被芝加哥大学解聘,其和帕克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持续到1918年就戛然而止,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两人的关系是成就芝加哥学派辉煌成就的滥觞与源头(Matthews, 1977: 97-103)。
三 早期的学科贡献、特色及地位
1.贡献:美式社会学教育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以研究生教育为中心的主旨,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提供社会学研究生教育的院系。这意味着除了继续到德国进行深造外,现在芝加哥大学也能满足人们继续学习的需要,为那些年轻学者提供在美国本土接受社会学研究生教育的机会(Herbest, 1965)。要知道,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之时,大多数教师拿到的都是德国学位:1879~1881年,斯莫尔在柏林和莱比锡求学;1888~1889年,托马斯在哥廷根和柏林学习;1890年代晚期,亨德森在莱比锡上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889~1903年,帕克曾在柏林、斯特拉斯堡和海德堡游学,并最终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88~1891年,米德求学于莱比锡和柏林。在1915年之前,除了文森特以外,几乎所有人都曾在德国进修过一段时间(Park, 1972)。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在当时的德国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后果就是早期社会学系的教师几乎没有人系统地学习过社会学:斯莫尔学习的是政治经济学;托马斯学习的是人类文化学和大众心理学;虽然在柏林时曾上过齐美尔的课,但是帕克主攻的是温德尔班德的哲学。
作为一所新成立的大学与一门新创建的学科,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工作还缺乏一个完整的规划,但是,仍然在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早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895年到1915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累计为36位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授予了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不仅为美国社会学输送了大量人才,而且使得社会学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进入了专业化阶段,这意味着未来社会学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接受过系统化训练的专业学者,而非半路出家者。
2.特色:学科融合的传统
如前所述,早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师资队伍受到德国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客观上塑造了芝加哥大学学者们的心智倾向,即欧洲学术界开放,希望了解欧洲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调查方法。除了对来自欧洲思想的融涵,早期芝加哥学派成员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自身的学科边界非常模糊。以托马斯为例,他像拉扎勒斯、斯泰恩泰尔和心理学家冯特一样,吸收了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生理学家雅克·罗布(Jacques Loeb)、心理学家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等人的思想。斯莫尔则坚信社会学的使命是综合“特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为此,他要求研究生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科学、政治经济学、神学和家政学,认为学习这些课程极为重要。
有三个领域或者专业与社会学关系非常密切,也极大地影响了芝加哥学派的轮廓。其一,社会学系与神学院的关系密切。希海勒·马修斯(Shailer Mathews)——斯莫尔以前在科尔比学院的同事,在加盟了神学院(最初,斯莫尔想把他拉到社会学系)之后,成为神学院与社会学系之间联系的纽带,在他的努力下,促进了社会学家们对《圣经》的社会学认知。和马修斯一样,斯莫尔、亨德森和祖柏林全都是牧师;文森特的父亲是卫理公会教的一名主教,而托马斯的父亲也是一名牧师。在神学院获得了社会学倾向性的同时,早年的社会学系也表现出明显的基督教倾向。神学院和社会学系的合作不仅表现为两个系共同进行研究生教学,而且还表现为在神学院内共建一个部门教授“神职社会学”(Diner, 1975: 540-543)。早年社会学系的许多研究生都有牧师身份或者曾学习过神学。有些人像托马斯那样,迅速地确立了自己长期的研究方向,但是,还有一些人受到自由派新教徒的很大影响。
其二,社会学与社会福利之间的联系也非常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由最初的亲密无间转变为冷漠与隔离。部分原因大概在于知识分子的成熟和社会学逐渐与社会改革划清界限,社会学最终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社会福利管理的课程由社会学系老师上,先后讲过这门课程的社会学系老师有亨德森(直至1915年去世)、马里恩·塔尔波特(至1904年)、格雷厄姆·泰勒(Graham Taylor, 1902~1906年以客座教授的兼职身份上课)、克拉伦斯·瑞恩沃特(Clarence Rainwater, 1913~1916)以及伊迪斯·艾伯特(Edith Abbott, 1913~1920年以兼职身份上课)。1920年,在索芬尼斯伯·布莱金瑞吉(Sophonisba P. Breckinridge)和伊迪斯·艾伯特的推动下,该课程从社会学系独立出来,被纳入芝加哥大学正式院系行列,重命名为社会服务管理学院(Diner, 1977: 1-68)。
其三,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紧密联系。整个1920年代,在爱德华·萨珀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推动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与人类学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交互影响。直到1929年之前,社会学系一直和人类学系合在一个系内。但是,在1923年之前,人类学对芝加哥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托马斯。斯塔是哈珀招募的最不成功的人才之一,几乎完全不能胜任他主讲的课程,不仅长期缺席实地调查,而且对大学事务毫无兴趣。只有当1923年斯塔退休、弗艾·库珀-科尔(Fay Cooper -Cole)接替他的职位之后,人类学才开始为芝加哥学派做出显著贡献(George, 1979)。
3.地位:美国社会学圣地
斯莫尔的管理与组织才能,辅以亨德森和托马斯的学术影响力,再加上他们创制的研究生教学项目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共同铸就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此后的辉煌成就。1915年,芝加哥大学就已经确立起在全美社会学专业领域中的卓越地位。在那时,尽管芝加哥大学已经不再是全美唯一能够培养研究生的社会学院系,但是,像萨姆纳的耶鲁大学、罗斯领的威斯康星大学以及库利的密歇根大学仍然是社会学领域的次中心。也许,只有吉丁斯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可以在社会学研究生教育上与芝加哥大学媲美,特别是在20世纪的头15年,它是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分庭抗礼的另一个中心(Shils, 1981: 183 ff)。但是,到1915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影响力就已经日薄西山。
1895~1915年的20年间,共有98人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其中,芝加哥大学36人,哥伦比亚大学24人,耶鲁大学10人,宾夕法尼亚大学13人,纽约大学8人,威斯康星大学6人,密歇根大学和俄亥俄大学各1人(Hinkle, 1980: 14)。 形势非常清楚,到了1915年,芝加哥大学已经成为全美社会学研究生教育最好的大学,吉丁斯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只能屈居次席。
形势非常清楚,到了1915年,芝加哥大学已经成为全美社会学研究生教育最好的大学,吉丁斯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只能屈居次席。
1915年之后,先在托马斯和帕克的领导下、后在帕克和伯吉斯的努力下,社会学系无论是在学术质量上还是在学术数量上都蒸蒸日上,而哥伦比亚大学却日渐萎缩与凋零。在1928年退休之前,晚年吉丁斯对社会学系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官方系史对吉丁斯做出如是评价:“既未能成功地创建一个与芝加哥大学比肩的社会学系,也未能使社会学系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的其他社会科学院系媲美。直至退休之时,他仍然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唯一的正教授,而且从事的基本上是学院式社会学。诺斯科特说他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独断专横的人物,对自己的观点不容置疑’。院系中的其他同事纷纷抱怨吉丁斯的教条主义,并且一起抵制扩大社会学系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影响。”(Lipset, 1955: 292)
1915~1930年,芝加哥大学无论是在发展速度上还是在成长势头上都全面超越了哥伦比亚大学,这里有两组数据可以佐证。在1900~1915年前15年芝加哥大学培育了24名博士生,而自1916~1930年后15年中则培育了59名博士生。在前后两个15年中,芝加哥大学培养的硕士生分别为53人和101人。自1900年到1930年,除了其中一个5年期芝加哥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没有增长外,其他每隔5年,社会学系培养的博士生较前一个5年期都有较大幅度增长。截至1930年,社会学系培养的博士生人数已经由第一个5年期(1900~1905)的7人增加到最后一个5年期(1916~1930)的28人。与此相似,1900~1930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毕业生也在同步增长,由第一个5年期的10人增加到最后一个5年期的46人(Faris, 1970: 135-150)。
数量并非优秀的保证,但是,至少可以为质量提供人才基础。在前40位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中,不少于19人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或者是当前或曾经的教师,当然,有些人既是毕业生也是教师(Odum, 1951)。1923年之前,13位学会主席中只有3人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有关。但是,在1924~1950年,26位学会主席中16人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或者是它的教师(参见表2 -2)。这意味着,1915年之后芝加哥大学在美国社会学机构中取得了显赫地位。
表2-2 1924~1950年与芝加哥大学有关的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

芝加哥大学唯一的竞争对手是哥伦比亚大学。表2 -3显示,1921~1950年,30位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中7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有关。除了麦克埃夫(MacIver)外,其他人都是吉丁斯的学生。比较表2-2和表2-3可以看到,与芝加哥大学相比,哥伦比亚大学的挑战是苍白的;而且哥伦比亚大学主要是在20世纪头10年培养了未来的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从1912年到193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培养的博士中,有4人出任过学会主席,而同期芝加哥大学则有7人。
表2-3 1922~1950年与哥伦比亚大学有关的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

可以清楚地看出,1915~1935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取得了辉煌成就,1915~1935年也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巅峰时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崛起于20世纪前25年所形成的特殊学术环境与制度背景中。正是这些独特的学术环境与制度背景为黄金时代托马斯、帕克和伯吉斯等人的社会学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