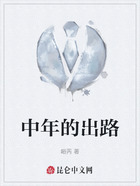
第6章 突然的叩门声
防盗门上的猫眼突然被阴影遮住时,陈默正把骑手工装往衣柜最深处塞。林悦手忙脚乱地收拾餐桌上的美团保温箱,保温箱上的油渍在灯光下格外刺眼——父母从老家打来电话说“路过顺便看看“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会是此刻的狼狈。
“默啊,开门!“母亲的声音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混着行李箱轱辘碾过地砖的声响。陈默的手指在门把手上停顿三秒,才想起扯掉围裙口袋里的骑手工作证。门开的瞬间,父亲的目光就落在他磨破的袖口上,老人手里提着的蛇皮袋还沾着老家的泥土,里面装的应该是新收的核桃——就像每年秋天都会准时寄来的包裹,只是这次,寄包裹的人突然出现在眼前。
母亲的视线扫过客厅角落的电动车充电器,又落在茶几上没来得及收的止痛贴。“瘦了。“她伸手想摸儿子的脸,却在触到他手腕的烫伤时猛地缩回手。陈默看见母亲的喉结滚动,那个在电话里总说“家里一切都好“的女人,此刻眼里泛着水光,就像他高考失利那晚,躲在厨房抹眼泪的背影。
父亲的沉默更具杀伤力。老人盯着阳台晾衣架上的黄色工装,上面“美团专送“的 LOGO在暮色中格外醒目。他蹲下身检查电动车的电池,手指划过车筐里的订单小票,纸角的褶皱里还夹着片梧桐叶——那是上周在雨桐学校门口等单时飘进去的。“电机该上油了。“父亲突然开口,声音比记忆中沙哑,“当年你爷爷的二八杠,我也是每周都擦。“
晚饭在异常安静中进行。林悦把煎蛋推到公婆面前,母亲却把蛋分成两半,塞进两个孙女碗里。小女儿雨欣突然指着陈默的工牌挂件:“爸爸的新玩具!“塑料小熊在灯光下摇晃,撞得不锈钢餐勺叮当响。雨桐慌忙踢了踢桌下的父亲,却看见陈默正在给母亲夹菜,筷子尖在瓷碗边缘颤抖,像极了他第一次向父母坦白考研失败时的模样。
真正的崩塌发生在睡前。陈默在阳台给电动车充电,父亲摸黑走过来,手里攥着他藏在鞋柜里的离职证明。月光把老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落在满是划痕的电动车外壳上。“当年你娘在镇上水泥厂扛水泥,“父亲用指甲刮掉车把上的贴纸,“总说等儿子出息了就享福。其实啊,“他突然转身,眼里映着远处的路灯,“能看着你好好活着,比啥都强。“
母亲在主卧发现了林悦的记账本。泛黄的纸页上,房贷、学费、老人药费的数字被红笔圈了又圈,最后一页画着歪歪扭扭的存款进度条,离女儿的钢琴课费用还差一大截。“这是我攒的养老钱,“老人把存折塞进儿媳手里,塑料封皮还带着体温,“密码是你爸的生日,别告诉那倔老头子。“林悦想拒绝,却看见母亲袖口露出的膏药贴——那是上个月在老家搬煤块时扭伤的,她在电话里只说是蚊子咬的。
母亲在沙发上坐了整夜。陈默半夜起来喝水,看见老人对着手机屏幕眯眼研究,指间反复划过“家政服务““钟点工“的招聘信息,银发在落地灯的光晕里泛着微光——那是他初中时母亲为了凑学费,在镇上医院值夜班落下的病根。
“我年轻时在县医院扫过病房,擦玻璃比你们年轻人利索。“天蒙蒙亮时,母亲把打印好的简历推过来,歪歪扭扭的字迹里夹着泛黄的健康证,“小区张姐说,现在雇主都爱找岁数大的,说做事踏实。“陈默盯着简历上“照顾老人经验:3年“的条目,突然想起父亲上次住院,母亲在陪护床上蜷缩的身影,比记忆中矮了整整一头。
父亲的修鞋摊在三天后支了起来。老人从老家带来的铁制工具箱磕在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惊飞了停在电动车把手上的麻雀。雨桐放学回来时,正看见爷爷蹲在单元门口,用砂纸打磨客户的皮鞋后跟,老花镜滑到鼻尖上,像极了她课本里画的手艺人。“爷爷,您怎么在这儿?“小姑娘攥着满分试卷的手微微发抖,父亲抬头时,镜片上的反光恰好遮住了发红的眼眶。
第一个客人是雨桐的班主任。女老师抱着断带的高跟鞋笑得亲切:“早就听说雨桐爷爷有门好手艺。“父亲的手在接鞋时突然顿住——那是双价值不菲的真皮女鞋,鞋跟处的磨损痕迹显示主人常穿它奔波。当老人用锥子扎穿鞋底时,陈默正提着外卖箱往家走,看见班主任转身时向他点头,目光里没有同情,只有成年人对生活的默契。
母亲的第一单钟点工在周五下午。她系着从老家带来的蓝布围裙,在雇主家擦玻璃时,突然听见主卧传来争吵声:“都说了不要超过 45岁的!““这个阿姨干活特别仔细...“陈默站在小区花园里,看见母亲从六楼窗户探出身的剪影,突然想起自己 12岁那年,母亲也是这样趴在学校教学楼的外墙上,为他够挂在窗沿的风筝。
冲突在某个雨夜爆发。陈默发现父亲的修鞋箱里藏着降压药,空药瓶上的标签显示已经过期半个月。“省点钱给雨欣买奶粉。“老人擦着潮湿的工具箱,雨滴顺着遮阳棚边缘滴落,在地上砸出深浅不一的水洼,“我这身子骨比你想象中硬朗,当年在供销社扛化肥...“话没说完就被剧烈的咳嗽打断,陈默看见父亲偷偷把揉皱的招工传单藏进工具箱底层,上面印着“夜班门卫,55岁以下优先“。
真正的和解发生在雨桐的生日宴。母亲用做钟点工攒的钱买了奶油蛋糕,父亲把修鞋赚的第一笔钱塞进雨欣的存钱罐,硬币相撞的叮当声里,老人摸出个磨得发亮的铁皮青蛙——那是陈默小时候最爱的玩具,不知被母亲从哪个旧箱子里翻出来的。“当年你爸摆修鞋摊,“母亲抹着奶油说,“总把赚的第一笔钱给你买糖人,现在轮到你们的孩子了。“
深夜,父母房间传来窸窣声。陈默透过门缝看见,父亲正在台灯下修补他的骑手工装,母亲给衣服的前面绣了“平安”两字,针脚细密得像她当年绣的手帕。老人的老花镜滑到鼻尖,却固执地不肯戴上——他们总说,不想让儿子看见自己老去的样子。
周末清晨,陈默送父母去车站。母亲往他口袋里塞了把晒干的蒲公英,父亲则把修鞋箱绑在电动车后座:“小区门口那棵梧桐树下,我跟物业说好了...“
父亲在旁边咳嗽着补充:“你王大爷的儿子在县城开了家电脑维修店,缺个懂技术的...“话没说完就被陈默打断,他看着老人期待又忐忑的眼神,突然想起自己第一次领工资时,父母也是这样小心翼翼地盼着,盼着儿子在城里站稳脚跟。
话没说完就被汽笛声打断,老人在进站口突然转身,背影像座风化的石碑:“默啊,当年你非要留在城里,我们怕你委屈;现在你想回家,我们也给你留着门。“
公交车驶离站台时,陈默看见母亲在车窗上画了个笑脸,父亲的修鞋箱在行李架上摇摇欲坠,却始终没有倒下。口袋里的手机震动,是张涛发来的面试通知,附带一条消息:“我爸说,他那辈人把面子看得比天重,其实啊,一家人能凑在一起吃苦,比什么都体面。“
阳光穿过云层,照在母亲缝的保温箱罩子上,那朵歪歪扭扭的向日葵正在微风中舒展。陈默突然明白,父母的到来不是揭开伤疤,而是带着针线,把他破碎的生活重新缝补——用他们的皱纹,用他们的老茧,用那些藏在修鞋摊和钟点工里的、笨拙却温暖的爱。
电动车在晨雾中穿行,他听见后座的保温箱里传来轻微的响动,是母亲偷偷塞进去的山药——就像二十年前塞进他大学行囊的、带着泥土的温暖。后视镜里,父母的身影渐渐模糊,却又无比清晰,如同他心中永远的灯塔,照亮着这个中年男人在生活迷雾中,继续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