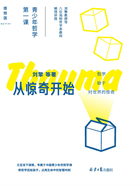
真假问题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对第一类问题——“真假问题”的讨论。“真假问题”主要属于认识论领域,但同时也涉及本体论哲学、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等领域。我们分4个小节讨论10个思想实验,它们都对我们似乎确信的知识提出了挑战,让我们陷入某种矛盾或困惑,使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某种直觉、信念和知识是否为真。
实在论问题
在真假问题的第一小节,我们来讨论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感知的“现实”是确确实实的真的存在吗?或者说是“实在”(real)的吗?你可能会感到奇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思想实验。(以下用“Thought Experiment”的缩写“TE”表示思想实验。)
TE1 如梦初醒
假设你们中的一位同学,或者你可以想象有一个孩子,他做了一个噩梦。在这个梦中,有一头凶猛的野兽,突然从窗口闯入了他睡觉的房间。当然他非常害怕,然后在梦里开始和这头野兽搏斗,搏斗越来越激烈,非常紧张。在快要被野兽吃掉的那一刻,他猛然惊醒。他发现自己大汗淋漓,然后松了一口气,心想“还好这是一场梦”。
但正在他庆幸而放松的时候,一头野兽真的闯了进来,然后又是一场激烈的搏斗厮杀,结果怎么样?他被野兽吃掉了!不是的,他又惊醒过来了。原来他刚才没有从第一个梦中真正醒过来,只是进入了第二个梦。
这种连环梦的经历,大家可能也有过体验。现在他终于醒过来了,松了一口气,开始平静下来。可是,突然有一个念头抓住了他,他问自己:“我怎么能知道我现在是真的醒过来了?有没有可能我仍然在梦中?”于是,他又开始紧张地注视着卧室的窗口……
类似地,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我们这个讲座是否真的发生了。你敢保证你现在不是在做梦吗?这位同学好像很确定这是真的,are you sure?有没有可能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有个通知,告知你这个讲座由于台风被取消了,但是你是那么渴望参加这个讲座,以至你做了这样一个梦,梦到你早上醒来,出门冒着大雨赶到了这里,坐下来听这个讲座,讲座现在正在进行……而这一切都是你的梦境,只不过你梦得很真切。
TE2 柏拉图的“洞穴寓言”
我们还可以讲一个经典的“洞穴寓言”。在《理想国》第七卷,柏拉图讲过这样一个寓言:
有一个山洞,一群奴隶从生下来就一直被关在这个山洞里。他们戴着枷锁被绑在石凳上,面朝洞穴的顶端岩壁,头也不能转动。在他们的背后有燃烧的火把,火把发出火光,将他们的影像投射在洞壁上。这些影像是他们唯一能看到的东西,是他们从生下来就看到的所有东西,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些影像就是现实世界,就是reality。可是,其中有一个奴隶,被人打开了枷锁,他从岩洞往上走,最后走到了洞穴之外。他看到了太阳,开始感到一阵晕眩,但后来他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阳光,终于看到了阳光下的现实世界。但是,当他再回到洞穴中,告诉他的同伴,说你们看到的只是幻影,你们一直生活在幻觉中,没有人愿意相信他。而且他们会说,你脑子或者眼睛被弄坏了,连明明白白的现实(洞壁上的影像)都看不清了。
柏拉图的这个洞穴寓言非常有名,而且有多种含义和不同的解释。但在这里,我们关注的仍然是那个问题:如何区分幻觉和实在?那个被解放了的奴隶,因为他看到了真相,才能区别什么是幻影、什么是现实,但完全陷入幻影的人,就会将幻影本身当作真实的现实。而且,这个寓言还可以有更复杂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追问,那个被解放的奴隶怎么知道自己在洞穴之外就看到了真正的现实?如果他走出洞穴之后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洞穴,那里的太阳只是一个巨型的日光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连环梦”一样,从一个梦境转到了另一个梦境中。
TE3 缸中的大脑
洞穴寓言是很古老的,在当代哲学中,也有一个经典的思想实验叫“缸中的大脑”(Brain in a Vat),是哈佛大学哲学家普特南[3]提出来的。这个思想实验是这样的:
想象一下你的大脑被人从你的身体内取出,放在一个缸中,其中有能够维持大脑生理功能的液体。大脑上插着电极,把你大脑的神经感知系统连接到一些电脑上,电脑给你一些模拟日常生活的感官刺激,那么你完全会以为自己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有各种活动,而不会知道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缸中的大脑”。
如果你们看过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4],就很容易理解上面的思想实验。以上三个思想实验提出的问题就是:现实是否存在?我们的“现实感”是不是真实的?
英文“realism”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被翻译成“现实主义”,而在哲学领域中,它一般被译作“实在论”。世界究竟是什么?存在的本质是什么?这在哲学上称为“本体论”(ontology)问题。而实在论是对世界本质的一种看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说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实实在在地在那里,独立于我们的主观意念。
实在论的观点听上去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还会有什么问题吗?但上述几个思想实验恰恰质疑了我们的直觉或常识。因为我们总是要通过感官来感知现实,那么我们如何能保证我们的感知反映了客观的存在?我们又如何区分幻觉与实在?
我们常常陷入幻觉而不自知,将幻觉误以为真。幻觉可能是梦境所致,或者是“邪恶的魔鬼”对我们施加了魔法,制造了我们的幻觉。因此,与实在论相左的观点就出现了,比如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这两种观点认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世界是否实际存在;还有“反实在论”,就是认为世界其实并不实际存在,“世界”只是我们自己大脑的主观想象。
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实在论的挑战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就怀疑自己的感官体验的真实性,由此怀疑一切感知的“存在”是否可靠,甚至提出了他自己是否存在的问题。经过苦思冥想,他最后发现,只要他在思考就证明他自己是存在的,这是可以确信的起点,所以就有了笛卡尔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到了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乔治·贝克莱[5]也说过一句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这句话最极端的解释,就是说所有的存在不过是我们的感知而已。
你可能会说:“不对啊,我有童年的记忆。”但是,你怎么知道那些童年的记忆是真的发生过的?你只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你有这样一个童年的记忆,你不能证明有一个外部世界。你可能会问:“如果没有外部世界,我怎么会有我对世界的一套认知和想法呢?比如,每天早上太阳会升起,有冷有热。”请注意,你在做出这个结论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所有的感受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先有了外部世界,我们才有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可是,这样一个假设是不可证明的。为什么必须有一个外部的原因才能导致你有心灵的感受呢?就像我们做梦,不一定有事情真实发生我们才会做梦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讨论这些事情也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这里涉及我们的科学是不是能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科学会首先假设世界是存在的,对于这些存在,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去发现或者描述。对于描述这个世界的模式,我们叫作科学,这也是非常特定的一种描述方法。有人说,这个世界跟我们的感受一致,但其实,科学对世界的描述跟我们日常经验的感受是非常不一致的。比如说,你看得见分子、原子、质子吗?
现在,大家可能开始明白,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我们不是上帝,能直接知晓或“看到”世界的本质,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就不一定可靠。在哲学上,本体论问题的争论后来就转变为认识论问题,发生了所谓“认识论转向”。以前哲学家苦思冥想“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在认识论转向之后,问题就转变为“我们怎么知道世界是真实的”。刚才那几个思想实验,就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提出的挑战,质疑你所相信的真实世界可能是错觉,那么坚持实在论观点的人,就需要提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这些质疑,进而为实在论做辩护论证。
那么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很难达成定论。现在有相当多的哲学家是持不可知论或者怀疑论立场的。当然,持实在论立场的哲学家也并不是无所作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辩护和论证。我简单谈一种论证,可以叫作“最合理解释”论证。基本的思路是说,我们的确无法直接知道世界是实在的,但我们可以先假设世界现实存在,而这种假设与人类广泛的感知和观察相一致,就是说,比假设“世界并不实际存在”更好地符合我们的感知和观察,那么在哲学上最合理的解释,就应当支持实在论的假设,而不是相反。
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来解释一下。比如,我们看到这张桌子,实在论者说,这里有一张桌子,它的存在不依赖我们的主观意识,我看到这张桌子存在,当我离开这个房间后,虽然我看不见它了,它仍然是一个存在。反实在论者可以说,这张桌子的存在只是你的感知幻觉,你离开了,这张桌子也就不存在了,那么你回来后呢?你的幻觉也回来了,这张桌子又出现了,所以你以为这张桌子是客观存在的,但实际上并不是。到此为止,两种观点都可以解释我们的感知经验。
可是,有一天发生了事故,这个房间装修得不太好,房顶上有一块天花板塌掉了,在你离开房间的时候,天花板的残落物掉落在这张桌子上。回到房间后,你看到桌子上有一堆碎片。这个现象对于实在论者来说很容易解释,但对反实在论者来说就相当麻烦。因为反实在论者假设,在你离开房间的时候这张桌子也消失了,是你回来之后桌子才重新出现的,那么如果天花板掉落,就不应该在桌子上看到残落物,残落物应该在桌子下面,掉落在地上,这张桌子应当是干净的。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反实在论者就必须发明一套更复杂的解释模型,就必须说你的幻觉不只是包括桌子还包括天花板,或者说,虽然你离开的时候桌子消失了,但当天花板掉落的时候,这个你幻觉中的桌子就会奇迹般地出现,正好接住了天花板的残落物……反正非常复杂。大家想想,如果我们这个讲座不是真实发生的,而是你的幻觉,需要多么复杂的模型才能解释那么多巧合:你认识的同学也到了,他正好和你乘坐同一班地铁等。
总的来说,实在论提出了一种世界模型,对比反实在论提出的世界模型,前者比较简单合理,而后者非常麻烦,甚至需要假定有奇迹出现。那么“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实在论假设的世界模型是正确的。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相当复杂,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
同一性/身份问题
在真假问题的第二小节,我们来讨论同一性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既包括事物的同一性问题,也包括人的自我同一性问题,特别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问题,以及时间意义上的变化和连续性问题。我们先来介绍一个非常古老的思想实验,出自希腊作家普鲁塔克[6]的记载。
TE4 忒修斯之船
雅典人觉得国王忒修斯从克里特岛归来时搭乘的木船很有纪念意义,就一直把它保留了下来。可是时间久了,船上的木板逐渐腐朽,于是雅典人就用新的木板更换朽坏的木板,腐烂了一块,就更换一块,最后船上所有的木板都被换掉了。问题来了,被换掉了所有部件的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忒修斯之船吗?或者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你如果说不是,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不再是原来那艘船了?
后来,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忒修斯之船上更换下来的所有老木板拼起来建造一艘船,那么在这两艘船中,哪一艘船才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
这里有一个局部和整体的关系问题,也有时间上的连续性问题。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自己在一个大学任教,华东师范大学,这个大学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最初建校时的老师都已经退休了,当时的学生也都毕业了,那时候的房子所剩无几,而且我们的主校区也搬迁到了闵行的新址,那么,为什么我们还可以视其为同一所大学,它仍然是华东师大?这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不仅是一艘船、一所大学或机构有同一性问题,人也有同一性问题。对于人,我们往往会说“身份认同”,二者对应的英文其实是同一个单词:“identity”。我们再来讨论一个思想实验。
TE5 器官移植
实际上,人的身体也和忒修斯之船一样,是在不断变化的。
如果你昨天剪过指甲,你的身体和前天就不完全相同了,但这点细微的差别无关紧要。要是你整容了,变化就明显了。现在有不少人到韩国去整容,回国进入海关的时候,就有点麻烦,因为他和原来护照上的照片判若两人,海关官员会怀疑他伪造身份。还好,现在韩国的整容医院会提供一个证明,其中会有整容前后的照片。所以在进入海关的时候,整容的人可以说“这就是我,只不过换了一张脸”。
整容会带来身份认同的麻烦,但问题还不大。如果我们的身体有问题,需要做器官移植。比如,我换了一个肾,我可以说是“我”换了一个肾。哪天我的腿也不好了,我就换了一条腿,我仍然可以说这是“我”,是换了一条腿的我。但如果哪天我身体的所有器官都被换掉了,会怎么样?最后,连我的大脑都被换掉了,我还可以说这是“我”吗?
器官移植的例子与忒修斯之船的例子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刚才有同学说了,如果有人换了大脑,那就比较麻烦。我们一般倾向于说,是那个保留了大脑的人换了身体,而不是那个保留了身体的人换了大脑。因为我们会认为,人的身份认同是跟大脑紧密相连的。那么,人的自我同一性是取决于大脑吗?
好像是的。但我们可以继续一个思想实验,设想一下:如果有一种技术,能把你大脑中的所有记忆和思想变成“数据”,下载之后上传到另一个人的大脑中,同时把那个人大脑中的“数据”上传到你的大脑中。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大脑中的数据交换了一下,那么这两个人中究竟哪个才是你?
有的同学似乎认为“数据”更重要,但确切地说,对于人的同一性而言,人的记忆、思想和自我意识比大脑、身体都更重要。比如像金星老师那样,做了变性手术,身体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个人是金星老师,是舞蹈家金星。
但是问题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可以想一想,你大脑中的“数据”和你的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如果两个人相互交换了大脑中的全部“数据”,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会被看作哪个人?假设一下,如果刘翔和姚明之间交换了大脑“数据”会怎么样?装着刘翔大脑“数据”的姚明的身体,会被邀请去打篮球吗?他会答应吗?但他实际上没有专业水平篮球运动员的意识,水平差很多怎么办?那么他说让我去跨栏吧!他有110米栏的运动意识,但他带着姚明的身体,根本跑不到那么快,怎么办?
其实这还不够极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思想实验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大胆想象),要是让姚明和章子怡之间相互交换了大脑“数据”会怎么样?大概他们两人都会疯掉吧,也就是说,他们会完全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这告诉我们,人的同一性也可能并不仅仅取决于大脑“数据”(记忆、思想和意识)。
那么,有人会说基因才是最重要的,看基因就能确定人的身份。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同卵双胞胎(identical twin)兄弟,基因和你完全一样,你能说那个兄弟就是你吗?高考之后,你考上了北京大学,他落榜了,然后他拿着你的录取通知书去读北大,你同意吗?
关于同一性问题的研究非常复杂,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做进一步的阅读。我们在网上可以找到一篇通俗、有趣的英文文章,题目是“什么使你成为你”(“What Makes You You”),作者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网络作家蒂姆·厄本(Tim Urban)。如果要看更专业的研究,我推荐大家读30多年前出版的名著《理与人》,作者是当代重要的英国哲学家帕菲特[7]。
我个人对此没有深入的专业研究,有些想法完全不成熟,但可以提三个要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同一性概念本身可能不够精确,有一定的含混性。它可能不是精确到一个点或者一组确切的标准,而是包含着一组条件的程度或范围。当事物或人的属性落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可以认定同一性,但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就怀疑是否还能保持同一性。当然,这个范围的边界是有点模糊的。比如刚才谈到的大学的例子。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在某一天,华东师大的所有教师都同时集体退休或辞职,学生也同时全部毕业或退学,然后学校换了完全不同的一批师生,我们就很难说这仍然是华东师大了。所以,局部的而非整体的、逐渐的而非突然的变化,维持了某种时间上的连续性,这可能是保持同一性的某种条件。
第二,同一性不是由单一变量(要素)决定的,可能取决于多变量的共同作用。在“忒修斯之船”的例子中,所有木板和部件都更换了,为什么我们还不能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另一艘完全不同的船?除了这种变化是渐变的过程之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它的结构完全没有变,目标功能也没有变。也就是说,一艘船的同一性不只是取决于它的材料,还取决于其结构和功能。那么对于人来说,我认为用单一要素来决定身份可能是错的。以上关于思想实验的讨论,就是用假想的情景来考察单一要素是否能充分解释同一性的构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以身体、基因、大脑、记忆与意识来决定,可能都不充分、不可靠。也就是说,人的同一性无法被“化约”为任何单一的要素。
第三,现在哲学上有个比较吸引人的理论,叫叙事的自我(narrative self)。人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角色。我们是学生,是老师,是孩子的父母,是公司的员工等,我们怎么能把这么多的身份、这么长的历史,与我们的现在拼接起来呢?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故事。如果我们能够讲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连贯的、内部自洽的、一体化的故事,我们就有了统一的自我。
注意,叙事自我理论的要点,不是说我们先有一个自我、再讲关于自我的故事,而是把故事讲出来以后,才有那个自我。否则我们的同一性是不存在的。并非有一个现成的自我,而是由我们的故事建构了统一的自我。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刻会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当你陷入分裂、强烈自我矛盾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你的身份(identity),你的同一性就会变得四分五裂。比如,陷入爱情后你突然失恋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分裂了(falling aparts),然后就像电影、电视剧里说的要把你自己装起来(put yourself together)。讲故事就是把自己装起来。
对一所学校、一个组织来说也是一样。比如,如果像刚才说的那样,华东师大突然换了一批新的师生,我们就很难说它还是华东师大,因为我们讲不好这个故事了。虽然自2006年以来,我们换了主校区,换了那么多人,但它依然有一种传统、一种精神在延续,在与时俱进。这时候,我们可以合理地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
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类或者组织的自我理解,是建构的结果。讲述的过程需要很多材料,有点像你在制作一部关于自己的电影,有些是硬核素材,有些是你对它的理解和阐释。你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之后,同一性才存在。那么,忒修斯之船就很好理解了,如果你能把这条船的来龙去脉讲通了,它就仍然是忒修斯之船;如果你讲不好,它就很难维持它的同一性了。
所以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重新阐释或者恰当阐释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件,对于维持一个民族国家的同一性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很长的历史,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和旧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它需要一个历史叙事。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个人来说,要讲一个融贯的故事是不容易的,是一项使命,而且我们需要不断地重讲。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有一套论述,经过改革开放又有一套论述,这个故事是不断加工和重塑 (making and remaking)的过程。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你们还很年轻,对于现在感到的困惑,可能会觉得很痛苦,但到二十年之后再看,这些“痛苦”说不定就是你未来的财富,你人生的电影是可以被重新剪辑的。
人生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人不是石头。石头的本质是固定的,但人是不断自我生成、自我重构的,生命是一个生生不息展开的进程。这虽然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很多麻烦,但这也正是人生精彩之所在。
我们何以知道我们知道?
接下来我们进入当代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我们何以知道我们知道(how do we know what we know)?也可以说,如何判断我们的知识是真确的?什么是知识的标准?这是对知识可靠性的探索。首先,知识与感官经验有密切的联系。一般流行的看法是,知识源自感官认识,但我们必须有亲身的感知才能获得确切的知识吗?知识与经验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相当复杂。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思想实验。
TE6 黑白玛丽
假设有一个名叫玛丽的天才科学家,专门研究颜色。她阅读了大量人们对于各种颜色的感受和反应,也精通关于颜色的物理学,知道各种颜色对应的光的波长。但是,她自己是一个严重的色盲,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色盲,她只能分辨黑白两种颜色,也就是说,她完全处在一个黑白的世界中。因此,玛丽知道所有关于色彩的理论知识,但实际上她从未有过“彩色”的感官体验。那么,我们能够说,玛丽明白颜色是怎么回事吗?或者她真的具有颜色的知识吗?如果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位极为高明的医生,她的色盲被治愈了。从此之后,她能看见色彩缤纷的世界了,她会对颜色感到惊奇吗?她在治愈之后获得了关于颜色的新知识吗?
这个思想实验是1982年由哲学家杰克逊[8]提出的,旨在挑战所谓“物理主义”的认识论。物理主义坚持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物质的,人的意识活动也无非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物理活动(神经系统的电流脉冲刺激等)。但这个思想实验试图表明,玛丽在治愈之前,虽然知道一切关于颜色的物理学事实,但仍然不知道颜色是什么样子的。这意味着感官体验所引发的意识活动并不能被物理知识所涵盖,这就质疑了物理主义的观点。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讨论知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物理知识是客观的,但因为玛丽缺乏关于颜色的主观感受,缺乏“第一人称”的亲身体验,所以她对颜色的知识似乎总是缺失的。但我们可以说存在“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这两种知识吗?或者,恰恰是因为以前的玛丽因为视力缺陷而陷入了褊狭的“主观”,无法完全把握“客观的”知识?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本质”与“现象”的角度来思考。玛丽通过物理学的研究知道了颜色的本质,但她似乎不明白颜色的现象。那么关于本质的知识与关于现象的知识是不同的吗?无论如何,我们的直觉是,玛丽在治愈之前和之后对于颜色的认知是不同的,她后来感受到了色彩斑斓的世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说治愈之后的她获得了关于颜色的新的知识?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呢?有人提出了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知识是被确证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简称JTB理论。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JTB理论。知识(knowledge)是区别于一般意义的信念(belief)的,在此,“信念”是指你碰巧相信的某种陈述。JTB理论可以用形式化的语言表达为:某人S知道一个陈述P为真(S具有关于P的知识),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当且仅当:(1)P为真;(2)S相信P为真;(3)S确证地或有理由相信P为真。比如,你知道今天下雨,也就是你具有关于今天下雨的知识,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今天的确在下雨,你也相信今天真的在下雨,而且你有理由确证——比如你刚才没打伞,身体被淋湿了——从而相信今天确实在下雨。
JTB理论听上去充分而完备,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再来看一个思想实验。
TE7 你究竟知道什么
有一天你到书店买书,排队付钱的时候,你看到在你前面有位中年男子,他买了很多书,当时他的手机掉了出来,手机上有个Hello Kitty的挂件,你对此印象很深,觉得这个叔叔还用这样可爱的挂件,比较萌,你就记住了他的样子。
第二天,你在一个十字路口目睹了一场车祸,那个被车撞倒的人不幸身亡,他的手机掉了出来,手机上有那个可爱的挂件,再仔细一看死者的面容,他就是前一天你在书店遇到的那个叔叔。然后警察来了,你作为目击者做了笔录,说前一天你还见过这位不幸的遇难者,他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过了几天,你去图书馆借书,突然发现阅读区坐着一位读者,和你见过的那位叔叔长得一模一样,而且桌子上就放着带着同样挂件的手机。你吃惊得几乎要叫出来了。这位读者似乎明白了你的惊讶,轻轻告诉你,他的双胞胎兄弟前几天在车祸中遇难了。他们兄弟俩都喜欢读书,也都喜欢Hello Kitty的手机挂件。你恍然大悟。但问题来了,你知道这对双胞胎兄弟中的谁遇难了吗?你对警察做的笔录是你真正知道的事情吗?
这个思想实验的最早版本来自美国哲学家盖梯尔(Edmund Gettier)在1963年发表的很短的一篇论文,后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刚才讲的这个版本当然是我模仿原版改编的。所有这些反例,都是用来质疑JTB理论的。按照这个理论,这个例子满足了所有三个条件:第一,“一个爱读书的、手机上带着可爱挂件的叔叔在车祸中遇难了”,这个陈述本身是真的;第二,你也相信这是真的;第三,你有理由去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你在车祸前一天见过他。但是,你真的知道是谁遇难了吗?你在书店见过的那个叔叔可能是遇难者,也可能不是,说不定他是你在图书馆遇到的那位读者。如此一来,你并不真正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或者说,你对于谁遇难了没有真正的知识。你对警察说,“这个遇难者前一天还在书店买了很多书”,这句话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盖梯尔的论文发表后,引发了许多讨论,有人想做些小修改,来弥补JTB理论的缺陷,后来发现没这么简单。
在讨论我们的信念或者感知的时候,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语词来表达我们的感知,但语词的意思有时是含混不清的。语言问题不只限于认识论领域,而是涉及整个哲学,所以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哲学界开始出现了一个“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哲学研究的趋势。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具体的小问题:是否存在“私人语言”。当我们讨论个人感受,比如说“疼”——头疼或者牙疼,我们怎么知道我说的“疼”和你说的“疼”是相同的意思,是同一种疼?因为你并不是我,你不能亲身感受到我的疼,反过来也一样。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在说疼,你也在说疼,但我们在说的不是一回事?也就是,当我们大家都在说疼的时候,说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这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的“私人语言”问题。大家可能知道,维特根斯坦不是一般的哲学家。如果哲学家中有“天才”,他就是一个天才,人类历史上几百年可能才出现一个。他在《哲学研究》第293节中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来探讨“私人语言”的问题。
TE8 甲虫游戏
假设有几个孩子在玩一个游戏,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盒子,盒子里装着某种东西,但他们彼此不能看别人的盒子。每个人都将自己盒子里的东西叫作“甲虫”,但他们从不对别人描述自己的“甲虫”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在游戏中可能会说,今天我的甲虫“长大了”或者“变多了”或者“消失了”,等等,但每个人都看不到别人的盒子里究竟是什么。问题是,他们说的甲虫是同一个东西吗?如果不是,这个游戏能继续下去吗?
当然,这里的“甲虫”可以类比我们说的“疼”。维特根斯坦主张,不存在“私人语言”,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用“甲虫”只是来指称各自盒子里不同的东西(甚至是空盒子),那么“甲虫”这个词就不可能进入我们的日常语言游戏,这个游戏就无法继续下去。要使得“甲虫”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语言游戏中获得意义,它必定是在指称某种公共对象,而不是某个私人对象。同样地,疼可能指私人的感受,但如果“疼”这个词要有意义地进入语言游戏,那么我们的“疼”一定是大致相同的经验,那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私人的疼”会在语言游戏中被淘汰掉,被取消或者完全被视为不相干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当然不会否认私人经验,但他认为,如果你用一个名词来专门指称你自己与众不同的私人经验,这个名词就不可能在日常语言中有意义地被使用。为什么会这样呢?比如说,你说的“疼”其实是某种“痒”的感觉,我说的“疼”其实是某种“酸”的感觉,他说的“疼”其实是某种“胀”的感觉……大家都去医院找医生,医生给大家开了止痛片,但无法止住你的“疼”。那么你就会问:为什么仍然在“疼”呢?在不断辨析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你不恰当地使用了“疼”这个词。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说,语言规则源自共同的用法,语义是在语言游戏的使用中形成的,而语言游戏是公共游戏,你一个人不能独创一套有意义的语言。
逻辑的力量与困惑
在真假问题的最后一个小节,我们简单来讨论一下与逻辑学有关的思想实验。
首先是伽利略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大家知道,在伽利略之前,人们大多相信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质量越大的物体下落得越快。伽利略认为这是错误的,于是他站到比萨斜塔上,手里拿了两块质量大小明显不同的石块,让它们同时“自由下落”,结果它们同时落地,于是,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观点就被推翻了,这成为物理学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但问题在于,伽利略为什么有这个自信站到比萨斜塔上做这个自由落体实验呢?他怎么就知道自己能驳倒权威?是的,他用不着做这个实验就知道亚里士多德是错的。实际上,比萨斜塔实验可能只是个传说,伽利略根本没去做这个实验。他之所以有这个自信,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思想实验。
TE9 自由落体
如果有a和b两个物体,一个重一个轻,现在把这两个物体捆在一起从高处扔下去,会发生什么结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假设,如果a是一个更重的物体,b是一个更轻的物体,那么a的速度要比b的速度快。把一个运动速度快的物体和一个运动速度慢的物体捆在一起,会怎么样呢?运动速度快的会拉着运动速度慢的,这样运动速度慢的就比原来要快一点;而运动速度慢的要拖着运动速度快的,所以如果a和b是被捆在一起的,它们一起的速度应该在a的速度和b的速度之间,这是一个结论。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a和b被捆在一起后,它们质量的总和既大于a的质量也大于b的质量,所以a和b共同的运动速度就应该既大于a的运动速度又大于b的运动速度。于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假设里,我们推出了两个彼此矛盾的结论:一个结论是,a和b被捆在一起后,它们的速度应该在a的速度和b的速度之间;另外一个结论是,它们的速度既大于a的速度当然也大于b的速度。
伽利略就想,唯一使这两个结论不发生矛盾的方式就是,a、b的速度和a+b的速度一样,也就是说,一个物体下落的速度跟它的质量是无关的,但都是自由落体。
伽利略只是用一个逻辑的思想实验就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观点,可见思想实验有时候是很有效力的。反讽的是,亚里士多德是西方逻辑学的开创者之一,竟然没有察觉到他物理学观点中的逻辑错误,这有点让人不可思议。
逻辑很有力量,会帮助我们清晰地思考,但有时候又会迷惑我们,因为会出现逻辑悖论。之前网上有个调查问:你认为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还是多数人手中?结果16%的人回答说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中,84%的人回答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你看,根据16%的人的说法,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中,那么84%的人的看法应该是真理,但84%的人却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这就和“说谎者悖论”差不多。一个人说:“我现在说的这句话是谎话,你不要相信我。”那么他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话?罗素说的“理发师悖论”也是如此。一个村子里有一个理发师,他说:“我只给那些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理发师的头发谁来理呢?因为村子里只有他一个理发师,一旦他给自己理发,他就要马上停下来;可是一旦他停下来,他就应该马上给自己理发。这就变成了一个悖论。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思想实验,可以算作“芝诺悖论”的一种。
TE10 芝诺悖论
芝诺是古希腊的数学家,他提出了好几个悖论,这些悖论在性质上都是思想实验,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表述。我们从中国人熟悉的龟兔赛跑寓言谈起。兔子和乌龟开始100米赛跑,但这个兔子太骄傲了,想着自己先睡一觉再说。但它睡得太久了,等它醒过来时,发现乌龟已经快到终点了,兔子赶紧飞跑,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寓言警示我们“骄傲必败”的道理。下面这个思想实验,就是我们根据龟兔赛跑的寓言改编的。
假设兔子虽然有点骄傲,但没有那么过分地骄傲,它在乌龟只爬了10米的时候就醒过来了。那么兔子还会输吗?
经验告诉我们,兔子当然会赢,它一定会在某一点超过乌龟。
但芝诺说,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只受伤的兔子吗?
不是的,这只兔子很健康,比刘翔跑得还快。
芝诺让我们这样想象:因为乌龟已经领先10米,兔子要追上乌龟,就必须先跑过乌龟已经领先的10米,对不对?
但是,这时候的乌龟并没有闲着,也在向前爬,虽然速度比兔子慢。假设兔子的速度是乌龟的10倍。当兔子跑过开始的10米时,乌龟又往前爬了1米,那么兔子要赶上乌龟,就必须跑过落后的1米。
但在这段时间里,乌龟又往前爬了10厘米,兔子又必须跑过落后的10厘米。
但这时候乌龟又领先了1厘米……
因此,兔子永远也无法赶上乌龟!
类似地,还有“飞矢不动”悖论。
你射出一支箭,这支箭要飞到100米,但要飞到100米,就要先飞过一半的距离,也就是要飞50米,但要到达50米,也要先飞到其一半的距离,就是25米……以此类推,到达再微小的距离,都要先飞过其一半的距离,而一半的一半可以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最后就会得出“飞矢不动”的结论。
芝诺的逻辑很强大,但和我们的经验完全不符。我们都知道,在兔子无限接近乌龟之后,有一个瞬间一定会超过乌龟,一支射出的箭不会因为我们在逻辑上“要求”它先飞过一半的距离而不动。所以这就成了一个悖论。
按照芝诺的逻辑,运动是不可能的。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在芝诺的时代,没人能解决这个悖论,这要等到牛顿、莱布尼茨的时代,等到有微积分概念的时候,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芝诺的“诡计”就是,显示了“微分”而隐瞒了“积分”。
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所谓运动是物体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有限的距离。但任何一段有限的距离,在其内部又是无限可分的,1米可以分为100厘米,又可以分为1000毫米,无限可分。芝诺把距离的无限可分性突显了出来,但同时“隐瞒”了时间类似的性质。任何一段给定的时间,内部也是无限可分的,1分钟有60秒,1秒钟还可以继续分为毫秒和微秒,一直分下去。但芝诺是以有限的时间概念来对照无限可分的距离概念,换句话说,他强调有限距离的无限可分性,而回避了或者掩盖了有限时间的无限可分性,所以就出现了悖论。其实,这个无限可分的时间可以克服无限可分的距离,就是说他只做了微分而没有做积分。
逻辑悖论还有很多,这些悖论都是思想实验,也都非常有趣。在历史上,许多悖论推动了数理逻辑和语言哲学等领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