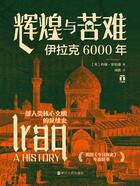
伊拉克民族构成与社会形态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资源与潜力清单都会在史料中重点列出,主要包括国民历史、发展能力和主要贡献等。在这样一个工程中,要想穷尽无遗地列出伊拉克此类名录的多样性和方方面面,任务之艰,几无可能。但是,如果人们从更为宽泛的范围来审视此类清单,那么伊拉克社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便一览无余。这一切多是历史变化的产物,外来移民和入侵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竞相进入伊拉克,常常带来灭顶之灾。但也有人定居下来,与比先他们之前到达的或已经定居此地的人民进行互动交流,积极融入当地生活,并且富有成效。这些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受制于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甄别,以群体的自我维系与生存发展为标准——换言之,即他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维系生存并获得庇护的。
目前,人类学家已经确定了人类社会普遍践行过的四种基本生活方式。最早期的生活方式是狩猎采集。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寻觅食物,收获自然生产的食物资源,或是狩猎野生动物,采集坚果、浆果等野生植物的果实,以及诸如小麦和大麦等植物的野生祖先。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伊拉克北部一个名叫沙尼达尔洞穴的地方出土了关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大量实物证据,自此之后人们在这里又发现了更多的证据。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是早期人类唯一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万年左右,从现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开始,然后扩至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北部。一些狩猎采集者可能面临着野生食物短缺的危机,因为该地区气候在进入最后一次冰河时期后变化剧烈,导致他们无法找到足够的食物,于是这些人开始尝试种植和培育谷物,驯服诸如绵羊和山羊之类的动物,发展到后来是喂猪养牛。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第二种生活方式出现了:从事农业的群体开始定居在永久占据的村落,开启了农业生产,如今这种农业群体广泛分布在整个中东地区。在伊拉克,扎格罗斯山脉和托鲁斯山脉的山麓丘陵地带,以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周边的北部平原地区每年都有足够的降雨量来维系农业耕种。因此,伊拉克便成为地球上最早的农业中心之一——伊拉克人民为全球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农业文明便是其第一批贡献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住在村中的农民似乎已经排挤出或同化了那些狩猎采集者,尽管这些农民还将继续利用野生动植物,将其作为食物的来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乡村里的农民开始向南迁徙,到达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冲积平原,并在那里安居下来。在那里,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这批居民成为最早发明灌溉技术的人,并开始利用两河河水来灌溉土地。公元前4000年左右,农耕村落已经遍布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直至现在我们还能发现这些村落的踪迹。时至近代,伊拉克的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北部人口都是吃苦耐劳的农民。或许在此之前2000年,第三种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在伊拉克显现出来,当时一些群体开始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游牧”。这种生活方式主要基于畜牧绵羊和山羊,公元前6000年,通过人工干预,人们将野生的绵羊和山羊驯化为家养动物。这些群体通过放牧他们的牲畜来确保它们能够获取足够的食物,而他们自己也主要通过步行、骑驴或骑马的方式进行迁移,前往根据季节变化就可以找到食物的地方。夏季的时候,他们必须将牧群赶往山区,避免中暑,并在那里搭建帐篷,建立营地。而在冬天到来的时候,他们便要拔起插在地上的木桩,收好帐篷,将他们的牧群从高原山区带回河边低地,进行避冬。
然而正是在这里,他们接触到了农业文明。传统意义上,在历史学家与游记作家的笔下,“沙漠游牧与农耕播种”之间产生冲突乃是必然,他们对此总是大做文章,这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古代伊拉克的最早文献也揭示了农耕民族对游牧生活心存芥蒂。而且,游牧民族时常袭击农耕民族的村庄,也是中东地区几千年来的生活事实。尽管如此,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如果没有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提供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几千年来,这两个群体都不可能达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繁荣昌盛。研究这两个群体关系的现代学者,往往将更多的目光关注于两者之间的共生互荣与协同运作,而非他们之间的紧张冲突。游牧民族通常用他们放牧的绵羊和山羊,为村民提供羊毛、皮革、肉类和奶制品等用来丰富他们的饮食结构,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从事农业的农民也可以向游牧民族提供他们谷物之类的农产品,以此来满足游牧民族的生活需要。也许还有一点对牧民来说更为重要,那就是村民们通常允许他们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放牧,这样牧民们的绵羊和山羊就可以啃食地上的残茬。而农民就此得到的回报便是这些牲畜留下的粪便,以此来给他们的土地施肥。这样的放牧权利对游牧民来说不可或缺,但是牧民和农民之间或是游牧群体之间对这些权利的争执,往往便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紧张关系和冲突的根源。
一旦这些群体之间或内部的关系恶化并爆发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各自组织起来保护群体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特权,寻求所谓的正义。这些基本原则都与群体内部的亲属关系相关,简而言之,就是所谓“血缘联系”,或者用专业的新闻术语就是指(因血缘关系构成的)“部落”。伊拉克诸多部落的起源、历史及部落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层见叠出的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素材,然而任何一个简单的考证研究并不能公正地揭示出这些研究对象的复杂与微妙关系。“部落”背后隐含的最基本理念是所谓亲属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说,他们共享同一个男性祖先的血统(不管这血统真实与否),其历史存在有时很难追寻,历史上也无法证实,但其“后代子孙”强烈地认同这个血统。历史上总有那么几个时期,部落以“联盟”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但总体上看,联盟比较实际,于是部落便成为部落下面的子群体的组成成员——先是“宗族”,其下便是“家庭”——由是,这些村民和牧民,及其子孙后代迁移到伊拉克的各大城市,开启了另一种方式的生活。因此,人们会发现此种情况见怪不怪,即一个村庄中的大多数居民或游牧群体的大部分成员属于同一个大家庭或属于其中几个大家庭。在这样的情形下,保持亲属群体的团结一致,便是从家庭到氏族到部落的共同需要,对他们而言,这种需要甚至也许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价值。与这种需要密切相关的还有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其中包括荣誉、英雄气概、女性贞洁美德、对陌生人的热情好客,以及须对群体受辱尽报仇雪耻的义务——不论是群体成员遭到的杀戮或创伤,还是群体性荣誉受到的玷污。
在这样的群体中,个体通常将其最基本且最为持久的忠诚归于血亲——家庭、氏族和部落。然而,正是这种对血亲的忠诚导致了自伊拉克文明诞生以来最持久的社会和政治的紧张态势,历史上的伊拉克一直动荡不安。从诸多方面来看,文明的诞生便是这种紧张态势的主要原因,因为随之而来的就是伊拉克历史上第一批城市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城市诞生在伊拉克南部。
伴随着最早城市的诞生,人类学家所谓的四种生活方式中的最后一种也随之出现:城居生活。而且,城市居民还发明了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字。现今的历史学家正是从城市居民数百年间所写的文字记录中发现了伊拉克的悠久历史,但是这些文字记录并不客观,更多地反映了那些城市居民的兴趣爱好、态度立场,倾向性明显,有时几乎就是从他们的立场看待世间万物的。于是,城市居民的出现便将村民与牧民推到了我们历史雷达屏幕的边缘。
公元前2700年左右,古代伊拉克的第一批城市成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第一批国王的权力中心。这些国王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并加强以城市为基石的“政权”,从而对城市的周围乡村进行统治。而乡间民众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忠于地方权威,并从中寻找领头人,这种权威一直体现在家庭、氏族和部落中。因此,从伊拉克文明诞生起,这种组织形式便造就了历史上一直困扰伊拉克的紧张局势。
文字的发明使得我们能够谈论公元前3000年甚至更早的伊拉克,包括其复杂多元的种族与语言。如今,伊拉克的时事常以广泛多元的种族和宗教等类别进行报道。一些新闻记者和评论员常将伊拉克人归为几个大类,诸如什叶派阿拉伯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还有一些属于少数民族的土库曼人,直至最近,其境内的雅兹迪人和曼达人才偶尔被人们提及。此外,在伊拉克境内,包括波斯人在内的伊朗人,偶尔也会被人提及,他们通常被一些伊拉克人视为外来人士,会威胁这个国家的安全。如前文所言,从伊朗向西方迁移到伊拉克境内的伊朗人对伊拉克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通常将这些人归类为波斯人,他们在改变伊拉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天,仍然还有许多人类学家认为,“种族”的概念和范畴在科学上一无是处,但是在几十年前,专家们用这个概念阐释伊拉克境内的不同“种族”,而且是见怪不怪。较为有用的策略是要根据族群进行类别划分,主要依据这个群体所使用的共同语言以及他们所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来进行族群定义。据此尺度,那么现在伊拉克人口中最大的群体便可以归类为阿拉伯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说阿拉伯语,该语言是闪米特语系中最为通用的语言。如今,说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在中东地区占主导地位,但从语言学视角来看,伊拉克的通用阿拉伯语与埃及等地的阿拉伯方言有着明显差异。因此,那种认为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是如今沙特阿拉伯境内移民后裔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尽管还有很多人仍持这样的观点。公元前的最后几百年间,确实有一些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人们迁徙到了现在的伊拉克。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开始了对外征服,阿拉伯人入侵伊拉克,也是穆斯林大征服的一部分,这次征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的人口结构。但是,今天的伊拉克阿拉伯人当中也包括许多比他们更早居住在伊拉克的族群后裔,这些族群往往经过几个世纪的同化,渐渐地接受了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熏陶,转变成为所谓的阿拉伯人。这些族群先民当中,还有一些人操与阿拉伯语相关的闪米特语,其中包括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他们说阿卡德语。还有阿拉姆人,他们使用的语言阿拉姆语至今还在伊拉克北部的一些偏远地区流行,主要用来陈说那里古老的基督教团体礼拜时的祷告。其中还有一些先民,诸如苏美尔人、胡里安人和凯喜特人,他们说着与闪米特语系相关联的语言,而他们自己的本族语言在几千年前就已弃之不用。在如今的伊拉克,阿拉伯人差不多占到总人口的70%。近年来伊拉克战乱频仍,体系化的人口信息普查资料缺失,这个数据虽可能不太精确,但基本可靠。
伊拉克人口的第二大组成部分是库尔德人,也是其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库尔德语属于印欧语系,这就意味着它不仅与伊朗的通用语言波斯语(Farsi,波斯语拼写形式)有着亲密的关系,还与英语、法语和其他的现代欧洲语言有着很多的亲缘关系。库尔德人最早进入伊拉克的确切日期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库尔德人传统上认为自己与古代的民族米堤亚人(Medes,一译“米底人”)有着关联。公元前1000年左右,米堤亚人和波斯人曾征服过伊朗。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主要分布在伊拉克东北部的扎格罗斯山区,与这片区域关系密切。在这里,他们以农耕、放牧和市民生产交易为生,自食其力,坚守本族的文化习俗和家庭观念,并以此实行自治。历史上,库尔德人学会了在夹缝中求生存,曾强烈地捍卫他们的独立,不断地抗争,寻求自治和独立,并常常获得相当大的成功。库尔德人占主导的地区称为“库尔德斯坦”,不仅包括伊拉克境内的这一部分,还包括现代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的毗邻地区。历史上统治过这些现代国家的诸多政权,普遍将库尔德人视为一个制造麻烦的少数民族,经常采取迫害和诉诸暴力的方式控制他们,压制他们独立、自治的愿望。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库尔德人采取极端高压手段,并将其征服,自此,库尔德人便一直参与伊拉克政府的管理,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着高度自治。自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垮台后,他们当中仍然有许多人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抱有希望。
尽管库尔德人怡然于山区生活,但这个民族曾一度成为这个地区的统治者,他们曾横扫亚述帝国,势力拓展到整个中亚和中东地区。而突厥人(一说土耳其人)作为中亚骑马游牧民族,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也只是星星之火闪烁在历史的星空之上。公元8世纪和9世纪,阿拉伯统治者将他们引入伊拉克地区,利用他们作为雇佣兵和奴隶战士为阿拉伯人战斗,因为突厥人骁勇善战,骑兵技艺高超,而且凶猛残暴,往往挥舞复合弓就能造成致命伤害,从而受到了阿拉伯统治者的高度评价。到了公元11世纪中叶,突厥部落军队因其中一位大可汗(或酋长)塞尔柱而为世人所知,曾经横扫伊拉克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公元1071年,塞尔柱人在安纳托利亚消灭了一支拜占庭军队之后,便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短命的帝国,统治中东100余年,直到公元1100年,其后这个帝国在土耳其境内又延续了许多年。塞尔柱王朝臻至鼎盛的几个世纪后,另一群突厥人,同样也是以早期一个伟大的酋长奥斯曼的名字命名,他们首先牢牢控制了土耳其西北部,进而锁住了东南欧,最终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纳入版图,其中也包括伊拉克。他们建立起来的奥斯曼帝国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今天生活在伊拉克境内的这些突厥人的后代,被人们称为土库曼人,他们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与闪含语系的阿拉伯语、印欧语系的库尔德语没有什么语言上的亲属关系。虽然人口数量不占优势,但是伊拉克境内的土库曼人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团结意识。
总之,尽管在今天的伊拉克,波斯人很难算得上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语言群体,但自从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缔造者——伟大的居鲁士大帝征服伊拉克以来,波斯人便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斯人和米堤亚人差不多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一起到达伊朗,并在法尔斯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伊朗西南部(法尔斯省)建立了一个小小王国。在居鲁士大帝征服伊拉克后的几百年间,波斯的国王、官员、行政管理人员和一些学者在伊拉克文化创新和政府治理模式改革方面厥功至伟。今天,现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宗教等级制度很大程度上对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既然谈及宗教话题,我们还必须承认,伊拉克的种族多样性与其宗教多样性不分轩轾。现如今,在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但在全世界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中,伊拉克情形比较特殊,难得同时拥有人口众多的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不过,逊尼派全球信仰者人口众多,而什叶派,全球信仰者较少。这种关键性的差异,其根源将在后面的论述中详细探讨。不管怎样,这种差异对伊拉克历史的影响持久而深远。
历史上,没有一次人口普查能筛查出伊拉克境内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具体人数,但大多数专家认为,伊拉克的什叶派人数远超过逊尼派人数,差不多占总人口的55%到60%。尽管许多逊尼派穆斯林拒绝接受这些数据,宣称他们逊尼派才是伊拉克人口最多的。不过历史上,伊拉克也有大量人口信奉过另外两种宗教——以一神教信仰为主的宗教,分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接下来,我们将详细地介绍伊拉克这两类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小群体的起源和历史。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有大量的犹太人从巴勒斯坦迁徙到伊拉克,而且直到几十年前,伊拉克境内的犹太社区仍是世界上最大最为富裕繁荣的犹太社区之一。在公元1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就出现了基督教团体。直至现在,基督徒仍是伊拉克境内重要的宗教团体,尽管像犹太人一样,他们的人口数量在最近几十年里急剧下降,尤其2003年西方国家入侵伊拉克后,战争的困扰(和宗教清洗)使得伊拉克动荡不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纷纷逃离伊拉克。
但是,并不是仅仅穆斯林、犹太教和基督教是伊拉克宗教遗产中幸存下来且为数不多的几个宗教。还有一些古老的教派,如雅兹迪人、曼达人派和什叶派的沙巴克人,他们信奉各自的宗教信仰已经长达几百年。公元7世纪时,入侵伊拉克的阿拉伯部落成员便将伊斯兰教带到这里,在此之前,犹太教社区和基督教社区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们时常与早已安居此处的另一个宗教社区进行密切的接触,而且富有成效。这个宗教派别的成员遵循伊朗导师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拜火教的创始人)所宣扬的道德教义。西方主要是通过他的希腊名字拼写方式认识了这个人,即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为希腊语称法)。尽管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众数量锐减,但是他们的社区至今仍活跃在伊拉克和伊朗的一些地方。
潜藏在伊拉克这些一神教的背后,是几千年来这些多神信仰的阶层融合与持久的文化累积。要知道,伊拉克人民曾经崇拜过数以百计的诸神,这些多神信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当时的人们通常将成功与繁荣甚至幸存下来的唯一希望,寄托于超自然神力,无数超自然力量与此密切相关,因此需要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因为它们会带来盛宴或饥荒、丰盈或贫困。为了侍奉这些神灵,早期的伊拉克人建造了城市和神庙,并征服了周边庞大的帝国。他们还创造出了大量的艺术,设计了各种礼仪仪式,其内核要义甚至还萌生出了现代的科学和技术思想,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故事与诗歌等文学作品,至今还在吸引着我们,教化着我们。
总而言之,伊拉克特殊的地理位置极大地影响了伊拉克的历史,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得益于其高度发展的农业与商业,同时又受到资源匮乏或分布不均(如矿藏、木材和降水)的限制,而今却又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富甲天下。今天,石油对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的繁荣富强至关重要,因此伊拉克也常常让他们垂涎三尺。伊拉克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好处也给伊拉克带来了分裂与苦难,因为它让外来者嫉妒不已,引来了不必要的垂青。这些外来者总是骚扰进犯,想要染指这些好处。相对而言,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向世人提供了相对开放的走廊,这些外来进犯者时常通过这些开放走廊入侵伊拉克,对其实施控制。然而,外来者也带来了种族和文化上的丰富性、多样性,从而塑造了伊拉克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