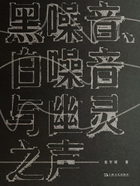
二、《起源》:音乐的“起源”
《起源》标题中的“兼论”似乎暗示着音乐在该文中仅列于附属地位,但实际上,卢梭在这里要达到的主要结论是,语言在当代衰落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它失去了与音乐之间的本质关联(语言与音乐,原初本为一体)。从这个角度看,音乐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在该文的一开始,卢梭简要区分了视觉形象和话语声音之间的差异,随即明确指出语言起源于“精神的需要,亦即激情(passions)。激情促使人们联合,生存之必然性迫使人们彼此逃避”(19)。 因而,人类最初的语言形态并非有着清晰规则和体系的理性语言,而是源自激情的诗和象征的语言(将激情之“幻象”[illusion]转化、凝结为“隐喻”[métaphorique])。这里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激情指向的是人与人在心灵或精神层次上的联结,因而超越了单纯的物质和肉体的需要(“将激情传达于他人,既要入耳,又要入心”(20))。二是仅从声音表现力的角度来看,原始语言要比日后越来越“精确化”“观念化”“理性化”(21)的语言丰富得多:“声音无穷无尽,置入重音,声音数量又倍增;……在声音与重音的组合之上,再添上节拍(temps)或者音长(quantité)。”(22)显然,原始语言更接近音乐,或更准确地说,从源头上来看,二者同样指向着浩瀚绚烂的声音海洋。(23) 但在卢梭看来,语言演化的历史却也恰恰是不断偏离这个源头、不断失却与音乐联系的历史。字母文字的出现或许更有利于不同个体或不同种族之间的沟通交流,但它所导致的结果亦是“改变了语言的灵魂。文字以精确性取代了表现力。言语传达情意,文字传达观念”(24)。 当语言失却了它的激情的源泉,也就逐渐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和“灵魂”,蜕变为苍白的观念符号。
由此卢梭试图回到语言的萌发时代,去探寻那已然失落的情感源泉。虽然他对所谓南方和北方语言起源的描述更多像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翻版或拓展(25),但其中对情感方面的论述确实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对比起来,南方语言起源于情感,而北方语言起源于需要。从卢梭的论证语境来看,显然前者更为关键,也占据了大量篇幅。除却细节,南方语言的情感起源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地球孕育了人类。第一需要使人分散,但其他需要又使人联合,只有到了这一时刻,他们才言说且成为别人言说的对象。”(26) 换言之,真正催生语言的并非人类之初的那种处于“分散”状态时的种种恐惧、焦虑、敌视的情感,而是将人们联结、维系在一起的情感。此种“社会情感”(affections sociales),最初即表现为怜悯(la pitié):“通过推己及物(En nous transportant hors de nous-mêmes),与其他受苦难的存在者连为一体(identifiant)。”(27) 这里,“推己及物”即是情感将自我带向超越自身的运动,其最终的目的正是为了形成一个更高的统一性的总体。
既然音乐与语言分享着共同的源头,那么也就同样可以从此种社会情感的角度来对音乐的起源进行解说。所以卢梭在论“音乐的起源”一节的起始就明确肯定,“无论是第一次吐字,还是第一次的声音(son),都是与第一次的发声(voix)一同形成的,它们的基础就是支配着它们的激情”(28)。催生语言和音乐的情感是相同的。更进一步说,在起源之处,二者简直就是浑然一体、难解难分的。这一断言不难理解。但德里达点出的一个深刻观察却道出了不寻常之处:“语言之前无音乐。音乐源于言说而不是声音。…… 如果音乐以言语为前提,它就会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29)其中,“音乐源于言说而不是声音”,这足以道出卢梭音乐哲学的最为核心的界定。初看起来,这是一个极为令人费解的论断。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解,音乐难道不正是对声音进行组织、从而对人的感觉以至心灵产生审美效应的艺术形式?但对此卢梭做出了极为明确的否定,“音乐并不是将声音组合使之悦耳的艺术”(30),或者说,“音乐对于心灵的力量,不能归因于声音”(31)。那么,我们倒要追问,离开了声音这个源头,音乐的力量还能源自何处?卢梭亦给出明确答案:音乐最终是一种“摹仿”的艺术。但摹仿什么?或许正是原初的“社会情感”。不过,语言不也同样是对此种情感的“摹仿”?看来更为关键的问题不是摹仿什么(这一点在卢梭的论述中本没有疑义),而是摹仿的方式。“是什么使音乐成为另一种摹仿艺术呢?旋律。”(32) 那么,旋律的摹仿有何特别之处?“它摹仿(各种)语言的腔调,摹仿其俗语,使其与心灵的特定运动产生共振。”(33) 显然,即便说音乐和语言皆同样指向着心灵的“特定运动”,但二者之摹仿作用是不同的,最终仍然是语言占据了主导地位:音乐的摹仿归根结底是“语言性”的。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旋律会在卢梭的音乐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诚如当代音乐哲学家彼得·基维结合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里德和哈奇森)的观点所指出的,“人声音乐在音乐中的明显相似物是旋律线,在独唱和咏叹调中,旋律线当然是另一种人声语言:也就是说,歌唱。”(34)而将音乐的起源归结为歌唱,这也是卢梭向来的立场。这一切本是顺理成章的推论:既然情感是本源,而人声和歌唱又显然是情感的最为直接的表达,那么与之密切呼应的旋律也就当然成了音乐之中的核心和本质。所以说“诗、歌曲、语言不过是语言本身(la langue même)而已”(35)。
如此,我们终于领会了德里达观察的深刻之处:之所以卢梭要隔断音乐和声音之间的“自然”维系,从而将音乐最终拉向语言这一边,其实质正是为了将音乐的起源置于人类社会之“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必然会断言音乐“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事实上,他不是确实说“诗、音乐、语言同时诞生”(36)吗?但接下去,与其跟随德里达的脚步,对自然/社会、内/外之间的“替补与间隔”的关系进行一番玄奥高深的思辨,还不如结合音乐这种具体而特殊的艺术形式,来进一步对卢梭的论述进行反思。
实际上,卢梭音乐哲学的缺陷实在是过于明显了(但这又何尝不是其力量所在)。他的论述毫不掩饰地将音乐中的一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剔除了出去—那就是所谓“纯音乐”(music alone)(37)。事实上,就整个西方音乐史而言,自从音乐脱离“社会功能”之束缚成为一种“自律”的艺术形式之后(38),纯音乐毋宁说就成为音乐范畴之中极为重要的形式。即便就在卢梭写作《起源》的时代(39),所谓纯音乐亦已经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那么,他的这些有着如此明显缺陷或“偏颇”的论述是否能够恰当揭示音乐的真正本质?
仅从其音乐哲学的基本立场来看,回答似乎是否定的。主推纯音乐的基维着力批判的两个流派(再现主义和情感主义)似乎皆汇聚于卢梭的身上:卢梭既明确将音乐的根源归于情感,又将音乐表达的基本方式归于对原初情感的“摹仿”。但仔细想来,却又不仅如此。结合上文论述,卢梭的“摹仿”既不同于简单的“再现”(比如对具体对象的摹仿),亦不能等同于基维所说的“深层的再现”(以叔本华为代表),即将音乐指向某种超越的本体或秩序。诚如杜根和斯特朗的敏锐观察:“这样,音乐就是认知性的,这并非说它指示出物之所是,而只是说它确立起与物之间的恰当关系。”(40)换言之,音乐的“摹仿”其实并非旨在“复制”或“指示”,而更在于确立关系,并传播“效应”和“作用”。由此卢梭才将音乐称作“激发的艺术”(the art of arousing),以此区别于其他作为“说服的艺术”(the art of convincing)(41)的表象性的艺术形式(尤其是戏剧)。说服的艺术将他人的情感和意志强加于观者,而激发的艺术则旨在真实地引发主体自身的情感与意志。(42)说服的目的在控制乃至奴役,而激发的目的则在于引导与启发。在这个意义上,其实音乐更为接近启蒙的精神,因为它将体验和判断的权力和能力再度交还给主体自身。诚如杜根和斯特朗所言,“音乐是属于我们自身的”(43)。从这个基础出发,音乐才能真正进一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通。
而卢梭音乐哲学在这个方面的深刻意义,当然是坚持认知主义立场的基维所难以企及的。实际上,基维对纯音乐的论述无非只是突出了西方音乐中的“文本支配性”和“规则的限定性”这两个方面,而忽视了更具启示性和“升华性”的“灵感”的方面。(44) 而基维对更具技术性的和声对位的强调亦与卢梭对旋律的精神性的界定形成鲜明反差。如若从卢梭的立场来看,基维的认知主义亦恰好可以作为其批判的对象:所谓“无意义、无参照或无具象特征”(45)的纯音乐难道不正是卢梭所论述的失却了情感—言语源泉的、“蜕变”(dégénéré)了的音乐形式?音乐的蜕变和语言的蜕变亦是同时进行的,当二者失却了原初的情感维系,便各自分裂为抽象的形式—规则的系统。基维可以断言说“音乐思维是思维,音乐理解是理解。无论你是否相信,思维完全是语言学的”(46)。 但如此理解的“纯”音乐是全然没有生命力和感动力的音乐,正如这样理解的语言亦是全然没有音乐感的抽象符号系统。
“这就是音乐,当局限于振动组合的单纯物理效果时,最终是如何丧失其对于精神的影响的”(47),—卢梭的警示理应让我们直面这个根本难题:如何保留音乐的“纯粹性”(即其与声音之间的自然关联),但同时又不丧失其“灵性”的源泉和旨归(实现个体之间的心灵联结(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