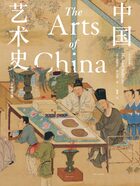
西周
商王朝末年,处于西陲的诸侯国周,在文王的统治下,势力日益膨胀,已经实际控制了商王朝领土的三分之二。最终,大约在公元前1045年,文王之子武王攻陷安阳,末代商王自焚。在武王年幼的继承者成王统治时期,历史上著名的强有力的周公摄政巩固了周王朝,建立了封建制度,将商人的势力钳制在其他诸侯的包围之中。然而,他仍然允许商人的后裔在弱小的宋国里延续下来,维系世代相传的对祖先灵魂的祭祀。周公是周王朝制度最主要的设计师。尽管在周王朝晚期,国家陷于无休无止的内战之中,王室因此分崩离析而最终消亡,但是周王朝仍然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留下了特色鲜明的机制。
商代青铜艺术传统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突然中断。包括孔子在内的东周史学家和哲学家将周代先王描绘成道德楷模,为讨伐“腐朽没落”的商王朝正名,将文王、武王时代看作“黄金时代”,但是周人克商之前的文化鲜为人知,与商相比,实属蛮夷。
在周人统治下,庙堂礼仪和祖先崇拜都成为维系王朝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宗教生活仍然以对上帝的崇拜为中心,但是,含糊而无所不能的“天”的概念逐步替代了“上帝”。周王室和诸侯公室成为繁缛礼仪的核心,礼仪最终集结形成《周礼》等典籍。君主在每天清晨和黄昏临朝听政,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1912年。敕命书写在竹简上,当众宣读出来,然后转交给官员们去执行。从穆王时代(公元前947—前928年)开始,这些命令铸在青铜礼器上保存下来渐成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铭文不断增长,成为研究周代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尚书》中若干章节记载了商末周初的事迹。这些文献不仅证明历史感是中国文明最显著的特色之一,而且也揭示出书写文本在中国文化中极其崇高的地位。
西周初年的青铜礼器可能是亡国之后幸存的商人工匠制作的,因此有时难以与商代铜器区分开来。随着周人逐步稳定政权,尽管商代纹样母题还不时可见,最显著的是作为“复古风格”孑遗的饕餮纹,但是,周人对更粗放、厚重和充满活力的形态的偏爱也渐趋成形,我们将其称为“西周中期风格”。就算对于在礼仪中使用青铜器的周代贵族而言,这些纹样的确有所意味,我们也无从探究。
周代城市
目前,我们对商代建筑的了解远远超出了对西周建筑的了解。就西周建筑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得不依靠文献资料,尽管商末周初诸侯国的都城和贵族墓葬的发现迅速改变了这一景象,有的甚至填补了文献空白。研究西周制度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被认为于西汉时期编辑而成的关于礼制和政府管理的文献《周礼》。编辑者透过重重历史迷雾,回望遥远的黄金时代,整理出多少有点理想化的西周礼制和政治生活的图景。尽管如此,《周礼》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记载往往被后世试图遵循古代礼法制度的人当成原典。言及古代周人的城市时,《周礼》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13]
多年来,我们几乎不知道西周权力中心所在何方。20世纪70年代晚期,在西安以西100余公里的岐山,考古学家发现了包括宫殿建筑在内的一处西周城址遗迹。克商之后一段时间内,周人仍然在岐山统治全国。过去30年来,考古学家在西安附近的沣河两岸发现极其丰富的西周墓葬和铜器窖藏(图2.33),那些铜器窖藏可能是公元前771年匆忙迁都时埋下的。[14]

图2.33 青铜器窖藏,出自陕西扶风庄白村,西周
周代晚期,独立的诸侯国越来越多,城市的数量也在剧增。有的城市规模非常宏大,比如山东齐国都城临淄,由东向西达1.6公里,由北向南达4公里,周边围绕着一圈高达9米的夯土城墙。河北发现的燕国都城燕下都规模更大。对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而言,东周时期的城市和极其丰富的附属墓葬无疑是一座座取之不尽的宝藏。
建筑和雕刻
《诗经》收录了几段关于宗庙和宫殿的生动描述:
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约之阁阁,椓之槖槖。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君子攸跻。
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哙哙其正,哕哕其冥,君子攸宁。
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15]
这些歌谣提供了一幅高台广厦的景象。高台之上,粗壮的柱子支撑着巍峨高宇,屋檐虽然没有采用飞檐形式,但却像鸟儿平展双翼,地面上铺满了厚厚的草垫,宛如日本的榻榻米一般,给人以一种温暖、明快和舒适的感觉。最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是宗庙,其中的宫殿和房屋一般都很宽敞,有些甚至如同今天的豪门大宅一样,采取多进式院落的形式。图2.34所示是1976年在扶风发掘的一组建筑,数个庭院沿中轴线分布,门口有一道影壁,和后世宫殿、豪宅和庙宇布局大体相当。这座建筑屋顶覆盖茅草,但同时期的其他建筑已经使用陶瓦。

图2.34 陕西凤雏宫殿复原图,长45米,宽32.5米,西周
周王朝礼制性建筑中很重要的还有明堂,明堂是一个象征土地的多间式方形建筑,周围环绕一圈象征着上天的场地。早期文献详尽但相互矛盾地记录了明堂。周代明堂遗迹并未发现,但是西汉时期曾经试图复原,图2.35就是汉代明堂的复原图。[16]同样,《左传》也记录了建立在夯土台基上的木构高台,常常被诸侯们用作要塞、宴饮,或者仅仅是瞭望的场所。

图2.35 明堂复原图,西汉
青铜礼器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商代铜器传统,最主要的变化发生在铭文上。商代铜器铭文仅仅简单地表明对祖先亡灵的供奉,到了西周,铭文的宗教功能减弱,转而成为沟通家族祖先和记录在世贵族取得的荣耀和成就的方式,用来彰显权力和地位。因此,铭文有时长达数百个字,本身就构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献。明尼阿波利斯的皮尔斯伯里收藏(Pillsbury Collection)中的一件西周铜簋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维王伐 鱼,从伐淖黑。至燎于宗周,赐郭伯捱贝十朋。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考宝尊彝,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17]
鱼,从伐淖黑。至燎于宗周,赐郭伯捱贝十朋。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考宝尊彝,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17]
商周革命之后,商代青铜器风格延续长达一个世纪(图2.36),特别是在现今河南北部,即周代征服者用来安置商遗民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流行的商式铜器式样,如觚、爵、觥和卣逐渐消失,而浅腹盘变得更常见,也许,这反映了饮酒习俗的渐衰和周王室影响的逐渐加强。鼎在这个时候定型为广口、浅腹的三足器形态。

图2.36 令方彝,高35.6厘米,西周,现藏于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
与晚商铜器相比,西周铜器看起来制作粗糙,仅就形式而言,显得下垂而沉重,扉棱粗壮并伴有牙状突出,中国的古董鉴赏家们对西周铜器的重视不在其形式,而在铭文。商代装饰中占主导地位的动物形纹饰在西周铜器中已经分解成为条带、波折纹和鳞纹(图2.37和图2.38)。饕餮、龙和其他神异动物的消失暗示着统治阶级宗教信仰的变化,周人不再将鸟类等动物看成具有保护功能的部族族徽,而是应该被后羿等人性化英雄征服的敌人。后羿射落了灼烤大地的十个赤乌中的九个。尽管如此,青铜礼器仍然偏好使用动物形态,在缺乏西周时期雕塑的情况下,它们仍足以说明当时对质感的认知。周代早期的精美铜器可以以弗利尔美术馆的一对铜虎为代表。铜虎体形浑圆,充满力量,表面通体装饰着与它所从属的礼器上一样的纹饰,这种纹饰的韵律动感极大地加强了动物形态的活力(图2.39)。

图2.37 青铜簋,高30.4厘米,铭文断年为公元前825年,西周,布伦戴奇收藏,现藏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图2.38 青铜壶,高45.5厘米,西周,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图2.39 青铜虎,长75.2厘米,西周,现藏于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
玉器
周代早期和中期玉器的可信的考古学材料非常稀少,但近年来的新发现迭出不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考古学家在河南浚县辛村发现一批周代玉器,其中大部分在扁平表面上浅线浮雕而成,只是商代玉器的粗糙翻版。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证实,玉器工业在西周早期开始衰败。但目前科学发掘出土的周代玉器只是冰山一角。不那么乐观的出土情况,与玉器工艺传统守旧乏变的传统形式结合在一起,导致玉器在西周被埋藏时已经被视为古董,因此,对单件玉器的准确断年尤为困难。
我们注意到四川三星堆墓葬坑中出土的礼玉。早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纪早期,巴蜀首都如果的确存在的话,业已迁移到成都西郊的金沙。遗址上仍在进行的工作揭示出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金器和玉器,不过玉料本身乏善可陈。
值得庆幸的是,周代礼制和葬仪用玉的意义和功能比较清楚。根据《周礼》,一定形状的玉器与特定的社会阶层对应(图2.40),[18]“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有的玉器则用来彰显王室权威,比如牙璋用来调遣王室军队,一剖为二的虎符涉及军事机密,琰圭保护官方使节。[19]同样,特定的玉器被用来保护墓葬中的尸体,有些玉器甚至在发掘之时还保留在原始位置上。一般而言,尸体仰身埋葬(有别于商代葬俗),胸部放置玉璧象征天,背部放置玉琮象征地。东侧是圭,西侧是琥,北部脚侧是璜,而南部头侧则是璋。尸体的七窍都被玉塞封住。而一个扁平的玉片常常被做成蝉形,名为“玉琀”,放置在死者嘴里。这样,尸体就可以免受任何侵害,同时,也将任何不祥之气封锁于体内。贯穿整个周代,放置在死者尸体上的玉片和装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西汉时达到巅峰,当时的皇帝和帝室成员埋葬时都身穿完整的玉衣,我们将在第四章详述。

图2.40 礼玉和葬玉
除了丧葬用玉,周代早期的玉工和在商代时一样,也刻制各种各样的佩饰和装饰品,但是东周时期的治玉变得更为精美和漂亮,我们将在第三章中予以详细讨论。
陶瓷
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比,西周和东周早期的陶器大多比较质朴,乏善可陈。最精美的陶器多是铜器的粗糙仿制,尽管形态上大体相似,纹饰却仅有牛头或饕餮面具得以保留。虽然我们也发现了少量红陶器,但西周陶器的主体由粗糙的灰陶构成。最常见的陶器形态是圜底广口陶罐,器物表面布满绳纹。
近年的发现显示,在大量的无釉陶器之外,一种更复杂的陶瓷艺术已形成暗流。中文将陶土器区分为两类,陶和瓷。如果我们不将瓷器的定义限定在成熟形态的话,某些西周时代的陶器就可以算成瓷器了。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1972年河南洛阳北窑村一座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带釉陶罐(图2.41)。西安附近的普渡村的年代在穆王时期的墓葬中也包含了类似器物。它们一般装饰水平状条带纹,器表覆盖了薄薄一层蓝绿釉质,与商代釉陶的黑釉和黄釉截然不同。河南、江苏和安徽墓葬中出土了釉陶器,根据同出青铜器铭文可以推断出自公元前11—前10世纪。也许,它们就是后世青瓷的先声。

图2.41 黄褐釉陶罐,高27.5厘米,出自河南洛阳北窑村,西周
早期中国书写艺术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保存至今的早期中国的书写包括迄今尚未破译的可能表示数字的符号,某些实用器物的族属、制作者和使用者的名称,但它们很难被冠以“书法”的称呼。这些符号并未连缀成句。被后世金石学家称为“甲骨文”的铭刻在卜骨上的陈述和问句,以及更正式的、铸造在青铜器上的“古文”是句法结构的最早证据,年代在青铜时代早期。
正如我们所知,西周青铜铭文趋长,其书风为“大篆书”。最著名的一例是唐代发现的石鼓铭文,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镌刻。图2.42所示就是其中之一。适于篆印的大篆体保存至今,被学人誉为极富古韵的书体。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纪,大篆书被改进成小篆书(图2.43),后者在秦始皇帝统治期间(公元前246—前210年在位)成为官方书体。秦始皇帝统一了分裂的战国诸雄,对帝国生产和使用的所有物品都实施了统一化管理。

图2.42 (左)大篆书,石鼓文,西周晚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右)拓片,现藏于日本

图2.43 小篆书,泰山刻石拓片,秦(公元前3世纪)
由于篆书长期保存在青铜器、印鉴以及石鼓上,人们猜测篆书可能是此时使用最为广泛的书体。但是,现在已经明确的是,当时最主要的书写是用笔墨以更为自由的书风书写在木牍和竹简上。虽然最早的有字简牍的年代在公元前6世纪,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更早的时代,笔墨书写就用于书信和敕令、计数和账目等实用目的。汉代出现了记账和官方使用的隶书(图2.44)。隶书见于众多汉代石刻和拓片上,强健而有波磔,水平笔画常得到强调,而显得夸张。

图2.44 隶书,泰山刻石拓片,汉
汉以前的书写能被称为“书法”吗?书与礼、乐、射、御、数一起合称“六艺”,根据儒家传统,每个君子都要力求掌握。显然,书写娴熟是受人推崇的。但是,汉以前没有任何文献将书法视为艺术形式,或者讨论其美学价值。因此,我们仅在以后的章节才讨论作为高雅艺术的书法。
[1] L. Carrington Goodrich, “Archaeology in China: The First Decad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no.1(1957): 5–15.
[2] 对于夏问题和商文化的综述,参见Robert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 vol.1(Washington, D.C., and Cambridge, Mass., 1987)。
[3] Jessica Rawso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Designs in Jades and Bronzes”,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hinese Art History, 1991, Proceedings: Antiquities, Part I(Taipei, 1992), pp.73–105.
[4] Robert W. Bagley, “Panlo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bei”, Artibus Asiae 39, no.¾(1977): 165–219.
[5] Robert W. Bagley, “An Early Bronze Age Tomb in Jiangxi Province”, Orientations 24, no.7(July 1993): 20–36.
[6] Robert W. Bagley, ed., 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Seattle and Priceton, 2001).
[7] “壳在甲申日占卜:妇好要生孩子了,是好是坏?三十一天后的甲寅日,验证:妇好生下孩子了,不好,是个女儿。”吉德炜(David Keightley)翻译。
[8] Shelagh Vainker,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London, 1991), p.27.
[9] S. Howard Hansford, The Seligman Collection of Oriental Art, vol.1(London, 1957), p.9.
[10] Max Loehr,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Ⅶ(1953): 42–48.
[11] Kwang-chi. 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p.65.
[12] 水野清一,《殷周青銅器と玉》(东京,1959),第9页。
[13] “设计师按照每边九里的方形式样设计国都,每边开三个门和三条道路。这样,国都之中就有九条横向大道和九条纵向大道,每条大道的宽度允许九辆马车并行。祖庙在左侧,社土祭坛在右侧;前面是朝堂,后面是集市。”索柏(Alexander Soper)译,据E. Biot, Le Tcheou-li, ou Rites de Tcheou(Paris, 1851)。
[14] 对扶风和其他东周窖藏的讨论,铜器纹饰表现的西周信仰和礼制的变迁的清晰说明,参见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1000–250 B. 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Los Angeles, 2006), pp.30–41。窖藏铜器组合并不完整,可能表明器群主人携带了最珍贵的器物东迁。
[15] “继承先妣先祖,筑成房屋百堵。向西向南开户。全家来此居住,说说笑笑相处。绑扎停停当当,敲打叮叮当当,风雨都能挡住,雀鼠不能穿破,君子安居之所。象人立那么端正,象箭头那样有棱,宏壮象大鸟举翅,彩檐象雉鸡飞升。君子举足登临。前庭平平正正,楹柱高大齐整。亮处十分轩敞,深处也是宽明。君子得到安宁。下有莞席上有竹覃,舒舒服服就寝。君子睡罢起身,叫卜人推详梦境。”余冠英译,选自《诗经选译》(北京,1985年),第119—120页。
[16] 众多学者曾经讨论明堂建筑,尤其是王莽时期(9—23年)宣称复兴儒学,仿周制兴建的明堂。参见Nancy Steinhart,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New York, 1986), pp.70–77,以及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Stanford, 1995)。
[17] “王起兵攻击 鱼,顺道攻击淖黑。王返回后在宗周举行燎祭仪式,赏赐我(郭伯)十朋贝。我冒昧颂扬王的美德,为我去世的父亲制作了这件簋。希望我的子子孙孙永远珍惜和使用它。”苏立文译,据Bernhard Karlgren, 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Bronzes in the Alfred F. Pillsbury Collection(Minneapolis, 1952), p.105。最后一句表明这些器物是用器而非葬器。
鱼,顺道攻击淖黑。王返回后在宗周举行燎祭仪式,赏赐我(郭伯)十朋贝。我冒昧颂扬王的美德,为我去世的父亲制作了这件簋。希望我的子子孙孙永远珍惜和使用它。”苏立文译,据Bernhard Karlgren, 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Bronzes in the Alfred F. Pillsbury Collection(Minneapolis, 1952), p.105。最后一句表明这些器物是用器而非葬器。
[18] 近年发现揭示,《周礼》无法复原周代之前玉器的象征性用法。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已经表明璧和琮虽广泛见于东海岸地区,但并不同出。例如,瑶山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现了众多玉琮,但不见玉璧。《周礼》的重要性表现在它所定义的某些玉器的礼制和象征性意义在后世朝代得到严格的遵循。
[19] 葬玉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参见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section 24, pp.314–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