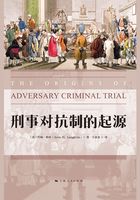
导言
所谓的对抗制,即律师主导的刑事审判,是普通法国家刑事司法的典型特征,它包括英国和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的其他国家,如美国等。英美国家的刑事司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区别在于,不仅是对抗式诉讼允许控辩双方的律师参与审判,欧洲大陆法系的刑事程序也同样允许。英美法系对抗式审判的显著特点是:我们将收集、选择、出示和调查证据的责任移交给维护各自利益的双方律师。传统上讲,由法官监督指导下的陪审团是我们的审判法庭,但陪审团自己并不进行证据调查。在双方律师的相互争斗中,法庭对他们提供的证据进行甄选、判断,然后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判。
相比之下,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收集证据的职责是由法官或类似法官的调查人员、负责查明真相的其他公职人员等来承担。刑事调查被认为是(国家的)公共职能,而不是私人职能。在审判中,主审法官负责询问证人在内的证据调查。控、辩双方的律师发挥从属作用,主要是建议调查的内容,有时还补充法庭对证人的询问。
两大法系关于刑事调查组织和刑事审判组织的这种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刑事审判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过去事实的裁判。正如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所言:“已有的经验充分证明,当我们的诉讼有一百多件源于事实争议,仅有一件是源于法律争议的。”(1)比如,交通信号灯是红灯还是绿灯?是被告还是其他人开的枪,是被告还是其他人拿走了钻石?案件事实确定了,法律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对抗式刑事诉讼有两个显著的缺陷,我在本书下文中也会提到,即争斗效应和财富效应。关于争斗效应,我指的是对抗制中有害于真相的因素。在英美审判中,每个对手的工作都是为了赢得法庭上的斗争。赢得诉讼经常需要采用扭曲或阻碍真相的策略。例如,隐瞒相关证人、隐瞒有利于对方的信息、教唆证人以影响其庭上证词、滥用交叉询问的权利,等等。关于财富效应,我是指对抗程序赋予有钱人的巨大优势:他们能聘请技艺高明的辩护律师,能支付得起由当事人主导的事实调查费用。而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的被追诉人,由于他们大多数是贫穷或者接近贫穷的,因此财富效应是对抗制刑事审判程序中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缺陷。
本书探讨了对抗制刑事审判制度的历史渊源。律师主导的刑事审判在英国法制史上出现得较晚,而且发展迅速。直到16世纪90年代,辩护律师在所有严重犯罪案件中仍然被禁止,其中包括叛逆罪和其他重罪。控方律师被允许参与审判,但除了在叛逆罪案件中国王一直由律师代表参加,其他案件中实际上从未聘用控方律师(参加)。一个世纪后,即到17世纪90年代,对抗制刑事审判的主要特征在严重犯罪案件中已经形成。
一、内容概要
从没有律师参与的刑事审判到律师主导的刑事审判,我们的研究起点是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即所谓的早期近代社会,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使我们对出现在中世纪末期的审判程序有基本的理解。本书第一章阐释了相对松散的控辩双方“争吵式”刑事审判。这种审判的主要目的是给被告人一个机会,即亲自对指控罪名及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进行辩解,我把这种诉讼的类型称为“被告人陈述式”审判。根据这种审判的理念,在被告和法庭之间,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空间。实际上也确是如此:对于事实问题,辩护律师事实上是被禁止参与的。该规则的逻辑是迫使被告在为自己的辩解中能够陈述事实。出台禁止辩护律师的规则,一定程度上是担心辩方律师会干涉法庭从被告人那里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后来的实践表明,这种担心确有必要。
16世纪和17世纪刑事诉讼的运作中,不仅没有律师,而且没有公诉人和警察。然而,通过所谓的“玛丽式审前程序”确能加强私人的控诉,该调查程序是由非专业的治安法官(2)(又称“和平法官”或“太平绅士”)主导进行的。第一章阐释了玛丽式审前程序如何加强这种没有律师参与的刑事审判程序,以及如何对被告的辩解或陈述施加压力的。
在18世纪,人们仍自信地宣称,禁止辩护律师(参与审判)有利于被告。如果被错误指控,被告可以通过其简单且无辜的反应澄清自己的清白;如果被告有罪,其反应将有利于揭露真相,而别人代替其作虚假辩护,则不利于发现真相。(3)
“禁止辩护律师参与审判有助于发现事实真相”的观念,在斯图亚特王朝晚期的一系列著名叛逆罪中受到质疑,尤其在天主教阴谋案、拉伊住宅阴谋案以及血腥巡回审判案中。第二章回顾了这些恶意的起诉,他们用伪证将无辜者(包括政治贵族)定罪并纷纷处决。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后,对这种司法不公的深恶痛绝催生了1696年的《叛逆罪审判法》。该法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核心是允许叛逆罪的被告在审判中以及审前获得律师帮助。第二章还对法案的主要规定进行了分析,尤其关注1696年的改革者们为何将刚刚萌芽的对抗式程序局限于少见且不典型的叛逆罪。(这是因为)法案的设计者认为,对叛逆罪的指控是问题丛生的。在普通犯罪的审判中,国王不存在重要利益,因而在实践中并无控诉律师出庭;而叛逆罪案件则不同:国王作为利害关系方主导对犯罪的指控,并始终有出庭律师为其效力。此外,由于法官们的职位仍受制于国王的好恶,因此他们不可能中立地对待叛逆罪的被告。1696年法案的解决办法就是,允许叛逆罪的被告获得维护其利益的帮手——辩护律师。
因此,设计这种对抗式刑事审判程序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专门适用于叛逆罪案件,旨在抵消这类指控给被告带来的风险。这种新的审判模式专门服务于被控叛逆、阴谋的达官贵人以及有钱人,其中大多数涉及王朝更迭以及宗教存废。对他们来说,支付律师费只是一个小问题(不用为支付律师费发愁)。直到后来,发生了当时他们无法预料的情形,对抗式程序才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普通重罪案件。这种程序原本是为了维护贵族利益,让他们免受叛逆罪的指控;后来,竟然用它来审理平民偷鸡摸狗或窃取商店物品的案件。第三章探讨了在18世纪30年代,法官取消了重罪案件对辩护律师的禁令,开始允许辩护律师参与审判,主要是允许被告在询问和交叉询问证人时获得律师的帮助。辩护律师成为对抗式刑事诉讼得以运行的实际承担者。律师开始逐渐主导重罪案件审判,到了18世纪后期,这种现象日益明显。
本书的主题是:法官允许辩护律师帮助重罪案件中的被告,是为了应对诉讼实践中发生的复杂变化,尤其是伦敦及其郊区的变化。第三章指出了三个要点:第一,在诉讼中,控方律师的使用率逐步增多,尤其是使用事务律师去调查或者处理某些刑事指控,同时也包括在诉讼中更多地聘用出庭律师。第二,根据当时的奖励制度,他们提供丰厚的报酬来鼓励对严重财产犯罪进行指控,这增加了证人作伪证的风险。第三,为了促使团伙犯罪中共犯提供证言而采用的污点证人制度,就是很大程度上导致证人伪证风险的刑事指控技术。
到了18世纪30年代,这些新型指控技术让法官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多数刑事审判已经不再像之前的“控辩争吵式”刑事审判了。特别在伦敦,当时的刑事指控正日益成为律师和职业捕贼人的业务范围,职业捕贼人获得奖赏的动机受到质疑。这些职业人士的强烈目的和动机,使法庭上的控方证据出现虚假的危险性不断增加。一方面是势单力薄而又无助的被告人,另一方面是职业化、准职业化且指控能力不断加强的控方。法官们为了平衡二者之间的失衡状态,允许辩护律师对控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
18世纪30年代的法官们重新借助辩护律师(参与审判)来平衡控辩双方的关系,正如国会在1696年《叛逆罪审判法》中所采用的方法。辩护律师可以在审判中帮助被告审查控方证据,揭露可能存在的伪证,特别是通过对控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的手段来实现。
在英格兰,用于调查犯罪的机构和其他资源长期不足。一直到城市工业化时代,英国都采用私诉制度,这种私诉制度和英国长期存在的业余治安法官制度及业余乡村警察制度相匹配。第三章着重介绍了这种早期审前制度的缺陷为何在正式审判中显得如此突出。法官们对审判程序的前述调整就是为了补救审前制度的这种缺陷。法官决定允许辩护律师以主导者的身份在对抗式刑事审判中出现,就是对审判制度的一个很大调整;其他的进步还包括刑事证据法的形成,这个问题将在第四章中进行讨论。虽然本书的中心是审判模式的演化,但是审判和审前的关系是始终关注的主题。审前制度直接决定并塑造了审判制度。如果英格兰政府能够直面问题,投入精力和资源,在审前阶段中解决刑事调查和指控的问题,那么18世纪的刑事审判也就不会向律师开放。对抗式审判便是法官在审判阶段对审前程序的回应。
在18世纪30年代,法官虽然允许辩护律师们参与重罪的审判,但是他们仍然被禁止向陪审团发表陈述。这个限制就使得辩护律师不能作开场陈述和结尾陈述,因此也使他们无法直接回应对被告的指控和不利证据。这种限制的目的是迫使被告对指控事实进行陈述,并继续充当法庭的信息来源。
除了允许重罪被告人拥有辩护律师外,法官还进一步努力,在正式审判阶段提供保障措施,减少审前阶段收集有罪证据给被告人带来不断增长的危险。刑事证据法(这种保障措施)便应运而生了。第四章主要追溯了这种新的法律部门在18世纪的产生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两项规则,即针对同伙供证的补强规则和排除审前嫌疑人口供的自白规则,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抵消新刑事指控方式所带来的危险,这与法官们允许辩护律师参与刑事审判的目的一样。虽然刑事证据法是司法的创造物,但由于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和审查——这原本专属于法官和陪审团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开放给了双方律师,证据法也因此被操控于律师之手。
关于对抗式刑事审判的发展和证据规则的形成,我阐述的主要依据是《老贝利法庭刑事庭审实录》和18世纪的其他分散的资料。对于初审法院发生的事情,这些《庭审实录》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但不完整的视角。这些资料最近几年才被法史学家们发现,在本书第四章中,我讨论了它们的价值和缺陷。
对抗式刑事审判如何取代旧式的“争吵式”审判?并且如此快速?通过允许辩护律师参与重罪审判的过程从而创制对抗式审判的法官,他们自己并没有法律革命的意识和意图。为了达到帮助被告对证人询问和交叉询问的有限目的,法官允许辩护律师参与审判。法官认为律师(的行为)仅仅是对被告自行辩护的一种补充,因而仍然禁止辩护律师向陪审团陈述事实或解释证据。因此,法官认为,他们应该允许辩护律师参与审判,但继续保留“被告人陈述”的审判模式。第五章解释了法官们的这种想法为什么未能实现。辩护律师的参与使刑事审判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突破了原先集中在被告人身上的两种角色:辩解和陈述事实。通过阐释和加强控方的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出庭律师将被告人从“法庭信息源”的角色中解脱出来。这种变化催生了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我着重强调对抗制的发展动力改变了整个刑事审判的理论。旧式的“争吵式”审判给予被告一个机会,使之能够对指控的内容和证据作出回应;而对抗式刑事审判则是让辩护律师代替被告审查控方的证据。
随着律师逐渐主导了审判活动,他们削弱了法官和被告人在庭审中的作用。法国人科图作为一位观察者,在1820年写道:在询问和交叉询问证人的过程中,英格兰的法官“对这一过程显得漠不关己”;被告人极少亲自辩护,以至于“即使用根杆撑着他的帽子作为他的替身出庭,也无碍于事”。(4)第五章主要探讨了这种确立已久却日渐没落的英格兰司法职能理念是如何进一步促进对抗式程序的发展的。英格兰法官的责任就是将案件提交给陪审团处理。法官们收到的证据一直是由他人提交的。法官从来不负责收集证据,他们缺乏资源、权力和责任感去调查他所审理的案件。对他们提交给陪审团处理案件的真实性而言,法官与其说是案件的裁判者,不如说只是管理者而已,所以在不断形成的对抗较量而同时有害于真相的审判制度中,他们很容易适应管理者的角色。
第五章进一步指出,对抗式刑事审判的基础虽不牢固,但未受到挑战的关键原因是:18世纪下半叶,人们对死刑制度的日益反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英格兰刑法滥用死刑的观念得到普遍传播,因此刑事审判的主要作用是在“血腥法典”威胁下的大批死囚中筛选出真正的罪该处决者。如果我们要理解政府当局为什么没有干预这种有害于真相的对抗式刑事审判,上述背景将会有帮助:更多的真相,意味着更多的死刑,因此这种审判程序在这个时期更加巩固了。此后,在19世纪中叶,英格兰正视其过度依赖死刑而引发的问题,大量废除了死刑的适用,仅保留在很少一些犯罪中。“血腥法典”虽然被废除了,但是它遗留下来的对抗制审判却在损害真相的刑事诉讼中流传下来。
作为总结,本书对英格兰未选择的道路(欧陆模式)进行简单介绍,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对欧陆刑事诉讼中更能发现真相的审判模式却不屑一顾。
二、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
16、17世纪没有律师参加的英格兰刑事司法,不仅和18世纪形成的对抗制刑事司法形成强烈对比,而且与允许律师参加的英格兰民事司法形成鲜明对比。一定程度上,对抗制刑事诉讼的形成,可认为是吸收了民事诉讼中已经存在的对抗制模式。此后,英格兰的法律制度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对抗制程序方面,都展示出高度的相似性。
在英格兰法律制度中,民事司法处于首要地位,刑事司法就成了民事司法的附属物。直到近来,英格兰才出现专门的刑事法官和刑事法院。在各地的巡回法院和伦敦老贝利法院主持审判的法官,都是从管辖民事案件的三个中央法院临时调派而来的,每年几周从事刑事审判的工作。
从16世纪到17世纪出版了成百上千卷的法律报告,这些法律报告主要记载民事案件,这说明了民事司法的主导地位。尽管存在大量的民事法律报告,我们都对19世纪之前的民事审判行为知之甚少。法律报告只告诉我们关于双方的诉讼请求、法律问题的裁决及初审法院裁决后的上诉审查,但没有告诉我们民事审判实际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虽然民事审判在英格兰居于中心地位,但它对刑事对抗制审判模式形成的影响仍然有限。由于刑事司法是以审判为中心的,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法律制度就是要把大部分刑事案件在正式审判中解决,而英格兰的民事司法则尽量避免正式审判。在民事方面,普通法院的中心功能在争点整理程序中,这个程序主要把那些不经正式审判即可解决的法律问题和提交给陪审团裁决的事实问题分别挑选出来。即使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其审判通常也会在范围上比刑事审判受到更多的限制。民事争点整理程序尽量减少提交给陪审团的事项,在某些情况下从大量交易中分离出纯粹的事实问题以及通过筛选减少证据。
导致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审判的范围缩小和效率急剧下降的另一个因素是禁止当事人在法庭上作证。当事人由于利益关系而被剥夺了作证的资格,换言之,对于存在争议的事项,他们被视为不具有证人资格。显然,这是为了避免他们禁不住作伪证的诱惑,也是防止法庭接受虚假的证据。剥夺民事当事人的证人资格,巩固了英格兰私法中几个世纪以来的努力,即鼓励交易各方通过书面文件的形式实施重大交易,尤其是官方封印后的书面文件和法庭记录的供述。(5)这些文件所具有的决定性效力,往往能够不经诉讼就能避免或解决纠纷。
虽然因利益关系而剥夺证人资格的规则也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但收效甚微,因为刑事诉讼中的原告被认为是国王而不是公诉人,(6)允许被害人宣誓作证,被告人只能未经宣誓而陈述。比较而言,民事诉讼禁止当事人作证,便失去了民事案件中最有价值的潜在证人,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就只限于他们律师的陈述。
因此,在对抗制刑事审判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两者关系的许多细节是我们不知道的,但这并不障碍我们对其基本情况的把握。对抗制模式来源于民事诉讼,当事人通常为了维护各自利益而去聘请律师,由律师操控整个诉讼的进程。当对抗制模式被移到刑事领域中,对抗制模式的重要价值就显著提升了。在一般的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势不两立,而且证据的数量也要比大多数民事审判中多;在民事审判中,争点整理程序和官方书证优先规则缩小了留待解决(陪审团裁决的)的事实范围,而最有可能的事实证人即当事人,却被剥夺作证的资格。
对抗制刑事审判模式的形成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司法裁判的正确性取决于双方提交的证据,而将收集、提交证据的工作赋予存在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这是一种不利于发现事实真相的程序,如何论证它的正当性呢?这个问题迄今在英美法传统中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民事纠纷起源于私人利益,因此法律无须考虑公共利益而放心地鼓励当事人和解。相比而言,刑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因此在欧陆法律传统中,就是把重大犯罪案件的调查和裁判工作视为一种公共职责赋予中立的专业人士,因此由他们动用国家资源,是因为这既可以打击犯罪,又承担保护被告的功能。对抗制刑事审判在英格兰逐步形成的这段传奇,是法理学的议题,也是法律史的主题,因为它描述了在刑事诉讼理论根基尚不坚实的情况下,如何调整我们生活的一段历程。
(1) 3 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330(Oxford 1765—1969)(4 vols.)[hereafter Blackstone,Commentaries].布莱克斯通所论系指民事纠纷,但此论至少也适用于刑事案件。
(2) 该词语的英文为“magistrate”或“the justice of peace(JP)”,在现代英美国家主要指一种较低级别的司法官员,如在英国可对刑事案件享有简易裁判权,在美国州法院可对民事或刑事案件行使有限管辖权,同时也指美国联邦法院的基层司法官;因此,一般译作“治安法官”。但在“刑事对抗制”尚未形成的时期,该类人员仅指由国王任命的地方治安官,其职能是犯罪调查和帮助被害人提起控诉,不仅不具有现代社会的裁判功能,而且其调查也是不中立的;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并非“法官”,只是“治安官”而已。然而,为了避免两种不同称谓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本书统一译作“治安法官”。——译注
(3) William Hawkins,A Treatise of the Pleas of the Crown 400(London 1716,1721)(2 vols.)[hereafter Hawkins,PC].
(4) Charles Cottu,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in England 88,105(London 1822),translation De l'ad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 in criminelle en Angleterre(Paris 1820)[hereafter Cottu,Administration].
(5) 拙文曾专予论述,inJohnH.Langbein,“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Law of Evidence:A View from the Ryder Sources,” 96 Columbia L.Rev.1168(1996)[hereafter Langbein,“Evidence”]。
(6) 详细内容,see 2 Hawkins,PC 433—434;又参见第一章注释(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