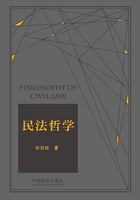
第五节 民法的确定对象
民法的确定针对主体和客体两者。容分述之。
一、民法对主体的确定
民法对主体的确定分为赋予人格和确定身份两个途径。容分述之。
(一)人格之赋予
1.人格的定义。人格即国家赋予自然人、社会组织或目的性财产充当民事主体的资格。尽管都是国家赋予的,但古今人格很不同。在罗马法中,人格制度是生物人与法律人之间的分拣机,只有同时具备自由、市民、家父、名誉、宗教等身份的生物人才能成为法律人,拥有人格,因此,当时的人格是制造不平等的工具。
在现代,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的民法继续使用人格的概念,如葡萄牙、魁北克和中国澳门地区[140]。人格在这些地方与权利能力的概念并用,前者是每个国民都有的、平等的、不可剥夺的,后者也是每个国民都有的,但由于可以被剥夺或限制,受剥夺或限制者的权利能力就不可能与未受此等剥夺或限制者的权利能力相同。所以,人格在现代具有了与其古代对应物完全不同的形象,成了平等的象征。
承受人格之授予的民事主体有自然人和法人。由于人格为自然人社会化生存的必要,所以从他们出生时起法律自动授予他们人格。法人没有“出生”,通过国家的核准登记程序就是它们的“出生”,国家在它们完成设立程序之时授予其人格。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合伙企业、企业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等非法人团体,对外签订合同、参与民事活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法律也授予它们一定的人格,承认它们属于民事主体。
人们经常说国家是特殊的民事主体,这等于说国家授予自身人格,这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危险的,因此,国家应设立一些独立于自己人格的机构从事民事活动,以避免这样的不合逻辑和矛盾。代表国家进行民事活动的主要是国库,我认为把国库说成民事主体比说国家是特殊的民事主体要科学。
2.人格的性质。(1)由于人格是国家授予的,这一概念表达的是纵向关系,因此,人格是民法的确定事项而非调整事项;(2)人格属于基础权利,这是与具体权利相对立的概念,也就是作为行使权利之条件的权利。基础权利和具体权利的二分来自康德的天赋权利与获得的权利的两分法,但天赋权利显然不符合人格的纵向赋予性质,所以我将之改成基础权利。那么,区别基础权利与具体权利有何区别呢?区别在于前者是不可放弃、不可转让、不可交易、不因时效消灭的,而后者可以。[141]
3.相关概念。(1)权利能力。与人格相似的概念有权利能力,它指人适合于充当权利和义务的拥有者的状态。除少数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同时规定人格和权利能力外,多数国家的民法典只规定权利能力,把它当作人格的同义词,我国就是这样的。所以,上面关于人格的说明,都可适用于这些国家的权利能力制度。不过,权利能力的一元制留下了缺乏平等标示的缺憾,尽管人们尝试以“权利能力人人平等”的口号来弥补,但失权制度——剥夺和限制权利能力制度——的存在明确证明了这一口号的虚假性。(2)主体资格(Soggettività)。许多学者认为主体资格与权利能力同义,也有学者把权利能力看作像人格一样不可剥夺或限制,但认为可对主体资格施加这样的剥夺和限制。[142](3)人格权。人格权是自然人、法人对其自身精神要素享有的权利。自然人的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是这两种民事主体拥有的基本人格权。人格与人格权不同。人格本身也是一种权利,是一种前提性的权利,其他权利都要以它为依据取得,所以是派生的权利,人格权即为这些派生的权利的一种。人格是国家赋予的资格,表现了国家与民事主体之间的纵向关系;而人格权主要体现了民事主体之间自由空间的划分,属于横向关系。因此,在阿根廷西班牙语中,把前者叫作derecho personale或personalidad,把后者叫作Derecho personalismo,以图区别两者。
4.人格的财产基础问题。人格与财产两个要素的关系是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在国内,梁慧星教授提出了“穷汉无人格说”[143],大意是没有财产的人没有法律人格;在国外,法国学者夏尔·奥布里和夏尔·劳提出了“财团是人格的流露”(le patrimoine est une émanation de la personnalité)的反向理论。[144]前者认为积极财产是法律人格的基础;后者认为包括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的财团是法律人格的基础。两者有所不同,共性是把民事主体看作单纯的财产活动的从事者,代表了物文主义的民法观,是错误的。
“穷汉无人格说”的错误首先在于不适用于自然人,如《德国民法典》第1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该条中的“权利能力”就是人格。第1条告诉我们此等人格由自然人当然获得,并未附加具有一定财产的条件。如果附加这样的条件,会破坏平等原则,造成穷人无人格,富人有人格,在富人中,财产多的人人格大,财产少的人人格小的不幸局面。
“穷汉无人格说”中的“汉”字就说明持论者的考虑范围没有超出自然人,但“穷汉无人格说”适用于企业法人却是可行的,因为这类法人有最低资本额要求。就企业法人的设立而言,确实是无财产即无人格,但它们一经设立,也不能对它们适用“财产多者人格大”的衍生命题。而且对于事业法人,由于无设立最低资本额的要求,“穷汉无人格说”不能适用。
“财团是人格的流露说”的错误在于把人理解成了单纯的经济动物,同时把民法理解成了单纯的财产法。它与“穷汉无人格说”的关系依财团中积极财产与消极财产的比例不同而不同。当积极财产大于消极财产时,两种物文主义观点形成共振;当消极财产大于积极财产或为零时,法国人的上述学说可转化为与“穷汉无人格说”对立的命题——“无财产亦有人格”。一种理论具有如此对立的解释空间,这本身就说明它极为糟糕。
(二)身份之确定
1.身份的定义。身份是影响主体人格和其他权利或客体的移转自由度的立法者安排。身份是一个兼用于主体和客体的概念。就主体的身份而言,它具有对偶性和分配性,换言之,身份总是成对地设置的,其中一个给主体带来利益,谓之正身份;另一个给主体带来不利益,谓之负身份,立法者正是通过确定这正负两种因素的归属来实现身份的分配性的。因此,身份对人格的影响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起前种作用的身份如国民,反之,起后种作用的身份就是外国人了。在所有的国家,外国人在民事方面可以受到合法的歧视,因为民法的事理之性质还是一国国民的法,尚不存在一种以所有国家的国民为主体的民法。
2.主体的身份的功能。主体的身份是立法者在主体开展民事活动前对他们的定位,以实现社会组织。自由人与奴隶、市民与外国人、家父与家子是三对古老的身份。前两者关系到社会的宏观组织,表征阶级关系和内外关系,后者关系到社会的微观组织,表征家庭关系。两类身份的存在表明了身份一词含义的混杂:公法因素和私法因素兼有,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兼有。到了近代,自由身份随奴隶制的消灭而不具有法律意义;市民的身份随着部门法运动的完成逐渐主要成为国籍法的内容,只有家族的身份保留下来并经受了平等化改造,于是,家族的身份一度成为近代民法中唯一的一种身份,潘德克吞学者谈论的作为民法对象之一的身份关系就是家庭关系。实际上,在家庭法之外的民法内容中也存在身份,如未成年人的身份和消费者的身份,这两种身份的对立身份是成年人身份和生产者身份,它们都是强者的身份,与它们对立的都是弱者的身份。对于未成年人,立法者赋予他们“不倒翁”地位,交易对他们有利则有效,不利则无效,对于消费者也是如此,在生产者起草的合同条款可能存在多种解释时,做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总之,在当代,亲属法外的身份正日益频繁地成为立法者运用的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3.身份的分类。《法国民法典》的奠定者之一让·多马(Jean Domat,1625—1696)认为,身份有自然资格(Qualità)与民事资格之分。前者如性别、出生、年龄、家父或家子的地位、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地位等;后者如拥有自由权的状态、受奴役的状态、诸种社会的和职业的身份等级、臣民的地位、外国人的地位等。自然资格与私法有关;人为的或武断的资格与公法有关。[145]这样的技术选择把涉及人的人为资格的规范从自然的私法中排除出去,表达了对罗马法中公私混杂的身份制度安排的不满,把部门法运动推进到人法领域,导致现代民法中的身份基本上就是自然的资格。
(三)人格与身份的关系
关于这一问题,有如下学说:
1.身份为人格要素说。此说为优士丁尼罗马法所持。在这种法中,主要有自由人、市民、家族、名誉、宗教五种身份,自由人身份把生物人区分为自由人和奴隶;城邦的身份把生物人区分为市民、拉丁人、外邦人;家族的身份把人区分为家父和家子;名誉的身份区分好人和坏人;宗教的身份区分正教、正统与异教、异端。自由人身份和市民身份的丧失导致人格大减等,即主体资格的完全丧失;市民身份的丧失导致人格中减等,引起前市民被拟制为外邦人的后果,换言之,变成有限的权利能力拥有者;自权人被出养或养子被解放,造成人格小减等,它使过去的完全权利能力者变成无能力者或相反。名誉身份的减损导致公私法能力的降低;宗教身份的不正导致受排斥。由此可见,同时具有上述五种身份者,才具有人格,即完全的主体资格或法律能力。丧失五种身份的任意一种,都引起主体资格完全或部分丧失的结果。身份是人格的基础,人格的大小以身份是否完全为转移。[146]
2.同一说。著名德国法学家卡尔·萨洛莫·扎恰利亚就持此种观点,在其《法国民法教程》(1843年)中,他给身份下了这样的定义:“身份由一个生物人的人格构成。”“身份是未受民事死亡的人享有的权利能力。”[147]“身份是一种权利能力,个人依此可约束他人服从自己并约束自己服从他人。”[148]他的前一个定义声明了身份与人格的同一性,后一个定义声明了身份与其现代形式权利能力的同一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扎恰利亚理解的身份就是我们理解的人格。这种对身份的独特理解不具有普遍性,以之为基础建构的理论意义不大。
3.互相独立说。该说认为身份是在人格之外的对人格进行限定的因素。在这里,身份被理解为给主体带来高出或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待遇的地位,它与人格的关系是这样的:人格反映着普通的权利能力;而身份反映着权利能力的超出(特权)或受到贬损(受歧视)的状态。因此,“身份只是人格本身受到限制的领域”。[149]英国法学家维斯特雷克(John Westlake,1828—1913)把身份定义为:“人的特别的状况,由此法律把赋予普通公民的权力不赋予该人。”[150]这种学说实际上只有在把身份限缩为负身份时才能成立。
4.基本无关说。这是身份为人格要素说的改良版。认为人格与身份在现代法中已基本没有关系。这是我的私见。人格之所以与身份基本已无关,乃是因为在现代民法中它已经被虚化,变成一个人人都有的东西,外国人除外,其过去的功能被权利能力制度取代,因此,现代的身份只影响权利能力,不影响人格。由于权利能力是人格的现代衍生物,它仍然受到身份的影响,尤其受到公民身份的影响,因此说人格只是基本与身份无关。
二、民法对客体的确定
(一)物的身份概述
民法对客体的确定是通过赋予不同的物不同的身份来实现的。对于我国学者来说,物的身份是个崭新的表达,实际上,这个概念十分古老,因为它产生于530年的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第1卷第8题的标题“物的分类和身份”(de divisione rerum et qualitate),如题所示,其中规定了各种物的分类及其身份。该题昭示了物的分类与对它们的身份赋予的同步性,至少就人法物和神法物的分类而言,这本身就意味着不同处遇的身份划分,侵犯神法物中的神护物(城墙和城门等)的,要遭到死刑的制裁。而且,我国立法者一直利用物的身份划分来达到自己的调控目的。所以,从实质来看,我在这里提出来的物的身份的概念不过是对现实的总结。
像人的身份划分是对主体进行法律调整的前提一样,物的身份划分是对客体进行法律调整的前提。物的分类都具有身份划分的意义,如动产与不动产的身份划分就在于重要性不同,根据这种不同设定难易不同的移转程序。这样的身份划分太普通,这里只讲五种常见的物的身份划分。
(二)主要的物的身份
1.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人财产。这种物的身份划分从主体的角度看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私有制企业法人的区分。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了客体的身份划分与主体的身份划分之间的关联。在我国的历史上是优待国家财产,平待集体财产,歧视私人财产。当然,这种情况目前改善了不少。上述区别对待雄辩地说明了立法者作出身份划分并非出于体育锻炼的目的,而具有切实的分配目的。
2.国库财产与一般财产。前者受特殊保护,后者受普通保护。故优士丁尼《法学阶梯》2,6,9规定,国库的物不能以时效取得。这一法言说明优先保护国家财产的原则自古有之,并非苏联法的创造。优先权的赋予是任何立法者都可运用的调整手段。这种做法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利益与不利益的分配是否合理。
3.赃物和一般物。《十二表法》第八表第17条规定:盗窃物不能以时效取得。立法者把赃物设定为一种劣后的财产,以此打击盗窃犯罪。
4.奴隶劳动产品与自由劳动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出于维护人权的目的,前种产品遭到抵制,后种产品则可自由流通。
5.适用财产规则的物、适用责任规则的物和适用不可转让规则的物。耶鲁大学教授圭多·加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和道格拉斯·梅拉梅德(A.Douglas Melamed)律师提出了这种物的划分。适用于不同财产的规则的差异在于对财产的国家干预的程度和转让财产时的价格确定方式。财产规则是要求相对人获得财产必须向所有人偿付其主观评定的价值的规则,在财产规则运作的情形之下,国家只限于确定所有人对财产的初始所有权,对转让财产的价格不作干预。责任规则是在所有人不愿出售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偿付某些外在确定的价金(所谓的市场价)取得财产的规则,在责任规则运作的情形之下,国家不仅可以决定财产的归属,而且可以决定其价格。[151]适用财产规则的是重要的财产,适用责任规则的是相对次要的财产,不可转让规则涉及的可以是重要文物或武器毒品。所以,三种规则针对具有不同身份的物适用,以身份定保护的方法和保护力度。
(三)立法者对客体身份的赋予根据时代的条件而改变
自由的财货与财产是客体的一对重要的身份。在资源—环境状况较好的时期,立法者可以把更多的客体留在自由的财货的范畴中,在相反的条件下,就会把一些过去的自由的财货纳入财产的范畴。近年来,在美国发生了“自由的财货的财产化”运动,把一些过去看来不能被拥有的有体世界中的弥漫资源或公共物变成了财产。从1990年起,美国把空气本身作为国家财产,以控制污染性地使用空气。[152]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把海洋渔业资源确定为国民财产,捕鱼者必须购买配额。[153]这些都是立法者对客体身份的赋予根据时代的条件而改变的例子,从侧面印证了客体的身份关系的纵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