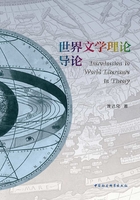
二 歌德与世界文学
(一)“我愈来愈深信……”
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一书,记录了歌德极为著名的一段话:
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创作出来。……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的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23]
在这里,歌德所讲的“诗”(poesie)很明显不是指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诗歌”(韵体或自由体诗歌),而是有其他的意思。[24]对于当时的德国浪漫主义者而言,“小说变成了一种延伸表达诗意的工具”[25]。当时的浪漫主义文论家席勒[26]也曾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即小说这种文类便是浪漫主义式的,而“浪漫的”(romantic)对席勒来说则意味着“诗意的”(poetic)。而且,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1795—1796)是引起这种小说观念变化的主要诱因。[27]此外,歌德还曾认为,“艺术家是天生的,诗就是灵感和天才”[28]。在另一些场合,他也反对将“诗”当成科学和艺术,而认为“它是在灵魂中孕育出来的,因而应当叫做天才”[29]。我们如果从这方面去理解的话,这里歌德所讲的“诗”便是指那种创作的灵感或天才,这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也正是通过这类灵感或天才的书写,才能打动我们共通的情感,即普遍的人性。当歌德说,“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的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这一句中的“每个人”有特别的所指,如上论及,尤其是针对那些年轻的爱国诗人、年轻的浪漫主义诗人。所以他说,“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歌德的话语中“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呢?自民族国家兴起至今,文学史家其实无时无刻不面对着解析这两者的辩证关系。中国学者会因为代表他们传统民族小说最高巅峰之一的《红楼梦》被外国的读者忽略无视,不被纳入“世界文学”的世界,而深感愤愤不平。仿佛“民族性”,唯有在他者的世界才能得以彰显,才能显示其价值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在歌德的世界文学图景里,“世界性”与“民族性”两者并非相互排斥的概念,而是合二为一的概念,民族文学必借世界文学而得到发扬光大,流播更远,影响更深,而世界文学脱离了民族文学则只会是无根的空谈。也即是,没有各国文学的相互叠加或相互映衬,也就没有所谓的世界文学。最后,歌德天真地期望:“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在这一段话里,歌德用了一种先知式的语气,来作一种乌托邦式展望。对他而言,“世界文学”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理想,一种将要完成的未来。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老年歌德的期望——希望借助这种世界文学的愿景,来推动各民族文学逐渐打破孤立的、割裂的状态,以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妨碍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现在我们可以说,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是一种合乎世界潮流的未来主义理想。歌德看到了一种在后拿破仑时代已经存在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如同商品,以原文或翻译的形式在跨越国界而流通。所以,“世界文学”又可以看作一个无形的平台,给各民族人民提供了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机会。歌德渴望推动世界文学的形成,在这样的过程中,德国文学将扮演着“光荣的”“美好的”角色。因而世界文学是彰显民族文学价值的场所。歌德希望在这种世界文学的世界中,德语文学逐渐壮大,如同其时的法国文学一样有重要的地位。
这个案例还证明了一个不平衡的世界体系的存在。歌德的世界文学与翻译的世界市场极为相关。这个市场是极为不平衡的,受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和文化政治所影响。以下几例便可为证。
(1)法语和英语是当时欧洲主要的通用语言。歌德正是通过法语和英语译本的中国/东方文学来了解中国/东方。
(2)1827年1月29日,歌德从魏玛公共图书馆借出汤姆斯(Peter P.Thoms)英译《花笺记》(Chinese Courtship)一书,1月31日、2月2日两天的日记里都记录了他在研读和讨论一首中国诗。[30]
(3)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一开始出版,是伪造为一位德国作者作品的法译本。后来由法语原著译为英文出版时,才开始改署伏尔泰的名字。这说明了世界市场对于他者文学的需求。
(4)易卜生的戏剧出版后,默默无闻,由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等人译成英文和法文后,才具备了其世界性。最后,还来到了五四时期的中国,在中国的影响可能超过了在其母国的影响。[31]
(5)歌德甚至说,当他读到法语译本的《浮士德》时,他甚至认为法语版更像是原版,而德语版反而像是翻译本。
…………
为了更好地解释翻译、世界文学和世界市场的关系,下文我们将以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为例,来作进一步的讨论。
(二)一个世界文学的案例
晚年歌德与年轻诗人爱克曼之间的关系颇不平常。换言之,爱克曼对歌德的感情,远不止是助手对作家、学生对老师或者学徒对大师的感情。他用一种崇高的感情,在书写中神圣化了歌德,同时也崇高化了自己。这种崇高化,经爱克曼个人发起,充满了其异乎寻常的情感。[32]
1823年5月,爱克曼带着他的诗集从德国北部城市汉诺威(Hanover)出发,步行了一周多,长途跋涉,忍受着炎热的天气和糟糕的路况,经哥廷根(Göttingen)、维拉塔尔(Werratal),到达了魏玛(Weimar),来到歌德家门口扣门拜谒。在出发之前,他已经寄了“一束诗”给歌德。他最初的想法是请歌德推荐,帮其在耶拿(Jena,德国中部城市)出版个人诗集。同时,他在诗集中,还加入了一篇评论文章《论诗:以歌德为例》(Beiträge zur Poesie,mit besonderer Hinweisung auf Goethe)。他没想到歌德那么爽快,初次见面便答应了,而且赞扬他的诗写得很好,“它本身就是极好的自我推荐”。歌德还给了他许多写作的建议,帮助他向出版社推荐诗集,还将他留下作为自己的秘书。1823年,74岁的歌德刚刚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失恋。当时他托了一位伯爵向一位刚满十八岁的乌克兰少女求婚,然而遭到对方家长的严词拒绝。他带着伤心的心情回到了魏玛,大病了一场。颓唐之中的歌德意识到了自己的年迈,他需要一位稍有才华的年轻人作为助手,来帮自己整理一生的文字事业。此时,31岁的诗人爱克曼寄来了表达对他崇拜的诗歌,而歌德将失恋的悲伤转化为工作的动力,设计了许多写作的计划。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使其更加疲惫不堪。所以,当爱克曼出现时,歌德便满怀感情地说:我想要你在魏玛留下来……爱克曼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要招聘一位助手帮助整理文稿的需求。就这样,爱克曼进入了歌德的文学圈,也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一个世界文学交流的平台,一个以歌德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的世界。此时年迈的歌德已经意识到,一方面,他高强度的、高效率的工作,需要一个助手相助;另一方面,他已经出版的书,需要整理、结集重版,爱克曼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是较为合适的人选。对照两人各自所记的日记和《歌德谈话录》便可以发现,此后九年(1823—1832),两人经常见面,有时朝夕相伴。
1832年歌德逝世,其生前曾立遗嘱请爱克曼编辑其一生的著作。爱克曼的后半生,一度贫病交加,无人照应,再后来陷入了长年的忧郁状态。自1823年始爱克曼花了十二年才将《歌德谈话录》(前两部)编成,于1835年年底1836年年初在当时欧洲的一个出版中心莱比锡出版。虽然此书的编辑在歌德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有许多日记的条目表明,歌德是知晓其记录的,许多内容也征得了歌德的肯定或受其监督完成。然而,我们还是不应否定爱克曼的高超才能,不能仅仅将其当成一部录音机——忠实地记录下真实,而无添加修饰的成分。
那么,对于爱克曼而言,歌德和这一部书,意味着什么?《歌德谈话录》的前两卷出版之后的另一个十二年,爱克曼与他人一起合作出版了该书的第三卷。前两卷呈现出了一个接近于真实的歌德的形象,后一卷不可信的地方不少。他在《歌德谈话录》的第三卷前序说:“我与他的关系是如此独特、如此亲近。这就像是学者与大师、儿子与父亲,浅陋的后学与博学鸿儒的关系。他将我带进了他自己的圈子,让我参与其中,让我得以享受到更高层次的身心愉悦。”[33]达姆罗什曾调侃地指出,在两人的合作关系中,歌德更像是一个年长的富有经验的恋人,而爱克曼则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而《谈话录》则像是用恋爱中少女的语气所记录下来的爱情的证明。[34]1820—1823年,爱克曼在他的日记和文章中处处透露出他心里只有歌德。“我只想着他,读书无味,无法思考。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身处何方,也无论我是在散步,还是在处理日常事务,他都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甚至夜里还进入了我的梦乡。”[35]这种爱,当时被他的未婚妻发现了。他的未婚妻有时会不耐烦地嘲讽他说“你那伟大的歌德”(your great Goethe)[36]。诗人爱克曼对歌德真是一种“爱人的态度”,但又是一种出于崇拜而超越一切标准的无限度的爱。进入歌德的圈子、进入世界文学的世界、其文学的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以及得到歌德惺惺相惜的爱护……这些对于像爱克曼这种出身贫穷、缺乏机会的文学青年来说,已是超乎其所希望,可以说是实现了其人生的主要目标了,而男女欢爱和婚姻反而退居其次了。[37]
《歌德谈话录》第三卷中,爱克曼的序言写得非常之抒情,远甚于前两卷。
我们谈着一些伟大的和美好的事物。他向我展示出他性格中最高贵的品质,他的精神点燃了我的精神。两人心心相印,他伸手到桌子这边来给我握。我就举起放在身旁的满满的一杯酒向他祝福,默然无语,只是我的眼光透过酒杯盯住他的眼睛。[38]
我们看到的《谈话录》中的歌德,虽是源自现实中的歌德,但更是爱克曼记忆中的歌德,一个被崇高化了的完美形象。这里的问题是:爱克曼的口述史与真实是否存在着差距?爱克曼过度的爱恋、明显的神圣化笔法,常常让人深深怀疑他所说的“这里所显现的是我的歌德”的真实性。其实,爱克曼在书中一再地使用了“我的歌德”这样的表述,这不正是说明了他的记录掺杂着某些主观性么?
爱克曼在《歌德谈话录》全书最后一段用一种极为伤感的笔调写了他在歌德逝世次日去瞻仰逝者遗容。
歌德仰面躺着,安详得如同睡熟了似的:高贵威严的面容神情坚毅,笼罩着深沉的宁静,饱满的额头似乎还在进行思考。我想得到他的一缕卷发,然而敬畏之情制止我去剪它。……我对遗体那天神一般的伟岸美丽惊叹不已。……面对这样一位完美、魁梧的男子我无比惊讶,一时间竟忘记了不朽的精神已经离开了他的躯体。我把手扪在他心口上,四处寂静无声,我转身往外走,以便让噙在眼里的泪水痛痛快快地流淌。[39]
在这一段里,爱克曼看到的不只是眼前歌德的遗体如生前一般完美而伟岸,还极为痛苦地看到人类世界刚刚逝去一个伟大的天才,一个如“天神”一样的、完美的、不朽的歌德。
《歌德谈话录》可看作一种“爱之纪念”:爱克曼用一种抒情的笔调写作,暗寓了对逝去爱人的怀念。[40]奥克森福德(John Oxenford,1812—1877)在将《谈话录》头两卷翻译成英语时便已发现,爱克曼使用了一种过度抒情的笔调。[41]奥克森福德在翻译过程中,被爱克曼的过度自恋和过度抒情折磨得厌烦不已,于是凡遇到令人生疑的、过度抒情的地方,都一律删去。这方面达姆罗什已指出了,“奥克森福德系统性地在全书范围内削减爱克曼的分量,大幅删减他的自叙、引论,在正文中则悄悄剔除了那些看起来太过情感外露或自我标榜的语汇。”[42]爱克曼像对待爱人一样对待歌德,然而这种爱又是超越了一般感情的崇拜之爱。他对歌德敬若神明,即便是在结婚之后也没有变化。爱克曼每天到歌德家中服务,像个神职人员每日到庙里,但歌德从来不曾邀请过其妻子,这多少让她有点失望。在歌德逝后,歌德对爱克曼仍有很大的影响,这具体反映在爱克曼的写作风格上。可以说,他几乎一直都将歌德当成一个完美的榜样,试图模仿歌德,向其学习。然而,多少年过去了,爱克曼生前逝后,都是声名寂寂。
达姆罗什对爱克曼的这种过度爱恋、过度神圣化的分析表明,在某些章节中,爱克曼自己化身为“圣母”,而“歌德”无疑便是一位救世的“圣子”。[43]他借助《歌德谈话录》创造了一个歌德,然而在多年后的翻译版本中,他的名字反而不存在了,此书有时变成了歌德著《与爱克曼的对话》。爱克曼是谁,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似乎并不重要。爱克曼的地位和成就,迄今还是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因为他活在歌德这尊光芒四射的神像的阴影中。他不可能被认为是一位创作者,一位写了《对话录》、描摹出了苏格拉底的柏拉图,而仅仅是一只学舌的鹦鹉,或者一个录音机罢了。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曾在其著《人性的,太人性的》中认为《歌德谈话录》是一部“智者之书”,是“打开歌德创作之门的一把钥匙”,是一部“最好的德语作品”[44]。还有一些人赞颂如是,“这部书是歌德思想和智慧的宝库”。“它给了世界一尊栩栩如生的歌德‘全身塑像’。”然而事实上,这部作品一开始并不被时人接受。

图1-1 奥克森福德英译本《歌德谈话录》(两卷)第一卷封面[45]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的“重生”和经典化,是在这个文本经由翻译旅行到异域完成的。[46]其中,该书奥克森福德的英译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1836年,《歌德谈话录》刚出版时,并不受人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歌德还未被完全经典化,其经典性地位还未稳固,还遭受到年轻一代的爱国者、民族主义者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爱克曼此时不过是一位二流诗人,贫困潦倒、声名不彰。他是那么的“不重要”,以至于差不多被时人和后人完全遗忘。《歌德谈话录》最早的一个英译本是由北美的女学者福勒(Sarah Margaret Fuller)于1839年在波士顿译成出版。[47]这其实是一个节译本,也没有像后来第二个译本那样引起很多读者的注意。在这个译本中,福勒多数时忽略了爱克曼的存在,有时也对其冷嘲热讽。福勒说:“他(爱克曼)只不过是大师手上演奏的各种音符的发声板。无论是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来看,在这里我们发现的是:这不是谈话(conversation),而是独白(monologue)。”[48]福勒的译本是删节本。奥克森福德译本篇幅更长但也有删节,而且将原书名“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反转改为了“Conversations of Goethe with Eckermann”。[49]爱克曼的原文《歌德谈话录》第三部(1848)出版之时,第一、二部赢得的很少的读者或是已经故去,或是对第三部没有兴趣。第一、二部虽然并不受欢迎,但仍有一些读者,第三部的读者则更少得可怜,在最初两年里仅卖出了几百本,而直到1867年,销量也只达到一千五百本。[50]
到了1883年,奥克森福德的英译本首次并入了第三部,而且译者依编年体的方式重排了所有的条目,让这本书读起来如同一部非常详细的日记。[51]福勒译本在1852年之后便没再重版,而奥克森福德的版本则由于译者本人在批评界和译界的大名而逐渐流行开来,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歌德经典地位已经稳固,像尼采这样的后辈也一再追认其重要性,并承认其在德国文学中的地位。这一部作品《歌德谈话录》,也就顺利地进入了经典的序列。奥克森福德译本后来被收入了非常著名的“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No.851),流传至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最常见的英译本。
歌德晚年对年轻一代的浪漫主义者、对爱国的诗人,持怀疑和疏远的态度,故而备受年轻一代作家诗人的攻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歌德的逝世(1832)。甚至到了歌德百年诞辰时(1849),也几乎没有作家为其庆祝或表达纪念。爱克曼生不逢时,《歌德谈话录》第一、二部(1836)和第三部(1848)也同样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的世界动荡不安,充满政治骚动,而比歌德更年轻的一代作家已成熟,集体起来反对歌德的种种观念。[52]爱克曼最终在艰难困苦之中度过了最后的几年,直到1854年去世也几乎没人知晓。[53]他自此被人遗忘,直到奥克森福德的译本大为流行之后,德国读者,甚至魏玛的居民才惊觉本国本地曾有这么一位诗人爱克曼,他是歌德晚年的秘书,记录下了伟大歌德关于文艺、人生和世界的种种洞见。
(三)歌德与世界文学
在世界文学方面,歌德并不是一位空头理论家,事实证明他在其时代已经充分地参与了世界文学的发展,可谓“积极地促使其早日来临”。歌德积极地参与“世界文学”的最突出证明是他的两本诗集《西东诗集》(West-östlicher Divan.erschienen,1819;erweitert,1827)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und Tageszeiten,1829)。前者受波斯诗人哈菲兹[54]影响,后者受中国戏剧和小说影响。
据德国学者卫礼贤[55]的调查,歌德是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英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译本来接触中国和中国文化的。[56]歌德对中国的兴趣,最早可以推溯到1781年,当时他读到一篇法国人写的中国游记,便开始对儒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96年,他第一次读到中国的作品《好逑传》,是帕西(Thomas Percy,1729—1811)的英译本。[57]在1815年,他重读了《好逑传》,并与其好友席勒和威廉·格林[58]讨论此书。1817年,歌德读到德庇时(John F.Davis)英译本中国戏剧《老生儿》。[59]1827年,他读了汤姆斯英译本《花笺记》(1824)及其附录《百美新咏》。[60]同年,他还读了法译本的中国故事选集和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的法译中国小说《玉娇梨》。[61](请参表1-1)歌德接触到的这些(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促使了他在其文章中进行讨论,也促使他将某些重要的诗文重写成优美的抒情诗。早在1823年9月,爱克曼便对歌德说,“我想写一部大部头的诗作,用一年四季做题材,把各种行业和娱乐都编织进去”[62]。爱克曼并未完成该作品,但是歌德在1827年读了翻译的中国小说之后,写了一组十四首的诗作,名曰《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这一组诗作,被公认是歌德后期最好的抒情诗。
卫礼贤对这组诗的评论非常有意思,在此不嫌烦琐引述如下:“总体来看,歌德的这组诗只是从《花笺记》中吸收了一些很不确定、极为一般的启发,然后他完全独立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加工。不过,他越是自由地深入到这种自我理解中,便愈加直接地接触到中国原本的思想。”[63]这种自由翻译或改写,反而更为接近中国原本的思想,这无异于是说,歌德的翻译或改写使得原作得以更好地留存和传播。换言之,在这里,译作在译文环境中读上去如同原作在原文环境中一样,而且两者在思想上趋同相近。这恐怕会令人怀疑并非事实。然而,卫礼贤这种较为诗意化地理解歌德的改写,一方面证明了歌德所说的“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即文学创作的才能以及共同理解的可能),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印证了歌德非凡的写作才能——即便是改写,也证明了其充沛的写作动力和极为罕见的文学才能。
简言之,歌德既是“世界文学”口号的提出者,也是当时世界文学的践行者,在阅读、翻译和改写世界文学方面,他也做出了一些贡献。同时,他为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争取到了一定的地位,使其“扮演了光荣的角色”。
表1-1 1827年之前歌德阅读的外语译本的中国文学作品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