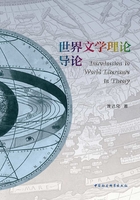
一 肇始:一个事件、许多问题
(一)引言
本书预设的读者,是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研究,以及对所谓“世界文学”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无论对方有没有修读过相关的文学课程。故而,本书的行文中对每个具体现象的讨论会不吝笔墨,剖析入微,尽量给一般的读者提供一种入门的途径。笔者的建议是,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若是遇到较为熟悉的、已掌握的知识点,便不妨跳过,跳读的过程中若发现有难以理解的地方,则请再回头寻找相关答案。当然,若有不足之处,责任在于笔者。
第一章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世界文学”,涉及“世界文学”概念的形成,其历史和影响,以及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世界文学理论的启发。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为一般读者廓清迷雾,解释一下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相关的一系列知识背景。在开篇前,笔者还将不厌其烦地对相关概念做一番解释,希望引导一般读者来到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起奔向同一个思考方向,去探索共同关心的问题。
一般意义上,按范围大小和领域分类来看,我们所讲的文学研究有如下三类,即:国族文学/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comparative literature)和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这三大类别的简要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文学现象和具体文学作品的情况。
第一种类别是“国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这是以单个民族国家为单位来把握的国别文学。比如,“中国文学”或“英国文学”,便属于国族文学。请注意,“国族文学”中的“国”是现代的民族国家,而非古代世界帝国或任何王朝。我们现在处于民族国家的时代,习惯使用的是民族国家的逻辑和思维模式,因而看待文学也常常沾染上所谓“时代的特色”。这也导致了我们在看待民族文学时会难以将其与所建构起来的民族历史做清楚的区分。民族国家的文学史书写方式,有时隐含着某些进化论和民族主义式的自满和偏见——这是应当警惕的。“国族文学”这个概念,随着17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产生到今天已经被普遍接受。[1]然而,与这个概念并行的另一个可能更为适应文学研究的概念是:某种语言的文学——比如汉语文学或日语文学。国族文学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有其合理性,清晰的国别疆域有益于看到写作和阅读的主体所受的政治与社会观念的影响,也能突显出文学作品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国族文学研究尤其适合针对单个民族的国家,或者民族特色比较独特的区域。然而,很多时候,讲国族文学,还不如讲某种语言的文学更为妥当,毕竟文学始终是语言写成的,而语言才是最接近于文学内在价值的层面——当然这并不能说是唯一的层面。
第二种类别是“比较文学”。这也是一个学科。让我们引用前辈对于“比较文学”的定义来简单说明这个领域。曹顺庆曾给出如下定义:“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2]再简明扼要的解释便如张隆溪如下的高度概括:“不同语言而又可以互相沟通的文学作品之比较。换句话说,相对于民族文学而言,比较文学是跨越民族和语言的界限来研究文学。”[3]
在中国教育体系内,自1997年学科调整之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方向合并,成为一个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4]这样的设置是为了适合21世纪的学科发展需要,迎合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当然,其不妥之处也较为明显。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个学科放在中国语言文学系这个一级学科之下并不合理,更合理的做法是要像“世界史”调整成历史学领域的一级学科一样,将“比较文学”调整成文学方面的一级学科,并为其成立独立的研究院系。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作为一个学科,要远远大于国族文学研究。从理念上说,比较文学应当包含了各种国族文学的跨界研究,支持这种说法的最简单理由便来自比较文学学科的自身要求,即要求相关研究应当有“四大跨越”——跨国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或跨文明。本书讨论的“世界文学”,其实也是在比较文学的范畴之内,可看作是比较文学理论新近二十年的新发展。
有的读者(甚至是文史专业的相关学者)可能会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个领域抱有两种态度,其一是质疑专业定位,其二则是质疑相关研究和研究者的水平。
(1)关于专业定位。笔者所在的院系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下属的专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个综合的学科,把这个专业放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不知情者,都很容易误将其等同于“外国文学”专业方向,即作为中文系中国文学方向的陪衬专业。有些学者可能会觉得这真的很奇怪——一个“外国文学”相关的专业,为何会被放在“中国语言文学系”呢?这种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尽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教师一般会给学生提供“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等方面的课程,但是这个专业领域绝不是只研究外国文学,也不只是研究中国文学。当然,此外还必须澄清的是“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学者伽列(J.M.Carré)所说,“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区别开来”[5]。
(2)关于相关研究和研究者的水平。中文系出身或身在中文系的学者,在具备了中国文学素养的同时去研究西方文学,有一定优势,当然也有其短板,即对外语的掌握和对其他文学传统的不够熟悉。反过来,外文系出身的学者,虽然外文能力较好,也精熟某一个或多个外国文学传统,但是在研究中外比较文学时也应该需要补足中国文学相关时段的研究状况。也即是说,研究者必须具备深厚的中外文学功底,中外传统必须兼通,内外必须兼修。所以学者在精通中国文学的同时,也须精通研究的外国对象,这样做出来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才更靠谱一些。普遍调查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有趣的现象:在当下北美的学术圈,有许多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其本科学术训练是外语系或其他非中文学科的,而且长期在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任教,所以即使他们研究的是中国文学,他们的知识生产领域还是应当天然地归类进比较文学。另外,现下的所谓“海外汉学”涉及文学的部分,也是一样应归类入比较文学。又,在中国大学院校中文系里的比较文学学者如果受限于语言能力、学科视野,使用的仅是汉译作品,又或涉及的仅是中国或者仅是外国的内容,那样的研究恐怕也难以称为“比较文学”。当然,比较文学从学科创始之时,对相关的从业学者素质的要求非常之高,比如要求研究者熟练使用多种学术语言、掌握多个学科的知识、具备较为广阔的视野,并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学术研究早已经是全球共享的事业,不再受地域的区隔,也不应受民族主义的限制。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无论是身在中文系还是外语系),无论是研究法语文学、日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或者古罗马拉丁语文学,都必须努力做到与国内外第一流的同行对话交流,要做到你的研究对象涉及的外国学者都不能忽略你的研究成果,那样才算是达到基本的要求。
第三种类别是所谓的“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在这里“总体”对应英文是“general”(一般的),故而又称“一般文学”。这里的“一般”,是哲学上的“一般”,即与“个别”相对的某种普遍性、抽象性。这也不难理解,总体文学的研究,是为了研究多种国族文学的一般规律,即所谓“文学的共性”或“人类文学发展的共通规律”。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比较文学这个领域的发展目标是走向世界文学,走向总体文学。中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比较文学导论》曾提出,“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通过对文学现象相同与殊异的比较分析,来探讨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寻求并认识文学的共同规律,目的在于认识民族文学自己的独创特点(特殊规律),更好地发展本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6]这里提及的“共同的规律”便是总体文学,其作用便在于用来反观和比较民族文学的特殊样式。
假如以“墙”为喻,国族文学就是墙内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则是跨墙的文学研究,而总体文学则是临空鸟瞰,即是墙垣上面的文学研究。请注意,这里的譬喻,既非优劣对比,也不包含任何褒贬或价值评判。在这三种类别之外,还有与三者密切相关的第四种类别“世界文学”。那么,什么是“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 / world literature)?
在讨论“世界文学”的概念之前,这里有两个问题先供大家思考。
问题一:非经典的、没有或尚未进入经典序列的文学作品,比如当代文学作品(比如《哈利·波特》),可被当作世界文学吗?
问题二:非外国文学作品,比如中国文学作品(比如《西游记》),可以当作世界文学吗?
第一个问题,试析如下。评论界尤其是当代文学方面的学者,有时会有意无意地使用、误用一个词组“当代文学经典”。这明显是一种错误的表达,究其原因在于内部词义的相互悖反。“经典”,必须具备一个时间的维度,即一部作品需要经过多代读者的相继确认,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方能被接受视为经典。而“当代”则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断向过去告别,不断向未来增益。所以“当代文学经典”这个内在自我悖反的词组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即有以下的两种“凡是”:(1)凡是经典的作品,便不可能是当代的作品;(2)凡是当代的作品,便不可称为经典。这些判断隐含的问题是,在一般读者的印象里,“世界文学”可能就是指一个序列的经典文学作品,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名著名译”丛书或其他世界文学名著。然而,“世界文学”是不是一定就是经典文学?如果是的话,谁决定这个经典作品的序列?它是各民族文学经典的汇总吗?我们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哈利·波特》这样的当代文学作品,可以被当作世界文学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世界文学就不必然与“经典”或“经典性”挂钩。
在中国的大学学科体系内,“世界文学”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往往是与外国文学相关的科系,然而却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这一个一级学科,那么问题是:中国文学也可以被当作世界文学吗?最为理所当然的回应是: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中国文学肯定也就包含在“世界文学”这个总体当中。这个说法中的“世界文学”指的是一种所有国族、所有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的总和。在这里,我们暂且举两个小例子简要地作一个回答。为何像《哈利·波特》这一类影响巨大的文学作品,可以被当作世界文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世界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指经典文学,而更多的是指有世界性影响(最低意义上便是跨国影响)的文学。两者的区别在于,文学经典尤其是超级经典在“文学的万神殿”中所占据的地位一般变化不会很大,而世界潮流则有涨有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流行的东西则较容易很快地变成“明日黄花”。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不妨借《西游记》的外译为例,作一种引申解释。《西游记》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学经典,然而在何等意义上它可以被当成世界文学?中国读者在中国境内阅读和研究的《西游记》,我们并不能将其称为世界文学,而当这一部作品跨越了其原有的语境(汉语、中国)而在其他文化语境当中(无论是以原文还是翻译的形式存在)被其他国族的读者阅读和研究时,我们才能将这部作品称为“世界文学”。同样地,在最泛化的意义上讲,美国文学,对中国读者来说可以看作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文学,无论是哪一部作品,无论是经典与否,对阅读该书的美国读者来说也应当属于世界文学。因而可以说,世界文学具有三种基本的特性:相对性、流通性、跨界性。这一个例子与上面《哈利·波特》的例子并不冲突,假如《哈利·波特》仅在英语世界流通,不产生跨国、跨语言、跨文化的大影响,那么也就不能将其称为世界文学。因而同理,在中国境内被阅读的《西游记》,也同样不能称为世界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范畴内,我们是以流通的、变化的、跨越的视角来看待文学作品的消费、阅读、生产与再生产,以及这些方面的文化活动带来的文学方面的增益。下面我们便正式进入讨论“什么是世界文学”这个问题。
以上我们讨论了国族文学、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三种文学研究,在此引入并简要介绍另一个概念:“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一个难题,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这里整整的一本书便是结合当代文论和比较文学的案例来讨论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各个层次内容。
较笼统地讲,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量”“质”和“观念”,去观察、理解“世界文学”。
(1)量:世界各国各族、以各种语言写就的所有文学的总和。
(2)质:享有世界性声誉的经典文学作品。
(3)观念(ideas):一种思想观念、研究方法或视角。
第一,从“量”的层面来看,“世界文学”可以是包含了世界上所有语言写就的所有的文学作品,即所有文学的总和。然而,一个包含了所有的概念是一个无效的概念,一个没有边界的范畴是不能把握的范畴。在未有合适的分析工具之前,我们只好暂且存而不论。
第二,从“质”的方面考量,“世界文学”可以是指各个国族各种语言文学系统中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大合集。不过,这个合集要有多大,要容纳多少文本,才算是合适的?如果说是“质”的集合,那么经典的序列肯定不会非常长,而且在不同的时代,这个名单上的人物和作品的次序可能还会有所调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核心基本固定,但又会不断调整的清单。另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是:如何做到公平公正?在这样一个政治和文化格局无法均衡的世界,由谁(哪一个群体)来决定经典,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部作品,在一个国家里家喻户晓,被奉为“超级经典”,但是在另外一个完全是异质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则有可能没有什么地位,甚至不为其国读者所知晓。比如,在中国,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或许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剧作,但他/她至少也会知道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莉叶》(Romeo and Juliet),又或者《哈姆莱特》(Hamlet)。但若是一位中国学者到欧洲或美洲去,问一个当地的大学生或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是否知道中国的《红楼梦》或《西游记》,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体现了经典的相对性,体现了维持公正的难度,也同时证明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存在。如果世界体系的不均衡架构仍然一直存在,某种文化霸权肯定会在择选经典的过程中起到作用,这样选出来的世界文学作品则难免受人质疑。所以说,“经典”(尤其是民族文学经典)还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经典是一个有限的清单,一般有较为稳定的结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增益或变动。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有一种理论可用来解释“经典系统”内部秩序的变化。他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经典”(canon)及其系统。[7]
(1)超级经典(hyper-canon):地位一直稳固,甚至越来越显要。比如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剧作。
(2)反经典(counter-canon):在大传统之外、有争议的、被低估的、用非主流语言创作的作家,但是有朝一日会反转,并进入了主流圈,终被奉为经典。
(3)影子经典(shadow canon):曾经一代或几代人的经典,后来越来越被忽略,隐身退去,消失在超经典的背景里,成为影子经典。
伟大作家在万神殿里肯定有其非常显要的位置。超级经典无须再多举例,那些重要的名字一般读者都能耳熟能详,而且他们备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膜拜。“反经典”和“影子经典”则可用以描述经典的流动性——两者其实是以相反的方向向经典的中心发生位移,反经典越来越靠近中心,而影子经典则逐渐远离中心。在这里达姆罗什预设了一种体系或者结构,在这个体系或结构当中有边缘和中心之分。我们用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解释反经典和影子经典: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中,出现的一系列作家,从边缘进入了中心,被世界文学史接受。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因获得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也就迅速由边缘的国度、边缘的语言进入了世界文学的中心。印度的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8]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显见的例子。泰戈尔在语言、文化和地理上,都属于世界文学体系中的边缘,但是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特地表明:他被接纳了,属于“西方文学的一部分”,变成西方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文学史中的例子则有:东晋的陶渊明要到宋代才被追认为一代大诗人。陶渊明等了五百多年,才进入了经典的中心,而且越来越重要。这就是“反经典”的案例。关于影子经典,达姆罗什还举了这样的例子:193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在当年大红大紫,而在今日却几乎成为除了专业学者研究之外,一般读者都不会问津的“影子作家”。与高尔斯华绥同时代的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则相反,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乔伊斯更应当、更配得上获得诺奖(或任何重要的文学奖),但是他并没有获得该奖。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发现乔伊斯的两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1922)和《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1939),足以使其跻身于世界文学万神殿现代一侧的显赫位置。
第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研究方法或观察视角的世界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变成了国内外学界热门讨论的话题。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
总之,本书对20世纪末以来的世界文学理论,作一番梳理,以求让一般读者和学生熟悉。同时,笔者会援引许多与中国文学相关的案例来证明这些理论,或者反证并提出纠偏的意见。
(二)一个事件和许多问题
1827年1月31日,年轻的诗人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作为歌德晚年的秘书,记录下了他与歌德的一段谈话。这段谈话只是两人无数次文艺对谈中的一次,却因为触及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及其相关的方方面面而具备了独特的意义。在那段谈话里,歌德首次提及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尽管歌德并非是第一个使用该词的人,他在随后的谈话中却赋予了其独特的意义。甚至不过分地说,这等同于宣告“世界文学”这个学科的开始。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并非清晰而成系统的,故而引来了许多延伸的阐释,甚至有许多讨论早已超出了歌德的话语所涵盖的范围。迄今一百多年过去了,许多国族文学史家、比较文学学者、历史学家、翻译学学者、思想史学者,甚至是社会学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20世纪60—90年代的后现代思潮中,世界文学领域的学者借机开始重思或重构(西方中心的)经典序列,将焦点转移至非西方的文学作品,并强调文学作品的世界性,尤其是文化生产、流通、翻译和阅读等方面。当代国外、境外学者如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卡萨诺瓦(Pascal Casanova,1959—2018)、达姆罗什、阿普特(Emily Apter)、莫莱蒂(Franco Moretti,1950—)、普伦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提哈诺夫(Galin Tihanov)和张隆溪等,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世界文学理论的大讨论。在21世纪全球文学、文化研究圈内,“世界文学”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域,许多教学、会议、论文和著作都围绕着它展开。哈佛世界文学研究所每年召开的暑期学校(Institute for World Literature)和2016年新创办的《世界文学杂志》(The 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是促进这一领域快速发展的两大阵营。世界文学这一领域在国外学界极为热闹,而在中国近年才逐渐发展起来。方维规201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世界文学方面的会议,最终在2017年结集成书《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世界文学》便是对这一思潮的回应。[9]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竞技场,现已有许多著名学者加入了讨论。这本书正是对这一方兴未艾的潮流作一种回顾和暂时的总结。当然,这也是对古老问题的一个遥远的回应,因为从民族国家和国族文学自15世纪在欧洲产生至今,类似的问题早已存在。
方维规曾指出,“歌德没有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10]。然而后世关于世界文学的诸多讨论却从此而来,这让我们有必要回到歌德的语境,去理解他谈及的内容。我们追问的问题是:歌德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及这个概念,又有何独特的意义?歌德的“世界文学”是指什么?爱克曼对这一事件的记录是否可信?爱克曼或歌德所处的历史语境是怎么样的情况?在歌德之后,“世界文学”概念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歌德所讨论的范畴,那么,这个概念经历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代表性的论述?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论述?
1827年1月31日,青年诗人爱克曼记录了当天他们谈论的一部译成法语(一说英语)的中国小说,将其与当时流行的法国小说作了对比,歌德进而确认中国小说所寓寄的道德标准远远高于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国小说。此时,歌德用了一种先知式的口吻说道(此前他早已感觉到了这种苗头):
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创作出来。……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的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1]
这可能是每一部世界文学史都必须提及的一段话。在过去的一百多年,读者经常能看到对它书面或口头的引用。它几乎变成一句老生常谈,以至于人们都忽略了它原有的语境和涉及的问题。
关于这一段话,我们有多少种阐释?我们能提出什么问题?笔者若是一位提问者,肯定会追问如下的这些问题:
(1)歌德读到的这部小说是哪一部?或可能是哪几部?
(2)同一时段,他读到的中国作品,甚至是东方作品有哪些?
(3)这些作品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4)当他将这部译成法语的“中国小说”(或者他笼统意义上的中国小说)与当时的法国小说(或者笼统意义上的法国文学)作比较时,这种比较说明了什么问题?
(5)为什么歌德需要用这部小说,或一个他者文明中的文学作品,来对抗法语小说或法语文学?
(6)歌德说的“世界文学”,具体是指什么?
(7)为何歌德要在德国爱国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正在大力推广“民族文学”的时刻,却呼吁迎接“世界文学”的时代?这两个概念,是否自相矛盾?
(8)歌德提到这个概念时,他说他喜欢环顾四周看看其他外国民族的文学发展情况,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给予了歌德这样的视野?
(9)他为何要劝“每个人”这么做?“每个人”是泛指,还是特指?
(10)此前他讨论的是小说的情节,为何在紧接着的总结中,论及的却是“诗”?他所说的“诗”,又是指什么?
(11)所谓的“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是指共同的精神文明财富吗?
(12)当歌德对比其读到的法译中国小说和法语小说时,这可看作是中国小说与法国小说的对比吗?
(13)当我们问及上一个问题时,涉及的问题可能还有:翻译的文本与原文是否可看作是同质同类的?如果不行,两者在何种程度上有哪些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内容,甚至是译者的心理?
…………
以上这些问题,仅是笔者联想到的问题(还能提出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前提,去进入并思考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相关内容,对关于世界文学的思考或许不无裨益。下文试着从历史语境进入讨论,并以《歌德谈话录》作为一个案例来讨论世界文学涉及的方方面面。
(三)向全球化前进: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
歌德为何能够在1827年的德国提起“世界文学”的概念?换言之,是什么样的文化环境,给予了歌德这样的动力,是什么样的知识背景给予了他那样的“奇思异想”,去想象一种将要出现的新的文学世界。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答案是: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为他和爱克曼创造了可能。
在歌德的时代,德国还不能算是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在他之前,德语文学在欧洲各国的市场上毫无地位可言。在此时的欧洲,从影响方面而论,用法语和英语写成、译就的文学才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12—1786)使用当时的通用语法语来写作,在巴黎被视为一位法国作家,而他本人对此没有反对意见,反而有点沾沾自喜。[12]只有在歌德出现之后德语在世界文坛上才有了占据重要位置的作家。1774年,年轻的歌德出版了其第一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该书为其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可观的财富。一位评论家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卷了英国和法国之后,又向意大利挺进,从此以后,德国文学才有机会获得外界的承认并享有更高的地位。”[13]《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欧洲各国的翻译和流通,正是歌德所描绘的世界文学的现象,也正是他期望看到的事情:德语文学在世界文学这个平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晚年的歌德驰誉欧洲,各国名人、政要和作家,都来德国魏玛拜访他。这时,歌德在魏玛的居所,便成了当时世界文学的中心之一。让我们再往前回溯追问,是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了歌德,以及歌德为何可能在那时讨论到世界文学?
1815年6月18日,法军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的战败,标志着拿破仑法国称霸欧洲的结束,也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的结束,随后相继建立了一些现代的民族国家。延续了十几年之久的“拿破仑战争”[14],可看作一种全局性的战争,在造成欧洲生灵涂炭的同时,也促进了各地区、民族的文化交融。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传统向现代跨越,封建君主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更重要的是一个国际市场已是稍具模型,而各国的文化产品(书籍)也在这个市场中流通——尽管有时是以翻译的方式。欧洲各国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运动,也给歌德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呼唤他有所回应。德国狂飙突进运动[15]中的旗手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与歌德亦师亦友。我们讨论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和世界主义理想,都不能忽略了赫尔德的思想对歌德的重大影响。
赫尔德的许多文艺观念,直接地影响到了歌德。赫尔德对于他国文学的兴趣,特别是收集和研究各地民歌,并认为民族文学是民族精神的一种最为明显的体现等观念,直接影响到了歌德对其他国族文学的态度,促使歌德也开始研习欧洲之外的文学作品。此外,赫尔德喜欢创造新词,用德语前缀“welt-”创造了一些词汇,受其影响,歌德也创造性地使用起“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一词。尽管早在歌德提及这个词汇的三十年前,另一位德国作家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在其手稿中已经使用了该词,[16]但是唯有在歌德这里这个词才有了学科史的独特意义。
尽管“民族”(nation)一词的历史非常长远,民族语言的勃兴也早在15世纪就已开始,但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则是在像拿破仑战争这样的全局性战争之后才勃发起来。概要而言,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战争波及欧洲的一些王国,但也促使了欧洲各民族和各区域的人民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法军的入侵。后来在这种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最为常见的民族国家体制。欧洲民族主义思潮最先兴起的当属德国。此时浪漫主义作家参与了德国民族精神的建构。正因为拿破仑的兴起,法国在欧洲的势力迅速崛起,很快便达到了几乎雄霸欧洲的状态,法语也顺着这股潮流攀上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圈的高位。[17]此后拿破仑军队虽然溃败,但法国在欧洲文化的战场上并没有那么轻易便退军。战争带来了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各种文化知识的积极交流。而在这种思潮中,赫尔德代表了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大力地鼓吹种种浪漫主义论说,同时也促进了德国民族精神的成形。因而德国的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根据现存的材料可知,1813—1815年,二十出头的青年诗人爱克曼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了德国军队以抗击拿破仑军队的入侵。战争和政治的动荡带来了满目疮痍的世界,也带动了不同区域的人们非常频繁的交流,而交流的结果有时反而是使各自陷入某种偏执或自我中心。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固守着各自的利益,许多作家和组织也被卷入其中,在德国的这边则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因而歌德在此时平静而温和地提出他的“异见”——世界文学的时代要来临了。“民族文学”的兴起,也可如此看。在1827年1月31日,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其实并不是特别受欢迎。因为同时代还有一些浪漫主义者——比如卡尔·施莱格尔(Karl W.F.Schlegel,1772-1829)等人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召唤民族精神,批判法国凭借其文化优势而催毁其他民族的民族性,呼唤德意志人参与建设德国的民族性和反对外国文化侵略的“圣战”。[18]最不能被歌德或后人认同的一点是他们不愿提及德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将本国文学受到他国文学的影响,称为国际文学关系中所负的“外债”)。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是,民族主义作家在提倡民族文学、民族精神之时,不大愿意承认本国文学所受的外国影响,而认为本土的文学传统自成体系,似乎用这种“自足性”“纯洁性”来证明本国的传统、祖先的文化更为伟大。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少见。年轻一代的浪漫主义者这种狭隘的做法,本意是“正本清源”,还原德国文学的纯粹性,要将德国文学所欠的“外债”目录完全勾销。此时的德国浪漫主义者和爱国者在提倡“国族文学”时,企图整理出本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以证明其是一个自足完满的体系。民族主义情感遮蔽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没能看到更广阔的风景。歌德则不同于此,其视野更为宏阔,更有前瞻性。
早在1808年,歌德在编选《德国诗选》时,便清楚地意识到德国诗歌从其他国家的诗歌(或原作或翻译)中获益甚多。可以说,歌德在谈及“世界文学”概念时,有特别针对的对象,尤其是当时德国的浪漫主义者、爱国作家,也针对代表着当时流行的法语文学,尤其是那种带有色情的、堕落的、恶趣味的作品。歌德坚持的是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艺术真理,一种他称为真善美的标准,但这种理念源头不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古希腊文学和哲学。这也难怪歌德对比了中国小说与法国小说之后,紧接着说:“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19]
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还延续着各种大小战乱。而此时的德国仍是公国林立、尚未完成统一。德语文学还不能算是具有大影响的文学,伟大的作家(歌德)虽然已经出现,但德语文学还未像英语或法语文学那样得到世界性的承认。所以当狭隘的浪漫主义作家在推动德语民族文学时,歌德一下子便看到了他们的弊端。他说他自己也得益于德语之外的其他文学,比如他热衷称道英国戏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剧作。所以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得懂外语,或者至少得多读读翻译的文学作品,以便从中获取某种滋养,进而壮大本国的文学。有趣的是,这一点直到20世纪仍为一些德国评论家所继承而奉为圭臬。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许多中国当代作家外语不好,成就不高,这是因为无法从外文原文或翻译中获取滋养。[20]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歌德的迥异时流,他在民族主义文学兴起的时代推动文学的“普世主义”“世界主义”,有其前瞻远见。
自1770—1771年的那个冬天歌德结识赫尔德后,他的许多观念都受到了后者的影响。赫尔德在18世纪德国文学复兴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正是赫尔德促使了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而其史学思想,尤其是那种世界历史的意识则影响了现当代的许多历史学家,比如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21]歌德的“世界主义”观念,也来自赫尔德。除此之外,歌德至少还受到赫尔德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对欧洲(或欧洲主流文学)之外的文学,尤其是对民歌的喜欢。赫尔德曾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民歌,而歌德在其影响之下也对世界各地的民歌有着极为深厚的兴趣。“歌德完全接受了赫尔德的观点。他采集并且仿作民歌,分享了赫尔德对莪相和荷马这些古典风格的诗人所怀有的热情……”[22]即使是在其生命的后期,歌德仍会热烈地讨论塞尔维亚的民歌和中国的诗歌。歌德《浮士德》(Faust)第一部的序言之一,便是以他曾仔细阅读过的、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戏剧《沙恭达罗》(Sakuntala)为基础的重新创作。从模仿外国作品而创作这一点看,歌德绝不是“世界文学”的空头理论家,而是其实践者。他也将他读到的法语或英语译本的中国文学作品,重新改写成德语的诗歌。再者,赫尔德和歌德开始使用一些以德文词根“welt-”(世界的)组成的词汇,并赋予了它们独特的意义,这一点也与他们观念中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密切相关。他们创造出了一些新的词汇,除“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一词之外,还有“weltbürgertum”(世界主义)、“weltbürgerschaft”(世界公民)、“weltmarkt”(世界市场)、“世界信仰”(weltfrömmigkeit)和“世界灵魂”(weltseele)等等词汇。这还令人联想起康德的“世界和平论”。在德国的现代学者和哲学家的著述中,也常见这种世界主义的追求。在这里,“世界性”(普世性)和“民族性”(本土性)并非冲突的,而是相互包容的。换言之,民族性在“世界”这个更大的体系中存在,而不丧失其特性。也唯有保持这样相对的共性和特性,才能保证“世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共同体。在歌德看来,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中的一名公民,还必须首先是人类的一员。这也同出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