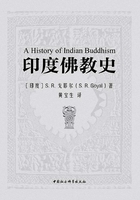
二 思想骚动
思想观念领域变化的诸因素
这样,我们看到随着吠陀时代结束,部落“边缘人”的时期告终,货币经济和铁器时代开始,第二次城市化革命导致城镇增多和商业发展。商业发展的结果是出现极其富裕的商人阶层,工匠组织成行会,对种姓体系造成影响。所有这些变化一方面唤醒精神探索,另一方面导致人们对一些阶层兴旺发达的背景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觉,虽然 G.C.般代认为社会危机“仅仅表示需要不决定其性质的新思维。社会变化是一种起因,而非精神变化的原因,提供它的前件,而非逻辑联系”[173]。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这样一种变化不能不反映在这个时代的宗教思想和实践中。对吠陀祭祀宗教最早明确的批评出现在早期奥义书中,但只是采取温和的形式。祭祀或许有某种效用,但不能拯救人的死亡。而对于宇宙,旧有的仪式主义宗教不能作出令人完全满意的解释。探索第一原理实际上早在《梨俱吠陀》的晚出部分中已经存在,现在得到奥义书仙人的强化。新的建议和原理被提出,依据由苦行和沉思获得的超自然洞察力”[174]。“在同样的转折时代,中国圣人依据更新社会的手段提出互相冲突的理论,也涉及第一原理。但印度最优秀的思想家对于社会不抱有幻想,认为社会依随宇宙必然衰亡的过程是日益恶化的。对于印度圣人,拯救(或解脱)只是少数人能获得的事,而非整个社会的事。后来,智者们以‘经’ 和‘经论’
和‘经论’ 的形式整理编订正统的社会习俗规范。但是,在佛陀时代,人们的思想转向摆脱习惯的束缚,而非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175]
的形式整理编订正统的社会习俗规范。但是,在佛陀时代,人们的思想转向摆脱习惯的束缚,而非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175]
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恒河中游地区有“奇趣堂” 即休憩和辩论的场所。这些场所不仅用作宗教导师在雨季的安居处,也便于吸引听众。城市生活释放好奇心和自由思想,当时的一些导师加以利用,因为他们急于要向大量听众宣说[176]。他们的教导向所有人开放,或许与婆罗门林居者的说教相比,较少神秘性。“一位导师的重要性取决于他的信众规模,也取决于他阐述的理论。这种成规模的信众在大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区更容易获得。讨论的主题多种多样,但基本问题集中在人类经验、知识和本能的普遍性。这些场所常常位于花园,围绕成排的树木,令人想起森林。……这些奇趣堂由富裕的市民维持,或由王室恩赐,成为讨论各种学说的重要场所。通常说到他们讨论的话题着重宗教和伦理,但必定也包括人们关心的其他问题。在奇趣堂中的集会无疑也是确定哪个教派会受到恩宠的一条途径。”[177]
即休憩和辩论的场所。这些场所不仅用作宗教导师在雨季的安居处,也便于吸引听众。城市生活释放好奇心和自由思想,当时的一些导师加以利用,因为他们急于要向大量听众宣说[176]。他们的教导向所有人开放,或许与婆罗门林居者的说教相比,较少神秘性。“一位导师的重要性取决于他的信众规模,也取决于他阐述的理论。这种成规模的信众在大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区更容易获得。讨论的主题多种多样,但基本问题集中在人类经验、知识和本能的普遍性。这些场所常常位于花园,围绕成排的树木,令人想起森林。……这些奇趣堂由富裕的市民维持,或由王室恩赐,成为讨论各种学说的重要场所。通常说到他们讨论的话题着重宗教和伦理,但必定也包括人们关心的其他问题。在奇趣堂中的集会无疑也是确定哪个教派会受到恩宠的一条途径。”[177]
一些学者在佛陀时代的宗教运动中,发现一种种姓关系,一种刹帝利对婆罗门的反叛[178]。事实上,耆那教和佛教,这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宗教,是由两个刹帝利王子创立的。他们强调刹帝利的地位高于婆罗门,为这种理论增添色彩。但是,正如我们在别处看到的[179],甚至在奥义书时代,刹帝利就已经对宗教哲学追求发生兴趣。在《薄伽梵歌》(4.1—2)中,提到王仙  的瑜伽传统。此后,也明显提到婆罗门参加各种非吠陀或沙门团体。有些人将这种知识活动仅仅归诸沙门,这也是不正确的[180],因为这个时期毗湿奴教和其他正统的虔信派的兴起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思想骚动的结果。
的瑜伽传统。此后,也明显提到婆罗门参加各种非吠陀或沙门团体。有些人将这种知识活动仅仅归诸沙门,这也是不正确的[180],因为这个时期毗湿奴教和其他正统的虔信派的兴起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思想骚动的结果。
公元前五、六世纪流行的哲学
在佛陀时代,业报说( 和
和 )及其对立的无业报说(
)及其对立的无业报说( 和
和 )似乎是讨论最多的问题。耆那教和佛教都相信业报说。按照B.C.劳,
)似乎是讨论最多的问题。耆那教和佛教都相信业报说。按照B.C.劳, 和
和 这两个词没有区别,都表示业报说[181]。但是,更可能这两个词有某种区别[182]。大致说来,这两个词表示人的苦难不是由时间、命运、偶然或灵魂,而是由自己的行动引起,因为人的行动含有一种道德束缚力,其结果不可避免。与这种学说对立的是永恒说(
这两个词没有区别,都表示业报说[181]。但是,更可能这两个词有某种区别[182]。大致说来,这两个词表示人的苦难不是由时间、命运、偶然或灵魂,而是由自己的行动引起,因为人的行动含有一种道德束缚力,其结果不可避免。与这种学说对立的是永恒说( ,即终极真实是永恒的学说)和偶然发生说(
,即终极真实是永恒的学说)和偶然发生说( ,即偶然性起因的学说),其结论是没有任何行动能称为道德或不道德,因为它既不引起任何变化,也不是自由的行动。在《大品》
,即偶然性起因的学说),其结论是没有任何行动能称为道德或不道德,因为它既不引起任何变化,也不是自由的行动。在《大品》 中,尼乾陀·若提子认为佛陀相信无业报说
中,尼乾陀·若提子认为佛陀相信无业报说 。有时这个段落被略去不提,因为无关紧要,只是偶尔出现的指责。但是,正如密希罗(G.S.P.Mishra)所指出,如果我们注意两者提出的“业”(
。有时这个段落被略去不提,因为无关紧要,只是偶尔出现的指责。但是,正如密希罗(G.S.P.Mishra)所指出,如果我们注意两者提出的“业”( 和kamma)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这种指责就变得清晰。按照耆那教,强调行动的肉体性质,每种行动必然产生一种结果,影响一个人变成什么。例如,如果一个人从事杀生行动,他必定获得罪孽,他自己有意识或无意识从事这种行动并不重要。而另一方面,佛陀强调人的行动的精神方面。他认为,一种行动除非伴随有意愿和意识,否则不成其为行动,理由是人不受那些无意识的行动的结果影响。因为耆那教不接受这种观点,尼乾陀·若提子指责佛陀相信无业报说
和kamma)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这种指责就变得清晰。按照耆那教,强调行动的肉体性质,每种行动必然产生一种结果,影响一个人变成什么。例如,如果一个人从事杀生行动,他必定获得罪孽,他自己有意识或无意识从事这种行动并不重要。而另一方面,佛陀强调人的行动的精神方面。他认为,一种行动除非伴随有意愿和意识,否则不成其为行动,理由是人不受那些无意识的行动的结果影响。因为耆那教不接受这种观点,尼乾陀·若提子指责佛陀相信无业报说  [183]。
[183]。
除了无业报说,断灭说  也受到佛教和耆那教的贬斥。这是对伦理和宇宙问题的唯物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哲学的基本点是唯有肉体是真实的。灵魂并非是有别于身体的事物。在身体瓦解后,不存在灵魂、生命或业报。一旦死亡,所有一切断灭。
也受到佛教和耆那教的贬斥。这是对伦理和宇宙问题的唯物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哲学的基本点是唯有肉体是真实的。灵魂并非是有别于身体的事物。在身体瓦解后,不存在灵魂、生命或业报。一旦死亡,所有一切断灭。
在佛陀时代的其他哲学理论中,也可以提到时间说  。它见于《阿达婆吠陀》,也见于《摩诃婆罗多》。“受到不可抗拒的时间悲剧的打击,产生一种深刻的宿命感,怀着强烈的畏惧谈论时间。”[184]自性说
。它见于《阿达婆吠陀》,也见于《摩诃婆罗多》。“受到不可抗拒的时间悲剧的打击,产生一种深刻的宿命感,怀着强烈的畏惧谈论时间。”[184]自性说  似乎与下面将会讨论的数论和拘舍罗的观点有接触点。它确认通过内在力量发展的理论,但否认自由意志[185]。命定说
似乎与下面将会讨论的数论和拘舍罗的观点有接触点。它确认通过内在力量发展的理论,但否认自由意志[185]。命定说  相信命运或必然性,可以意味一种自然的(因果的)、超自然的(命定的)、道德的(业报的)或逻辑的必然性[186]。与之对立的是否认因果业原理的偶然说(
相信命运或必然性,可以意味一种自然的(因果的)、超自然的(命定的)、道德的(业报的)或逻辑的必然性[186]。与之对立的是否认因果业原理的偶然说( )[187]。
)[187]。
这个时期的其他两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的意识形态是苦行说  和戒律说
和戒律说  。苦行说许诺通过实施严厉的苦行能获得最终解脱,而这种苦行包含身体的剧烈痛苦。这种观念在婆罗门苦行者以及非吠陀苦行者如生命派和尼乾陀派中流行。而佛陀宣说“中道”学说,不赞同这种信仰。戒律说主张为了达到人的目的,应该接受一些固定的行为规则。正因为如此,佛陀和大雄以及其他的导师为他们的信徒制定戒律。
。苦行说许诺通过实施严厉的苦行能获得最终解脱,而这种苦行包含身体的剧烈痛苦。这种观念在婆罗门苦行者以及非吠陀苦行者如生命派和尼乾陀派中流行。而佛陀宣说“中道”学说,不赞同这种信仰。戒律说主张为了达到人的目的,应该接受一些固定的行为规则。正因为如此,佛陀和大雄以及其他的导师为他们的信徒制定戒律。
关于世界、灵魂和人生至善,在这个时期流行若干种哲学。有好几部佛教和耆那教经文以及一些早期奥义书之后的婆罗门教文本中提到或详细讨论这些观点。但是,《长尼迦耶》中的第一部《梵网经》 系统地论述这些观点。这部经中讨论以下这些问题。
系统地论述这些观点。这部经中讨论以下这些问题。
1.四种永恒说  。
。
2.四种半永恒说  。
。
3.四种有限和无限说  。
。
4.四种油滑说  。
。
5.两种偶然发生说  。
。
6.十六种死后有想说  。
。
7.八种死后无想说  。
。
8.八种非有想和非非有想说  。
。
9.七种断灭说  。
。
10.五种现世涅槃说  。
。
所有这些观点[188]在小乘和大乘佛经中都被称为“邪见” ,并归诸那些坚持“有身见”
,并归诸那些坚持“有身见” 的人,即认为身体或身体的任何特殊因素都是灵魂(“自我”)[189]。
的人,即认为身体或身体的任何特殊因素都是灵魂(“自我”)[189]。
关于佛经论述这些问题的目的,佛音  和后来的大乘学者认为出于阐述“空性”
和后来的大乘学者认为出于阐述“空性” 的必要。佛音所谓的“空性”意味“人空”
的必要。佛音所谓的“空性”意味“人空” ,而对于大乘学者,则意味“人空”和“法空”
,而对于大乘学者,则意味“人空”和“法空” [190]。然而,按照现代一些学者,这部经的目的是简要概括佛陀时代北印度流行的非佛教学说。而按照达多(N.Datt),这部经并无这样的前提[191]。他指出五位外道导师和大雄的学说,还有奥义书中发现的哲学观点,都在这部经的视野之外。按照达多,这部经的主要目的是勾勒萦绕在那些隐士(“沙门-婆罗门”)头脑中关于世界和灵魂的可能性理论的名单。这些隐士凭借直觉或沉思获得某种力量而没有达到最高状态。“所谓的‘六十二见’显然是系统说明隐士或思想家的经验,而很少涉及那时的观点。或许在‘六十二见’中的某些观点和体现在奥义书中的哲学教义之间稍许有些一致之处,但不能确定这部经的撰写是针对它们的,一致的原因或多或少是偶然的。”[192]然而,按照G.C.般代,虽然“毫无疑问,这部经归功于佛教的系统化,但要接受达多的观点,需要用以下事实予以修订:(1)在《梵网经》中提到的一些观点能表明是非佛教思想家实际持有的。(2)按照这部经本身,应该相信有些观点出自理性思辨,而非特殊的神秘经验。(3)许多‘佛教僧侣的经验’与某些或其他非佛教思想家的经验是同样的”[193]。
[190]。然而,按照现代一些学者,这部经的目的是简要概括佛陀时代北印度流行的非佛教学说。而按照达多(N.Datt),这部经并无这样的前提[191]。他指出五位外道导师和大雄的学说,还有奥义书中发现的哲学观点,都在这部经的视野之外。按照达多,这部经的主要目的是勾勒萦绕在那些隐士(“沙门-婆罗门”)头脑中关于世界和灵魂的可能性理论的名单。这些隐士凭借直觉或沉思获得某种力量而没有达到最高状态。“所谓的‘六十二见’显然是系统说明隐士或思想家的经验,而很少涉及那时的观点。或许在‘六十二见’中的某些观点和体现在奥义书中的哲学教义之间稍许有些一致之处,但不能确定这部经的撰写是针对它们的,一致的原因或多或少是偶然的。”[192]然而,按照G.C.般代,虽然“毫无疑问,这部经归功于佛教的系统化,但要接受达多的观点,需要用以下事实予以修订:(1)在《梵网经》中提到的一些观点能表明是非佛教思想家实际持有的。(2)按照这部经本身,应该相信有些观点出自理性思辨,而非特殊的神秘经验。(3)许多‘佛教僧侣的经验’与某些或其他非佛教思想家的经验是同样的”[193]。
无论如何,人们可以同意达多(N.Dutt)所说《梵网经》已经用于两个目的:消除我们头脑中对于世界和灵魂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提醒我们不要以先入为主的观念解释佛陀的学说。例如,可以指出自我  作为一种永恒的和纯洁的实体存在于我们的体内,不受我们的行为(“业”)影响,这种观念很可能会歪曲佛经中关于
作为一种永恒的和纯洁的实体存在于我们的体内,不受我们的行为(“业”)影响,这种观念很可能会歪曲佛经中关于 (“自我”)和puggala(“人”)的真正含义。同样,断灭说(
(“自我”)和puggala(“人”)的真正含义。同样,断灭说( 或 natthatta)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无我”
或 natthatta)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无我” 或“空性”
或“空性” 学说的解释。作为一个典型例子,达多引用《中尼迦耶》,讲述一个永恒论者听了佛陀教导通过灭除激情、欲望和邪见等获得涅槃,便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佛陀是一个断灭论者[194]。
学说的解释。作为一个典型例子,达多引用《中尼迦耶》,讲述一个永恒论者听了佛陀教导通过灭除激情、欲望和邪见等获得涅槃,便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佛陀是一个断灭论者[194]。
沙门和婆罗门
早期佛教时代的宗教派别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前者称为正统派 ,后者称为非正统派
,后者称为非正统派  。正统派或婆罗门教派并不意味有神论教派。它表示这些体系确认吠陀及其分支为至高的权威。例如,数论通常被认为是无神论哲学,而仍然是一种婆罗门教体系,因为它接受吠陀的权威
。正统派或婆罗门教派并不意味有神论教派。它表示这些体系确认吠陀及其分支为至高的权威。例如,数论通常被认为是无神论哲学,而仍然是一种婆罗门教体系,因为它接受吠陀的权威  。佛教和耆那教被认为是非正统派或非婆罗门教派,因为他们不接受吠陀经典的权威。摩奴将“非正统派”界定为挑战吠陀权威者
。佛教和耆那教被认为是非正统派或非婆罗门教派,因为他们不接受吠陀经典的权威。摩奴将“非正统派”界定为挑战吠陀权威者  。按照另一种观点,正统派是相信存在未来世界等。按照这种解释,佛教和耆那教不是非正统派。著名的佛教学者龙树
。按照另一种观点,正统派是相信存在未来世界等。按照这种解释,佛教和耆那教不是非正统派。著名的佛教学者龙树  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说“非正统派必定下地狱”。这样,将佛教和耆那教称为非正统派,便成为一种误称。他们宁可被称为“非吠陀派”(avaidika)。
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说“非正统派必定下地狱”。这样,将佛教和耆那教称为非正统派,便成为一种误称。他们宁可被称为“非吠陀派”(avaidika)。
佛教和耆那教文献似乎将所有的非婆罗门体系称为沙门,通常的用语是 (“沙门或婆罗门”)。在那个时代,这是共同的实践,即一个人想要过出家人生活,想到凭他个人的努力不能认识真理,于是拜师求道。这样的导师身边围绕有大批信徒,王舍城优楼频螺和珊阇夜的那些束发者导师便是明显的例子。在《妙吉祥光》
(“沙门或婆罗门”)。在那个时代,这是共同的实践,即一个人想要过出家人生活,想到凭他个人的努力不能认识真理,于是拜师求道。这样的导师身边围绕有大批信徒,王舍城优楼频螺和珊阇夜的那些束发者导师便是明显的例子。在《妙吉祥光》 [195]中,沙门明显不是那些出身婆罗门家庭而抛弃世俗生活的人,同时婆罗门是那些出身婆罗门家庭而对宗教和哲学比对世俗事务更感兴趣的人。在波你尼
[195]中,沙门明显不是那些出身婆罗门家庭而抛弃世俗生活的人,同时婆罗门是那些出身婆罗门家庭而对宗教和哲学比对世俗事务更感兴趣的人。在波你尼 [196]、钵颠阇利
[196]、钵颠阇利  [197]、梅伽斯梯尼(Megasthenes)[198]的著作以及阿育王铭文[199]中,被发现婆罗门和沙门这两个词结合使用。按照钵颠阇利,沙门和婆罗门属于两个对立的群体。在佛经中,“出家人”
[197]、梅伽斯梯尼(Megasthenes)[198]的著作以及阿育王铭文[199]中,被发现婆罗门和沙门这两个词结合使用。按照钵颠阇利,沙门和婆罗门属于两个对立的群体。在佛经中,“出家人” 和“苦行者”(tapassino)一般指称沙门。在《破戏论》
和“苦行者”(tapassino)一般指称沙门。在《破戏论》 中,一个活命派圣人被称为沙门[200]。耆那教和佛教通常使用“沙门”一词指称所有的非婆罗门教苦行者。
中,一个活命派圣人被称为沙门[200]。耆那教和佛教通常使用“沙门”一词指称所有的非婆罗门教苦行者。
婆罗门和沙门之间的对立如此尖锐,以致被钵颠阇利说成是类似蛇和猫鼬或猫和老鼠的关系[201]。婆罗门深深嵌入共同体,不能作为共同体外的另类存在。而沙门和弃世者刻意脱离社会,反映在奥义书和梵书中,他们的主要意图是摆脱社会义务而思考和行动。这些群体的成员一般限定为高级种姓,而进一步保持距离[202]。而沙门——尼乾陀派、活命派、佛教和其他派别——选择一种中间道路。在一个层面上,他们抛弃社会,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他们又回到社会,依靠居士共同体[203]。事实上,佛教居士( ,“优婆塞”)信众在支持教团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反过来,比丘给予他们帮助。出于对活动基地的需求,比丘依靠居士共同体建造寺院。在这方面,各种新教派以及他们与婆罗门之间存在竞争。在意识形态层面存在对抗,同时在接受赞助层面存在竞争。而他们最大的怒火直接针对斫婆迦派
,“优婆塞”)信众在支持教团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反过来,比丘给予他们帮助。出于对活动基地的需求,比丘依靠居士共同体建造寺院。在这方面,各种新教派以及他们与婆罗门之间存在竞争。在意识形态层面存在对抗,同时在接受赞助层面存在竞争。而他们最大的怒火直接针对斫婆迦派  或顺世论派
或顺世论派  ,因为后者甚至嘲讽僧侣的用处[204]。
,因为后者甚至嘲讽僧侣的用处[204]。
婆罗门和沙门对待苦行的态度基本不同。这些不同出自他们对社会和道德问题的一般看法。早期的吠陀文献中含有印度人道德意识的最初表达。在这里,我们发现强调意志、选择和行动,强调依照宇宙规律或法则  指导他们的必要性。法则
指导他们的必要性。法则 或正法(dharma)的概念逐步结晶成三种具体的社会秩序——种姓制度、生活阶段以及家庭经和天启经仪轨[205]。我们已经讨论种姓制度的演化,也已经讨论原先只是确认前两种个人生活阶段,然后接受第三种林居生活阶段,这是仪式衰微和沉思
或正法(dharma)的概念逐步结晶成三种具体的社会秩序——种姓制度、生活阶段以及家庭经和天启经仪轨[205]。我们已经讨论种姓制度的演化,也已经讨论原先只是确认前两种个人生活阶段,然后接受第三种林居生活阶段,这是仪式衰微和沉思 流行的结果[206]。确认第四种生活阶段的时间较晚,而且十分勉强,旨在适应那些人,他们已经开始相信与一个人的“业”一致的再生这种出世的悲观主义意识形态,而且这些人的数量日益增长。同样,早期的吠陀社会只是设定三种人生目的(trivarga),即追求符合正法(dharma)的爱欲
流行的结果[206]。确认第四种生活阶段的时间较晚,而且十分勉强,旨在适应那些人,他们已经开始相信与一个人的“业”一致的再生这种出世的悲观主义意识形态,而且这些人的数量日益增长。同样,早期的吠陀社会只是设定三种人生目的(trivarga),即追求符合正法(dharma)的爱欲  和利益(artha)。而在这三种人生目的上增加解脱
和利益(artha)。而在这三种人生目的上增加解脱  作为最高的人生目的,从而出现四种人生目的(caturvarga或
作为最高的人生目的,从而出现四种人生目的(caturvarga或 )。这种发展显然源自奥义书思想家确认获得梵为人生至善。
)。这种发展显然源自奥义书思想家确认获得梵为人生至善。
然而,从实际的观点看,人对于从社会和诸神那里获得恩惠予以回报的义务继续成为吠陀社会伦理的基石[207]。与此对照,沙门主义削弱人对诸神的依赖感,并打击社会义务说。它用业力取代诸神,人获得什么并不归诸诸神,而归诸他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而,因为人不能逃避他的行为的道德结果,他必须摒弃个人主义和暴力等这些主要罪恶,而追求道德。因此,在各种苦行宗教及其派别的寺院戒律文献中,可以发现他们的苦行主义理想的具体形式。这些戒律用于规定食物、饮料、衣服、住处、乞食和僧侣的宗教实践乃至微小的细节。这些苦行派别甚至也为男女居士制定戒律,虽然在性质上不很严格。例如,耆那教为僧侣制定《大戒》 ,而为居士制订《小戒》
,而为居士制订《小戒》 。同样,佛教《长尼迦耶》的《悉迦罗经》
。同样,佛教《长尼迦耶》的《悉迦罗经》 讲述“家主戒律”(gihivinaya),即佛教居士的戒律。而在讲述家主的责任时,沙门教派更强调社会义务。
讲述“家主戒律”(gihivinaya),即佛教居士的戒律。而在讲述家主的责任时,沙门教派更强调社会义务。
婆罗门奉吠陀为圣典,允许一个人成为弃世者,仅仅在他经历前三个生活阶段之后,因为在这三个阶段,他已经完成对社会的所有义务。按照这种理论,只有再生族(dvija)能成为出家人 [208]。而沙门一般不太考虑年龄或种姓。佛陀认为正如许多河流流入大海后,失去它们各自的身份,同样,一个人无论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或首陀罗,一旦寻求他的僧团庇护,也就放弃各自先前的名字、族姓(gotra)或种姓
[208]。而沙门一般不太考虑年龄或种姓。佛陀认为正如许多河流流入大海后,失去它们各自的身份,同样,一个人无论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或首陀罗,一旦寻求他的僧团庇护,也就放弃各自先前的名字、族姓(gotra)或种姓  [209]。苦行者通常生活在森林中,尽可能避免与社会接触,只是为了乞食或受到邀请而前往村庄。他们从一处向另一处游荡。如果佛陀连续三季停留在一处,就会招致社会不满和斥责。然而,在雨季,苦行者们生活在一起。这称为“雨季安居”
[209]。苦行者通常生活在森林中,尽可能避免与社会接触,只是为了乞食或受到邀请而前往村庄。他们从一处向另一处游荡。如果佛陀连续三季停留在一处,就会招致社会不满和斥责。然而,在雨季,苦行者们生活在一起。这称为“雨季安居”  。雨季安居和雨季结束时的“自恣”
。雨季安居和雨季结束时的“自恣” 已经形成习惯。按照《大品》,每个苦行派别的信徒在双周第八、第十四和第十五日集会,进行教义讨论,居士们前来聆听[210]。这种仪式称为“布萨”(
已经形成习惯。按照《大品》,每个苦行派别的信徒在双周第八、第十四和第十五日集会,进行教义讨论,居士们前来聆听[210]。这种仪式称为“布萨”( 或upavastha),甚至在婆罗门教的仪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经由频毗沙罗的提示而引入佛教僧团的。
或upavastha),甚至在婆罗门教的仪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经由频毗沙罗的提示而引入佛教僧团的。
这些苦行派别对待不杀生和非世俗性等有基本相同的看法,但在衣服、食物、托钵和寺院生活细则方面互相不同。他们穿戴不同类型的衣服,同时有的抛弃所有衣服,选择裸体生活。佛教允许使用三件衣服。大雄自己抛弃所有衣服,但允许他的信徒穿一件衣服,由此他们被拘萨罗派称为“单衣派” 。关于托钵,佛教允许使用铁制或陶制。而活命派谴责使用托钵,只用双手接受乞得的食物。关于接受的食物,各派之间也有不同。婆罗门苦行者不接受甜食,仅仅接受那些自动脱落的植物。活命派可以接受冷水、不煮熟的种子和特别准备的食物,而耆那教禁止所有这三种。然而,佛教徒可以接受任何食物,但一天只能乞食一次,并且在正确的时间。关于接受其他物品如火炬、木杖和水罐等,也有不同观点[211]。
。关于托钵,佛教允许使用铁制或陶制。而活命派谴责使用托钵,只用双手接受乞得的食物。关于接受的食物,各派之间也有不同。婆罗门苦行者不接受甜食,仅仅接受那些自动脱落的植物。活命派可以接受冷水、不煮熟的种子和特别准备的食物,而耆那教禁止所有这三种。然而,佛教徒可以接受任何食物,但一天只能乞食一次,并且在正确的时间。关于接受其他物品如火炬、木杖和水罐等,也有不同观点[211]。
佛陀时代的沙门派别中,佛教和耆那教占据主要地位。与他们同时的其他派别没有留下独立的文献资料。他们经常在佛陀和大雄的说法中受到批评。然而,佛教和耆那教经文中常常不呈现他们最好的方面,也可能常常不正确地描述他们的学说。所有这些派别似乎有以下共同特点。
(1)他们挑战吠陀权威。
(2)他们允许任何人加入他们的团体或僧团,不考虑种姓或生活阶段。
(3)他们遵守一套伦理规范。
(4)他们奉行脱离世俗的生活,追求摆脱世界的束缚。
(5)他们能在童年之后就过出家生活  。
。
虽然像婆罗门那样,沙门奉行乞食( ,“比丘行”),而在沙门传统中,梵行
,“比丘行”),而在沙门传统中,梵行  有不同的含义。在婆罗门中,“梵行”一词开始时意味遵守某些规则,要求学习吠陀。在一个老师身边学习者称为“梵行者”
有不同的含义。在婆罗门中,“梵行”一词开始时意味遵守某些规则,要求学习吠陀。在一个老师身边学习者称为“梵行者” 。人的第一生活阶段称为“梵行期”。但是,在奥义书时代,梵(brahman)意味最高真理。因此,这时的梵行表示一种旨在获得最高真理的特殊生活方式[212]。在沙门传统中,“梵行”这个词也表示获得最高真理的生活方式。这样,这个词的原始意义表示生活阶段,而现在在苦行规则的背景下,新的意义表示精神的努力和培养,适用于任何种姓出身的人。在佛教文献中,一般使用这后一种意义。追求真理的沙门在这个阶段的生活自然不是轻松的。它包括食物、衣服和住处等方面的艰苦,这导致相信自我折磨和严酷的苦行是解脱的唯一源泉。提婆达多(Devadatta)要求在佛教僧团中引入更严格的戒律,其动机可能出自真切感受到当时围绕他的社会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佛教寺院的戒律显得相当世俗和宽松[213]。耆那教依据他们自己的立场,指责佛教徒生活奢侈,因为佛教的“中道”说倾向减弱梵行中的艰苦性。
。人的第一生活阶段称为“梵行期”。但是,在奥义书时代,梵(brahman)意味最高真理。因此,这时的梵行表示一种旨在获得最高真理的特殊生活方式[212]。在沙门传统中,“梵行”这个词也表示获得最高真理的生活方式。这样,这个词的原始意义表示生活阶段,而现在在苦行规则的背景下,新的意义表示精神的努力和培养,适用于任何种姓出身的人。在佛教文献中,一般使用这后一种意义。追求真理的沙门在这个阶段的生活自然不是轻松的。它包括食物、衣服和住处等方面的艰苦,这导致相信自我折磨和严酷的苦行是解脱的唯一源泉。提婆达多(Devadatta)要求在佛教僧团中引入更严格的戒律,其动机可能出自真切感受到当时围绕他的社会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佛教寺院的戒律显得相当世俗和宽松[213]。耆那教依据他们自己的立场,指责佛教徒生活奢侈,因为佛教的“中道”说倾向减弱梵行中的艰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