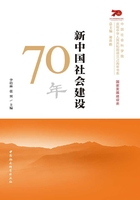
第五节 计划生育与未来人口政策改革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在实践中“试错”,又在实践中“纠偏”的政策。从最初的节制生育,到后来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再到20世纪80年代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最后发展到现在的“全面二孩”政策,经历了反思性的回归过程。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生活资料供给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压力性矛盾,也伴随着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与家庭计划生育偏好之间的矛盾,更伴随着学术界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和政府对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性的坚守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运动的过程,型构了人口发展与结构变化过程,也成为将结婚、生育这种家庭行为与生育率这个政府控制指标的连接纽带。由此串接成一幅将个人、家庭、企业、社会、政府等有效地捆绑在一起的波澜社会史,显现出了新中国70年发生的最宏大的社会变迁。
不管是节制生育,还是计划生育,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缓解人口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压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二战”之后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 “二战”之后的“人口爆炸”,也是世界人口史上发生的短期内规模最大的“人口爆炸”。中国为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不得不选择了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之路。
实际上,在“大国办大事”体制下,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增速,有效缓解了人口存量和人口增量对生活资料的供给压力,提升了百姓的生活水平,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基本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工业体系,完成了GDP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再向以后工业为主的转变过程。计划生育缩小了家庭规模,减轻了家庭育儿压力,使家庭有能力积存资金,并将这些资金集中使用在孩子身上,顺利推进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相继提高了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促使中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计划生育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在冥冥之中消解了盛行整个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思想,增加了女童和女青年在各个年龄段的入学率,从而提升了女性的人力资本,缩小了教育、就业和职业方面的性别差距。计划生育也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同时,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少儿负担系数,减轻了抚养成本,促进了社会发展。计划生育与孕期检查,迅速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保障了胎儿的健康孕育,降低了出生缺陷率。计划生育还延长了女性的就业时间,改善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力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计划生育在城市和乡村的政策性区别,大大加快了城市的老龄化水平,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民工进城预设了劳动力人口的需求空间,加快了中国的城镇化速度。总之,计划生育的客观结果,在计划生育执行的后期渐显其积极意义,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人口红利。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时期——尤其是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时期,以缩减的劳动力态势降低了失业率,减轻了国家的治理成本,在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时期形成过渡期,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转型成本,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人口转型或人口转变,在发生正功能的同时,也在潜在衍生负功能,并越来越强烈地显现负功能。人口实践证明,由人口转变制造出正功能的速度越快,其迎来负功能的可能性也就越快。人口的转型,是社会发展与计划生育两个因素促进的转型。政府和学术界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重视了政府之手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市场和社会之手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起抑制的人口增长,逐步减少了后来的劳动力人口供给,并在2000年之后逐渐出现劳动力人口连年净减少的问题,从2018年开始出现就业人口净减少的问题。当前的人口老化,就是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连年少生的结果,使中国成为世界人口史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政府促动的计划生育与家庭对男孩的需求之矛盾,也造成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现在正通过人口流动以放大其负面影响的方式形成了婚姻挤压。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家庭网和亲缘网支持体系,在家庭的小型化过程中逐步弱化,使社会不得不建构新的支持体系以缓解不良事件的冲击。那种认为一旦政策放开就能够打开人口生育阀门的幻想,已被现代化和现代性无情击碎。从世界各国人口干预效果上得出的唯一可靠的结论是:政府能够有效降低生育率,但却很难通过刺激提升生育率。因为鼓励生育的政策实施成本远远大于抑制生育所投入的政策成本。《公开信》中所说的要在2000年把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目标没有实现,但认为“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之后才会出现”的判断却出了问题——从2000年开始中国65岁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达到7%左右,2018年已经达到11.9%(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7.9%)。部分计划生育执行较严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户籍人口已经过渡到老龄型阶段(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4%)。2018年北京市户籍人口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25%——对于这类城市来说,其如果离开流动人口中的劳动力人口,将很难正常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现在及未来一个时期,伴随高生育时期人口进入退休年龄,老龄化速度会加快。尤其是在人口金字塔顶部的老化和底部的收缩中发生的老化,其负面影响会更为严重,中国将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时期步入更快的老龄化过程。在人口红利消退之后,中国将在人口老化速度与科技进步速度之间展开长久的赛跑,如果科技进步跑赢人口老化速度,则发展将比较顺利;如果老化速度跑赢科技进步速度,则发展战略就需要长期进行波动性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人口政策将不得不在以下方面进行实质性改革:
第一,适时废除《计划生育法》。在叫停《计划生育法》的同时,废除社会抚养费征缴制度,清理整个法律法规及政府文件中限制生育的条文,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或放松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为自由生育政策。虽然现代化水平越高,人类的生育率会越低,但终有一些夫妇存在生育孩子的偏好——这些生育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断崖式下跌的生育水平,平缓人口下降趋势。
第二,适时出台“失独家庭保障条例”。对于那些在计划生育过程中响应国家号召,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认领了独生子女证的,独生子女又出现意外伤亡的脆弱家庭,提供人道主义支持。尤其是对于逐渐进入老年失能阶段的失独家庭,必须提供与时代发展水平相一致的保障支持。
第三,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社会公共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真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弱有所扶“七有”号召,建立家庭友好型社会或生育友好型社会。如果幼儿园入园价格畸高、学习费用难以降低、劳动收入差距不能缩小、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不到解决、养老压力加大、住房价格高企、脆弱群体得不到扶持,则生育率就很难回升。
第四,在全国建立免费的公立幼儿园。普及公立幼儿园,鼓励民营企业兴办托儿所或幼儿园,政府购买入园位。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制定差额入园费,即对低收入水平家庭免除入园费或少交入园费。等到国力发展到既定水平,则实行公立幼儿园完全免费的政策。减轻家庭育儿压力。
第五,以家庭为单位建立个税征缴体系。对以夫妇方式报税的,或者对以携带子女生活家庭方式报税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个税税负,或提高个税起征点。对生育了第二个子女的家庭,进一步降低税负。对生育了三个及三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实行负所得税制,即对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某一标准的多子女家庭,将其收入补足到核定标准。
第六,鼓励地方政府出台刺激生育政策。采取先实验再普及的方式,率先在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这类户籍人口老龄化水平畸高的地区出台刺激生育政策,为新出生的幼儿提供生活补贴费用。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可以为生育第二孩的孩子实行既定额度的生活补贴政策。
第七,实行非婚生子女合法化政策。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都应该一律平等对待。在离婚率迅速上升、结婚年龄逐渐推迟、社会的个体化背景下,不再以婚生为生育的基本合法单位,给予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平权身份和地位。
第八,积极发展人工智能等机器人。提高生产效率,缩短工作时间、减轻劳动过程的人力消耗,延长假期、提升生活质量。从发达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实践可以看出,即使出台成本极高的鼓励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也很难上升到2.1的更替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从长远发展动力之激发计,需要集中力量开发机器人,并发展机器人替代人力的各种技能,在人口老龄化逐渐加深的背景下,保障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通过人机互动或人机社会的建设,减轻养老压力,增加新动能,争取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以上建议可以概括为“三步走”的人口政策:第一步,在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之后废止原有限制生育的政策。第二步,在2021—2025年实行家庭友好型社会建设,逐步但富有实效地减轻父母的育儿成本。第三步,2026年之后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先从第二孩开始为未成年子女提供一定生活补贴及其他可能的社会服务,从育龄妇女的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刺激生育。
[4]1950年国家内务部公布的全国(包括台湾)人口数是4.8亿左右,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是4.83亿左右。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中国人口总量为4.75亿。
[6]参见1978年10月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
[7]张翼:《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化与改革趋势》,《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8期。
[9]1979年马寅初获准平反昭雪。他在《新人口论》中主张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