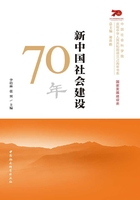
第四节 低生育水平的维持及人口政策的调整(2001—2018年)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如果能够理智看待普查得到的极低的总和生育率这个数据,正确估计计划生育制度的强制性实施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可能就不会出台,即使出台也不会是现在这种表达的文本结构。可惜的是,政府仍然怕人口形势出现反复,还希望继续下大力气巩固来之不易的结果。于是,2001年12月颁发了这一法律[11],并言明“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城市、乡镇、农村地区,根据户籍人口的稠密程度并照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形成了以下格局:在全国的城镇地区以及4个直辖市加江苏和四川等地的农村,对汉族居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除以上各省市之外的农村,如果第一胎生育的是女孩,可以安排五年后再生育一个孩子;但也有5个省和自治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如果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则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对人数比较少的少数民族实行更宽的生育政策。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总和生育率只有1.22,这个结果与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结论的趋势高度一致。但学术界还是有人怀疑这个数据,政府有关部门也对此持怀疑态度。这就出现了国家统计局与国家计生委各说各话的现象。国家统计局坚持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很高,国家计生委坚持说漏报影响了总和生育率的结果。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继续表明,总和生育率为1.34。为什么这个数据高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这个数据给怀疑派以部分支持。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再次证明数据所呈现的趋势的稳定性,即该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其中城市为0.88,乡镇为1.15,农村为1.43。虽然有关部门仍然选择怀疑这个数据,但学术界越来越多地开始相信这些数据,或者开始怀疑原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在人口研究领域比较有影响的两个杂志(《中国人口科学》和《人口研究》)中发表的文章,2010年之后几乎都会涉及人口政策的改革这个话题。
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再一次证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仅仅为1.047,但仍然没有人相信这个数据是真实的。有关这些的争论仍然在进行。
表1—4 1960—2017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 locations=CN,国家统计局数据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或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整理。
但中国中央政府逐渐接受了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施“夫妇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即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4年初,各省人代会陆续通过了新的计划生育条例,开始实施新的人口调控政策。受此政策影响,通过表1—5可以看出,2014年全年出生人口数量达到1692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1687万),这个数据高于2013年的1644万。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2015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却下降到1659万,低于2014年。“单独二孩”人口政策的红利仅仅释放了一年。于是,2015年底中共中央快速反应,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2016年1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生育二孩无须审批,家庭完全可以自主安排生育。
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上升到1791万(国家统计局公布数为1786万),比2015年增加了131万。但政策红利并没有像很多预测所预期的那样继续增加,2017年出生人口数又降低到1728万(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是1723万)。很多人解释说由政策红利产生的生育高峰有可能在2018年出现,但2018年出生人口数又开始下降,只有1527万(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是1523万)。
表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净增人口数 单位:‰、万人

表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净增人口数 单位:‰、万人续一

表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净增人口数 单位:‰、万人续二

资料来源:1978—2015年数据来自2016年《中国人口与劳动统计年鉴》, 2016—2018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净增人口数据根据总人口与相应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增率计算得出。因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由四舍五入得出,故这里计算得到的数据与统计局公布的确切数据稍有出入,但差距很小。
为什么政策放开了,人口出生率却继续下跌呢?其中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每年的结婚对数持续降低。也即是在1980 年“公开信”发表之后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期出生的女性进入结婚生育年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差不多都在2300 万左右,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每年新出生的人口数量就降低到1900 万到2100万之间,而且呈现越来越低的趋势。等到“85后”和“90后”开始结婚时,每年初婚的结婚对数就开始急剧下跌,比如说,2013年初婚对数为1341.13万对,2014年初婚对数降低到1302.04万对, 2015年初婚对数降低到 1220.59 万对,2016 年初婚对数降低到1138.61万对,2017年初婚对数继续降低到1059.04万对[12], 2018年包括了再婚对数的结婚对数只有差不多1010万对——初婚对数已经不足1000万对。初婚对数的降低,不仅会降低初婚后的出生率,还会在长期趋势上降低整个社会的出生率。
第二,每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人数日益降低。现在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恰好是原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时期出生的人口,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人口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对应出生的男婴数迅速上升,打破了原有的相对平衡特征。[13] 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口出生性别比的上升,使这些出生队列进入婚姻期之后的女性适婚年龄人口不足,这会导致一部分男性因为找不到配偶而难以结婚生育。根据2017年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15—19岁年龄段的性别比是117.70, 20—24岁年龄段的性别比是110.98, 25—29 岁年龄段的性别比是104.47。如果15—19岁年龄段人口进入婚育旺盛期,结婚难、结婚贵的问题还会趋于严重。但最严重的影响,是降低了婚育年龄段的女性人口数,一方面加大婚龄年龄段男性的结婚压力而形成婚姻挤压,另一方面也会降低出生率,使每年新出生的第一胎生育人口数量趋于减少。在整个新出生人口中,由育龄妇女的存量所生产的二孩比重已超过50%。
第三,离婚率上升与初婚年龄推迟。城镇化、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后工业化与女性收入的增长以及常态化的人口流动等,一方面提升了离婚率,另一方面也推迟了女性人口的初婚年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先是普及了义务教育,接着又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进入21世纪绝大多数地区都提升了高中阶段教育的入学率[14],最近又迅速提升了大学毛入学率。1978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仅为1.55%, 1988 年是 3.7%; 1999 年大学扩招,2002 年上升到15%, 2007年达到23%, 2010年达到26.5%, 2018年达到48.1%, 2019年超过50%,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从大众教育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这些因素使女性初婚年龄迅速推迟,从1990 年到2017 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1.4岁推迟到25.7岁。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升到26.8岁。在某些大城市、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会更迟,在上海或北京,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甚至推迟到29岁或30岁左右。初婚年龄的推迟必然继替性地提升初育年龄,缩短婚龄女性的生育期,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出生率。
第四,生活成本的上升降低了生育愿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步入了快速城镇化的轨道。在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仅仅为17.9%,但到2018年底上升到59.6%左右。城镇化并不会均等地将各个年龄段人口都移入城市,而是有选择地将那些年纪较轻、劳动就业能力较强的人率先吸纳进城市,而这部分人口又恰恰是婚育旺盛人口。可最初城镇化的年轻人,一方面需要照顾家乡的老人(计划生育减少了这些出生队列的兄弟姐妹数量,加大了他们的养老负担),另一方面还需要养育自己的子女,满足当前的生活消费需要。但城市房价的上升,消费品价格的坚挺,使得他们的生育意愿难以提升。在避孕工具日益多样化和便捷化过程中,意愿生育率的降低直接削减了现实出生率。
第五,有待改善的生育环境抑制了整个社会的生育需求。“单独二孩”政策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之所以难以释放出持续性的生育红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深受入托难、入学难、就业难、育儿难、看病难等现实问题的影响。家庭的小型化和流动化,以及“80后”结婚之后家庭观念和生活观念的变化,使原来依靠父母亲照顾小孩的支持体系有所减弱。家庭保姆价格的上升,也使一般青年夫妇很难雇得起保姆照顾小孩。工作场所严明的纪律与长时间的加班等,缩短了青年一代的闲暇时间,也很难使现在的青年一代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孩子。孩子从出生到上学直到大学毕业,期间的花费居高不下。孩子要结婚,还得买房或添置嫁妆。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务工经商,但没有完全转变为城市市民,户籍制度还没有回归人口信息登记功能,城市公共服务还难以均等化。因此,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家庭生活领域,还需要继续建构有利于生育的家庭友好型社会。
正因为如上所述问题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实际生育率还大大低于政策生育率。而一旦一个国家或社会陷入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5或1.4的低生育陷阱,则这个社会或国家就很难跳出低生育陷阱,并持续性地处于低生育陷阱之中不能自拔,从而影响人口的年龄结构和赡养结构,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缩小支撑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形成畸高的养老金负债压力,使人口从红利阶段过渡到负债阶段,形成未富先老格局,滑落到易于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口结构。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中,人口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同构发生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两个陷阱又互相影响,形成有增长但无发展的局面,出现低水平重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