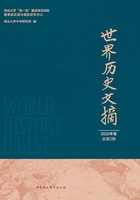
回归乡土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现代化危机
邢来顺[1]
摘要:德意志帝国时期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现代与传统的剧烈碰撞,形成“现代化危机”。传统乡土作为人们童年记忆中的安全之地,成为他们躲避“现代化危机”的本能选择,由此催生了精神文化和社会领域以回归传统乡土为取向的乡土运动。可以说,回归传统乡土就是人们用来化解“现代化危机”的一种传统取向的求解。回归传统乡土不仅给怀念前现代乡土生活形态的人们以精神慰藉,使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的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得到一定的保护,而且促进了德国文化和自然景观保护传统的形成,对于构建和谐合理的传统与现代关系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德意志帝国 现代化危机 乡土运动
在当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的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可谓独树一帜。它起步晚,19世纪30年代中期才开始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2]但进展快,到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8年)就完成了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变,由传统农业国一跃成为引领性现代工业化国家,并且实现了城市化。[3]
然而,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并非只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快速进步,相伴而来的还有现代与传统剧烈碰撞引发的诸如传统乡土衰落等各种问题。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速现代化让许多原本悠然于传统生活形态中的人们难以适应。他们渴望在精神和社会层面寻找一种缓冲空间,对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行反思和调适。于是,人们所熟悉的前现代传统乡土社会,作为曾经的安逸生活的原点和情感落点,成为大众注满思念和牵挂的乡愁所在,也成了人们平衡和抵御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及其带来的诸多问题的精神和社会堡垒。人们渴望回归记忆中田园诗般的地方乡村,躲避现代工业城市中紧张而动荡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希望能够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中保存所熟悉的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这些现实压力和情感需要就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以回归传统乡土为取向的乡土运动(Heimatbewegung)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乡土运动作为德意志帝国时期应对“现代化危机”的一场广泛的精神和社会运动,在欧美史学界不无关注。然而由于它涉及精神、文化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相关研究关注视角也不尽一致。美国等国学者侧重于探究德国人的“乡土”观念以及“乡土”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例如,著名文化学者西莉亚·阿普尔盖特(Celia Applegate)以考察德国人乡土概念演变为出发点,认为德国人的“乡土”带有一种“共同所属的情感”表达,既有民族国家的内在意涵,也带有地区属性的烙印;著名学者阿隆·康费诺(Alon Confino)则认为德国人的“乡土”就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地方隐喻”。[4]而德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则大都基于某种具体视角的考察。其中温弗雷德·施派特坎普(Winfried Speitkamp)主要从纪念物等传统文化保护和维护的角度论及德意志帝国时期“有组织的乡土运动”;托马斯·洛克莱梅尔(Thomas Rohkrämer)等学者则站在“文明批判”的角度,将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视作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至上”价值观的一种抵制;而赫布斯·伊沃·恩格尔斯(Hebs Ivo Engels)等学者则主要从自然保护的角度溯及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视其为德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发端。[5]
笔者以为,德意志帝国时期以回归乡土为取向的乡土运动绝不仅仅是一种乡愁乡思乡情的简单宣泄或是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认同表达,也不只是一场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保护运动,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与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为应对“现代化危机”的一种传统取向的求解,是人们希望通过精神和社会层面回归乡土,安抚、消解由于经济、社会和生活领域急速现代化带来的阵痛和不适。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一运动对于日后德国人构建传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科学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拙文拟从以上视角,尝试着对德意志帝国时期乡土运动的动因、实践及其历史影响进行审视和探讨。
一 高速工业化城市化与乡土传统的沦陷
任何一种重要历史现象,都有其内在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就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而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危机”则是其主要根源。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德国经济出现了跳跃性增长,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对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无所顾忌的扩张提出质疑,对一味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而罔顾乡土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希望能够重新审视传统与发展的关系。
实际上,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高涨之时,保守派社会学家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就已经从传统角度“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进行批判”,对正在展开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出了批评。他指责现代工业化“瓦解了整个社会的各种独特的历史职业,从根本上将各种社会等级的差别匀化为单一的结构特性”。[6]他也反对现代城市的快速扩张。他认为快速城市化正在使德国的城市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城市“趋同”,并因此而失去“鲜明的民族特性”;同时他也批评城市化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耗尽传统乡村的生命血液。这不仅会动摇着作为“德意志的真正民族性”所在的乡村的基础,而且会造就一批庞大而危险的“无根”城市无产者。[7]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受益于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和法国巨额战争赔款等有利条件,加之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以新兴电能、内燃机和合成化学等新兴产业,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跳跃性发展,传统乡村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结构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以“现代化危机”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愈加凸显,并因此引发人们对于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更广泛、更深刻的反思性“文明批判”。[8]
德意志帝国时期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酿成的最突出“现代化危机”在于,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工业地区和城市,乡村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在工业发展和城市迅猛扩张中遭到损毁,乡村地区因此陷入快速衰败之中。
由于受到工业地区和城市中更多工作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吸引,德意志帝国时期出现了普遍的“逃离农村”(Landflucht)现象。大量农村人口纷纷离开家乡,向工业地区和城市迁移。总体上看,东部的东、西普鲁士、南部的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等农业地区的人口都出现了负增长,而西部的威斯特发伦、莱茵兰等工业地区和柏林等城市的人口则大幅度增长。根据1900年德国国内人口迁徙统计结果,东、西普鲁士和波森三个农业省份分别净迁出人口45.19万、18.53万和32.21万人,而工业发达的威斯特发伦和莱茵兰则分别净迁入人口26.01万和29.17万,拥有大都市柏林的勃兰登堡更是净迁入97.74万人。[9]这一统计还不包括本地区内部乡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失还可以从城市人口扩张中窥见一斑。著名煤炭和钢铁工业中心多特蒙德1870年仅有居民5.14万人,1913年则增长到了39.46万人。其新增人口主要来自迁入人口。而大都市柏林1907年的约200万人口中,流入人口竟然占将近60%。从大城市数量的增长看,1871年德国超过10万人口的大城市只有8个,1910年达到了48个。[10]这显然不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能解释的。
大量人口逃离农村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许多村庄因人口锐减而空心化,甚至一些中心乡镇也因此受到影响。很多乡镇学校因此而学生人数减少和师资萎缩,有些乡镇由于人手不足还出现了身兼多职的“全面型”官员。[11]农村经济更是因为劳动力流失而大受影响,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危机形势”。[12]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萎缩,由1870年的40.5%快速下滑至1913年的23.2%。[13]
传统乡村景观也在城市和工业企业的不断扩张中遭到破坏甚至消失。研究表明,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不断扩张曾引发巨大的“土地消费”。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为了满足工业的发展和大量人口流入的需要,1877—1910年间先后进行四次行政区域的并入和扩张,城市面积由7005公顷扩大到13477公顷。由于城市建设用地量极大,在弗兰茨·阿迪克斯(Franz Adickes)担任市长期间,曾通过了专门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地块分配法”,即“阿迪克斯法”(Lex Adickes),用以规范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其他城市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突破老城区地界向周围乡村扩张的模式,以便建立新的工业区,或建设近郊聚居区,安置大量新涌入的人口。[14]城市大规模向外快速扩张的直接结果就是周边大量传统乡村景观遭到破坏和损毁。大量为人熟知的传统乡土景观的快速消失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的失落感,“景观损毁”(Landschaftszerstörung)于是成了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乡村“普遍衰落”又一的重要证据。[15]
以上种种使人们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感觉,即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让传统“农村家乡”变成了“一个衰落概念”。[16]而乡村的衰落对于已经习惯于前工业社会生活形态的人们而言,显然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农民生活和农业经济才是一种理想化形态,农村生活也是最幸福的。国家和社会的繁荣首先取决于农民阶层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健康。[17]而今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大量农民逃离乡土和农村空洞化,毁灭传统乡村景观和文化,因此自然成了他们“批评的焦点”。[18]
德意志帝国时期“现代化危机”的又一体现是,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传统乡村生活中不曾有过的诸种严重“社会问题”。
工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直接职业危害是当时非常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时期正处于工业化黄金时代,人们完全沉浸于创造财富的喜悦中,过于追求工业的高增长而忽视对劳动者的保护。结果,数以万计缺乏合理保护的工人由于工伤事故和工业排放的有毒物质而死亡和伤残。根据官方的《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统计,在1886—1898年间,仅仅是投保企业范围内的工伤事故总人数就达到607933人,其中死亡66037人,完全丧失工作能力者26794人,部分丧失工作能力者327322人,伤后痊愈者187770人,受伤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19]这些统计数据中还不包括大量未投保企业的工伤事故人数。
严重的工业环境污染是另一个前所未闻的“社会问题”。在一些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河流和水源受到工业排放物和生活垃圾的污染尤为严重。在工业发达、城市遍布的莱茵地区,大量的工业污水和生活垃圾甚至使美丽的莱茵河变成了“下水道”。在鲁尔重工业区,水道污染情况更是达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有一份呈递给国家的报告中曾这样描述当时鲁尔的水道污染情况:“在许多地方,流动的与其说是水,不如说是一团黑色的东西在缓慢地向前推进。”鉴于水污染问题的巨大压力,普鲁士于1901年初专门成立了“王家供水和污水处理研究与检测机构”,德国政府也不得不直接出面,于1905年与科学界、医学界在美茵茨召开联合会议,讨论相关解决办法。[20]
此外,煤钢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大量废气和煤灰等,也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和对人们身体健康的损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人们极具画面感的灾难片式描述中得到证实:
“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然而人们在看到这光鲜的一面时,也必须看到大自然所呈现的令人悲伤的景象。周围一切都被煤灰所覆盖;路上是厚厚的尘灰;树木和草地失去了它们绿色的光泽。附近的村庄和小城镇的房屋都染成了黑色。在这里,那些脸色苍白、面带悲伤和浑身脏兮兮的人们昭示着,附近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苦难。”[21]
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也成为传统乡村从未遇到过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由于城市史无前例的爆炸性扩张和现代性人口密集聚居区的快速形成,城市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公共健康视阈下的‘卫生’问题”强烈呈现出来。[22]
在许多高速扩张的工业城市中,城市结构布局通常呈现为临时应急性特征,以满足大量人口涌入的需要,因此城市规划设计不合理和居民居住状况恶劣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许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后,只能居住在极度拥挤、卫生状况特别恶劣的出租屋聚集区,以柏林为例,1875年时,有71.8%的工人家庭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屋中,1905年时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74.7%。不少工人家庭甚至为减低房租支出,还将其狭窄的住房再转租出去一部分,而转租出去的往往是一个铺位。[23]恶劣拥挤的居住条件也导致霍乱、伤寒等传染性疾病的频发和流行,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多达万人以上。
大量生活垃圾和粪便的处理也成为城市公共卫生管理中每天必须直接面对的棘手问题。以粪便的处理为例,根据《德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1897、1898年统计数据,除了极少数城市采取化粪池方式外,像柏林、卡塞尔、杜塞尔多夫、慕尼黑等多数大城市都是通过下水道直接将粪便排入河流或城市周边的灌溉地,其结果是造成严重的污染。[24]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现代化危机”还体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出现了断崖式改变。许多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们因无法适应与乡村迥异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和环境而陷入极度焦虑和不安之中。
根据统计,到1907年为止,在德国6170万人口中异地谋生者约占50%。[25]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希望到城市和工厂中寻找发展和工作机会。然而,当他们来到城市后,他们却发现,等待他们的是一种与传统农村截然不同的现代城市工作和生活模式,一个急速转变中的工业社会和拥挤的城市空间。在这种全新的环境中,一切都处于一种高节奏的紧张和亢奋状态之中,工作和生活与慢条斯理的乡村世界形成天壤之别。在这里,原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悠闲乡村生产生活已然成为过去,确定时间的依据不再是自然的季节、白昼黑夜和农业生产需要,而是企业生产的需要和规定;人们必须面对现代工厂制冷酷的工作节奏和臭气、噪音等恶劣环境,还有城市聚居区狭窄的胡同和极具压抑感的昏暗居住环境。有人把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断崖式变化形象地比喻为“生活环境的殖民化”。[26]很多人由于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剧烈转变难以适应,陷入极度焦虑和“精神上的不安全危机”之中,以至于悲观地将城市中的工作和生活称为“慢性自杀”。[27]
对于习惯于前工业社会生活的人们而言,德意志帝国时期“现代化危机”还反映在以传统乡村为载体的传统道德的衰落,现代城市的逐利性物质主义取向导致传统的“品味、风格、文化和历史意识的丧失。”[28]
首先,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热爱家乡”(Heimatliebe)作为一种传统的基本“道德因素”在逐渐消失。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有两点:一是人们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中离开农村的村庄和乡镇共同体,在进入陌生的工厂和城市寻找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传统的、社会的和人际关系的所有条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家乡”。二是大多数人来到城市之后,短时间内难以适应新生活方式和环境,无法找到农村“家乡”的感觉,成了“空间的”和“精神的”双重“无家可归者”,因此“热爱家乡”也就无从谈起。[29]有鉴于此,在许多人眼中,与传统乡村生活相比,现代“城市生活”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道德意识方面的“先天”缺陷。基于同样的道理,人们从农村迁入城市,在远离乡村共同体的同时,也远离了家乡的风俗习惯,而现代城市生活中又难觅传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习俗,更多的是现代生活模式下的“同质化”。因此,在许多秉持和忠诚于传统乡土文化的人看来,缺乏传统风俗习惯的同质化的现代城市生活是“不自然和审美上没文化的”,这对于传统文化道德传承而言是“一种不幸”。[30]
其次,传统道德的衰落特别体现在现代城市生活与纯朴自然的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逐利特性。在许多秉持传统道德意识的人看来,现代城市是资本的乐园,这里的生活也因此具有极强的逐利特征。结果是,在这资本横行的世界中,“正直的公民意识、最坚定的品格在明目张胆的贪婪面前黯然失色,正派和美德已经被放纵的功利主义生活导向所取代”,人们完全陷入了一种“全然无视精神意识”的逐利性“物质主义生活”之中。这种逐利性的“物质主义”既是“城市‘道德滑坡’”的价值观根源,也是道德衰落的直接体现。[31]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极其悲观的看法,当时包括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哲学家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等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加入到了“敌视”现代城市的现代城市文明批评者行列,他们“妖魔化”城市,认为现代城市是“使人们在道德、文化和精神上堕落”的根源,是“堕落的庇护所”。[32]
上述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现代化危机”困境,引发德国社会具有反思倾向的“对立运动”(Gegenbewegung)。这种“对立运动”在精神和文化上就表现为一种回归乡土传统的取向。人们怀念传统的乡土文化,渴望并想象农村家乡的美好生活,希望以此消除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各种弊端,纠正以快速经济增长和物质利益至上为取向而罔顾传统的“过度文明化”。[33]于是,在浓烈的乡愁中,传统农村家乡成了“动荡不定的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寻找的安静港湾。”[34]当时有一本叫《奥尔登堡公国乡土寻踪》的小册子曾生动地描述了人们对于急速变化的现代生活的恐惧和回归传统乡土的渴望:
对于我们而言,(现代)生活越来越像脱缰野马无法控制,让人越来越眼花缭乱;科学、技术和艺术将人们越来越深地拽入它们力量范围。无法忍受的人们必须从这种漫无边际中归返传统乡土,回到熟悉的人群中,回到熟悉的环境中,回到家乡,去休养生息。[35]
德意志帝国时期以回归乡土为取向的乡土运动正是这种心理需求的产物。人们希望通过回归乡土,给那些已经流入城市的“异乡客”一块心灵的慰藉之地,“让他们重新拥有家乡”。因此,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可谓一种精神情感上的“内心移民”。[36]当然,除了这种心理层面的需要外,人们也希望通过回归乡土,保护受到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的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在社会层面消解以“现代化危机”呈现出来的各种弊端。
二 现代化危机的乡土求解
面对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危机”压力,人们本能地想到回归悠然安逸的传统乡土生活。一方面,人们期待通过从精神层面回归传统乡土来舒缓紧张的现代城市生活带来的各种焦虑和不适,进而获得些许心理慰藉;另一方面,人们也从文化和社会层面关注由于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而快速衰落和消失中的美丽乡村,希望保护好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处理好传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这两点来看,德意志帝国时期回归乡土的运动就是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危机”的一种传统取向的求解。而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在内容上也基本上突显出以上两类指向。
首先,大量以农村和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乡土文学作品和乡土教程、乡土志等乡土教育素材的呈献在推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回归方面扮演了先导性角色。它们在精神层面给处于现代化转型阵痛中渴望和怀念传统乡村生活的人们以心理层面的慰藉。
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快节奏、不稳定、不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导致人们在内心特别渴望回归温馨记忆中的农村家乡,怀念前工业社会曾经的乡村安逸和悠闲。许多人发现,他们背井离乡,从传统农村来到陌生的现代工商业城市,面对的不仅是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还有原有生活进程的“剧烈中断”。他们的眼前是一种与传统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快节奏工作和动荡生活环境。巨大的工作压力加上恶劣的居住环境,引发人们普遍的焦虑和不安,也唤醒了他们的“乡愁以及对家乡和传统的渴望”。[37]于是,回归记忆中熟悉而悠闲安定的乡土生活成为人们内心无法抑制的向往。当时有一位乡土志作者曾饱蘸真情地表达了离开故土入城谋生者对传统农村家乡的乡思乡愁。
最美和含义最丰富的词语是“家乡”。对于它,人们只有身处异乡,在陌生的语言和风俗环境中才能有最好的理解。人们常常挂念它,喜欢回味故乡的田野,回味童年时的嬉戏之地,思念回到难以忘怀的、熟悉的珍贵祖屋,即便它只是一栋贫寒的茅屋。人们的思绪会渴望并穿越其童年时代曾漫游过的家乡洒满阳光的田野和草地。……所有的一切都保存在童年幸福日子的特别记忆中,在灵魂深处萦绕,挥之不去。如果可爱的家里还有珍贵的亲人(父母、兄弟姐妹)、少年挚友等令其魂牵梦绕,乡愁难解,他会急切地期盼着去探视他们,与他们用亲切的乡音交谈。[38]
正是出于在精神上迎合和抚慰这种浓烈的乡愁乡思的需要,德意志帝国时期成了乡村小说、乡村故事等各种乡土文学作品大行其道的年代。从德国文学史的角度看,虽然早在17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作为“农民叙事文学”的乡土文学,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这类文学体裁才出现繁荣迹象。[39]当时一些浪漫派作家出于对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恐惧,遁入乡村,抛出了一些颂扬传统农村生活的乡土文学作品。到德意志帝国时期,确切地说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到20世纪初,作为对当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回应,乡土文学形成了高度繁荣的景象,涌现出诸如耶雷米亚斯·高特赫尔夫(Jeremias Gotthelf)、贝尔特荷尔德·奥尔巴赫(Berthold Auerbach)、彼特·罗瑟格尔(Peter Rosegger)等一批著名的乡村故事作家和《最后的雅各布》《雪绒花王》《寂静森林》等许多广受欢迎的“农民小说”。这些乡土文学作品美化传统农村家乡生活,推崇和颂扬乡土气息浓厚的农民“原初生活形态”,[40]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们对于快节奏、不稳定、缺乏安全感的现代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的不满和抵触,反映了人们在剧烈的现代化转型压力下从传统乡土中渴求安全和稳定的心态。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各类乡土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乡村世界无一例外地“被理想化为一种永恒和谐的存在”。它们“有一个固定的基本模式,封闭的‘村庄’空间是其一成不变的标志”。这些村庄都“被理想化为有共同体意识和安全感、具有美丽景观和健康的自然之地”。村庄里的农民则作为“土地拥有者”过着稳定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很显然,这些乡土文学中的传统乡村是一种“前现代的理想化”,“一种退行性的想象”。[41]这种乡土生活环境和模式与“无家可归(缺乏对所在城市认同感)、飘忽不定、秩序遭毁、习俗不古、人际关系淡漠,工作环境非人化,价值体验空洞化”的现代城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42]正是在这种对前现代乡土生活的“怀旧式建构”中,传统乡村生活被想象成了一种家庭和谐、生活悠然、亲近自然的“田园诗”,“现实的社会紧张关系和单调的生活由此得到慰藉”。[43]现代化的诸多弊端和缺憾也在这种前现代乡村生活的美好想象中实现了一种精神层面的“补偿”。因此有学者形象地称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文学为一首“反现代的”“战斗的田园曲”。[44]
正因为如此,虽然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家在德国文学史家眼中属于不入正史的“无名之辈”,然而他们的作品却由于迎合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在当时的公共图书馆中最受欢迎,被借阅次数也最多。[45]这些乡土文学作品成了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渴望和怀念渐行渐远的传统乡土生活的精神快餐。而它们的广泛流行又反过来进一步激起人们对于传统乡土生活的渴望思念之情,也唤醒了整个社会的乡土关怀。
如果说乡土文学的繁荣从精神层面反映了人们回归乡土的情感渴望,各类乡土教程的编撰出版则从文化层面强化了人们对于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认知。虽然德国早在19世纪早期就开始出版乡土教程,[46]但是各地争相编撰出版乡土教程并明确将其列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却是德意志帝国时期才有的文化景观。这些乡土教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以最煽情的方式宣传家乡的文化和自然景观,通过散发浓烈的乡思乡情,培养人们的乡土情怀。以《韦尔茨海姆区乡土教程》为例,这虽然只是一本介绍符滕堡邦森林小镇韦尔茨海姆小镇的60余页的小册子,却能将掩映于浓密森林中的这座小镇的优美自然环境和独特历史文化如数家珍般呈现于人们眼前,进而唤起人们“满满的乡愁”。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该教程最后以著名诗人尤斯蒂努斯·克尔纳(Justinus Kerner)对家乡韦尔茨海姆森林恋恋不舍的优美诗句将人们引入绵绵不绝的乡土情思之中:
我真想永远陪伴你们,高耸神奇的森林!虽时光流逝,岁月经年,对你们的爱却始终让我梦绕魂牵。[47]
此外,各类乡土志[48]的编辑出版也同样成为德意志帝国时期提升人们传统乡土认同的精神食粮。在德国,乡土志是在乡土教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49]但内容比乡土教程更为丰富,功能上也突破了乡土教程的中小学教育语境,开始面向家庭和社会,最终成为“从各方面促进对家乡特性了解”的“家庭读物”,可谓培养乡土情怀的更高进阶形式。帝国时期的乡土志没有统一格式,内容庞杂,多为热衷于家乡事务者中一些“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编撰的“灰色文献”(Graue Literatur)。[50]它们因受众广泛,乡土气息浓厚,特别有助于人们“认识家乡,了解其历史,感悟其美丽”,增进乡土情感。[51]例如,泰克山下基尔希海姆只是符滕堡的一个小镇,其《泰克山下基尔希海姆及其附近乡土志》却能通过收录诸如“泰克山上的女巫”“林堡的恶龙”“红公鸡”等乡土气息浓郁的本地民间故事,把“家乡原汁原味的教育材料”呈献给学校和家庭,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52]这些故事最终变成了泰克山下基尔希海姆的文化符号和离开故土的泰克山下基尔希海姆人牵挂乡土的情感载体。
德意志帝国时期回归乡土的运动还表现为积极保护和维护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使之免受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洪流的损毁,并期待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传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人们通过乡土文学作品和乡土教程、乡土志等乡土教育素材来慰藉对传统农村家乡的乡思乡情,只是在精神层面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中的传统乡土回归。但是这些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以“现代化危机”呈现出来的诸多现实问题。人们心目中的田园诗般的乡土世界正面临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村落衰败、传统文化消失、自然景观损毁等危机。为此,目睹这些变化的“德意志乡土保护联盟”主席的保罗·舒尔策-诺姆堡(Paul Schultze-Naumburg)曾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在古老的书籍和旅行文献中,人们常常会看到这类描述:德国是一个无限美丽的国度,漫游于这里的城市、乡村和森林,乃人生一大乐事。然而现在这种说法对于我们的孩子们而言,恐怕要成为一种过往梦境了。如今我们面对的是:德国,我们亲爱的祖国,正在失去她的特色,变成荒凉寂寞之地。长此以往,城市和乡村很快就会变成毫无差别的无产者聚居区,其建筑风格将像监狱一样;我们从祖先那里承继下来的一点优秀文化遗产,要么惨遭毁灭,要么沦落为纯粹的修复癖好物。我们的山毛榉和橡树林将被一系列乏味的松树等人工林木所取代。再也不会有让我们能够愉悦畅叙的花园,再也不会有和谐如画的教堂和小桥流水景观。我们国家的昔日美景将不复存在。[53]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人们在通过乡土文学、乡土教育素材等从精神层面回归乡土的同时,也开始在社会层面采取实际行动,保护传统乡村以及承载其上的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于是,在回归传统乡土的语境下又出现了由热衷于乡土事务者、乡土研究者[54]等推动、大批民众参与的社会性乡土保护运动(Heimatschutzbewegung)。
乡土保护运动的发起者是著名音乐教育家恩斯特·鲁道夫(Ernst Rudorff)。1880年,他震惊于自己家乡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冲击下正迅速失去原有风貌和传统文化,发表《关于现代生活与自然的关系》一文,首度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好传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后来他又连续发表“德国的自然景观和历史纪念物保护”、《乡土保护》和《还是乡土保护》等报告和文章,呼吁保护家乡的“自然和如画如诗的历史纪念物”,强调保护遭受现代文明威胁的乡村自然景观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及迫切性。[55]此外,“德国历史与古典学联合会”也在1888年的大会上也向“德国政府”发出了“尽可能保持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乡土外貌”的恳求,呼吁进行“纪念物保护”。[56]
恩斯特·鲁道夫和“德国历史与古典学联合会”有关乡土保护的呼吁引起广泛共鸣,整个德国范围内迅速形成了一场广泛的乡土保护运动。各地纷纷成立乡土保护社团,保卫“古老的城市和建筑、自然生活条件和景观、各种传统和生活方式”,以克服“现代文明中的现代性弊端”。[57]仅在南德大邦巴伐利亚就出现了“乡土教程促进联合会”“伊萨河谷联合会”“民族艺术和民俗学联合会”“德意志工艺联盟”“巴伐利亚自然保护联盟”“巴伐利亚邦乡土保护联合会—民族艺术和民俗学联合会”等一系列家乡保护社团组织。到20世纪初,德国各地已经普遍建立起乡土保护协会。回归乡土由此转变成了从实践层面推进保护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社会运动。1904年德国各地的乡土保护者在德累斯顿组建了全国性乡土保护组织“德意志乡土保护联盟”。[58]
各地方乡土保护社团和“德意志乡土保护联盟”不仅批评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弊端,而且明确提出要将“已经成为德意志乡土自然和历史属性”却正受到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威胁的各种动植物、历史纪念物、建筑、艺术、风俗习惯等纳入努力保护的目标,同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开展各种实际有效的对于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保护活动。[59]
在乡土保护运动中,各种在工业和城市文明扩张下迅速衰败和消亡的传统乡土文化景观成为首先要保护的目标。从实施路径看,当时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着力于对具有鲜明历史特征的传统建筑和艺术等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和维护。关于这种保护和维护的意义,乡土保护联盟发起者之一、著名作家罗伯特·米尔克(Robert Mielke)曾经从文化哲学的层面做了经典的解释。他认为,传统建筑及其风格是德意志文化的符号,承载着德意志民族的特性,保护它们就是保护德意志文化和民族特性。他以德意志农民的传统住房为例,阐释了民族特性与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真正的德意志农民住房“有一种道德规范的意义。在这种住房中,通过卧室的布置以及本地材料的民族形态,德意志民族精神得到集中体现”。因此,传统德意志农民住房就是德意志“民族艺术和民族精神的强大支柱。”[60]但是,诚如当时著名艺术家理夏德﹒比克纳(Richard Bürkner)所指出的,现实状况是,传统农村家乡正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的猛烈冲击下迅速“败落”,更有一些乡村盲目“模仿城市”,追求时尚城市生活形态。传统乡土文化和艺术因此受到严重损害,甚至陷入“蛮荒”状态。[61]有鉴于此,为了捍卫承载德意志民族特性的传统乡土文化,人们必须对分布于农村地区的旧广场、宫殿、学校、教堂以及教堂建筑艺术等进行维护甚至恢复。[62]
当然,保护传统文化景观并不意味着一味复古和完全拒绝合理的现代性改进,而是要以兼顾传统延续性和与时俱进为原则。关于这一点,理夏德﹒比克纳分别以村庄保护和旧城市改造为例,从文化和审美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关于村庄保护,比克纳认为,“村庄就是村庄,绝不能模仿城市。村庄有其独特的存在和结构,有其独特的设施和个性。”人们务必记住,“景观皆有其特色,绝不要出于美观考虑而移除每棵古老树木,也不要出于其他考虑而废除每一条旧田埂,正如完全没有必要把每一条弯曲小路都变成宽阔笔直的大道一样。”同样,也“绝不要将每一条小溪都裁直”,因为“弯曲也有其审美的和经济的价值所在”。[63]总之,“一个村庄只有像一些业已成熟的村庄那样,懂得在规划中不规则地适应各类景观和周围环境,才能成为一个美丽的村庄。”[64]
基于以上原则,乡土保护者按照德国传统村庄形态提出了散居式村庄、沿街村庄、围绕广场村庄、排列式村庄和辐射式村庄等规划模式,并明确提出在乡村景观保护实践中要尊重各地区的传统村庄以及农民房屋形态,使每个村庄则都能彰显其独特的个性魅力,不要因规则化而缺乏差异。为此乡村保护者们推荐了一些所谓的“示范村庄”(Musterdorf)。例如,在东部的波森地区,村庄形态主要是沿街村庄,高伦霍芬(Golenhofen)就是这类村庄的典范。在高伦霍芬,高大的学校、教堂等公共建筑坐落于市场广场旁边,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们,其他的农舍则静静地沿街而立。整个村庄由此构成了一幅和谐恬静的“农业经济特别展览会”画面。[65]作为乡土保护者的罗伯特·米尔克就特别推崇这类沿街村庄,认为这类村庄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生活,而且给人以美感。“它的每一栋房屋都各自有形,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又形成了一种统一性,仿佛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创作的令人愉悦的整体画卷”。[66]
其次,对于那些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下已经无法加以直接保存的传统乡土文化景观,则采取乡土博物馆(Heimatmuseum)等形式来抢救性地储存相关历史和文化记忆。据统计,在德意志帝国40余年的短暂历史中,全国建立了197座乡土博物馆。[67]这些乡土博物馆专门收藏与地方家乡有密切关系的自然史、文化史以及民俗学方面的物品和文献,通过这些展品和文献的展示,满足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于传统“乡土情感的心理需要”,同时通过搜罗和保存“现存证物”,提供一种“只能在有限的地方、在家乡发生的”“可视的长期存在”,以实物方式呈现和保存地方家乡的文化记忆,凸显地方家乡的历史文化特征。[68]在当时村庄和乡镇以及承载其上的乡土文化的快速消失的情况下,这些乡土博物馆就成了人们怀念和体验乡土历史文化的精神慰藉所在,也成为保护和弘扬乡土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以柏林附近雷克斯村(Rixdorf)在1897年建立的“新科隆乡土博物馆”为例,该博物馆由教师艾米尔·费舍尔(Emil Fischer)创办,主要收藏当地自然史、文化和民俗展览。之所以要创立这样一座乡土博物馆,就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末雷克斯村迅速城市化。快速城市化进程正剧烈地改变着这个曾经的普通村庄的原始面貌。在1890年到1897年间,雷克斯村的居民从3万多人增长到了7万多人,该村也一跃成了“德国最大的村庄”。1900年该村正式升格为市,到1905年时该“村庄”居民人数再翻一番,达到15万多人。[69]面对如此快速的变化,人们希图通过“乡土博物馆”的方式来抢救和保存一些该村曾经拥有的传统乡土文化、民俗和自然景观,以便由此留下一些对过去的念想,让人感受社会的剧烈变迁。
人们在对传统乡土文化景观保护的同时,也从多个层面强化对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扩张威胁的乡土自然景观的保护。乡土保护者认为,自然景观和“自然纪念物”同样是传统乡土“文化和历史的见证”,应该“像历史和艺术纪念物一样,同样受到保护”,因此,自然保护也是“一项文化任务”。[70]所以,早在1888年“德意志历史和古典协会总会”就已经明确提出要“保持”岩石、树木等自然物的“历史和传统的乡土形态”问题。[71]
当时自然景观保护的迫切任务是防止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自然生景观的肆无忌惮的功利性破坏和掠夺,其中对自然河流的保护显得尤其急迫。当时人们一味沉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对自然河流竭尽可能地进行各种开发和利用,诸如大规模地推进“河流运河化”,裁直和深挖河道,以满足大规模运输货物的需要;在河流上修建水电站,以满足工业发展和城市扩张对电力的需求,等等。然而这种对于河流的无节制开发和利用有如一把双刃剑,它们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如若处理不当,也会破坏河流的自然生态,甚至引发洪水等自然灾害。而后一种情况的典型事例就是巴塞尔到曼海姆之间莱茵河段被挖深裁直,水流下泄加速,导致该地区在1882年出现了19世纪最大的水灾。人们由此才认识到“每一种试图用非自然方式取代自然状况的激进企图最终都会遭到自然的报复”。[72]
鉴于以上情况,乡土保护者明确提出在开发和利用河流时,不仅要关注经济效益,也要尽可能保护好河流自然生态。[73]他们还将这种理念外化,转变为保护自然河流的实际努力。在这方面有一个典型事例。1900年巴伐利亚政府准备在慕尼黑南部引伊萨河水到瓦尔辛湖(Walchensee),以便为即将修建的水电站提供充足水源。该工程一旦付诸实施,不仅会破坏伊萨河的自然风貌,而且会影响到其上游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原始生态,因此遭到当地“伊萨河谷联合会”等乡土运动组织的强烈抵制,并引发整个社会的关注。巴伐利亚下议院为此进行了多次讨论,政府也对修建瓦尔辛湖水电站可能造成的自然生态问题进行反复论证,整个工程因此推迟十多年之久才动工。1904年巴登政府炸毁莱茵河上的劳芬堡险滩修建水电站的计划同样遭到“黑森林联合会”等当地乡土运动社团的反对。[74]
乡土运动者除了举行反对破坏自然景观的请愿和抗争外,还通过购买和租赁土地等方式直接建立自然保护区,主动践行自然保护的理念。1898普鲁士议会议员、布雷斯劳首席教师威廉·威特坎普(Wilhelm Wetekamp)提出效仿美国等国建立自然保护公园的建议,立即得到广泛响应。此后,人们开始在一些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地区建立大面积的自然保护公园。1909年自然保护者在慕尼黑成立专门的“自然保护公园联合会”,[75]提出自北向南设立瓦滕海(Wattenmeer)、吕内堡荒原(Lüneburger Heide)、巴伐利亚森林和阿尔卑斯山地等四类原始景观自然保护区的目标。到1914年,“伊萨河谷联合会”“自然保护公园联合会”等乡土运动社团成功地在吕内堡荒原等地建立起“大面积的保护区”,仅“鸟类保护联盟”建立的保护区就达26个之多。[76]
甚至当时帝国和各邦高层的一些统治者也被乡土保护者的热情所感染,加入自然景观保护的行列,最终将自然生态和景观保护上升成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表明,在乡土保护运动者们的呼吁和鼓动下,帝国及各邦高层中许多显贵最终都成了自然保护运动的支持者甚至自然保护组织的成员。其中,巴伐利亚的鲁普莱希特王储(Rupprecht von Bayern)是巴伐利亚“自然保护联盟”的“保护人”和“伊萨河谷联合会”等家乡保护组织的财政支持者;符滕堡和巴登的统治者是“鸟类保护联盟”的成员;甚至德皇威廉二世也在创立德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公园“吕内堡荒原自然保护公园”(Naturschutzpark Lüneburger Heide)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慨然批准募集资金建设公园,以阻止破坏自然景观和限制打猎活动。[77]
帝国及各邦政府也陆续建立自然保护机构,以具体的立法和财政投入措施支持自然保护活动。1905年巴伐利亚内政部专门召集“阿尔卑斯联合会”“伊萨河谷联合会”等10多个乡土保护团体,组建“邦自然维护委员会”。到1913年为止,该委员会已经拥有127个地方委员会,成员2330人。普鲁士则于1906年成立“邦自然纪念物维护处”,调查登记普鲁士的自然纪念物并拟定保护措施等。[78]帝国议会也支持自然保护。在1908年帝国议会有关鸟类保护法案的辩论中,主要党派议员一致支持采取严格保护措施。此外,各邦和帝国中央政府还积极拨款,在资金上支持自然保护。普鲁士文化部1905年投入的仅用于“自然纪念物”维护的资金就达1.5万马克,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帝国中央政府用于自然保护的预算资金也从19世纪80年代的每年12万马克增加到了1908年的每年43.5万马克。[79]
德意志帝国时期对于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保护有着非凡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在保护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各种努力以及由此而对于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纪念物的及时拯救和维护,更重要的是它唤醒了普通大众的传统乡土保护意识。关于后者,当时著名摄影师、作家兼乡土研究者特奥多尔·缪勒(Theodor Möller)感受尤其深刻:“近年来,所有人对于乡土意义的理解都在增长。”“人们日益关注乡土景观的特色和美丽,关注包括住宅、习俗、服饰、语言、传说、童话、歌曲、谚语、诗歌等从父辈和祖辈们传下来的丰富的乡土文化宝藏”,以至于“每个人都成了宝藏的发掘者和宝藏的保护者”。[80]
三 后德意志帝国时代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建构
德意志帝国时期出现以回归乡土为取向的精神和社会运动并非偶然。如前所述,这种回归乡土是人们为消除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危机”的一种传统取向的求解,是人们“目睹身边环境的变迁以及与之相伴的传统、安全和舒适性不断丧失”后,对于“传统文化和自然的崇敬、加倍珍惜、捍卫甚至再造”的体现。[81]同时我们应该更深刻地看到,这场貌似保守的乡土运动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人类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强大力量,即人类进步离不开“对于自然和历史的需求”。换言之,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能无视历史和自然,人们必须妥善处理好传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德意志帝国时期“现代化危机”之下的乡土回归就是在“历史面前的投降”。[82]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不只大大提升了当时德国人的乡土意识,使处于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激流中的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得到及时保护,就其历史影响而言,它对于日后德国人科学的传统与现代关系认知以及自然保护传统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从认知层面看,德意志帝国时期以回归乡土的传统取向来应对“现代化危机”有助于人们尊重历史惯性,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文化,对于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建构科学合理的传承与发展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德国学者在谈到德意志帝国时期乡土运动的后续影响时指出:“在19世纪晚期的德国,人们已经在坚持强有力传统因素的政策框架内表明了一种义无反顾的决心”,即在迈向现代技术文明的同时,倾心于传统文化的保存,“以为历史的见证”。[83]换言之,德意志帝国时期对于传统乡土文化景观的思恋和执着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德国人对待传承与发展的态度,也即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同时,不能无视历史延续性,不可抛弃传统文化,以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困境。这种貌似保守的认知实际是对于历史及其发展惯性的一种尊重。
事实上,1918年德意志帝国因一战失败而垮台后,传统乡土文化景观保护在德国不仅没有减弱,而且上升为一项具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国策。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承继者,魏玛共和国在其宪法中第一次将保护传统文化从法律层面确定下来,其宪法第150条中明确规定艺术纪念物和历史景观“享受国家保护和维护”。[84]同时,在保护和维护诸如传统建筑文化的实践层面,从魏玛共和国到联邦德国,人们都力图纠正现代化大潮中几乎“一边倒”的现代风格,反对割断文化的历史延续性,细心保护和维护哥特式、巴洛克式等风格的历史建筑以及各类舒适而和谐的中世纪小镇,强调“以传统为基础,不要放弃与我们的历史之间的联系”。[85]正是在这种保护传统文化和强调历史连续性认知之上,在当今高度现代化的德国,虽然不乏现代风格的建筑和文化,人们仍随处可见古朴宁静的村落、风格优雅的中世纪城镇和凝聚着厚重历史记忆的城堡教堂。置身于德国,人们仿佛穿越于时空隧道,漫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与此同时,德国人也很清楚,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要完全固守传统而罔顾发展,一味拒绝新事物,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关键是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对于这一点,德意志乡土保护联盟主席保罗·舒尔策-诺姆堡说得非常清楚:第一,历史与现实之间“不存在对抗问题”,人们需要关注的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发展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就是要“确保新的建设符合地方精神”,也即符合乡土传统,而不是将现代化发展建立于无视记忆的历史虚无主义之上。第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有机衔接,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人们把旧的谷仓改造成现代电力设施的安置场所或工业用房等就是明证。[86]正是在这种辩证认知之上,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策略也进行了调整,也即从德意志帝国时期出于恐惧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形成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回归乡土热“转向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从徒劳的否定和鲜明的保守主义转向积极的艺术性创造”,“积极主动地利用历史来建构当代”,“不是与工业化进行斗争,而是对这一现象进行建构,缓冲其后果”。[87]
在这种传统与现代兼容的理念之下,自魏玛共和国以来,人们在诸如建筑文化领域,包括建筑设计和乡村、城镇建设规划布局等,始终将“现代世界和传统延续性”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谐统一。[88]以乡村建设为例,一些传统村庄作为定居点虽然“已经丧失了最原始的农林渔等经济功能”,却开始担当起新的社会需要。它们不仅成为前现代乡土文化的载体,一种历史的见证,也成了生活于现代都市的人们休闲旅游和感受历史文化的去处。在北德地区,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具有明显大地产庄园结构印记的村庄。在这些村庄中,带有巨大庭院的贵族庄园主住宅被完好无损地保留着,人们可以从它们的“建筑结构和形态中释读出农业经济的本源,村庄中央则成了观察乡村定居点典型景观和现存自然状态的直接通道”。[89]与此同时,村庄建设也要与时俱进。“就村庄的建筑而言,虽然它们在构造方面是前工业时代的,但是它们也接受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创新”,“对旧建筑进行完善和改造”。在这方面,如瓦尔德克地区的新贝利希(Neu-Berich)、新布林豪森(Neu-Bringhausen)和新阿塞尔(Neu-Asel)等村落,都堪称典范。它们既保留着传统风貌,又折射出时代脉动,传统中蕴含着现代,有如一幅幅古典而充满活力的亮丽油画。[90]
其二,德意志帝国时期保护乡土自然景观的理念和实践,成为德国自然保护传统的原点,最终使德国人的自然和景观浪漫情结外化成了一种法律和制度。
德意志帝国时期以回归乡土来消解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危机”,其取向虽然保守,却“使广大公众第一次认识到作为工业化后果的各种生态负担”,[91]唤醒了人们的自然保护意识,“反对对于‘自然和景观’进行结构性改变和侵犯”逐渐发展成为得到法律保障的一种德国自然保护传统。
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乡土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保护运动继续发展,国家和地方层面先后建立起相关的法律保障。在国家层面,魏玛共和国宪法第一次确认“自然和景观享受国家保护”。[92]在地方层面,包括普鲁士、黑森在内的各邦也陆续通过了自然保护法。从社会层面看,则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然保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加入自然保护行列。1924年仅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自然保护参与者就达到100万之众。自然保护区建设也取向巨大进展。仅普鲁士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就从1923年的12个增加到1931年的300个。[93]
第三帝国时期,自然保护从立法到实践在纳粹当局“一体化”机制下继续推行。1935年纳粹政府通过了德国第一部国家自然保护法《帝国自然保护法》,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广泛和最严格一部自然保护立法”。[94]依据该法,德国在短时间内创建了一大批自然保护区。同年纳粹政府还出台了《帝国动物保护法》和《森林保护法》。根据这些法律,所有的道路、水利等现代工程建设都必须考虑“景观与现代工艺协调”,不得损害自然景观。[9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虽然政治上分裂为西部联邦德国和东部民主德国,但两个德国在自然保护方面仍延续着“追溯到世纪之交的自然保护传统”。[96]联邦德国完全继承了自德意志帝国以来的自然保护传统,甚至第三帝国的《帝国自然保护法》也作为联邦法的“例外”而“继续有效”,被各州视为“自然保护的法律基础”,[97]直到1976年底才以《联邦自然保护法》(自然保护和景观维护法)取而代之。民主德国同样高度重视自然保护。它一方面直接利用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的许多自然保护和景观规划专员如勃兰登堡自然保护专员马丁·赫尔贝格(Martin Herberg)等人贯彻自然保护政策,另一方面于1954年通过了《家园自然保持和维护法》(自然保护法),1970年又颁布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规划设计法》,即“国家文化法”,突出在自然保护方面的历史“连续性”,明确自然保护目标是“保持、改善和有效利用作为社会的自然生存和生产基础的”各种自然资源,“美化家园”。[98]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自然保护的重要性被提到新的高度。德国联邦议会分别于2002年和2009年两度修订“联邦自然保护法”,持续强化自然保护目标,突出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要本着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推进自然保护事业。[99]
从以上历史事实中不难看出,“自然保护和景观维护”已经成为德国的传统,成了当今德国自然保护观念的“核心”和立法焦点之一。[100]而这一切显然是与德意志帝国时期回归乡土语境下的自然景观保护诉求一脉相承的。就此而论,德意志帝国时期的自然景观保护具有原点意义。
结语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是人们以回归传统乡土来舒缓和消解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的“现代化危机”的求解,站在一种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它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德国人的一种社会发展理念,一种兼具与时俱进和稳中求进的社会发展观。这种社会发展理念完全契合于近代以来德国所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
众所周知,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德国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与英法等西欧国家不同的独特发展模式。这种独特性尤其表现在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德国通过“开明专制”旗帜下的一系列改革、19世纪初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大改革”等温和改革途径而非激烈的革命的方式,顺利实现了新旧社会的和平对接。[101]由于这种发展模式在顺应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大势的同时,也保留了大量旧的传统的或曰保守的因素,在德国批判史学派等学者的眼中,德国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了“防御性”的或曰“守势”的现代化模式。[102]而在笔者看来,德国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和平过渡实际上是德国人对于社会发展的一种理念和态度,即既要与时俱进,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又要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关于这一点,19世纪初普鲁士改革发起者施泰因说得非常清楚:“从旧事物形态向一种新秩序的过渡决不允许过于激烈”。[103]换言之,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转变中应该坚持稳中求进。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这种既与时俱进又稳中求进的社会发展理念。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竞逐富强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争雄世界的不二路径。故此,德国人在这一方面决然与时俱进,自19世纪30年代起一路高歌,甚至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后来居上,成为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引领者之一。另一方面,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的所谓“现代化危机”也使德国人从无所顾忌的现代化追逐中清醒过来。如前所述,面对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对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以及承载其上的传统社会的冲击和损毁,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希望通过回归传统乡土,舒缓和消解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阵痛和“危机”,并因此而重估传统乡土的价值。
要贯彻与时俱进、稳中求进的理念,兼顾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实现二者的和谐交融至关重要。诚然,在德意志帝国乡土运动初期,面对“现代化危机”的重压,人们有关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新思考中不乏极端保守的负面看法,但德国人最终在传承与发展的矛盾碰撞中建构起了有关现代与传统关系的科学认知。这种科学认知要求人们在推进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尊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拒绝无视传统记忆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而建立起一种历史与现实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有机和谐的衔接。正是在这种认知下,从德意志帝国时期到联邦德国时代,德国社会逐渐养成了严格保护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传统,其现代化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的有机交融中稳步向前,可持续和谐发展成了德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范式。
(原载《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1] 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德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8ASS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邢来顺:《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0—103页。
[3] 在工业化方面:1871年,德国第一产业领域价值创造为56.62亿马克,第二产业价值创造为43.84亿马克,1889年第一产业首次低于第二产业,分别74.74亿马克和83.49亿马克,1913年第一产业为112.7亿马克,第二产业则达到218.05亿马克。从就业人数看,1871年第一产业领域就业人数为854.1万人,第二产业领域为502万人,1905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首次低于第二产业,分别为992.6万人和1023.7万人,1913年则分别为1070.1万人和1172万人。Walther G.Hoffmann,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Jahrhundert,Berlin,Heidelberg:Springer Verlag,1965,S.454-455,205.在城市化方面:1871年德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9%,城镇人口占36.1%,1895年农村人口首次低于城镇人口,二者分别占49.8%和50.2%,1910年农村人口下降至40%,城镇人口上升至60%。Gerd Hohorst,Jürgen Kocka,Gerhard A.Ritter,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Band 2,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1870-1914,München:Verlag C.H.Beck,1975,S.52.
[4] Celia Applegate,A Nation of Provincials.The German Idea of Heimat,Berkeley,Los Angeles,Oxford:Un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Alon Confino,“The Nation as a Local Metaphor:Heimat,National Memory and the German Empire,1871-1918”,History and Memory,Vol.5,No.1(Spring-Summer,1993),pp.42-86.
[5] 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96;Thomas Rohkrämer,Eine andere Moderne?Zivilisationskritik,Natur und Technik in Deutschland,1880-1933,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Ferdinad Schöningh,1999;Jens Ivo Engels,Natur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Ideenwelt und politische Verhaltensstile in Naturschutz und Umweltbewegung 1950-198,Paderborn:Ferdinand Schöningh,2006.
[6] 转引自Nathali Jückstock-Kießling,Ich Erzählen.Anmerkungen zu Wilhelm Raabes Realismus,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04,S.129.
[7] 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S.29;John Alexander Williams,“‘The Chords of the German Soul are Tuned to Nature’:The Movement to Preserve the Natural Heimat from the Kaiserreich to the Third Reich”,Central European History,Vol.29,No.3(1996),pp.345-346.
[8] Thomas Rohkrämer,Eine andere Moderne?Zivilisationskritik,Natur und Technik in Deutschland,1880-1933,S.14.
[9] Johannes Müller,Deutsche Bevölkerungsstatistik:Ein Grundriss für Studium und Praxis,Jena:Fischer Verlag,1926,S.259.
[10] Wolfgang Köllmann,Bevölkerung in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Studien zur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4,S.109,117;Günther Schulz,Hrsg.,Von der Landwirtschaft zur Industrie.Wirtschaftlicher und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im 19.und 20.Jahrhundert,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Schöningh,1996,S.77;
[11] Claudia Prestel,Hrsg.,Jüdisches Schul-und Erziehungswesen in Bayern:1804-1933.Tradition und Modernisierung im Zeitalter der Emanzipation,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89,S.161.
[12] Hans-Otto Hügel,Hrsg.,Handbuch Populäre Kultur:Begriffe,Theorien und Diskussionen,Stuttgart:J.B.Metzler,2003,S.227;Wolfgang Köllmann,Bevölkerung in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Studien zur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S.109.
[13] Walther G.Hoffmann,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Jahrhundert,S.454-455.
[14] Dieter Rebentisch,“Industrialisierung:Bevölkerungswachstum und Eingemeindungen.Das Beispiel Frankfurt am Main 1870-1914”,in Jürgen Reulecke,Hrsg.,Beiträge zur modernen deutschen Stadtgeschichte:Die deutsche Stadt im Industriezeitalter,Wuppertal:Hammer,1978,S.99;Bayer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Ernährung,Landwirtschaft und Forsten Abteilung Ländliche Entwicklung,Ländliche Entwicklung im Wandel der Zeit:Zielsetzungen und Wirkungen,München:Schriftenreihe Materialien zur Ländlichen Entwicklung,Materialien Heft 36/1999,S.41-42.
[15] Christian Schwaabe,Die deutsche Modernitätskrise:Politische Kultur und Mentalität von der Reichsgründung bis zur Wiedervereinigung,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2005,S.175.
[16] Desanka Schwara,Unterwegs:Reiseerfahrung zwichen Heimat und Fremde in der Neuzeit,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07,S.9.
[17] Heinz Gollwitzer,Weltpolitik und deutsche Geschichte:Gesammelte Studien,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08,S.465.
[18] Rudolf Vierhaus,Über die Gegenwärtigkeit der Geschichte und die Geschichtlichkeit der Gegenwart,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8,S.19;Willi Oberkrome,Volksgeschichte.Methodische Innovation und völkische Ideologisier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18-1945,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93,S.31.
[19] “Unfälle und Ausgaben nach Versicherungsverbänden für die Jahre 1886-1898.1.Zahl und Folgen der Verletzungen”,in Das kaiserliche statistische Amt,Hrsg.,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Einundzwanzigster Jahrgang,1900,Berlin:Verlag von Puttkammer & Mühlbrecht,1900,S.199.
[20] Michael Wettengel,“Staat und Naturschutz 1906-1945.Zur Geschichte der Staatlichen Stelle für Naturdenkmalpflege in Preußen und der Reichsstelle für Naturschutz”,Historische Zeitschrift,Bd.257,H.2(Oct.,1993),S.355;Raymond Dominick,“Nasc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Second Empire”,German Studies Review,Vol.9,No.2(May,1986),pp.259-260;John Alexander Williams:“‘The Chords of the German Soul are Tuned to Nature’:The Movement to Preserve the Natural Heimat from the Kaiserreich to the Third Reich”,p.345.
[21] 转引自Johannes Kersten,Eichendorf und Stifter:Vom offenen zum geschlossenen Raum,Paderborn,München,Wien,Zurich:Ferdinand Schöningh,1996,S.80.
[22] Michael Wettengel,“Staat und Naturschutz 1906-1945.Zur Geschichte der Staatlichen Stelle für Naturdenkmalpflege in Preußen und der Reichsstelle für Naturschutz”,S.355.
[23] Karl Erich Born,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1867/71-1914),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1985,S.87.
[24] M.Neefe,Hrsg.,Statistisches Jahrbuch Deutscher Städte,Achter Jahrgang,Breslau:Verlag von Wilh.Gottl.Korn,1900,S.83.
[25] Wolfgang Köllmann,Bevölkerung in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Studien zur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S.107.
[26] Thomas Rohkrämer,Eine andere Moderne?Zivilisationskritik,Natur und Technik in Deutschland,1880-1933,S.13.
[27] Christian Schwaabe,Die deutsche Modernitätskrise.Politische Kultur und Mentalität von der Reichsgründung bis zur Wiedervereinigung,S.18;Wolfgang Köllmann,Bevölkerung in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Studien zur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S.107;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S.28,29,32.
[28] Willi Oberkrome,Volksgeschichte.Methodische Innovation und völkische Ideologisier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18-1945,S.30.
[29] Wolfgang Köllmann,Bevölkerung in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Studien zur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S.116;Paul Joachimsen,Vom deutschen Volk zum deutschen Staat.Ein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Nationalbewußtseins,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56,S.59.
[30] 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S.31.
[31] 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S.35;Willi Oberkrome,Volksgeschichte.Methodische Innovation und völkische Ideologisier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18-1945,S.30.
[32] Raymond Dominick,“Nasc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Second Empire”,p.261;Gilbert Merlio,“Die mythenlose Mythologie des Oswald Spengler”,in Silvio Vietta,Herbert Uerlings,Hrsg.,Moderne und Mythos,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2006,S.209.
[33] 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S.27;Karl-Werner Brand,“Naturschutz und Umweltdiskurs in Deutschland.Zur historischen Verortung ökologischer Kommunikation”,in Karl-Werner Brand,Klaus Eder,Angelika Poferl,Hrsg.,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in Deutschland,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97,S.13.
[34] 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S.27;Celia Applegate,A Nation of Provincials.The German Idea of Heimat,p.15.
[35] 转引自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S.37.
[36] Theodor Möller,Das Gesicht der Heimat,Kiel:Schleswig-Holsteinische Verlagsanstatl,1914,Krahira!(Ein Geleitwort),IV.
[37] Udo Gößwald,Hrsg.,Immer wieder Heimat.100 Jahre Heimatmuseum Neukölln,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1997,S.10.
[38] K.Schönchsen,Der Kreis Husum.Kleine Heimatkunde für Schule und Haus,Husen:Kommissionsverlag,1909,S.2.
[39] Jürgen Hein,“Die Dorfgeschichte im 19.Jahrhundert”,in Jürgen Hein,Hrsg.,Dorfgeschichte.Stuttgart:J.B.Metzler,1976,S.57.
[40] Jürgen Hein,“Die Dorfgeschichte im 19.Jahrhundert”,in Jürgen Hein,Hrsg.,Dorfgeschichte.Stuttgart:J.B.Metzler,1976,S.58.
[41] Friederike Eigler,“Critical Approaches to ‘Heimat’ and the ‘Spatial Turn’”,New German Critique,No.115(Winter 2012),p.29;Anne Fuchs,“Review:Heimat: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German Idea of Homeland.By Peter Blickle”,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Vol.99,No.4(Oct.,2004),p.1121.
[42] Hans-Otto Hügel,Hrsg.,Handbuch Populäre Kultur:Begriffe,Theorien und Diskussionen,S.227;Pia Janke,Hrsg.,Jelinek-Handbuch,Stuttgart:J.B.Metzler,2013,S.277.
[43] Celia Applegate,A Nation of Provincials.The German Idea of Heimat,p.9;Olaf Kühne,Annette Spellerberg,Heimat in Zeiten erhöhter Flexibilitätsanforderungen.Empirische Studien im Saarland,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10,S.15.
[44] Ulrike Haß,Militante Pastorale.Zur Literatur der antimodernen Bewegungen im frühen 2.Jahrhundert,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93.
[45] Erhard Schütz,Jochen Vogt,Einführung in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20.Jahrhunderts,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77,S.56.
[46] 1816年神学家兼国民教育家克里斯提安·威廉·哈尼施(Christian Wilhelm Harnisch)出版《地理指南》(Anleitung zur Weltkunde)一书,副标题冠以“乡土教程”(Kunde der Heimath)。参见Mathias Beer,Das Heimatbuch:Geschichte,Methodik,Wirkung,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 Verlag,2011,S.56-57.
[47] Gustav Kircher,Heimatkunde für den Oberamts-Bezirk Welzeheim,Stuttgartt-Cannstatt:Verlag von Gustav Hopf,1909,S.5,62.
[48] 德国的乡土志在体例、格式和选材方面与有严格要求的中国地方志不同,其内容宽泛而庞杂,涉及特定地区(地方)的经济、自然、景观、民俗、宗教生活、地方建筑、奇闻轶事、姓氏来源、地图等,主要由非专业的热衷于家乡活动者编撰,具有“群众性”特点。参见Jutta Faehndrich,Eine endliche Geschichte.Die Heimatbücher der deutschen Vertriebenen,Köln:Böhlau Verlag,2011,S.6;Mathias Beer,Das Heimatbuch:Geschichte,Methodik,Wirkung,S.17,74.
[49] Mathias Beer,Das Heimatbuch:Geschichte,Methodik,Wirkung,S.67.
[50] 灰色文献指那些没有进入正规图书交易渠道的私人印刷品、公司印刷物以及会议报告等出版物。OME-LEXIKON.http://ome-lexikon.uni-oldenburg.de/begriffe/heimatbuch/,2018-07-25.
[51] F.Flott,Heimatland OS:Ein Heimatbuch für die oberschlesische Jugend,Breslau:Schriftenreihe der Landesgruppe Schlesien des Bundes Deutscher Osten,1937,S.5.
[52] Karl Mayer,Heimat-Buch Kirchheim u.Teck und Umgebung,Kirchheim u.T.:Im Selbstverlag des Verfassers,31920,S.20-35,3.《泰克山下基尔希海姆及其附近乡土志》是《泰克山下》(Unter der Teck.)一书的第三版书名,前两版出版日期不详。
[53] 转引自Manfred Treml,“Eine Wurzel-viele Blüten-zur Geschichte der Heimat-und Naturschutzbewegung”,in Bayerische Akademie für Naturschutz und Landschaftspflege,Hrsg.,Beiträge zu Natur-und Heimatschutz,Laufen/Salzach:Laufener Seminarbeiträge 4/92,S.14-15.
[54] 热衷于乡土事务者(Heimatler)、乡土研究者(Heimatforscher;Heimatkundler)是德国人对于从事乡土自然、历史和人文等相关领域研究者的称呼。
[55] Ernst Rudorff,“Über das Verhältnis des modernen Lebens zur Natur”,Wiederabdruck des Aufsatzes von Ernst Rudorff aus dem Märzheft 1880 der preußischen Jahrbücher,in Geschäftsführender Vorstand des Bundes Heimatschutz,Hrsg.,Heimatschutz.Jg.6,Heft 1,1910,S.7;参见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S.30.
[56] Andreas Knaut,“Die Anfänge des staatlichen Naturschutzes:Die frühe regierungsamtliche Organisation desNatur-und Landschaftsschutzes in Preußen,Bayern und Württemberg”,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Sonderheft,Vol.15,Umweltgeschichte.Umweltverträgliches Wirtschaften in historischer Perspektive(1994),S.143.
[57] 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S.37.
[58] Manfred Treml,“Eine Wurzel-viele Blüten-zur Geschichte der Heimat-und Naturschutzbewegung”,in Bayerische Akademie für Naturschutz und Landschaftspflege(Hrsg.),Beiträge zu Natur-und Heimatschutz,S.18;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S.122;Thomas Rohkrämer,Eine andere Moderne?Zivilisationskritik,Natur und Technik in Deutschland,1880-1933,S.129;Christian F.Otto,“Modern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The Heimatschutz Discourse in Germany”,Art Journal,Vol.43,No.2,Revising Modernist History:The Architecture of the 1920s and 1930s(Summer,1983),p.149.
[59] Thomas Hertfelder,Franz Schnabel 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Historismus und Kulturkritik(1910-1945),Erster Teilband,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98,S.211,Fußnote 310.
[60] 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S.50.
[61] Richard Bürkner,Kunstpflege in Haus und Heimat,Leipzig:Verlag von B.G.Teubner,1905,S.9,10.
[62] 参见Richard Bürkner,Kunstpflege in Haus und Heimat,S.108-131.
[63] Richard Bürkner,Kunstpflege in Haus und Heimat,S.110-111.
[64] Verena Jakobi,Heimatschutz und Bauerndorf:Zum planmäßigen Dorfbau im Deutschen Reich zu Beginn des 20.Jahrhunderts,Band 1,genehmigte Dissertation,Fakultät VII Architektur,Umwelt und Gesellschaft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Berlin,2003,S.78-79.
[65] Verena Jakobi,Heimatschutz und Bauerndorf:Zum planmäßigen Dorfbau im Deutschen Reich zu Beginn des 20.Jahrhunderts,Band 1,S.105-108.
[66] Verena Jakobi,Heimatschutz und Bauerndorf:Zum planmäßigen Dorfbau im Deutschen Reich zu Beginn des 20.Jahrhunderts,Band 1,S.78-79,105.
[67] Alon Confino,“The Nation as a Local Metaphor:Heimat,National Memory and the German Empire,1871-1918”,p.59.
[68] Renate Schäper,Die Prosa V.G.Rasputins:Erzählverfahren und ethisch-religiöse Problematik,München:Otto Sagner,1985,S.182,Fußnote 1;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wörterbuch,Manheim: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21989,S.680.
[69] Udo Gößwald,Hrsg.,Immer wieder Heimat.100 Jahre Heimatmuseum neukölln,S.17-18.
[70] Michael Wettengel,“Staat und Naturschutz 1906-1945.Zur Geschichte der Staatlichen Stelle für Naturdenkmalpflege in Preußen und der Reichsstelle für Naturschutz”,S.356.
[71] Andreas Knaut,“Die Anfänge des staatlichen Naturschutzes.Die frühe regierungsamtliche Organisation des Natur-und Landschaftsschutzes in Preußen,Bayern und Württemberg”,S.143.
[72] Raymond Dominick,“Nasc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Second Empire”,p.262.
[73] Thomas Rohkrämer,Eine andere Moderne?Zivilisationskritik,Natur und Technik in Deutschland 1880-1933,S.135.
[74] Thomas Rohkrämer,Eine andere Moderne?Zivilisationskritik,Natur und Technik in Deutschland 1880-1933,S.135;Raymond Dominick,“Nasc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Second Empire”,p.263;Thomas Lekan,“A ‘Noble Prospect’:Tourism,Heimat,and Conservation on the Rhine,1880-1914”,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81,No.4(December 2009),p.826.
[75] 1844年丹麦就已经在哥本哈根北部建立了甘默尔(Gammel)沼泽地自然保护区;波希米亚(捷克)在1858年建立了库巴尼(Kubani)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美国于1864年建立了约塞米蒂(Yosemite)自然保护区,1872年建立了黄石国家公园。这些都成为德国乡土自然景观保护的“榜样”。Andreas Knaut,“Die Anfänge des staatlichen Naturschutzes.Die frühe regierungsamtliche Organisation des Natur-und Landschaftsschutzes in Preußen,Bayern und Württemberg”,S.144;Michael Wettengel:“Staat und Naturschutz 1906-1945.Zur Geschichte der Staatlichen Stelle für Naturdenkmalpflege in Preußen und der Reichsstelle für Naturschutz”,S.362.
[76] Raymond Dominick,“Nasc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Second Empire”,p.284;Jens Ivo Engels,Natur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Ideenwelt und politische Verhaltensstile in Naturschutz und Umweltbewegung 1950-198,S.95.
[77] Joachim Radkau,Die Ära der Ökologie:eine Weltgeschichte,München:C.H.Beck,2011,S.71.
[78] Andreas Knaut,“Die Anfänge des staatlichen Naturschutzes.Die frühe regierungsamtliche Organisation des Natur-und Landschaftsschutzes in Preußen,Bayern und Württemberg”,S.154-155;Raymond Dominick,“Nasc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Second Empire”,pp.272-275.
[79] Andreas Knaut,“Die Anfänge des staatlichen Naturschutzes.Die frühe regierungsamtliche Organisation des Natur-und Landschaftsschutzes in Preußen,Bayern und Württemberg”,S.147-148;Raymond Dominick,“Nasc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Second Empire”,pp.278,285.
[80] Theodor Möller,Das Gesicht der Heimat,Krahira!(Ein Geleitwort),IV.
[81] Karl Ditt,“Die deutsche Heimatbewegung 1871-1945”,i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Hrsg.,Heimat:Analysen,Themen,Perspektiven,Bonn:Schriftenreihe der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294/I,1990,S.135.
[82] Hermann Heimpel,Kapitulation vor der Geschichte?Gedanken zur Zeit,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3,vermehrte Verlag,1960,S.50.
[83] Rudolf Vierhaus,Über die Gegenwärtigkeit der Geschichte und die Geschichtlichkeit der Gegenwart,S.19.
[84] Udo Sautter,Deutsche Geschichte seit 1815:Daten,Fakten,Dokumente.Band II,Verfassung,Tübingen und Basel:A.Francke Verlag,2004,S.176.
[85] Christian F.Otto,“Modern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The Heimatschutz Discourse in Germany”,p.154.
[86] Christian F.Otto,“Modern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The Heimatschutz Discourse in Germany”,pp.150,152.
[87] Winfried Speitkamp,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1871-1933,S.40-41.
[88] Christian F.Otto,“Modern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The Heimatschutz Discourse in Germany”,p.148.
[89] Hartmut Rein,Alexander Schuler,Tourismus im ländlichen Raum,Wiesbaden:Springer Gabler,2012,S.46-48.
[90] Verena Jakobi,Heimatschutz und Bauerndorf:Zum planmäßigen Dorfbau im Deutschen Reich zu Beginn des 20.Jahrhunderts,Band 1,S.270,Band 2,S.90ff.
[91] Willi Oberkrome,Volksgeschichte.Methodische Innovation und völkische Ideologisier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18-1945,S.31.
[92] Udo Sautter,Deutsche Geschichte seit 1815:Daten,Fakten,Dokumente.Band II,Verfassung,S.176.
[93] Rainer Wolf,“Entwicklungslinien und Bilanz des Naturschutzrechts”,Natur und Recht(2013)35:S.2-3.
[94] Thomas Lekan,“Reg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Preservation in the Third Reich”,Environmental History,Vol.4,No.3(Jul.,1999),p.384.
[95] David Motadel,“Review Article:The German Nature Conservation Move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ontemporary History,Vol.43,No.1,pp.141-143.
[96] David Motadel,“Review Article:The German Nature Conservation Move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ontemporary History,Vol.43,No.1,p.151.
[97] Rainer Wolf,“Entwicklungslinien und Bilanz des Naturschutzrechts”,S.4.
[98] Gesetz über die planmäßige Gestaltung der sozialistischen Landeskultur(Landeskulturgesetz)GBl.der DDR Teil 1 Nr.12,S.67-68;Hermann Behrens,“Über Kontinuitäten im Naturschutz aus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ie DDR bis heute”,in Gudrun Heinrich,Klaus-Dieter Kaiser,Norbert Wiersbinski,Hrsg.,Naturschutz und Rechtsradikalismus:Gegenwärtige Entwicklungen,Probleme,Abgrenzungen und Steuerungsmöglichkeiten,BfN-Skripten 394,Bonn:Bundesamt für Naturschutz,2015,S.88-91.
[99] Gesetz über Naturschutz und Landschaftspflege (Bundesnaturschutzgesetz-BNatSchG),Bundesnaturschutzgesetz vom 25.März 2002(BGBl.I S.1193);Gesetz über Naturschutz und Landschaftspflege(Bundesnaturschutzgesetz-BNatSchG),Bundesnaturschutzgesetz vom 29.Juli 2009(BGBl.I S.2542).
[100] Jens Ivo Engels,Natur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Ideenwelt und politische Verhaltensstile in Naturschutz und Umweltbewegung 1950-198,S.38;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usfertigungsdatum:23.05.1949,Art 72:2,Art 74:29.
[101] 关于开明专制和19世纪初“大改革”,参见邢来顺、韦红《拿破仑统治时期的莱茵邦联改革运动》,《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邢来顺:《论德国政治现代化初期的“防御性”特征》,《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102] 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Band 1,Vom Feudalismus des Alten Reichs bis zur Defensiven Modernisierung der Reformära,1700-1815,München:C.H.Beck,1989.
[103] Eberhard Orthbandt,Illustrierte deutsche Geschichte,München:Südwest Verlag,1963,S.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