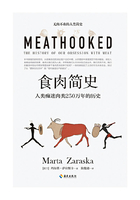
序言
你为什么渴望肉食?这里会有答案
2009年的夏天,我母亲决定成为一个素食者。她已经和素食者一同生活了许多年——我的继父和继兄弟都对肉敬而远之。她在波兰社会里是个贤妻良母,每日都会给他们烹饪素食,再单独做出一份有肉的饭自己吃。没人强迫她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而她似乎也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麻烦。但是在2009年,她偶然读到了一篇关于吃肉危害健康的文章。文中引用了一个样本数量超过50万人的研究数据:大量摄取肉类会提高女性的死亡率,其中因心脏病死亡的概率提高了50%,因癌症死亡的概率提高了20%。研究结果令人不安,母亲对此忧心忡忡。她不想让胆固醇(坏的那种)堵塞她的动脉,也不想让多环芳烃(在肉类烹饪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致癌物质)破坏她的细胞,她保证过要好好地照顾自己。于是她告诉我们,她不打算再吃肉了。
然而,我母亲仅仅坚持了两星期。那之后,美味多汁的火腿和奶油馅饼重新回到了她的冰箱里。从那个夏天开始,她数次尝试过放弃肉食,但从来没成功过。她的努力总是令我想起我的丈夫,他也从未真正地戒过烟。有一次,我问母亲:“您的素食主义进行得怎么样了?”
她耸了耸肩膀,说:“没办法,我就是喜欢吃肉。”
不过,对我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那之后,我的脑海中常常涌现出许多有关我们和肉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比如:动物蛋白质中究竟有什么东西令我们对它们如此渴望?为什么放弃吃肉那么难?如果吃肉对我们的健康真有那么大的伤害,为什么在进化过程中,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进化为食草动物呢?
两年后的2011年年初,我坐在新加坡的八珍(Eight Treasures)餐厅,俯瞰拥挤而嘈杂的唐人街时,从窗口飘来附近寺庙中焚香和赤素馨花的味道。窗外的世界还在喧嚣之中,餐厅里却一片平和。那时我已在新加坡居住了两个多月,渐渐熟悉了当地的文化,但在八珍餐厅里,我还是经历了一件令我大开眼界的事情。这间餐厅分明是个素食餐厅,但菜单上却出现了大鱼大肉的名字:羊肉咖喱、烤乳猪、北京烤鸭等,甚至还有在环保界臭名远扬的鱼翅汤。我十分困惑地叫来了服务生。
“你们这儿究竟是不是供应素食的?”我问。
服务生看着我,好像我脑子有问题,说:“这些都是素食。”
“你是说这些猪肋排……呃,并不是猪肉做的吗?”
“所有菜品都是素肉做的。”服务生回答。
瞧,关键词来了——素肉,这是一种以大豆或谷物为基础的混合物,有时会加入精炼油调味。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我想试试,于是点了一份“猪”肋排,结果出乎意料地好吃。它们外表像肉,质地与结构像肉,甚至吃起来口感也像肉。我仍然不敢百分百确定它们不是真正的肉,也许八珍餐厅的厨师们只是用动物蛋白质欺骗了这些素食者,令他们相信这些全是大豆混合物。但真正令我好奇的是,为什么素肉这种奇怪的东西会存在呢?我们不为那些坚果过敏的人们制作假坚果,也不为不吃根茎类蔬菜的虔诚的耆那教徒制作假胡萝卜(他们认为将植物从土地中连根拔起是一种很暴力的行为),那么,人们为何执着于制作素肉?我们对动物蛋白质的上瘾程度,已经到了宁愿吃含有化学物质的肉类替代品,也不愿意去尝试享受一份简单的咖喱蔬菜的地步了吗?令终身素食者也不能完全放弃的,究竟是肉的香味,还是它身上所代表的社会与文化的吸引力?
时至今日,我母亲也依然在吃肉。她甚至开始享用波兰的肉类美食,比如黑肉肠 ①和鸡肝。我不会执意测量我母亲盘内的食物,但如果她和大部分波兰人一样,那么她一年大概要吃掉70千克肉。美国人吃肉的速度更快,差不多一人一年要吃掉125千克肉。与此同时,不计其数的科学报告中宣扬着吃肉对健康的危害。这些研究表明,大量摄取熟肉和红肉的群体患结肠直肠癌的概率比少量摄取的群体高20%~30%。食用红肉与禽肉类,男性患上糖尿病的概率将提高40%,女性则提高30%。在一项对超过120 000人的调查中,研究员发现:“高度摄入红肉将会提高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死亡率,并预计大约9.3%的男性、7.6%的女性可以避免这种结果,只要他们每天都少吃半份红肉(大约42克)。”同时,研究显示,加州的素食者普遍比加州其他人的寿命长9.5年(男人)和6.1年(女人)。
类似的研究报告真的能阻止我们继续吃肉吗?其实不会,美国的肉类消耗量数十年来一直在增长。来自美国农业部(USDA)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我们每个人平均要吃掉比1951年多28千克的肉——这相当于60年来,平均每年多吃掉0.5千克牛排的水平。尽管关于癌症、糖尿病或心脑血管疾病的警告与日俱增,且这些警告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但也无济于事。并且,这种情况并不只存在于美国,放眼全世界,人们对动物蛋白质的需求量也一直在增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到了2020年,与2011年相比,北美地区的肉类需求量将会提高8%,欧洲地区将会提高7%,而亚洲地区则会大幅提升56%。中国的肉类消耗量从1980年起翻了4倍。众多科学期刊中涌现出关于中国人因激增的食肉量(也包含其他原因)而导致健康状态每况愈下的研究,但科学家们所描绘的这种可怕场景似乎并不能让亚洲人放弃宫保鸡丁和木须肉。
全世界的这种对于动物蛋白质的热爱,不仅仅在破坏我们的健康,同时也在破坏我们的地球。媒体日复一日地报道着这些:每一个汉堡对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约等于一辆美国汽车行驶320千米带来的影响。动物蛋白质中每释放1卡路里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比植物每制造1卡路里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不少。食肉行为应为全球大约22%的温室气体负责——相比之下,航空业只贡献了2%的温室气体。从一些最新预测来看,全球变暖最终会导致海平面上升4~9米,21世纪结束前,纽约和上海这种沿海城市将会被淹没。所以科学家和一些政治家试图找到解决方法,比如寻找可替代矿物能源的新能源、商讨如何鼓励人们减少能源消耗、驾驶更小的汽车等。但是,有一件事从理论上来讲是非常容易做到的——比发明太阳能汽车简单得多——还可以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减缓全球变暖,提高我们生存下来的概率,那就是成为素食者。只可惜,我们不想放弃吃肉。
肉食困境同样有着道德标准。从2003年盖洛普(Gallup)公司所作的民意调查来看,25%的美国人认为动物值得拥有和人类一样不被伤害和不被利用的权利。另一个研究调查显示,81%的俄亥俄州人认为善待农场中的动物应该和人们对待自家宠物一样重要。但我们并没有像对待自家的小狗、小猫那样对待农场里的动物,也并没有保证它们获得和人类相同的权利。相反,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我们剪掉了农场禽类的喙来防止它们在绝境下互相残杀。同样,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我们剪掉了猪的尾巴来防止它们失去理智后互相撕咬。我们将至少11只下蛋母鸡全部塞进一个小笼子里,使其无法活动,结果发现它们经常会卡在围栏里,然后饿死或渴死。其实,并不是我们对它们没有同情心,也不是就喜欢看着它们受苦,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困扰着我们,而这恰恰就是我们用复杂的心理暗示来回避这种伤害生物的负罪感的根本原因。我们告诉自己,这些家禽注定是要受苦的。我们说服了自己,这些家禽没有那么聪明。我们将鲜活的生物和盘子里的食物区分得一清二楚,科学家认为,一旦某类物种被打上了“肉类”的标签,我们就会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它们,并失去敬畏之心。
尽管吃肉对我们的健康、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以及我们的良心都有伤害,但人类没有可能真的放弃肉食。盖洛普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 1943年不吃肉的美国人占2%左右,到了2012年,认为自己是素食者的人群占比增至5%。但另一个调查显示,有60%自称素食者的人群其实仍在偶尔食用红肉、禽肉或鱼类,这就相当于素食人群比例又降至2.4%,与1943年不相上下。
而我自己,就是一个不怎么纯正的素食者。首先,我吃鱼,主要是因为我懒。我住在法国,一个钟情鹅肝和马肉的国家。当然,我指的不是巴黎,而是法国中部森林中的那些小村庄——那里的人对素食者非常不友好。我很喜欢在餐厅里和朋友们聚餐,如果我坚定地拒绝吃肉,那我现在应该已经吃了数不清的山羊奶酪沙拉了。当地的菜单上实在是没有什么不含肉的菜肴,所以我会点黄油大蒜酱白鱼或者烟熏三文鱼,但我并不会因为仅仅是吃鱼而内疚。有时,如果没人在我身边——这实在有些难以启齿——我会吃一根香肠或者一片培根。这种情况不多,大概每半年一次,但它们的味道通常会让我失望。我为自己伤害了那些可怜的猪、牛或者鸡而感到内疚,并且我发誓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然后,是的,这些事又会再一次发生。就像我母亲一样,我似乎也不能完全放弃肉食。肉里真的有一种奇妙的东西,可能是来自它的文化、历史、社会诉求,或者是化学合成物,让我流连反复。
在美国的书店里,摆放着许多说明我们对肉的痴迷有多么不健康的书籍,同样也有许多关于那些农场禽类是多么的可怜的书籍。大多数我都读过,但没有哪一本书真正回答了这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吃肉?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找到肉类究竟为人类提供了什么,无论它的代价有多大——我们内心的负罪感、对心脑血管的伤害、对地球的污染——我们却还是在不停地吃肉。就好像大自然给我们开了个玩笑,它给了我们对某种东西的渴望,尽管这种东西实际上对自身有害。
所以,是什么在驱使着我们?我母亲的答案是——“我就是喜欢”——这还远远不够。这个答案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青春期女孩儿告诉她焦虑的父母,不愿离开自己男朋友的原因是“我喜欢他”。然而,就是这一瞬间,我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但这位少女不是因为“就是喜欢”而喜欢她男——朋友的,她之所以喜欢这个典型的雄性人类,是因为他的身体散发出了足以吸引她的荷尔蒙;是因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她倾向于喜爱高大健壮的类型;是因为她被一个强势的母亲和没有安全感的父亲抚养长大,所以她喜欢他拥有的自由的灵魂。同样,我们不是因为“我就是喜欢”才吃肉,我们对肉类的渴求要远多于这些。
这本书是对人类无肉不欢的根本原因的深入研究,故事从15亿年前地球上唯一的海洋的温带水域中古老的细菌接触到其他肉类开始。这本书揭示了跨越几千年的、星球上的第一个幸存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最初的食肉动物诞生的过程。他们传承了古人类的血统,学会了食肉以及追踪猎物,他们是从偶尔食肉的动物中派生出的一系:他们拥有更先进的大脑和社会结构。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是食肉令我们成为人类,不仅帮助我们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甚至也是我们细软的毛发与发达的排汗系统的功臣(比起我们的近亲黑猩猩来说)。
伴随着人类进入现代,本书的内容也开始向生物学趋变。是不是肉里有什么化学元素令我们吃肉上瘾?它是否由2-甲基-3-呋喃硫醇或其他上千种挥发性化合物中的一种,组在一起构成了肉食特有的令人垂涎的香味?那是日文中说的多存在于肉类、蘑菇与牛奶中的“美味”吗?或者肉类其实是维持健康的必需品?尽管有得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但如果没有肉,人类变成了一种弱小的、免疫系统缺失的种群,会不会更糟糕?一些基因突变的人,他们不喜欢雄烯酮①的气味,注定是素食者;但另一些对水果和蔬菜中的苦味十分敏感的人,他们会更倾向于吃肉吗?这些是否只是年销售额1 860亿美元的庞大肉食产业所进行的熟练的市场营销与游说?或者,这说明我们对动物蛋白质的兴趣事实上与我们所能获取的最大利益相挂钩?或者也可能——仅仅是可能,我们吃肉只是一种习惯,因为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与历史中?毕竟,感恩节如果没有火鸡,夏日烧烤如果没有汉堡,那该是什么样子啊?也许,我们吃肉是因为多少世纪以来,它都象征着男子汉气概,象征着对贫穷、自然与其他国家的权力?我们对肉的喜爱是一种“瘾”吗?无论是生理上或是心理上,或者二者皆有?如果是,那我们能否打破这种“瘾”?告诉人们“要少吃肉”是否与让一个烟鬼去戒烟没什么区别?
正如本书所揭示的,肉食对我们的吸引力由许多因素组成。我管这些因素叫“钩子”。这些“钩子”连接着我们的基因、文化、历史、肉类产业的权威和我们政府的政策。我一个一个地详细研究了这些“钩子”,试图找出肉类吸引力中的个人原因——比如影响你可以吃多少牛肉的5-羟色胺受体基因的特殊多态性的重要性,或者美国27亿美元的玉米补贴对提升肉食欲望发挥的作用。在每一章中,我分析了这些或大或小的“关联钩子”。我的结论是,人类与肉类的这种关系依然会存在于未来。我们会开始限制肉食消耗量吗?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会发生什么?我们不久会开始食用实验室研制的牛排、昆虫汉堡或者在自家厨房用3D打印做出来的以植物为原料的鸡肉吗?
《食肉简史》不是一本讲述吃肉的危害的书,也不是一本讲述那些农场禽类遭受苦难的书,这种书已经太多了。我可能是个素食者,但我不会指导别人一天应该吃多少肉,或者是不应该吃肉。我只会提供事实:肉里的什么东西令我们上瘾、文化如何鼓励我们吃肉以及我们的基因中是如何根深蒂固地种下了食肉需求的种子,其他的则由你们全权决定。
如果你是一个狂热的肉食爱好者,那么这本书可以帮你了解是什么驱使着你的味蕾,并且可以让你意识到,原来吃肉也会影响你整个人的性格与行为。如果你是美国那39%在努力减少肉食的群体之一,那么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饮食习惯,通过让你理解减少肉类消耗之所以困难的原因,从而帮助你对症下药。正如在你不了解为什么对烟草上瘾的情况下,你就很难戒烟一样,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让你渴望肉食,那么你也很难减少肉食的消耗量。而对于那些坚定的素食者以及虔诚的素食者来说,本书则可以帮助你们去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不愿跟随你们的脚步,并且在你们鼓励吃素时他们时常会表现出愤怒。我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够帮助你们保持清醒,并提供一些饮食建议,而不是简单地、样板化地根据文化、习俗、不完善的政府饮食指南或是你母亲在孕期吃的东西来提出建议。
但归根结底,本书讲述了一个故事——我希望它能带你穿越历史和空间,从前寒武纪的深处到21世纪中期,从印度的牛排屋到贝宁的伏都庙,再到宾夕法尼亚的肉类实验室。这将是一个讲述人类痴迷肉类的故事:它如何开始,为什么越来越强烈,以及最终将怎样结束——如果真有那天的话。
① 黑肉肠,一种以猪血和猪肺为主料制作的香肠。(若无特殊说明,本文注释均为译注。)
① 雄烯酮,一种哺乳动物信息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