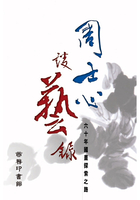
國畫題材(一)蔬果蟲魚
蔬果蟲魚可以說自有人類以來,便同時存在生長,而且是人類賴以延續生命的重要資源。隨着文明的進化,對它們的認識與日俱增,中古時期的典籍如《詩經》、《爾雅》等已有詳細的名實詮釋。野生土長的蔬果草木,逐漸移植到田畦園圃之間,許多禽鳥蟲魚皆可豢養玩賞,實用功能之外,成為人類的寵物,增添了生活的情趣,甚至成為繪畫的題材,以之寄興、怡情、養性,也是出於自然的事。
蟲魚果實禾穗之屬紋樣,在殷商、周秦、戰國、兩漢遺存古物上獲見實例。同樣的題材,要到兩晉南北朝時才逐漸有畫家的專題製作、在絹帛上以純粹繪畫成為卷軸、這在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上有很詳細的記載。至於花鳥畫成為專門的畫科,到唐末才漸告盛行,與山水、人物畫並驅,名家輩出。宋代御府珍藏的名畫,分錄在《宣和畫譜》上,可惜唐以前的畫作,現在大都已名存實亡,但看譜列名錄之富,畫家之多,足見歷代畫風之盛,傳統淵源之深。現存蔬果蟲魚之畫,在兩岸故宮博物院及省、市、縣各級博物館等均有收藏,其中兩宋以後所作,質量尚豐,可供欣賞、研究、揣摩之用。
畫蔬果蟲魚畫,須對古器紋樣、名實詮釋文獻、碑刻、帛畫、壁飾、卷軸名畫、時人佳作,仔細研讀、觀摩,並對實物進行寫生,使提高繪畫的修養和技巧,益以畫者個人不斷充實進修,畫作自當更有內涵。
中國繪畫傳統的延續和開拓,須以主觀的審美經驗,注入現代人的思想、感情,使作品成為具有生命力的新文人畫。
蔬果蟲魚畫可反映出中國人的生活和感情。這些題材廣泛而親切,普遍涵蓋在日常生活中,成為人們的精神營養。在平凡的蔬菜中,可以發現淡泊儉樸的永恆意義。在常見的果實中,可以了悟到造物的巧妙和圓滿。在微小的昆蟲中,可以感覺到生命的可貴和尊嚴。在隱現的游魚中,可以體驗到理想的自由和快樂。
1 蔬
在中國畫的傳統中,以蔬菜入畫,有一定的含義。古代儒家思想主張,人們在得意時要有匡時濟世,積極入世的志願;失意時則學圃灌園,過出世的隱逸生活。所謂「布衣暖,菜根香」、「菜根滋味長」等等。意思是節儉的生活可以減低慾望,減少罪惡,是一種美德。人的一生顯晦無常,但要做到得意不可忘形,失意不可喪志,有面對逆境的韌力,方算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幅蔬菜畫,如果沒有這種含意,就顯得淺薄了。另外蔬菜畫也存在美學與藝術上的審美價值。蔬菜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畫者對這些形象十分熟悉,而表現手法以疏淡簡約為常,與其他題材繁縟絢爛的畫面異趣。蔬菜畫大都出於水墨,樸素而率真。揮毫之際,每能在筆下透露畫者的素養、性情、人生觀,以及所寓意願。所以說蔬菜畫雖屬小道卻甚為可觀。
晉代郭璞註《爾雅》中說:「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辭海》釋蔬:「可作副食品的草本食物的總稱,也包括少數可作副食品的木本植物和菌類。」本畫譜所含除了草本蔬菜之外,亦有選取菌類、根莖、種子及水生植物。
蔬菜畫究竟在甚麼時候開始?如今實難以稽考。但可信的是,自古人類就發現了可以食用的植物;人將熟悉的物體形象,畫在巖石上、牆壁上以及所用的器皿上,這些圖樣提供了後人對先民生活的實際情況的了解,也算是繪畫蔬菜的開始。
美術史上最早的蔬菜畫,有在七千年前新石器時代,浙江餘姚河姆渡出土文物中,所發現的刻有水稻和海藻的殘片。另外距今約四千年前秦都咸陽所發掘的三號宮殿建築,在其殘存的東西兩壁上,有十枝麥穗畫。(以上兩說詳見王伯敏著《中國美術通史》第一冊第五四頁及第二六四頁。)這些均被認為是食用植物最古的圖樣了。
根據各種著錄,蔬菜畫家自唐代迄今,僅可得四十餘人,在眾多的畫家中佔數極少。在宋代《宣和畫譜》中,蔬菜與果類並列於第二十卷之末,所錄當時有遺存畫作者為陳朝顧野王、五代唐垓、丁謙,及宋代郭元方、李延之、僧居寧,僅六人而已。事實上花鳥畫著名畫家兼擅蔬菜畫者,尚有唐代的邊鸞、五代滕昌祐、黃筌父子、徐熙、徐崇嗣祖孫、宋代易元吉、趙昌祐等,可惜那些作品至今大都已名存實亡。至於有畫迹傳世者,有元代錢舜舉、王好文;明代沈周、徐渭、陳道復、孫克弘等;清代有朱耷、石濤、惲壽平、李鱓、黃慎、李方膺、虛谷、馬元馭、陸恢等人。迄近代有趙之謙、吳昌碩、任薰、任頤等;現代則有齊白石、張大千、李苦禪、潘天壽、來楚生、王個簃、王雪濤等。皆能寫生傳神,各擅勝場。
明清以後的蔬菜畫,往往在小品冊頁或在長卷中與花果同畫。常見的題材是:青菜、紫茄、竹筍、芥菜、蘿蔔、茭白、菱角、蓮藕、慈菇、芋頭、菌菇、百合、稻穗、生薑、綠葱等等。
歸納蔬菜畫的表現技法,計有:鈎勒、鈎填、點垛、沒骨、水墨、彩墨、工筆、寫意等。當代更流行大寫意、變形、變色的半抽象作品,其中造型、設色、構圖、題材以及書題,皆有與古人不同處,或古人未到處。
時至今日,中國繪畫仍以繼承、延續傳統為主,但同時要求更多開拓、創新。現代中國畫必須充滿現代人的生活氣息。
2 果
唐末五代以降,果實畫歷代皆有名手劇迹傳世。而民間習俗,神話傳說,歷史紀錄,有關各地風土特產的記載很多。可見時鮮生果對生活的重要。
鮮果可口美觀,時常作為供奉仙佛的食糧;也是饗宴必備的餐後佳品。投桃報李則是友誼交往的媒介。櫻口、梨渦比擬女性顰笑之美;而榴實多子、荔枝生利、桃熟千年、瓜瓞綿綿,色香兼味,充實圓滿,無一不隱藏着美好的象徵。
據傳戰國時大哲學家老子,在李樹之下誕生,因此姓李。漢代壁畫有春秋齊景公時「二桃三士」的故事。雖則是人物畫的配景,卻說明距今二千多年前,桃子已是大眾愛好的果子。東漢末孔融分梨,時至今日仍是教育兒童「禮讓」的模式。晉代俊美的潘安所經之處,愛慕他的婦女為之擲果盈車,傳為美談。「一騎紅塵妃子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等名句,留下唐、宋時期美人、名士嗜食荔枝的故事。
果實畫與蔬菜畫屬同一門類,一向附屬於花鳥畫。凡擅蔬果畫者,大都兼能花鳥;但畫花鳥畫者,未必兼善蔬果畫。蓋用筆、設色、形象、構圖皆有所分別也。
據宋《宣和畫譜》著錄,宋初徐熙及其孫崇嗣、崇矩的作品中,有不少以果實為題之畫。在徐熙條下有寫生果,如綠李、朱櫻、枇杷、銀杏、錦棠、木瓜等圖。徐崇嗣條下有寫生桃、折枝雜果、寫生瓜、寫生果等,並稱其「又有墜地果實,亦少能作者。」徐崇矩亦有擅寫果實之紀錄。相信蔬果畫的題材,頗合徐家野逸清淡的畫旨,所以在這方面的成就,超越黃筌家族以富麗精工為尚的院畫。
畫果實以寫生為主。古時即有「最為難工」之喻。宋《宣和畫譜》之〈蔬果敍論〉中云:「蓋墜地之果易工於折枝之果,而折枝之果又易工於林間之果也。今以是求畫者之工拙,信乎其知言也。」這說明畫果三種不同的表現程度。蓋墜地之果可任意安排,只須顧及果實本體之形狀、顏色;折枝之果須了解枝葉之形態與果實之配合,疏密、掩映之關係。林間之果尤須畫者觀察果樹之生態,描繪整體形勢與形象。如欲評鑑畫果枝藝之高下,余認為將此三者作為標準,才能算是「知言」。
宋時畫院有不少人畫果,但甚多沒有題畫者的名字。這些畫大都是當時進呈御覽的作品,傳到現在統稱之謂「宋人無款」畫。傳世的宋人畫冊中,有宋徽宗趙佶的水墨枇杷,林椿的荔枝、葡萄、林檎(即蘋果),馬麟的綠橘……等。皆設色明麗工緻,且比例正確,既寫實又生動,相信都是從寫生而來的。南宋牧谿僧法常,有「水墨花果長卷」傳世,上有明代沈周長題,譽其成就較之黃筌、錢舜舉尤有過之。又有水墨「六柿圖」,後世定為禪畫模式,現藏日本龍光院,並列為國寶。其畫作風靡畫壇,至今不衰。同時亦為西洋美術界所傾倒。美國蘇立文教授著《中國藝術史》中,稱他:「表現一種自然的精髓,它包括物體內在生命力的繪畫魅力。」
元代以錢選(舜舉)最擅蔬果寫生,他的技法與古為新,師法趙昌而別有風致,成為明清畫家師法的先導。又元僧溫日觀擅寫水墨葡萄,以草書筆法畫藤枝,筆力放逸而遒勁,意趣高華,為世所重。
明代莫雲卿(是龍)在「題孫克弘花果長卷」中,概括地敍述了花果寫生畫的歷史:「寫生肖物,非筆端神妙巧奪化工者不能。自徐熙黃筌父子後,則有勝國時王若水、張遠、錢舜舉諸人。我朝惟沈徵君石田、陳太學道復草草弄筆動有意態。邇來幾為絕學……。」此雖係泛論,亦可知後繼為難之情況。但揆諸事實,當時尚有徐渭(文長)、陳嘉言(孔彰)、陳洪綬(老蓮),及稍後之周之冕(服卿)等,皆卓然大成,承先啟後,不讓前賢。
迨至清代花果畫家不斷湧現,八大山人(朱耷)之崛起,開拓了以後三百餘年的新畫風,以率性簡筆為尚,後繼者如楊州畫派中之華喦、高鳳翰、李鱓、金農、黃慎、李方膺、邊壽民、羅聘等,都有抒情寄意,即景寫生的創作特點。憚壽平則繼承徐崇嗣的沒骨法而加以再創造,成為一代大家。清末民初留寓上海的張熊(子祥)遠紹周服卿、王忘庵,頗負時譽,並曾提掖任伯年。伯年老師任薰,有陳老蓮遺韻而自具面目。朱偁(夢盧)花果亦獨步一時。趙之謙、吳昌碩以篆隸書法筆意成畫,渾厚古拙,成為金石派巨擘。弟子王震(一亭)亦多新猷。虛谷畫疏秀冷峻,簡約生拙,耐人尋味。蘇州陸恢(廉夫)行筆流暢,設色雅淡,師承有緒,畫思雋逸,為吳門高手。廣東居廉(古泉)筆致工整,敷色妍麗,與兄居巢同負盛名。丁輔之專畫果實,狀物畢肖,用筆謹細,施彩漬染頗有獨到之處。
本世紀有于非闇之工筆鈎染,朱屺瞻之拙筆粗毫,天真稚拙,為時人傾倒;齊白石純厚含蓄,色墨爛漫,成為大匠;潘天壽線條如鐵,凝煉老辣而韻味深長;張大千偶作蔬果,雅逸過人,於取材主題頗多逾越古人,自成一家法;高奇峰、劍父兄弟,融合東洋畫法,每多彩墨渲染,自成新格,為折衷畫派先導;弟子趙少昂用色絢爛,造型生動,學之者甚眾;來楚生狀物傳神,簡括洗煉,筆法有金石味;唐雲取法八大,石濤推陳出新;王雪濤得力寫生,筆致率意,神采飛揚;石魯勇於創新,外觀草草而蘊意精謹;吾師張星階先生取法華喦、陸恢,晚年隨意點染皆有妙諦;柳君然先生師事陳摩(迦盦),四十年代吳中花果妙手,馳譽江南……
綜觀古今名畫,果實畫家於此竭盡智能創出新作,繼往開來,代代不息,畫者寄意而觀者愜心,成為樂事。果實入畫雖已歷時千年,但有演進,更多蛻變,蓋命意取材、諸種技法,俱已去古甚遠,早已脫出樊籬。時至今日,生活思感日新月異,展望前景,更多開拓,自有一番前所未有之新氣象。
3 蟲
古人以蟲豸入畫,衍傳至今仍是絕好題材。殷商時代的人,對於蟬、螳螂、蠶、虺、蛙、貝、龜之類特別愛好,在玉器、銅器、陶器上甚多此類紋飾及雕刻。這反映了先民與蟲類在生活上長久以來的關係,明顯地表達了他們對自然生命的尊重和愛護。憑着精細的觀察,塑造千姿百態、栩栩如生的形象,在圖紋上表現活潑的生命氣息,到達物我合一的境界。古人形容詩賦是「雕蟲小技」,蟲者,蟲書也,是秦書體中之一種。蟲書的鑄成,基於觀察蟲豸彎曲蠕動的形態。在應用上,需要鐫刻,這技術在當時是很普通的。漢代揚雄自謙他的賦,猶如雕刻蟲書那樣平凡。總括來說,先民觀察自然物體的形象,或組成文字,變為書法,或描出紋樣,成為繪畫,書畫源同異流,各自成為體系。小小一條蟲豸對於中華文化的影響,竟是如此巨大。
昆蟲一向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小生物,但是在中國花鳥畫中卻佔有重要的地位。有了它就會平添不少趣味和動感。相傳畫蟬,是由晉代顧駿之開始,同時代丁光亦能畫蟬。陳朝顧野王有草蟲圖。唐朝的嗣滕王湛然擅畫蜂蝶;邊鸞畫蟬、蜂、蝶,精於設色,濃艷如生,冠絕當代;周昉亦有蜂蝶圖;陳恪號稱蟲禽皆精。但是他們的作品只有文字紀錄,今已見不到真迹。
直到現在能夠目見的昆蟲畫,有五代黃筌畫給他的兒子居寶的一幅畫稿,名為「寫生珍禽圖」。畫上除了各式禽鳥外,尚有甲蟲、蜜蜂、黃蜂、蝗蟲、蚱蜢、蟬、天牛、蟋蟀等等。後人評之為「精工富麗,生動逼真。」根據這幅真迹,可以略為窺見他的老師滕昌祐、刁光胤輩的技法及畫風,同時亦足以肯定他能繼往開來,對後代花鳥草蟲畫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同時代的徐熙,相傳有一幅「豆花蜻蜓圖」,雖屬小品,卻有徐家落墨花法的特點。這幅畫歷時千年以上,天工清新,恍如剛畫不久,且對於蜻蜓的生態、結構、形象、色彩等等至為講究。由此足見古人對事物觀察精到,尤其能夠把握神韻,賦予永恆的生命,至為可貴。
稍後北宋徽宗皇帝趙佶擅畫粉蝶;易元吉有蜘蛛、蜂、蟬之畫,號稱「動臻精奧」。南宋林椿擅畫螳螂、蜻蜓、絡緯、甲蟲;馬興祖、李安忠均能畫蜂;朱紹宗畫飛蝶;韓祐、曹達臣輩畫草蟲,皆載於畫史。
元代花鳥畫衰頹,不復前朝之盛。花鳥畫家以錢選、王淵、陳仲仁等為宗師、對後世有深遠影響。能草蟲者有曾雪峰、方君瑞、堵信卿等,但傳迹甚少。
明代崇尚摹古,畫者雖眾,傑出者基少。畫草蟲馳名於世者屈指不出十人,計有王武、周之冕、陳洪綬、孫克弘、陳嘉言、陳繼儒、陸治、孫龍、文俶、郭詡等。
清代則以朱耷、李鱓、宋光寶、居廉、馬元馭、翁雊、袁江、沙馥、蔣廷錫、任薰、高其佩等為著名。
現代善花鳥畫兼擅畫草蟲者應推:齊白石、于非闇、劉奎齡、陳樹人、高劍父、高奇峰、程璋、張大千、丁衍庸、潘天壽、王雪濤、趙少昂、張星階、陳佩秋等,都有很高的成就,作品為人喜愛。
歷代畫草蟲的文獻,涉及繪寫的經驗和特點。
其一是在宋代《鶴林玉露》一書中,羅大經論畫:「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耶?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其二乃於公元一七〇〇年前後,清代王 等所撰《畫花卉草蟲淺說》中,提到畫草蟲須得其飛翻鳴躍之狀,及審察草蟲因季節不同而變色的要點,並提出在技法上的分別,「畫翎毛注重鈎勒,畫草蟲則多點染。」要訣更在於:「飛躍勢若生,設色工點畫,微細得其形,神先筆下得。」玩味所說並周覽歷代草蟲名作,覺得要將草蟲畫好,必須觀察,如曾無疑那樣從籠而觀之,再就草地觀之,以得其「天」——它的生態、神采、形狀的細節和動勢。
等所撰《畫花卉草蟲淺說》中,提到畫草蟲須得其飛翻鳴躍之狀,及審察草蟲因季節不同而變色的要點,並提出在技法上的分別,「畫翎毛注重鈎勒,畫草蟲則多點染。」要訣更在於:「飛躍勢若生,設色工點畫,微細得其形,神先筆下得。」玩味所說並周覽歷代草蟲名作,覺得要將草蟲畫好,必須觀察,如曾無疑那樣從籠而觀之,再就草地觀之,以得其「天」——它的生態、神采、形狀的細節和動勢。
除以上各說之外,清代鄒一桂的《小山畫譜》中有「四知」之說,如能通識,當能進入畫境的深度。四知者,知天、知地、知人、知物也。譬如「春景勿綴秋蟲」即屬知天的範疇;「折枝無蜂蝶之來採」則是屬於知物的常識。
春花秋卉,四時自然景色畫中綴以草蟲,風姿翩翩,清姿妙態,仿佛可以聽到它的鳴聲,看到它美妙的舞步,帶來花鳥畫生動的趣味,增加畫面的妍麗。
宋代梅聖俞〈觀居寧畫草蟲詩〉,研究草蟲畫者讀此可得一完整的概念,當大有助益,特拈出以作結。其曰:「古人畫虎鵠,尚類狗與鶩。今看畫羽蟲,形意兩俱足。行者勢若去,飛者翻若逐,拒者如舉臂,鳴者如動腹,躍者趯其股,鳴顧者注其目。乃知造化靈,未抵毫端速。」
4 魚
上溯史前彩陶上的紋樣,先民樂於應用魚的圖形,使得實用器皿留下家族的記號和美麗的裝飾。各地所發現的遺存實物為數甚多,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史迹,據此足以推測到先民當時的生活環境和習俗。魚形的選擇、應用,證明魚與民族生活的密切關係,在畜牧、狩獵、農耕之外,魚穫應是原始生活的重要資源。眾多的實證,直接說明了人對魚的需要和感情。反映在生活上衍化而來的種種象徵,諸如:鍾靈、信使、神通、辟邪、消災、祈福、吉祥、優游、愉悅、情愛、婚配、富裕、豐足、美食、友誼、教化,以至徽記……。它的功能有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包容至廣、影響悠久的歷史,融合在中華文化的巨流之中。
魚畫為水族畫中的一門,亦稱鱗介,包括龜鼈、蝦蟹、貝殼之類在內。水中動物種類繁多,繪畫則多選擇常見的有代表性的以及為人喜愛的鱗介,集中而概括地表現出它的形狀、生態和性格為要點。換言之,並非畫出狀如刻板的標本就算;而須着重在表現它的生命、意趣,以及畫者所賦予的寄託和思想感情,作主觀的代入,這是符合荀子所言「美善相樂」的審美標準的。
歷代繪畫文獻如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宋徽宗趙佶《宣和畫譜》、元湯垕《畫鑒》、清王 《芥子園畫傳》、清鄭績《夢幻居學畫簡明》……等,對魚畫均有所論。揣摩諸文內容,要旨在畫者觀物之生,體物之精。畫魚者須得噞喁游泳之狀,將鱗鰭簡化,如在水中若隱若現,與風萍水藻相配合,觀之活脫方為佳妙;畫水則須識翻濤巨浪、盤曲瀲灩、淺波漣漪、清流潺潺等種種水性。然則畫魚、水亦甚難矣。
《芥子園畫傳》、清鄭績《夢幻居學畫簡明》……等,對魚畫均有所論。揣摩諸文內容,要旨在畫者觀物之生,體物之精。畫魚者須得噞喁游泳之狀,將鱗鰭簡化,如在水中若隱若現,與風萍水藻相配合,觀之活脫方為佳妙;畫水則須識翻濤巨浪、盤曲瀲灩、淺波漣漪、清流潺潺等種種水性。然則畫魚、水亦甚難矣。
國畫家喜畫雙魚,有雙重意義。其一,源出古樂府,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後人乃以雙鯉代指情誼深重的書信。其二,歷來民俗,魚為吉慶之象徵,如「年年有餘」、「吉慶有餘」、「雙魚吉慶」等,均以雙魚為表現的主體,以魚與餘為同音之故。
又有以九魚為題,稱為「九如圖」,此亦因魚與如為諧音。其來源出自《詩經·小雅》〈天保篇〉,辭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又曰:「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詩中有九如字,畫家以九魚代之,為祝頌之畫。
鯉魚向為文人所重,昔時凡應考得中,輒曰:「鯉躍龍門」。表現於畫作,畫鯉魚躍出水面,並以朝陽作為背景,殊為壯觀。此風傳至東瀛,甚多名作。
自古到今所畫水族魚介,不外如下題材:鯉魚、鱖魚、鯰魚、 魚、鱸魚、河豚、金魚、黑魚、白魚、
魚、鱸魚、河豚、金魚、黑魚、白魚、 魚、小魚、蝦、蟹、蚌、蛤、螺、蛙、蟾、龜等。但文人寫意非特專畫某種魚類者,率意而為,則統稱之為「游魚」。
魚、小魚、蝦、蟹、蚌、蛤、螺、蛙、蟾、龜等。但文人寫意非特專畫某種魚類者,率意而為,則統稱之為「游魚」。
畫魚蝦尚須熟悉荇藻及水波的畫法。荇藻點綴使游魚載沉載浮,以欣以游。《詩經·小雅》〈魚藻篇〉上說:「魚在在藻」。漢《毛氏傳》:「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指繪魚兒游於有水藻的水中,適性而自得,故此畫魚須知曉水藻的種類與畫法,方可配置妥當,得心應手。大致水中的藻類有:龍鬚草、蒲草、馬尾草、馬鞭草、狐尾草、貓耳藻、水柳、粗葉水蘭、細葉水蘭、金魚草……。以上名稱,有以長短、粗細及色澤區分,餘如松針、羽毛、韭菜、柳葉、貓耳、狐尾等不一。
亦有不畫藻類及水波者,以留白為背景,一如齊白石所畫魚蝦,不着一筆水藻,反而主題突出,且有海闊天空,優游泅泳之樂,較之刻意求工者,更勝一籌矣。
自五代宋初開始,蝦蟹已見入畫,漸漸成為風尚,代有名手,如五代黃居寀、北宋徐崇嗣等。陳可久、劉寀則以畫魚著名於世。元代很少人畫水族魚類。畫史上載有釋仲山、俞巖隱等,但僅能知其名而難見其畫。
明代有徐渭、周之冕、孫克弘、王維烈、周天球、張翀、繆輔等,他們的水族魚蟹作品,在中國博物館藏品中可以見到,極有參考價值。
清代的朱耷是畫魚的高手;惲壽平、黃鶴、高其佩、華喦、李鱓、張風、袁江、翁雊、虛谷、馬元馭、任頤、蔡嘉輩皆善畫魚。又清時人嗜食河豚,認為天上第一美味,因此筆下常見畫河豚者,亦可反映當時流行食譜。
現代齊白石畫魚蟹蝦等,筆墨簡煉生動,舉世聞名。齊氏變古人獨蝦而成羣蝦,能銜接傳統而有所提高,自成一家。其餘如高劍父、張大千、汪亞塵、潘天壽、來楚生、李苦禪、張大壯、王雪濤、凌虛、趙少昂、劉獅等,雖學有偏專,藝有高下,惟皆聞名於時。
昔莊子與惠施在濠上有魚樂之辯。我雖非魚,但能畫魚,且諳魚之性情,乃深知魚之樂者。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