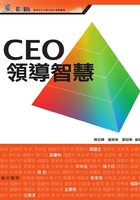
八十年代初和中國企業的合資體驗
因為董浩雲先生的公司是家族生意,我有機會一窺家族生意的典型面貌。東方海外持有青衣島上的一家船塢,它不大成功,就連我們自家的船要修理時都不去那家船塢,很明顯有問題。不少人已為它想過辦法,但也不成功,董浩雲先生要我給他一些建議。
那是八十年代初,剛好油價上漲,很多人都談論南中國海可能蘊藏大量石油和天然氣。我們又剛好收購了英國一家大型的航運公司Furness Withy。它有一家子公司叫Houlder Offshore,是英國北海最大的海上鑽探支援公司。於是我想到改建我們的船塢,配合南面的大海,來迎合未來預期的需求。我們可以把船塢改成石油供應基地,來支援海上的鑽探活動;也可以利用現時的設施,興建海上鑽井平台,出海勘探石油和天然氣。最後我們決定與中華船廠的王敏剛合作成立歐亞船廠,興建海上鑽井平台。
就像典型的家族生意環境一樣,我的建議獲接納,但同時要負責這項目。所以我除了管理自己的公司,也同時接管這個船塢。我亦因此獲委任為Furness Withy的董事會成員,並且代表他們和中海油談判,成立一家合資企業,這樣我們這家外資企業才可以在南中國海鑽探石油。那時是1983年,讓我分享一些和中國交手的有趣經驗。
和我一起談判的同事是英國人,那時中國缺乏優秀的翻譯員,大家對對方的理解只有一半,一來一回後便只剩四分一,彼此的溝通不太有效。故每天開會後,中海油的人員便來到我的房間,問我“究竟他們想要甚麼?我完全不了解這些外國人。”他們又說:“為甚麼要談這些?”商業合約細則總會列明,若出了問題,便要怎樣解決。但他們尚未熟悉這類合約,便說:“我們還未有結婚,為何就要談離婚?”
最後,我們的談判還是成功的,成立了一家50:50的合資企業,亦是全球首家海上鑽探的合資企業。中海油現已成為一家很大型的企業,去年他們還打算收購美國的石油公司Unocal。
當年和中國企業合資還有一個有趣特質。那時的合資企業的組成通常是50:50。主席一定是中國的,副主席是外國的;總經理是中國的,副總經理是外國的。到最後你會發現兩個不相關的結構,基本上是一個實體裏有兩家公司。雖然他們會坐在同一間房間,但溝通幾乎是零。那時一切還在摸索階段,大家都要透過這個過程去了解中國的合資企業是怎樣一回事。
身為合資企業的一方,我們負責培訓中海油的人員,及提升他們的鑽井技術,確保一切符合國際標準。他們派人來英國受訓,但語言始終是一大障礙。而在這個個案,雙方各自提供一個鑽井,雖然中海油也有一個符合當時標準的鑽井,叫Aker H3,但經年使用下他們作了多處改造,結果不符合國際標準,無法滿足國際油公司所需。基於時間壓力,我的英國同事大刀闊斧地修整他們的鑽井,沒有事事諮詢對方。寶貴的豬舍被移去了——他們為了吃新鮮豬肉,在鑽井上加了一所豬舍。他們修改過的起重機和各式各樣的東西,我們都要一一修正,但這並不討好中方。初時合資企業的運作良好,也就無風無浪;但遇到逆境時,他們便說我們自作主張,應該為這些單方面的決定作賠償。現在已事過境遷了。回想起來,簽這份合約實在令人興奮,合約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的,其中一位見證人是英國大使,因為Houlder Offshore是英國公司;桌上有中國旗和英國旗,我代表英方,感到很彆扭,但那是很有趣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