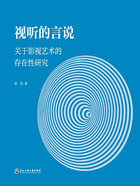
第二节 艺术的发生
艺术是如何发生的?对于这一问题,艺术发展史上有许多理论和学说。这些对艺术发生的研究,可分为两种研究的境界:第一种境界,是用史学的方法,对艺术现象发生的起源进行考证研究;第二种境界,是在人的一些活动中,寻找艺术发生的因子,以便找到艺术发生的逻辑起点。
对艺术进行史学研究,是把艺术作为一种“物”来看待,这说到底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研究。这类关于艺术起源的研究,问题在于:当我们将艺术作为对象来看待时,它其实隐含了一个先决前提,那就是——“艺术”,在它被作为对象研究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将它作为艺术来看待了。这种对艺术的史学研究,力求在时间上找到“艺术”发生的起点,这不是对艺术本体研究的根本旨趣之所在。艺术是对“道”的“生成”,是对那个“内化为人之生活关系”且“不可言说”的“道”的“生成”。因此,对艺术发生的研究,其旨趣应在于对艺术与人之生存关系的研究。
关于艺术的发生和起源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
一、模仿说
模仿说是关于艺术起源最古老的一个学说,它始于古希腊时期。模仿说认为,模仿是人类的本能。较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许多行为是对自然的模仿,他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为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身上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身上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身上学会了歌唱。” 他的思想奠定了西方艺术“模仿说”的基础。
他的思想奠定了西方艺术“模仿说”的基础。
其后,柏拉图也提出了模仿说,但他的学说是建立在理念论基础之上的。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源,艺术在本质上也是对“理念”的模仿。他在《理想国》中以“床”为例,认为世界上有三种床:“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 柏拉图所谓的“自然中本有的”指的是真理,也即“理念”。木匠所造的是“个别”的床,它是对床之“理念”的模仿;画家制造的床是对“个别”的床的模仿,所以与“理念”又隔了一层。这样一来,“现实世界”是对“理念”的模仿,是“理念”的“影子”;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因为与真理隔了两层,所以柏拉图认为艺术是比现实世界低一等的东西。
柏拉图所谓的“自然中本有的”指的是真理,也即“理念”。木匠所造的是“个别”的床,它是对床之“理念”的模仿;画家制造的床是对“个别”的床的模仿,所以与“理念”又隔了一层。这样一来,“现实世界”是对“理念”的模仿,是“理念”的“影子”;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因为与真理隔了两层,所以柏拉图认为艺术是比现实世界低一等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对模仿说进行了根本的改造,他提出了更加系统的理论。关于艺术的起源,他在《诗学》中写道(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诗”指的就是艺术):
一般说来,诗的产生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从孩提时候起,人类就具有模仿的本能。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善于模仿。我们喜欢模仿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喜欢观看对事物的最准确描述,尽管看到这些事物,比如,最低等动物的形象和尸体的状态,我们会觉得痛苦。这是因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快乐的事,不仅对哲学家,对一般人也是如此。只是对于普通人,他们的学习能力可能更有限。他们喜欢看见相似的东西,因为他们在看的同时,也在获得信息,判断所描述的事物是某一事物,比如,“这就是那个东西的画像”。如果我们以前从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所描述的事物,那么,我们的快感就不是由于对某件事物的模仿而产生,而是由于技巧、色彩或其他类似的原因而引起的结果。![[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模仿”的观点,但抛弃了理念论,他将模仿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肯定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对生活的模仿不仅真实,而且还可以高于生活真实。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模仿历史和现实,但它比历史和现实更具普遍性,他这样写道:
诗人的职责已经很清楚,他不是去描述那些发生过的事情,而是去描述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的事情。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个用散文写作,另一个用韵文写作。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在这样的修辞格式下,它也是一种历史,并不比它没有韵律的时候差。两者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叙述已经发生的事,一个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性,更值得认真关注。因为诗所描述的是普遍性的事实,而历史讲述的是个别事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它重客观现实的文论传统被后来的再现说所继承,这也成了此后现实主义信奉的基本原则。
不过模仿说和再现说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模仿说无法说清楚艺术为什么需要模仿现实生活。它将“模仿”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人的本能和天性,这是将艺术的发生导向了人的生物性。其二,再现说会导向艺术的工具论,艺术最终会被降格为再现生活的工具。而且如果把对现实再现得是否逼真,作为艺术的评判标准,那么在艺术中,艺术家的表现将不再发挥主要作用,倒是诸如照相和录像等能对现实生活进行逼真复制的活动,会被认为是最完美的艺术。
二、表现说
表现说认为,艺术是人主观情感的外化,情感表现是艺术发生的主要动因。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早期主要有雪莱、列夫·托尔斯泰等,比如雪莱认为艺术是“想象的表现”,他在《诗辩》中说:“诗可以界说为‘想象的表现’;并且自有人类以来就有诗的存在。”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艺术的起源是“情感表达”,他在《艺术论》中提出:“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艺术的起源。”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艺术的起源是“情感表达”,他在《艺术论》中提出:“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艺术的起源。”
表现说后来经过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和英国美学家科林伍德的系统阐述,形成了现代表现主义理论,同时它也为西方现代派艺术提供了理论依据。“表现”在克罗齐看来等同于直觉,直觉是克罗齐理论的核心,他认为直觉只能来自情感,基于情感。他主张造型艺术是主观精神的产物,是直觉的创造。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提出:直觉是心灵活动的起点,也是认识的最初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观点,克罗齐对美、丑分别做了界定,在他看来美是一种“成功的表现”,而丑则是一种“不成功的表现”。科林伍德继承和发展了克罗齐的理论,但科林伍德所谓的“表现”,是一种无意识主体的情感表现,他强调艺术家是观众心灵的代言人和预言家。科林伍德把主观的表现看作是造型艺术的本质,而他所谓的造型艺术就是“自我表现”。
与再现说相比,表现说重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艺术家个人的情感表达被提升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如果把艺术的表现简单归为艺术家本人的自我表现和欣赏,那么艺术与人的社会生活是脱离的。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就反对科林伍德的“自我表现”理论,她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苏珊·朗格虽然也持表现说观念,但她强调:艺术表现的是人类情感,而非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发泄。因此,她区分了“表现”和“自我表现”。此外,表现说的发展与近代心理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艺术是“潜意识里的意念”的表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主张:艺术源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用心理学的理论去解释艺术的发生,最终会导致艺术的研究变成一种科学的研究,它同样不能在根本上解释艺术的发生。
三、游戏说
“游戏说”认为,艺术与游戏一样都是非功利和纯粹审美的活动,艺术起源于人类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游戏本能。其代表人物是德国著名作家席勒和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因此在美学史上“游戏说”又被称为“席勒—斯宾塞理论”。
席勒认为人只有在精神游戏中,才能够彻底地摆脱实用和功利的束缚,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席勒理论中的“游戏”与原始艺术创造是等同的,它们的产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标志。席勒在《美育书简》第十五封信中这么写道:
在人的各种状态下,正是游戏,只有游戏,才能使人达到完美并同时发展人的双重天性,但为什么把它叫做单纯的游戏呢?按照您的概念,您把这看成是限制,但是按照我已证明的概念,我却把这看作扩展。所以我倒宁可反过来说,只有对于愉快的、良好的和完整的东西,人才是认真的。但是对于美,人却和它游戏。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想到现实生活中流行的那种游戏,它通常只是针对真正物质的对象。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这里所谈的美也是徒劳的。现实存在的美配得上现实存在的游戏冲动,但是理性提出的美的理想也给出了游戏冲动的理想:这种理想应该显现在人的一切游戏中。
……
终于可以这样说,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这一命题暂时看来似乎不合情理,当我们把这一命题用于义务和命运这两种严肃事情时,它将获得巨大而深刻的意义。我可以向您担保,它将支撑起审美艺术和更艰难的生活技艺的整个大厦。![[德]席勒:《美育书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第89-90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同时,席勒还认为,精力过剩是人们进行艺术这种精神游戏的动力,甚至连动物也只有在物质过剩、需求得到满足时才能游戏。因此,人的审美活动和游戏一样,是一种对过剩精力的使用。他在《美育书简》第二十七封信中写道:
当狮子不受饥饿所迫,无须和其它野兽搏斗时,它的剩余精力就为本身开辟了一个对象,它使雄壮的吼声响彻荒野,它的旺盛的精力就在这无目的的使用中得到了享受。昆虫享受生活的乐趣,在太阳光下飞来飞去,当然,在鸟儿的悦耳的鸣啭中我们是听不到欲望的呼声的。毫无疑义,在这种运动中是有自由的,但这不是摆脱了一般需要的自由,而只是摆脱了某种外在需求的自由。当缺乏是动物活动的推动力时,动物是在工作。当精力的充沛是它活动的推动力,盈余的生命力在刺激它活动时,动物就是在游戏。甚至在没有灵魂的自然界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力量的浪费和使命的松弛,就其物质意义来说也可以叫作游戏。![[德]席勒:《美育书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席勒对人的这种由“精力过剩”所引发的“游戏”,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区分:其一,是由物质过剩而引起的身体器官的“游戏”,但它属于未摆脱动物性的生理的快感;其二,是想象力的“游戏”,它是精神方面的过剩,是超出物质需求的。
斯宾塞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席勒的美学理论,他认为游戏和艺术都是过剩精力的发泄,是非功利的生命活动;美感起源于游戏的冲动,艺术在实质上也是一种游戏;游戏对个人和整个民族生存都具有生物学价值。
“游戏说”试图通过生物学、心理学等来揭示艺术,其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想,它同时也发现了游戏和艺术间的许多共同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艺术的某些特性。但“游戏说”把艺术活动仅仅归结为“本能冲动”,且侧重从生物学角度进行解释,这也难以从根本上揭示艺术发生的原因。
四、巫术说
在西方关于艺术起源的理论中,“巫术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巫术说”认为,原初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的活动中都包含有巫术的意义,巫术思维是艺术发生的原因。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
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以人类的智慧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样也是以人类的愚蠢为基础的一种能力。这是我们理解魔法的关键。人早在低级智力状态中就学会了在思想中把那些他发现了彼此间的实际联系的事物结合起来。但是,以后他就曲解了这种联系,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联想当然是以实际上的同样联系为前提的。以此为指导,他就力图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预言和引出事变,而这种方法,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具有纯幻想的性质。根据蒙昧人、野蛮人和文明人生活中广泛众多的事实,可以鲜明地按迹探求魔法的发展:其起因是把想象的联系跟现实的联系错误地混同起来,从它们兴起的那种低级文化到保留了它们的那种高级文化。![[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泰勒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遗留说”和“万物有灵论”。“文化遗留说”是泰勒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从现存文化现象中探寻原始文化的方法,为后来“巫术说”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思路;“万物有灵论”则奠定了研究原始文化和艺术的基础,泰勒通过世界各地详实的资料来证明这一观点。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写道:“万物有灵观构成了处在人类最低阶段的部族的特点,它从此不断地上升,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自始至终保持一种完整的连续性,进入高度的现代文化之中。……事实上,万物有灵观既构成了蒙昧人的哲学基础,同样也构成了文明民族的哲学基础。”![[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14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泰勒的著作里虽没有直接论及艺术的起源问题,但他的“万物有灵论”中,暗含了艺术起源的一些问题,这成为了后世“巫术说”研究的起点,所以他也被认为是该学说的首倡者。
泰勒的著作里虽没有直接论及艺术的起源问题,但他的“万物有灵论”中,暗含了艺术起源的一些问题,这成为了后世“巫术说”研究的起点,所以他也被认为是该学说的首倡者。
英国宗教史学家弗雷泽沿着泰勒的方向,进一步研究了人类的思维从巫术到宗教,最后发展为科学的历史进程,这为其后用“巫术说”来解释艺术的起源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代表作《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时至今日仍是研究巫术和宗教起源的权威之作。
在艺术起源问题上,李泽厚先生也赞同“巫术说”,他在《美学四讲》中写道:“中国最早的音乐、舞蹈、诗歌都是从巫术中产生出来的,它们都围绕着祭神。为什么很久很久之后乃至今天,某些少数民族的酋长、巫师口中念念有词地讲述他们部族的历史?这就是因为只有通过巫术、礼仪、神话、史诗、传奇,才能组织群体,动员群众,并把经验保持和流传下来。所以卢卡契说艺术是人类的一种记忆,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我认为是深刻的。艺术不是为审美而出现或创造的。”
“巫术说”对于理解原始艺术的发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应用这一学说也的确可以解释原始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原始艺术现象的发生,都归之于巫术活动的话,就有“泛巫术化”之嫌了。
五、劳动说
劳动说是将艺术的起源归之于生产劳动的一种学说。首先,它认为生产劳动是一切其他基本活动的前提,人只有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后,才能从事诸如艺术之类的其他的活动;其次,劳动是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此外,劳动过程中还产生了早期艺术形式,比如先民们的舞蹈是对劳动时动作的演化,他们对音乐的灵感来自劳动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
劳动说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就在一些民族学家和艺术史家中流传。俄国著名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是劳动说的有力倡导者,他说:“我坚决地相信,如果我们不把握着下面这个思想: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那儿我们将一点也不懂得原始艺术的历史。”![[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第93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普列汉诺夫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大量资料来证明原始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活动都起源于生产劳动,比如他说:“澳洲土人的划桨舞,或新西兰人表演的造船舞就是这样的舞蹈。所有这些舞蹈都是生产过程的简单描写。它们都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这是原始艺术活动和生产活动最紧密联系的明显例子。”
普列汉诺夫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大量资料来证明原始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活动都起源于生产劳动,比如他说:“澳洲土人的划桨舞,或新西兰人表演的造船舞就是这样的舞蹈。所有这些舞蹈都是生产过程的简单描写。它们都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这是原始艺术活动和生产活动最紧密联系的明显例子。” 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中主要批驳了斯宾塞“艺术起源于游戏”的思想,同时也阐明了自己“劳动先于艺术”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中主要批驳了斯宾塞“艺术起源于游戏”的思想,同时也阐明了自己“劳动先于艺术”的观点。
劳动说一方面以马克思的劳动观为基础,同时也结合了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方面的文献,以此来证明,史前艺术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可以在劳动生产活动中寻找到印记。但是,这一学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将马克思的“劳动”理解成了“具体的劳动”,所以它最终仍是从认识论出发去理解艺术,因此终究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艺术的发生问题。
六、对艺术发生的理解
以上五种关于艺术发生问题的学说,我们根据它们的研究方法和解答问题的走向,大致可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表现说和游戏说,它们主要强调人的心理和本能与艺术发生的联系,这类理论最终走向了生物学或心理学;第二类,模仿说、巫术说和劳动说,它们主要强调人生活的外部环境对艺术发生的影响,这类理论最终走向了民俗学或人类学。这些理论从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或反映了艺术的部分特性,或与艺术的发生存在某些关联,从某种角度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他们最终将艺术的发生归结为某一种现象,这仍是认识论层面上的理解,因而还不能从根本上回答艺术发生的本原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是真理的原始发生,这是从生存论层面对艺术进行理解,由此我们认为:其一,艺术与人类社会的开端是同步的;其二,艺术在原始的生存活动中,呈现出的形式是多元的;其三,劳动中包含着艺术的本源。
(一)人类社会的开端与艺术之发生是同步的
人的精神存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精神的存在,意味着人可以直观自身,这种直观是人对“道”(真理)的领会,也即人对自身生存之领会。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是真理的原始发生,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写道:
艺术让真理脱颖而出。作为创建者的保存,艺术是使存在者之真理在作品中一跃而出的源泉。使某物凭一跃而源出,在出自本质渊源的创建者的跳跃中把某物带入存在之中,这就是本源(Ursprung)一词的意思。
艺术作品的本源,同时也就是创建者和保存者的本源,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的本源,乃是艺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艺术在其本质中就是一个本源,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亦即真理历史性地生成的突出方式。![[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57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与真理的发生是统一的。艺术直接参与了人类感性生活的建构;而真理(道)是人对自身命运的领会,它被置于人的感性生活之中。正是艺术使这种领会得以成为可能,而此时的艺术就具有了本体论上的意义,因此,它的发生与人类社会的开端是同步的。
(二)艺术在原初人类的生存活动中呈现出多元的形式
艺术在人的原始生存活动中就已经真实地发生了,人们用它来保存生存情感,只是此时的艺术还未成为一种自觉的创作,也未定型为一种固定的程式,这种艺术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元艺术”。在原始生存活动的许多领域,如原始的巫术、游戏、历史神话以及日常器物的制作中都有“元艺术”发生。这些活动之所以可以被称为“元艺术”,是因为在这些活动中,人或多或少都不自觉地应用了这些形象的方式对生存的情感进行了保存。
西方艺术理论中,将巫术作为艺术起源的学说是有一定道理的。早期人类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对自然充满恐惧,因此人类想象出各种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神灵,并进行顶礼膜拜。巫术作为人与神灵沟通的方式,是原初人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活动,他们想借助巫术来寻求与自然,与动物,与他人,与死者之间的联系,最终期望达到控制自然及万物的结果。以汉字中的“巫”字为例,《说文解字》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褎舞形。与工同意。” 在中国古代,巫,为事鬼神者;祝,为以言语向鬼神祈福者;巫祝后来经常连用,用以指掌控占卜祭祀之人,他们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介,也是人类早期的知识分子。巫师与上天沟通的方式是舞蹈形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
在中国古代,巫,为事鬼神者;祝,为以言语向鬼神祈福者;巫祝后来经常连用,用以指掌控占卜祭祀之人,他们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介,也是人类早期的知识分子。巫师与上天沟通的方式是舞蹈形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 除了歌舞,还有天文、地理、历法、医药,追根溯源无不与巫术活动有关。比如最早“医”字的繁体“毉”,就从“巫”字诞生而出,这说明了早期医术与巫术之间关系密切。在原始社会生活中,巫术是和劳动同等重要的活动,在史前时代,原初人类的认知及知识,总是和巫术观念交织在一起,所以原初人类生活中的许多内容都或多或少有巫术的因子。从这种意义上说,巫术说主张原初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的活动都包含有巫术是有一定道理的。艺术在原初人类的生存活动中呈现出多元的形式,巫术、劳动、游戏等活动中都存在着艺术的因子。但是,巫术说将艺术的发生仅归结为人类现象世界中的一种活动,这就忽视了不同人群生存方式的多元性。
除了歌舞,还有天文、地理、历法、医药,追根溯源无不与巫术活动有关。比如最早“医”字的繁体“毉”,就从“巫”字诞生而出,这说明了早期医术与巫术之间关系密切。在原始社会生活中,巫术是和劳动同等重要的活动,在史前时代,原初人类的认知及知识,总是和巫术观念交织在一起,所以原初人类生活中的许多内容都或多或少有巫术的因子。从这种意义上说,巫术说主张原初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的活动都包含有巫术是有一定道理的。艺术在原初人类的生存活动中呈现出多元的形式,巫术、劳动、游戏等活动中都存在着艺术的因子。但是,巫术说将艺术的发生仅归结为人类现象世界中的一种活动,这就忽视了不同人群生存方式的多元性。
(三)艺术的存在问题是一个超验性问题
何谓超验性问题?要回答它,我们首先要理解先验、经验与超验这几个概念,它们同时也是我们理解康德先验哲学的基础。
经验,是以人的感性为基础的,它为人的判断提供材料和内容。康德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但“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他进一步提出:“是否真有这样一种独立于经验、甚至独立于一切感官印象的知识。人们把这样一种知识称之为先天的(a priore),并将它们与那些具有后天的(a posteriori)来源、即在经验(erfahrung)中有其来源的经验性的(empirische)知识区别开来。”![[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康德在此区分了两种知识,一种是经验的知识,另一种是先天的知识。先天的知识(即先验的知识)与从经验中得来的后天的知识相对立,它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是构成经验知识不可或缺的东西。在经验之先,人已经有了逻辑的形式。所以,人在进行判断时,其实已经具备了某种先天的形式,如概念、范畴等。因此,概念之来源,并非人从知觉表象中抽取其共性所得,而是人给了知觉一个普遍的规定,使之上升为了判断。人的这种先验能力,被康德称之为“纯粹理性”,它是经验世界的逻辑前提,人让对象进入自己的先验逻辑,由此具备了“为自然立法”的能力。“纯粹理性”参与构成经验世界,但它不能自行构成经验世界的真理,康德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因此,使思维的概念成为感性的(即把直观中的对象加给概念),以及使对象的直观适于理解(即把它们置于概念之下),这两者同样都是必要的。这两种能力或本领也不能互换其功能。知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思维。只有从它们的互相结合中才能产生出知识来。”![[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知识都是由先天成分和后天经验成分混合而成的,它是理智概念和感性直观的结合。“物自体”(thing-in-itself)对人的感官刺激使人产生感觉,同时人将知性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感性材料并进行判断,而形成知识。所以,我们所谓的知识,其认识的客体不是“物质实在”,而是“经验实在”。经验的知识里有先天的成分,它是知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保证,这为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科学知识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在经验领域里康德是一个可知论者。
知识都是由先天成分和后天经验成分混合而成的,它是理智概念和感性直观的结合。“物自体”(thing-in-itself)对人的感官刺激使人产生感觉,同时人将知性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感性材料并进行判断,而形成知识。所以,我们所谓的知识,其认识的客体不是“物质实在”,而是“经验实在”。经验的知识里有先天的成分,它是知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保证,这为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科学知识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在经验领域里康德是一个可知论者。
通过对康德先验哲学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经验问题”是科学领域中的问题,它存在于现象世界之中,用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说,它们都属于形而下者。而“超验问题”是与“经验问题”完全不同类型的问题,它们都超出经验界限之外,类似“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等问题,都属于形而上者,是本体世界中的问题。所以,对这类问题,我们不能指望通过科学的方法去寻求答案。
关于艺术,我们往往将它看成是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等各种艺术形式的集合,艺术的概念似乎只是各种艺术形式的统称。我们如此看待艺术,那么艺术的存在就还是经验世界中的事物,而且它的存在完全是依赖于艺术形式或作品的。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一开始就打破了人们固有的思维,他认为作品之所以为艺术作品,其存在的前提应该是艺术。他写道:
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彼此不可或缺。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全部包含了另一方。无论就它们本身还是就两者的关系来说,艺术家与作品向来都是通过一个第三者而存在的;这个第三者乃是第一位的,它使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获得各自的名称。这个第三者就是艺术。
……
人们认为,艺术是什么,可以从我们对现有的艺术作品的比较考察中获知。而如果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艺术是什么,我们又如何确认我们的这种考察是以艺术作品为基础的?但是,与通过对现有艺术作品的特性的收集一样,我们从更高级的概念做推演,也是同样得不到艺术的本质的;因为这种推演事先也已经看到了那样一些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必然足以把我们事先就认为是艺术作品的东西呈现给我们。可见,从现有作品中收集特性和从基本原理中进行推演,在此同样都是不可能的;若在哪里这样做了,也是一种自欺欺人。![[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2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的存在问题与真理的生成和发生相关,他认为:“艺术的本质先行就被规定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艺术就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因此,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51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因此,艺术的存在问题其实是一个超验性问题,而艺术史上传统的那些关于艺术发生的学说,其理论研究方法都是科学式的,譬如游戏说侧重于生物学,巫术说侧重于人类学,表现说侧重于社会心理学。这些研究都很有意义,也都有其合理性。但它们从现象出发,通过某一学科进行论证,这就把对“艺术本源”的研究从哲学问题变成了科学问题,因此,它们并不能真正解决艺术的原始发生问题。艺术的原始发生问题,作为一个超验性问题,它不在我们的经验中发生,也不是我们认知的对象。我们对艺术发生的理解,不能在现象界中而是要在本体界中去寻求它发生的“元因”,也就是去寻找“元艺术”,只有这样,艺术的发生问题才真正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
(四)劳动中包含着艺术发生的本源
我们都知道“劳动创造了人”,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劳动创造人”的含义并非是说“劳动创造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从生物学上看,人无非是动物界中,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中的一个物种而已。我们将自己标榜为高级灵长类动物,这个所谓的“高级”如果仅从生物学上进行考量,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自然界中,人并没有生存的优势。我们不能像鸟一样飞翔,也不能像鱼一样游弋;在陆地上,我们的野外生存能力远不及其他动物,论奔跑人不如猎豹,论体力人不如大象,论敏捷人不如猴子;况且人还怕冷,没有天然抵御寒冷的身体条件。所有这一切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视之,人之物种是应当被自然淘汰的。然而,就是这个在自然环境的生存上没有多少天然优势的物种,居然被冠为“万物之灵”,其原因何在?
有研究者将人之“高级”的原因归结为人的大脑的发达,对于这一观点,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何我们与动物用以比较高低的器官是“大脑”,而不是其他?或许有人会说:大脑是所有器官中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进一步提出质疑:心脏对于动物也很重要,为什么不以此作为界定的标准呢?因此,我们制定的这种界定高低优劣的标准,显然是带有人为的选择性的。实际上,人无非是在众多的条件中,选择了一个最利于自己的条件作为“游戏规则”。因而,“人为万物之灵”的判断,它并不是经过比较和归纳所得出的结果,它实质上只是人的一个信念而已。人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根据这一信念去寻找相应的佐证,最后将此信念转化成了规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生物机能上优劣的比较,并不能把人与动物进行本质的区分,因为它们都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比较。所以,当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时,其含义绝非指人的某些生物性高于其他动物;人之高贵在于人的存在是“超越生物性”的。这也就是说,人的存在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因此,劳动创造的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具有“精神”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说,这种具有“精神”的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作为精神的存在者,人是“自为”存在的,人的各种关系都是人自身所建构的,也就是说它们都“为人”而存在。正是由于劳动,使人在改造自然时具有了“自为”意识,同时也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劳动是人的生存方式,是社会生活的根源。人通过劳动不仅获得了物质资料,同时还产生了社会关系,所以劳动是“实践”的,即它是创生或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我们说“劳动创造人”,并不是说劳动可以改变人的某种生物性能,而是说人通过劳动,使自身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存在者。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创造的不是具有生物性的人,而是具有社会性的人,即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作为社会的人,其生命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最重要的是,他是具有文化生命的。文化生命是会运用思想的生命,这是人与动物最为本质的区别。
劳动是人的生存方式,是社会生活的根源。人通过劳动不仅获得了物质资料,同时还产生了社会关系,所以劳动是“实践”的,即它是创生或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我们说“劳动创造人”,并不是说劳动可以改变人的某种生物性能,而是说人通过劳动,使自身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存在者。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创造的不是具有生物性的人,而是具有社会性的人,即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作为社会的人,其生命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最重要的是,他是具有文化生命的。文化生命是会运用思想的生命,这是人与动物最为本质的区别。
除此之外,我们通常也将“制造和使用工具”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条件,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这其中包含着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有目的”是人“自为”存在的表现。动物在生存的过程中,也会借助外物,但它借助外物的活动是出自本能的,而不是“有目的”的活动,这与人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动物也有意识,但它的意识只是自然意识。自然意识下,动物是受制于物的,比如人和动物一样,饿了都需要补充食物,这是自然法则的规定。动物饥饿时无法拒绝食物,此时它受制于食物;而人饥饿时完全可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或者“不受嗟来之食”,此时人不受食物的控制,因此他是自由的。所以,动物只是自然的存在者,而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者,同时还是精神的存在者。
第二,“有目的”意味着人制造和使用的工具不仅是物质的存在,同时还是观念的存在。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精辟的论述: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878597-kQZ2NkvRJY5hV01FH5WUZqTcz84yxTGG-0-87fc96f6de33d0136910e592375846f6)
我们知道,动物有时也会借助外物去完成一些事情,但它们的这种活动,并不是使用工具的行为。外物之于动物不是观念的存在,而只是感性外观的存在。外物之所以可以成为人的工具,是人已经先行规定了物的本质,这种规定是观念上的规定,因此工具之于人是“本质先于存在”的(“物”的存在方式与“人”的存在方式不同,萨特认为“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工具的“本质”存在于人的观念之中,柏拉图认为,它存在于“理念”之中,比如椅子是我们用来“坐”的工具,它是木头的还是石头的,是圆的还是方的,并无绝对标准的形式。我们在现象世界中找不出一把完美的、可以永久作为标准的椅子,现象世界中的椅子都是具体的、特殊的,它们都是对人“理念”中的椅子的不完全“模仿”。椅子是人用来“坐”的工具,它的本质是被人所规定的,当我们把一块石头或一个木箱也用来“坐”时,此时石头或木箱不也是“椅子”?虽然这些东西日常的名称并不叫“椅子”,但在人的观念中已经把它们规定为“椅子”了,而且它们也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人“坐”的工具了。现象世界中的工具都会磨损乃至消亡,但是作为观念中的工具,它们是精神的存在物,因此是不朽的。工具消亡了,人可以根据观念中的工具重新制造,不受当下的情境限制,因为人具有“无限性”;而动物不是精神的存在者,其意识是自然的意识,其活动也只是本能的活动,它完全受制于情境。外物对于动物来说,如果在其视野之外,也就在其心智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