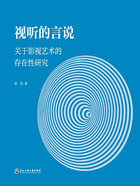
第一节 艺术与道
说到艺术与道的关系,我们自然会想到“文以载道”的说法,这一观点的源头是儒家“诗言志”的思想,《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到了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古文运动倡导者,为了反对六朝绮靡之风,曾把“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作为其理论纲领。“文以载道”在宋代被明确提出,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在《周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意思是说“文”是“道”的载体,就好像车是人的载体一样。如果车不载人,装饰得再好也没有用。周敦颐在文中接着说:“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所以文学在儒家看来是传播儒学之“道”的工具和手段。这种艺术“工具论”的观点对中国人的影响极其深远,我们强调艺术作品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和主题,就是“文以载道”思想的延续,只是不同时期对“道”的理解各有不同罢了。
一、器:对“现象”的认识
当我们把“文以载道”的“道”看作是某一种学说,或者某一种道理,抑或是某一种思想时,其实就已经落入“道可道,非常道”的窠臼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要了解“道”,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与之相对应的“器”。何谓“器”?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器”是“现象世界”中的存在物,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可以统归之为——“器”。“器”是社会存在物,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有形的“器”,如生活日用之物,无形的“器”,如各类典章制度。凡“器”者,皆可作为对象被经验所把握,它在我们思维规定的范畴之中,因此凡谓“器”者,皆为事实性存在之物。
自然界中的自然之物,如果它们可以被我们认识和把握,也属于“器”。马克思说:“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才对别人说来是他的存在和对他说来是别人的存在,才是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764750-iA6rKl3s9DYP0PBWKWsioxtH4xdaMqHI-0-347c2e4fa305aad33a4dbc8a11d9522c) “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也是无。”
“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也是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1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764750-iA6rKl3s9DYP0PBWKWsioxtH4xdaMqHI-0-347c2e4fa305aad33a4dbc8a11d9522c) 这一说法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比如一块天然的石头,它非制造产生,可能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石头就已经“自在”地存在了,它和我们的文明成果有何关联?“石头”在未进入人的生活之前,用康德的话说,它属于“物自体”或“自在之物”。“物自体”虽是现象的基础,却在人类的认识之外,是绝对不可认识的存在之物。当然此时并无“石头”这个名称,因为它只是“物自体”的“石头”。所以对人类的文明来说,给事物“命名”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一举动。当人给一个事物冠之以名时,它实际上表明了人与这一事物之间建立了原初的关联。事物不再是“自在”地存在了,它被卷入了人的生存之中。之后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看它,比如可以用物理的方式去“看”它(如石头的重量、体积、硬度等),也可以用化学的方式去“看”它(如石头的分子结构等),总之它是属人的“石头”。所以,一切所谓“物质的”存在物,其实都是社会的存在物。
这一说法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比如一块天然的石头,它非制造产生,可能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石头就已经“自在”地存在了,它和我们的文明成果有何关联?“石头”在未进入人的生活之前,用康德的话说,它属于“物自体”或“自在之物”。“物自体”虽是现象的基础,却在人类的认识之外,是绝对不可认识的存在之物。当然此时并无“石头”这个名称,因为它只是“物自体”的“石头”。所以对人类的文明来说,给事物“命名”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一举动。当人给一个事物冠之以名时,它实际上表明了人与这一事物之间建立了原初的关联。事物不再是“自在”地存在了,它被卷入了人的生存之中。之后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看它,比如可以用物理的方式去“看”它(如石头的重量、体积、硬度等),也可以用化学的方式去“看”它(如石头的分子结构等),总之它是属人的“石头”。所以,一切所谓“物质的”存在物,其实都是社会的存在物。
因此,对康德“物由心造”的理解,我们不能从字面上去臆想。“物由心造”的意思是说,作为我们认识客体的物之观念是由“心”所规定的,而不是说作为物质实体的“物”是由“心”制造出来的。在“心”所规定的范畴之中的“物”,都是我们认识和可知的对象。在中国哲学史上,王阳明“心学”的观点与之有些相似,在王阳明的《传习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段文字现在常常会被人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如果我们这么去理解王阳明的思想,未免过于简单,同时也容易对其思想产生一些误解。
误解之一来自对两种“花”的理解。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之花”属于“未名之花”,它还未进入人的生活世界,不在人的认识范畴,是“花”的“物自体”状态;而被人“看到的花”属于“名之花”,它与人的生存产生了关联,因而是人认识范畴之内的东西。因此按照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这两种“花”之所指是不同的,但是问题在于“未名之花”一旦被人用语言说出来,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正所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我们中国哲学在语言表达上的特点,它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充满逻辑和推论,并拥有一套精确的哲学术语。中国哲学的语言充满感性和文学色彩,哲学论著所用词汇也都是日用之词,所以像王阳明友人所问的“深山中之花”,它本是“未名之花”,但他一用语言表达出来,花就成为了“名之花”。这与王阳明所说的“看此花时”的“花”,在语言层面上的概念是相同的,这是误解的根源所在。如果我们试着用西方哲学语言来表述,那么王阳明这位友人所说的“自开自落之花”指的是“物自体的花”,而王阳明“看此花时”则是“思维对象的花”,经过这样转换,我们或许可以消除在字面理解上的一些误会。
误解之二来自对文中“看”的理解。“看”其实是人对思维和观念的“看”,康德说,“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这两者只有相互结合,才能产生知识。如果没有“纯粹理性”作为经验世界的逻辑前提,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混沌,是浩转流变。我们“看”的是由我们的“心”所造的“物之观念”,思维与存在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才具有同一性,因为它们两者在本质上是同构的。人的思维与外部实在的逻辑同构,其实我们是无法进行证实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人的一个信念而已。至于物之本体(物自体)虽是“物之观念”的基础,但它并不为人所认知,我们能“看”到的都是我们能思及到的东西。“花之实体”,即“花”的“物自体”状态,它是“花”存在的物质前提;而“花之观念”则是“花”存在的逻辑前提。所以王阳明所“看”到的“花”,虽然以“花之实体”为基础,但它却是要以“花之观念”为认识前提的。
二、道:对“生存”的领会
我们对“器”进行讨论,目的就是要说明“器”是人可以认知的对象。“器”的存在并非实体,凡是那些可以被人规定,可以作为概念,可以进行定义的东西,皆可归之于“器”。
与“器”相对的是“道”,“道”不仅无形,而且还不可作为经验和知识的对象。“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可言说的,一旦言说出来的“道”就一定不是“道”本身了。所以当有人将“道”解释成某一种观点、学说或理论时,这个所谓的“道”其实并不是“道”,而是一种“器”,无非它是一种“无形”的“器”而已。
既然“道”不可知,也“不可道”,那么“道”与人何关?“道”虽“不可道”,也不可作为知识的对象,但它却可以被我们体验和感悟。悟“道”是人对自身存在的终极领会。艺术、宗教、哲学都是悟“道”之路径,都是人对生存之“思”。这种“思”被黑格尔概括为“感性直观的思”(艺术)、“纯粹的思”(哲学)和“超验表象的思”(宗教)。在黑格尔看来,这是艺术、哲学、宗教共同构筑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们都使人的精神达到了自觉。黑格尔这里所说的精神自觉的境界,我们可以理解为“道”的境界。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这里的“精神”乃是“绝对精神”,它是作为宇宙万物共同本质和基础的精神实体。虽然这种“精神的种子”在历史的发展中展开,但它说到底还是一种理性,黑格尔最终也没有走出柏拉图理念论的局限,只是相比而言,他的理论表现出了更强的严密性和辩证性。
“器”由“道”生,因此所有的“器”在制作中,无不体现出对“道”的领会。在我们生存的社会中,“道”是无处不在的。《庄子》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或许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道”。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可见“道”并不远离我们的生活,宋代思想家邵雍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意思是说,“道”并不远离人的日常事物,它在天地尚未开辟之前就存在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对“先天”应该理解为以下两点。其一,“道”先于“天地开辟”,应该是指它在逻辑上,而不是在时间上早于“天地开辟”。因此,“道”是“天地开辟”的前提。其二,“天地开辟”不是在“自在的自然”中发生的,而是在“人化的自然”中发生的,因为对人来说,只有“人化的自然”才是具有意义的。因此,所谓“天地开辟”指的是人成为“精神”存在者之时。此时的人具有了“主体性”,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道”不是某一理念,也不是理性的存在,它是“理性前”的。也就是说,它是理念存在的前提和基础。“道”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存在的领会,这种对存在的领会是感性的,它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为“这一个”民族的根基。对“道”的领悟,不是指对具体的某一理论或学说的理解,它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实践,是一个民族的人民对自身生存的一种领会。因此,每一个民族对“道”的领会都是独特的,它们对“道”的阐释方式也是独特的。对“道”的领会不同,所产生的文化也就不尽相同。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也就意味着不同民族之间“道”的沟通和对话。这种交流有失败,也有成功。失败了,意味着我们没能领会另一民族的“道”,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成功了,意味着我们对另一民族的“道”有了一份领会,同时我们对其他文化也会获得一份认同。这种交流和沟通有时会对一个民族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
譬如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不同民族之间“道”的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因其思想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思想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刚开始在中国的发展非常缓慢。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经翻译者将老庄思想和佛家思想进行融合,如僧肇的般若理论,以“般若”代“道”,以“色空”代“有无”,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东晋南北朝时,因长期战乱,民不聊生,人们为了摆脱现实生活的痛苦,将生活的希望寄之于宗教。因此佛教思想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诸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思想,被人们广泛接受。由此,佛教也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人们相信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现实的生活是每个人前生所做所为的结果,生处乱世中的人们从这种信仰中得到了心灵的宽慰和解脱。到了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六祖慧能法师融儒道释三家之思想,创立了禅宗,提出了“顿悟成佛”的思想。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它的教义与最早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已经大不相同了,成了我国本土重要的宗教之一。至此,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中形成了儒道释三家并存的局面。此外,儒道释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比如宋明理学,就是在继承孔孟正统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心性学说,由此开辟了新儒学之路,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的发展又推向了一个高峰。
对“道”的领会是一个民族对当下“存在”或“生存”的领会,这里的“生存”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存活”于自然界中,而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31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764750-iA6rKl3s9DYP0PBWKWsioxtH4xdaMqHI-0-347c2e4fa305aad33a4dbc8a11d9522c)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生活”是“理性前”的,指的就是人的“生存世界”,而作为理性的意识则是对这种“生存”观念的表达。人的“生存”意味着人与周围事物打交道,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建立,而“道”正是由这种社会关系内化而成的。人与其周围的事物建立的社会关系是“感性的社会存在”,也就是“非观念性的社会存在”(有别于理论存在、科学存在等“观念性的社会存在”),它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向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生活”是“理性前”的,指的就是人的“生存世界”,而作为理性的意识则是对这种“生存”观念的表达。人的“生存”意味着人与周围事物打交道,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建立,而“道”正是由这种社会关系内化而成的。人与其周围的事物建立的社会关系是“感性的社会存在”,也就是“非观念性的社会存在”(有别于理论存在、科学存在等“观念性的社会存在”),它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向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实践”指的是创生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活动,“实践”也就意味着行“道”,它是人类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实践”指的是创生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活动,“实践”也就意味着行“道”,它是人类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社会生活”是“实践”的,也就是说“社会生活”是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人对“道”的领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不同时期人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会发生变化,所以人对“道”的领悟也会随之改变。譬如一种学说被广泛接受,我们往往会把原因归结为它表达的思想内容本身的优越性,但其实这个接受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人对“道”的领会。历史上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些学说刚出现时无人问津,若干年后才被人广泛接受。学说的内容未变,变化的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道”的展开也与之类似,它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从无数的学说中召唤出能够显现自己的那一种,然而在历史时机尚未成熟之时,那些学说并不受世人的关注。它如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理性”一样,会从茫茫的人海中,遴选出像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并将他推向历史的舞台。
“道”的展开也与之类似,它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从无数的学说中召唤出能够显现自己的那一种,然而在历史时机尚未成熟之时,那些学说并不受世人的关注。它如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理性”一样,会从茫茫的人海中,遴选出像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并将他推向历史的舞台。
“论道”,即对“道”的言说,它是使“道”由隐及显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民众对自我的“生存”有了一份领会和觉悟,我们从中国传统的一些文献典籍中,可以看出古人对“道”的领会,以及对“论道”的理解。譬如禅宗里有“指月”的公案,“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楞严经》卷二)。六祖慧能云:“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因为,“道”有如空中之“月”,文字有如“指月”之“指”。寻“道”如果执着于“指月”之“指”,就会错失“指外之月”。类似的譬喻,道家理论中亦有,《庄子·外物》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这里以“筌”和“蹄”喻“工具”,以“鱼”和“兔”喻“道”。得“意”(道)之后,作为“工具”的“言”(器)可以被忘记,因为对“道”的终极领会才是更加本质的事情。
这里以“筌”和“蹄”喻“工具”,以“鱼”和“兔”喻“道”。得“意”(道)之后,作为“工具”的“言”(器)可以被忘记,因为对“道”的终极领会才是更加本质的事情。
“论道”的思想被民众广泛接受后,就会形成相应的学说理论,由此还会制作和固化出一系列的“器”,如典章制度、知识体系等等这些“器”既可能体现“道”,也可能蒙蔽“道”,因为由“社会生活”内化而成的“道”是“实践”的,而“器”是固化的。当“道器对应”时,“器”能显“道”;当“道器分离”时,“器”不能显“道”,甚至可能会蒙蔽“道”,这时候我们就要打破“旧器”,制作能够体现“道”的“新器”了。
三、艺术:对“道”的生成
我们之前对“道”的阐释是中国式的,如果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对“道”进行阐释,那么这个词应该是“真理”。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中华民族寻“道”的历史,而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寻求“真理”的历史,用词不同,但意思相同。“道(真理)”是存在者对“存在”的领会,它来自于原初的艺术,海德格尔称之为“诗意创造”,他说:
作为存在者之澄明和遮蔽,真理乃是通过诗意创造而发生的。凡艺术都是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到达而发生;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都以艺术为基础;艺术之本质乃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由于艺术的诗意创造本质,艺术就在存在者中间打开了一方敞开之地,在此敞开之地的敞开性中,一切存在遂有了迥然不同之仪态。![[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51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673311/18824211001375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6764750-iA6rKl3s9DYP0PBWKWsioxtH4xdaMqHI-0-347c2e4fa305aad33a4dbc8a11d9522c)
在这里,海德格尔将这种原初艺术的发生称之为“诗意创造”。“诗意创造”意味着这种创造不仅是“形象的”,而且还是“情感的”。因为单纯的“形象创造”并不一定能够产生艺术,比如几何学里,那些线条优美、比例和谐的图形,我们不能称之为艺术。艺术是创造,这种创造既是“形象的”,也是“情感的”。它将人带入的是“存在”真理,这是人生存情感世界。艺术为人们敞开的这个真理世界,不是让我们通过理智去认识,而是让我们在情感上去体验。艺术是情感的产物,法国雕塑家罗丹认为,“艺术即感情”。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则把艺术看成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一代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对“什么是艺术”展开了讨论,其中在论及艺术与情感的关系时,他对感情之于艺术的重要性做了充分的阐述。托尔斯泰写道:
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以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辞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的活动。
然而,对情感的理解,我们容易仅从心理角度出发,将其归结为一种心理要素。人之喜怒哀乐无非是不同的心理形式。因此艺术往往会被理解为一种强烈的个人情绪,或者是自身情感的发泄。在西方有“愤怒出诗人”之说,在我国也有“不平则鸣”之说,这些个人的情感或情绪的表现,长期以来往往被我们认为是艺术发生的源泉。艺术的确保存和表现人之情感,但此所谓的情感并非“对象性情感”,而是人之原初的情感,它是指人之生存情感。生存情感是“超越性情感”,这与我们的日常情感,即“对象性情感”相去甚远。“对象性情感”是喜怒哀乐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它始终还是心理层面的;“超越性情感”是人之生存情感,是超越实际生活的,它是人对“道”的体验和领会,也即对超越性存在的体验和领会,人在此情感中观照自我,直接指认人之存在。艺术显现的情感正是人之生存情感,它通过形象的建构让这种情感得以保存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