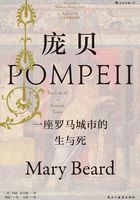
罗马世界里的庞贝
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是,在罗马世界里,庞贝是个无足轻重的闭塞之地。唯一可炫耀的只有它出产的鱼露。老普林尼曾不经意地夸赞过这一点(“……庞贝也因其鱼露而远近闻名”),庞贝生产的这种美味显然热销于整个坎帕尼亚地区,因为我们常常能挖出专门盛装鱼露的陶瓶。甚至在高卢地区也出现过。不过,仅仅发现一个庞贝陶瓶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一个繁荣的国际出口市场,它也可能只是某个庞贝人在旅行时携带食材的容器,甚至可能是一份礼物。庞贝的葡萄酒的名声仅次于鱼露,但显然质量参差不齐。有些牌子的酒很好,但普林尼警告过我们,当地的劣质酒很可能会让你一直宿醉到第二天中午。
人们通常认为,当罗马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庞贝人往往不受任何打扰,安然度日。首先是在那个自由而半民主的罗马共和国垮台后,独裁统治建立、内战不断,直到奥古斯都(公元前31—公元14年在位)成立罗马帝国、建立独裁统治;此后是在皇帝接连继位的时期,其中有的像奥古斯都本人或维斯帕先(公元69年在另一场内战后继位)一样,以正直和仁慈的专制著称,其他也有像卡里古拉(公元37—41年在位)和尼禄(公元54—68年在位)这样饱受诟病的疯狂暴君。大多数时候,这些风暴中心都与庞贝城相距甚远,尽管有时候也会因为靠得有些过近而受到牵连。例如,公元前1世纪70年代末,就在殖民地建立后不久,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军暂时驻扎在维苏威火山口附近,就在城北几公里远处。人们曾在庞贝一座房屋里发现过一幅粗糙的画作,它被后世的层层装饰遮住了。在其描绘的战斗场景中,有个骑在马背上的男子被标注为“斯巴达克斯”(Spartaks,奥斯坎语),于是这个事件可能就这样被永久铭记。这个想法不错,但这幅画更有可能描绘的是一场角斗士间的决斗。
同样,在极少数情况下,庞贝也会对首都和罗马文学产生影响,无论是因为某场天灾,还是公元59年的事故所导致的。那一年,一些角斗表演突然失控,紧接着,当地居民和来自附近努科利亚的“外援”血腥地厮杀了起来,直到伤员和死难者家属上诉到皇帝尼禄本人那里,才让事情告一段落。但总体而言,庞贝城的日子还是一如既往的慵懒,没有在罗马的生活和文学中留下太多痕迹——或者反过来说,庞贝城没有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和首都精英阶层间钩心斗角的太多影响。
事实上,西塞罗甚至可以嘲笑庞贝的政治生活的懒散。有一次,他谴责尤里乌斯·恺撒可以任意指派心腹进入元老院,而不经过一般的选举程序。其中一句妙语让人联想到现代人对唐桥井(Tunbridge Wells)或者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South Bend, Indiana)②的讽刺:据说他说的是要想进入罗马的元老院十分容易,“但在庞贝却很难”。热切的庞贝政治研究者常常抓住这一点,争辩说这里的政治生活实际上充满了竞争,甚至比罗马城本身的竞争还要激烈。但其实他们误解了这个辛辣的嘲讽。西塞罗的意思大概是,“要进入上议院比成为唐桥井市长还容易”——换言之,这比你所能想到的最容易之事还要轻松。
对于庞贝城的无足轻重,考古学家持两种不同的态度。作为罗马世界里唯一在细节层次上都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城市,庞贝却如此远离罗马的主流生活、历史和政治,这让大部分历史学家或公开或私下感到遗憾。相比之下,也有人为这座城市的平凡感到庆幸,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有幸得以了解古代世界居民的生活,而他们通常被历史忽视。这里没有好莱坞式的魅力来迷惑我们的眼睛。
但庞贝绝非像人们通常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块被遗忘的与世隔绝之地。没错,这里不是罗马;而且按照西塞罗的说法,这里的政治生活(详见第6章)也不像首都那样残酷。在很多方面,它都只是个非常普通的地方。但是,在罗马统治下的意大利,这些普通的地方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往往和罗马本身密切相关。通过赞助、支援和保护的纽带,它们经常与罗马精英中的高层人士有所往来。例如,我们从奥古斯都最赏识的侄子、有望成为继承人的马克鲁斯(Marcellus)的雕像上的铭文得知,他曾一度担任庞贝“恩主”这个半官方职位。这类地方的历史就这样与罗马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它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让首都的政治戏剧再度上演的舞台。它们的成功、问题和危机足以产生远远超越地域性的影响,甚至直达首都。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罗马治下的意大利正是一个“连动的”共同体。
庞贝在罗马城以南,仅有240公里远,其间路况良好。只要信使有足够多的坐骑换乘,紧急通知一天之内就可以从首都传达至庞贝。普通的旅行或许会花上3天,再磨蹭点儿就得要一周。不过,除了在古代的条件下从首都易于到达这一点,罗马精英及其随从们还有来庞贝旅行的好理由。那不勒斯湾那时是个广受欢迎的度假休闲胜地(至今部分地区仍是),常常被视为葱郁乡间的舒适“第二故乡”,最可贵的是还能眺望海景。公元前1世纪时,与庞贝城隔湾相望的巴亚(Baiae)城就已经是高级的享乐胜地的代名词,差不多类似于古代版的圣特洛佩(St Tropez)③。前文提到过,同盟战争时期,年轻的西塞罗在围攻庞贝的军队中还只是个新兵。25年后,他却在“庞贝地区”置了一所乡村住宅,尽管这有些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他把它当作远离罗马的藏身之处;公元前49年,内战即将打响,当他在为选择尤里乌斯·恺撒还是“伟大的”庞培而犹豫不决时,他住在这里是为了方便他随时从海路逃离。18世纪的学者确信他们找到了这座建筑,就在赫库兰尼姆门外的一大片地产中(自那以后又被掩埋起来,见彩图1)。但遗憾的是,他们只是稍微分析了一下西塞罗所有关于 “庞贝住宅”的描述,并结合了大量一厢情愿的设想,几乎可以确定,鉴定结果是错的。
20世纪也有这样一批学者体会到了同样的兴奋,他们在这座城市周边发现了另外一名显贵的住宅:这次是尼禄的第二任夫人波派娅(Poppaea)的;为了这位名媛,皇帝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和第一任夫人奥克塔维娅(Octavia),而波派娅自己也最终死在了丈夫手上,尽管他不是故意的(他在她怀有身孕时踢了她的肚子,尽管原本并不打算杀她)。和西塞罗的情况差不多,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她在当地有房产。人们在附近的赫库兰尼姆发现的法律文件上记载,“皇后波派娅”正是“庞贝地区”一些砖石(或瓦)建筑的所有者。她的家族可能就来自庞贝,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就是那座宽敞的“米南德之家”的主人。尽管在所有记载波派娅的(不良)品德和家庭背景的史料中都没有直接提及这一点,但是这些砖石建筑以及城里存有的大量关于当地有个著名的“波派娅”家族的证据表明,她很可能就出身自庞贝。
这本身已足以再次说明这个地区和罗马精英的世界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人们寻找波派娅当地住宅遗址的愿望过于强烈,就连务实的现代考古学家也不例外。他们的主要候选对象是奥普隆蒂斯(Oplontis,现在的托雷安农齐亚塔[Torre Annunziata],离庞贝大概8公里远)那栋大别墅。它也许是属于她的;因为这是一处庞大的房产,具有皇家规模。但是,尽管人们经常将之称为“波派娅别墅”,仿佛这已是既定事实一样,但证据其实是极为不可靠的,不外乎两三则模糊不清的涂鸦,甚至都不见得与波派娅或者尼禄有任何联系。以“伯里洛斯”(Beryllos)这个名字为例,它被刻在别墅的一面墙上。这也许指的是犹太史家约瑟夫斯在某处提到的那个伯里洛斯,他是尼禄众多奴隶中的一员,不过也很有可能不是。伯里洛斯是个普通的希腊名字。
我们还能从史料中看到庞贝与罗马之间的另外一种联系,在罗马史的记述中,庞贝这一次的露面是很出名的,仅次于火山爆发。此事是公元59年的露天竞技场暴动,罗马史家塔西佗的记录如下:
大概就在同时,一件很小的事故引起了罗马的两个殖民地努科利亚和庞贝之间的严重纠纷。事故是在李维涅乌斯·列古鲁斯(Livineius Regulus)主办的一次角斗士表演上发生的。关于列古鲁斯其人被逐出元老院的事情我在前文已经谈过了。在相互嘲弄的时候(这是外地城市中那些性情暴躁的公民的特征),他们对骂起来,继而就相互抛石块,最后更动起武器来了。庞贝的居民占了上风,因为比赛是在庞贝举行的。结果许多被打成残废的和负伤的努科利亚人被抬到罗马来,许多人为孩子和父母的死亡痛哭。皇帝把这一案件交给元老院处理,元老院又交给执政官。当案件最后再交到元老院进行裁决的时候,元老院决定不许庞贝市的公民在今后10年内再举行任何类似的集会,城内的非法团体均予以解散。李维涅乌斯和其他煽动事端的人则被给予放逐的处分。
和李维涅乌斯一起被放逐的是当时庞贝在任的双执法官;或者说这至少是个合理的推断④,因为在这一年,我们知道该职位上出现了两对官员的名字。

图16 该作品展现的是公元59年露天竞技场里那场暴动的高潮时刻。左边的露天竞技场刻画得非常细致,外面陡峭的楼梯、竞技场上的遮阳篷和外面摆设的各类货摊都清晰可见。而在右边,斗殴则已经延伸到了旁边的训练场。
城里遗留下来的一幅画作让这个故事更加令人难忘,这位画家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不知悔过的极端护城倾向?)选择(或者被命令)描绘这起臭名昭著的事件。那些乍看上去仿佛是在竞技场内决斗的角斗士们可能就是暴动的庞贝人和努科利亚人,他们也在这座建筑的外围展开了战斗。
现代人和罗马人一样痴迷于角斗士文化,这使这起事件被推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但塔西佗的记述并不仅仅是一场发生了骚乱的角斗士表演的生动剪影。例如,他指出这场庞贝的表演是由一个遭谪贬的罗马元老举办的,此人在几年前被驱逐出了元老院(遗憾的是,塔西佗所谓的“前文”那部分内容已经遗失了)。然而,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位在罗马失宠的富人将庞贝视为一个他可以在其中扮演施惠者和要人角色的地方。不仅如此,我们很难不去猜测,捐助这场表演的那个声誉不佳、或许有争议的人与表演所引发的暴力活动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在这里,塔西佗也暗示了地方社区可能能以何种方式使自身的问题在罗马引起关注。努科利亚人(尽管在其他情况下也有可能是庞贝人)显然能够前往首都,得到皇帝本人的关注,并让他给出切实的回应。至于他们是如何见到皇帝的(如果他们真的见到了的话),并没有得到说明。但这正是一座城市的罗马“恩主”(正如庞贝的马克鲁斯一样)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他或许会为“门客”们安排一场与皇帝或某位官员的会面,或者更有可能代表他们接手案件。规则是,意大利的地方事务在罗马的确是受关注的;至少在原则上,皇宫的大门是向他们的代表团敞开的。
可能是由于一个这类出使罗马的代表团,后来的一位皇帝介入了庞贝的事务。人们在城门外发现了一系列铭文,记录了维斯帕先的一位代理人的活动。这是一个名叫提图斯·苏维迪乌斯·克莱门斯(Titus Suedius Clemens)的军官,他“对一块被私人霸占的公有土地进行了调查,全面考察后将其归还给了庞贝城”。这个事件背后是罗马世界里经常引起纠纷的一个问题:国有土地被私人不法侵占,然后政府(罗马或者当地政府)又设法将其收回。一些历史学家猜想,新皇帝维斯帕先是自发介入上述事件的,似乎在帝国财政事务上扮演了一个新上任官员的角色。但更有可能的情形是,庞贝地方议会像之前的努科利亚人那样接近皇帝,请求他帮助收复国家财产,于是克莱门斯被指派处理此事。克莱门斯是一名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在把维斯帕先推向皇位的内战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塔西佗将其描述为一个好战的士官,随时准备拿降低军队纪律标准来换取手下的拥护。我们不知道当他来庞贝解决土地纠纷问题时是否已经改过自新了,我们只能希望如此。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远为广泛地介入了城内的事务(无论应邀与否)。在流传下来的一些公告中,我们能看到他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公开支持其中一位候选人:“请选举马库斯·爱比迪乌斯·萨比努斯(Marcus Epidius Sabinus)担任享司法权的双执法官之一,他得到了克莱门斯的支持。”我们也不清楚他在城中活跃了多久,但他似乎逃离了火山之灾。我们发现,他在公元79年11月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所谓的“唱歌的门农雕像”上(这实际上是一位法老的巨型雕像,黎明时分会发出奇怪的声响),它位于埃及内陆,是罗马游客的观光热点。
事实上,庞贝就是这样存在于罗马城的半影之中的,首都的历史、文学、文化和人民也以某些有时出人意料的方式深深嵌入了这座小城市的生活和构造之中。如果说穆米乌斯洗劫科林斯得到的战利品有一部分最后来到了这座城市,那么杀害恺撒的某个刺客至少有一部分家产也是如此。人们在一座小房屋的花园里发现了一根华丽的大理石桌脚,雕刻有狮子头,上面的铭文记载它归普布利乌斯·加斯卡·朗古斯(Publius Casca Longus)所有(见图17)。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最先刺中独裁官的那个人,而这座房屋可能归他的某个后代所有。但更有可能(考虑到这座房屋不大)的是,这并不是祖传家宅,而是朗古斯及有罪的其他当事人的部分财产,在恺撒被刺杀后,恺撒的侄孙、养子、继承人、未来的皇帝奥古斯都将其拍卖了出去。无论这根桌脚最终是如何来到庞贝的,对参观者而言,这都是一个有趣的历史话题,就像那根埃特鲁里亚立柱一样。

图17 庞贝城和公元前44年恺撒刺杀案之间有何关联?其中一名刺客的名字被刻在了图中的桌脚上,这是在城里的一座小房屋里发现的。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些罪犯的家产在罗马被拍卖了出去,最终来到了庞贝。
罗马城的人通常情况下是带着商业或者娱乐目的来庞贝的。除了在墙上涂鸦里留下“签名”的6名近卫军士兵,人们最近在庞贝的一块墓地中还发现了4块纪念近卫军士兵的墓碑。有的人军衔相对较高;死者里还有一名新兵,20岁的他刚刚服役两年。对于他们在庞贝城里做什么,我们只能付诸猜测——或许和克莱门斯一样,是在执行皇帝指派的任务,或者是忙中偷闲,暂时脱离护卫在该地区居留的皇室成员的职责,甚至可能是随同皇帝本人对庞贝城做“皇家访问”。
最近有很多学者投入了大量精力,想要重建尼禄和波派娅在公元64年来访的细节,彼时大地震刚过去不久,据说尼禄那一年还在那不勒斯的舞台上表演过。当然,这对夫妇可能确实曾造访此地,但可以想见,其证据远非通常认为的那样确凿。最有力的证据也就是城中一座大房屋里残存的几则涂鸦。这些涂鸦难以破译或解读,它们可能提及的是这对夫妇献给维纳斯的黄金珠宝之礼,以及“恺撒”(也就是尼禄)可能造访了维纳斯神庙——尽管如果我们没有认错维纳斯神庙的话,它此时应该是一片废墟,这使这种解释说不通。就算这样,想要证明尼禄与庞贝城的关系,与最近在庞贝城外莫列金(Moregine)的一座拥有整套豪华餐厅的建筑里发现的几幅绘画相比,这就算比较好的证据了。考古学家观察到,墙上有一幅阿波罗画像看起来与皇帝本人尤其相似(见彩图3),他们从这一点出发声称这里可能是个供给站或皇帝行宫,尼禄来访庞贝时就暂居于此。这个猜想别出心裁,足以媲美18世纪那些想象力丰富的古物学者。
从另一则涂鸦中,我们就能看出在解释这类证据时必须要多么谨慎。那是一句拉丁文:Cucuta a rationibus Neronis。a rationibus的职位差不多相当于“会计师”或者“簿记员”。因此这看起来就是个简单的签名,“尼禄的簿记员库库塔”,他或许是在陪同主人造访庞贝时将名字刻在了墙上。但这样就可能误解了这个玩笑。因为cucuta(或更通常地被写作cicuta)在拉丁文中意为“毒药”。这更有可能是一句嘲笑尼禄的讽语,而不是一个名字有些奇怪的人的个人签名。“毒药是尼禄的簿记员”,这句玩笑似乎暗指的是人们对他的谴责,因为在财政陷入危机时,他曾杀死他人以获取他们的钱财。庞贝城里的某个人显然熟知这类和皇室有关的流言。
不过,对于公元79年的来访者而言,罗马与庞贝之间最显著的联系可能表现在这座城市的构造——建筑和艺术——复制或反映了罗马的关切,或者甚至照搬了首都的建筑本身。这些联系包括城市广场的布局(象征了“罗马性”的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三神庙位于一端),还有几处用于崇拜皇帝的神庙,以及罗马著名纪念碑的自觉复制品。在广场上最宏伟的建筑之一优马奇娅楼(Building of Eumachia,由公元1世纪初捐助此楼的那名女性得名)的外立面,有两处尤其引人注目的对首都建筑的“引用”。关于这座庞大建筑的功用,至今仍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织布工人的会馆,近来又有人认为它是奴隶市场),但是从正面看,在沿广场一字排开的门廊下的墙上有两大段铭文,其上是必定一度被用来陈列雕像的壁龛。尽管带有神话色彩,其中一处铭文详细描述了埃涅阿斯的(他是维吉尔史诗的主角,在特洛伊陷落后出逃,建立了作为新特洛伊的罗马城)功绩。另外一处铭文详细描述了另一位神话中的罗马奠基者罗慕路斯的事迹。这两段文本都源自类似的铭文——在第一位皇帝的典范纪念场所,罗马的奥古斯都广场上,曾经有称颂包括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在内的数百位罗马英雄的功绩的铭文。来自首都的游客造访此地,可能不会感到陌生。
对于这个著名的纪念场所,游客还会在庞贝发现不那么正式的呼应之处。在我们今天称之为阿波坦查大道的那条主街旁,有一家漂洗坊(兼有织物加工和漂洗功能)的门面上装饰着两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绘画。其中一幅画的是手里拿着一件战利品的罗慕路斯(见图18),另外一幅是埃涅阿斯,正带着年迈的父亲逃离火光中的特洛伊。庞贝城里的某个机灵鬼不仅认出了第二幅画的是维吉尔描述的场景,而且还附上了一句对《埃涅阿斯纪》首行诗文(“我歌唱武器与人……”)的戏仿:“我不歌唱武器与人,我要歌唱漂洗工们……”不过这些画更为特定的意义也是一定可以被认出来的。因为,根据现存对罗马奥古斯都广场上的装饰的描述,漂洗坊前门外的绘画是基于在那里占据显要位置的两组著名雕像——一个是埃涅阿斯,一个是罗慕路斯——绘制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画师直接按照罗马的广场上的雕像绘制的。最有可能的是,画师依据的是优马奇娅楼门外立于铭文上方的那些雕像——大概就是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它们自身十分可能就和铭文一样是罗马城著名典范的复制品。

图18 在庞贝的一家漂洗坊的外墙上,画着两位罗马的奠基者。图中是罗慕路斯,扛着他打败的敌人的盔甲,呼应着另一幅描绘埃涅阿斯带着他的父亲逃离特洛伊的绘画。两幅绘画都是以立在庞贝广场上的雕塑为基础的,而这两尊雕塑又模仿的是罗马城里的雕塑。
在这里,庞贝这座小城笑到了最后。因为奥古斯都广场上的那些雕像原件也已经遗失了。这些绘画是复制品的复制品,装饰着一座小城里的工坊墙面,如今却成为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证据,以推想罗马城本身的一个主要的皇室委托项目及装饰规划。它向我们很好地展现了罗马和庞贝之间至今也难解难分的复杂关系。
①拉丁语中,字母c在Caius和Cnaius中发g的音。
②唐桥井市位于英格兰肯特郡西部,南本德为印第安纳大学分校所在地。两地位置闭塞,对政治缺乏兴趣。(Beard在邮件中的解释)
③位于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是名流和富人的消暑天堂。
④骚乱爆发时在任的两位执法官为格奈乌斯·庞贝乌斯·格罗斯弗斯和格奈乌斯·庞贝乌斯·格罗斯弗斯·加维阿努斯。有人认为,2017年在庞贝新发现的碑铭可能证实他们的确遭到流放,铭文中提到的Pompeios in patriam suam reduceret指的是两位庞贝乌斯被允许返还故土。但也有人认为,这里的Pompeios指的是庞贝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