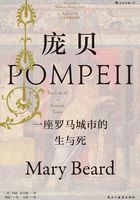
成为罗马人
公元前91年,所谓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爆发了,一批意大利盟邦(socii,战争因此得名)与罗马挥戈相向。庞贝也是其中之一。如今看来,这是一场十分古怪的叛乱。因为,尽管这些盟邦的动机引发了无尽的争议,但最有可能的是,他们之所以诉诸暴力,并非因为真的想要脱离罗马世界并摆脱其统治,而是因为记恨于自己没能完全成为罗马集团的一员。换言之,他们想要的是罗马的公民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庇护、权力、影响和在罗马的投票权。由于罗马和它的盟邦已经习惯了肩并肩作战,这场以野蛮著称的冲突实际上也就成了一场内战。很容易就能料想到,军事实力远为强大的罗马获取了胜利,但这些盟邦在另一种意义上取得了胜利,因为他们如愿以偿了。罗马向一些反叛之邦授予了公民权,立刻就把它们收买了。但即使是那些顽强反抗的,在战场上被击溃后也被授予了公民权。自那时起,几乎整个意大利首次在严格意义上成了“罗马人的”半岛。
在这场战争中,庞贝于公元前89年被著名将领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围攻,此人后来在罗马城里成了嗜杀成性的独裁官,尽管任期不长。(公元前82年到前81年,他出价悬赏500多个富有政敌的项上人头,若他们不自我了断,就只能等着被残忍追杀。)为苏拉作传的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年轻的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当时就在苏拉麾下,不到20岁,数年之后,他才在罗马法庭上以卓越的演讲技艺大获成功,并由此开启了政治生涯。对崭露头角的演说者和拉丁语学习者而言,他可谓是教科书式的人物。
我们至今还能在庞贝看到苏拉当年的所作所为,人们在遗址附近找到了无数的铅弹和弩炮弹丸(相当于现在的炮弹),城墙上还残留着零星的弹孔,它们据推测是原本用来清除防御工事的弹丸未能击中目标而留下的清晰痕迹。城内靠近北方城墙的那批房屋毁损尤为严重。例如“维斯塔贞女之家”(House of the Vestals),它得名自18世纪的一个毫无根据的想法,那时有人认为这里曾住着一群贞女祭司,即“维斯塔贞女”。这座房屋严重损坏,即便富裕的主人成功扭转了混乱和破坏的不利。他们在战后似乎获得了一些邻居的土地,极大地扩建了他们的房子。可巧的是,近2000年后,“维斯塔贞女之家”再次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同盟国的炸弹在1943年9月将其摧毁。经过发掘,现代的弹片与罗马时期的投石弹丸就这样同时呈现在我们眼前。
庞贝人抵抗罗马火力的投入程度或历时长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街角粉刷的那一系列奥斯坎语公告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了解他们是如何准备战斗的。通常认为这些公告是围城时留下的,在后来涂上的灰泥的层层遮盖下得以保存,又在灰泥剥落后重见天日。其含义虽然无法确定,但极有可能是对守城部队下达的指令,告诉他们应该在哪里集合(“在第12座塔和盐门之间”)以及听谁的指挥(“维比乌斯之子马特里乌斯[Matrius,son of Vibius]将指挥战斗”)。若是如此,那就意味着这里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并且市民的受教育程度足以让他们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书面指令。庞贝城也有外来的援助。一则关于同盟战争的史料记录了叛军将领卢基乌斯·克鲁恩提乌斯(Lucius Cluentius)前来解围的故事。他在第一次小规模交锋中占了上风,却不料苏拉杀了个回马枪,予以致命一击,将克鲁恩提乌斯的军队一直驱逐至附近的叛军大本营诺拉,据古人(未必可靠)的估计,苏拉杀了他们近2万人。庞贝不久后肯定也陷落了。
但与其他战败的盟友城镇受到的待遇不同,它没有遭受残酷的对待。不过,在战后不到10年、庞贝人已经被授予罗马公民权之后,苏拉采取了另外的报复方式。在希腊战场上的漫长战争结束后,由于需要安顿老兵,他将其中一部分安置在了庞贝,据保守估计,算上家属共有几千人。这使城市人口激增,可能使居民人数增加了近百分之五十。但它造成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罗马将此地正式纳为“殖民地”,当地政府也相应得到了改造。每年选举产生的官员被给予了新的名称,并且无疑也有了新的职责。原先奥斯坎人的行政长官(meddix tuticus)被双执法官(duoviri iure dicundo)取代,后者的字面意思是“宣布法律的两个人”。
为了反映新身份,城市的名称也发生了改变。这时庞贝的官方名称为“Colonia Cornelia Veneria Pompeiana”:Cornelia来自苏拉的家族姓氏(Cornelius);Veneria意指守护神维纳斯;换言之,它成了“受女神维纳斯神圣庇护的科尔内利乌斯的殖民地庞贝”(拉丁文和英文读起来同样拗口)。正如这个称谓所示,城市的官方语言也变成了拉丁语,不过直到公元79年,还是有当地人在私人场合使用奥斯坎语——无疑,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也只有这几个人或许能够破译今天还能见到的那些古奥斯坎语铭文。在这个城市最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某个人,可能是个嫖客,将其名字留在了一家妓院的墙上,用的就是特色鲜明的奥斯坎文字。
这些“殖民者”(他们现在常被如此称呼)使庞贝焕然一新。一个崭新的大型公共浴场在广场旁边兴建起来,在早期两位双执法官的资助下,许多其他建筑也得到了修缮,包括一个新建的桑拿房。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城市的东南角,现有的房屋被拆毁,修建了一座露天竞技场,这大概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石质露天竞技场。主入口上方的铭文显示,这个竞技场的修建要归功于另外两位杰出的新来移民的慷慨之举,他们还支持修建了一座全新的“有顶剧院”(Covered Theatre,或“Odeon”,它今天常被如此称呼),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掏腰包。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其中一位显贵盖乌斯·昆克提乌斯·瓦尔古斯(Caius Quinctius Valgus)①正是我们在拉丁文学中偶尔能见到的那个“瓦尔古斯”:他是普布利乌斯·塞尔利维乌斯·卢鲁斯(Publius Servilius Rullus)的岳父。卢鲁斯主张给罗马贫民重新分配土地,是西塞罗在3篇《反卢鲁斯》演讲中的主要攻讦对象。若是如此,如果西塞罗对他的评价至少有一半可信,那么这个出资兴建庞贝竞技场的人,就不是(或不仅是)一个为当地作贡献的毫无私心的慈善家了,而是一个趁着苏拉在罗马施行恐怖政策大发横财的无耻坏蛋。
至于这股新来的移民到底住在哪里,就不是很清楚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城内明显有一个“殖民者街区”。近来有观点认为,他们的大部分地产和土地都在郊区,既有小农场又有大别墅。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这是一个便利的解释,但并不全面。肯定有一些殖民者住在城里。在他们之中最富有的人(反正肯定不是最普通的)看来,理想的候选房产是城市海岸边的房屋(例如“黄金手镯之家”及邻近房屋)。它们位于城墙——一旦庞贝成了罗马人统治着的据说和平的意大利的一部分,城墙在战略上就没有必要性了——之上,是多层建筑,建在急剧降至海平面的陆地陡坡上,总建筑面积几近“农牧神之家”。豪华的娱乐套房内设有大窗和阳台,一度必定非常壮观的沙滩海景能够尽收眼底(见图15)。遗憾的是,这些房屋并不定期向游客开放。它们楼层众多,有着迷宫般的回廊和楼梯,更不用说全景的视野(谁说罗马人不在乎风景?),与我们对罗马房屋的标准印象完全不同。它们必定是这个城市里最时髦的一批房产了。

图15 “法比乌斯·鲁弗斯之家”(House of Fabius Rufus)坐落在城市西缘,旧城墙之上,从中能够看到令人艳羡的海景。为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房屋设有大窗和阳台。
在某种程度上,殖民者的到来直接使这里本来就已经启动了的“罗马化”进程提速了。毕竟,“农牧神之家”的主人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就已经选用拉丁文(HAVE)来迎接他的客人,除非那块特别的镶嵌画是后来加上去的。而在公元前1世纪早期兴建公共建筑的浪潮中,其中一些建筑的建造时间可能比殖民者的到来还要早,而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由后者发起的。实际上,除非有确切的铭文证据,否则很难确定这些建筑是在殖民地建立之前还是之后修建的。有观点认为这些建筑中有许多是殖民者修建的,但就算这并不必然是错误的,也几乎完全是循环论证(殖民者热衷于修建;因此所有公元前1世纪的建筑都是他们修建的;这又反过来证明这些殖民者热衷于修建)。例如,位居广场一端的献给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的三神庙究竟是由殖民者奠基的(近来有一位考古学家声称,其测量单位似乎使用的是罗马尺,这意味着它是一座罗马建筑),还是由一座原本单独献给朱庇特的神庙后来改建为典型的罗马三神庙的,仍然存在争议。鉴于罗马逐渐扩大影响力,在“前罗马时期”的庞贝就已出现大量“自发的罗马化”现象是毫不足怪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幅图景易于将当时的冲突程度予以淡化,毕竟在早期殖民时代,罗马移民和当地的奥斯坎居民之间矛盾重重。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引起的冲突;尽管我对某些现代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高雅而爱好戏剧的庞贝人有些难以接受粗鲁而爱好观看竞技表演的老兵,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对老兵不公,而且也过于高看庞贝人了。说得更确切些,这些移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把控了城市的日常政治生活,并将本地原来的居民排斥在外。
这种排斥在遗址本身上留下了迹象。在现存的殖民地头几十年竞选出来的城市官员名单里,没有一个出自传统的奥斯坎人家族,而是清一色的罗马人。纪念新露天竞技场的修建的铭文表示,瓦尔古斯和其他联合赞助人是将其献给“殖民者”的。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殖民者”也包括所有被正式称为“受女神维纳斯神圣庇护的科尔内利乌斯的殖民地”里的居民。不过,尽管在严格意义上或是如此,要说这个表述囊括了城里所有的原有家族,也还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在日常言谈中,“殖民者”和“庞贝人”通常被视为城中两股独立的对抗势力,事实上,西塞罗于公元前62年在罗马发表的一次演讲就证实了这一点。
这是西塞罗为独裁官苏拉的侄子普布利乌斯·苏拉所做的辩护演讲,因为后者被指控是卢基乌斯·塞尔基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的同谋;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喀提林这个负债累累的贵族和不幸的革命者在一场未遂的推翻罗马政府的企图中死去。20年前,正是这位年轻的苏拉在庞贝负责殖民地的建设。有人指控他怂恿庞贝人参与喀提林阴谋,这并非完全不可信;在回应指控时,西塞罗一度将罗马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对庞贝当地政治问题的讨论上。这个转弯抹角的辩护令人生疑,集中在城里的“殖民者”和“庞贝人”之间的争执。他声称,部分归功于苏拉本人的介入(信不信由你),这些争执都结束了;在苏拉的支持下,双方——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仍是两支独立的势力——都向罗马派出了使团。可是,这些争执到底是关于什么的?西塞罗含糊其词地提到了庞贝人对于“他们的选举”和“ambulatio”感到不满,后面这个拉丁词语既可以指“散步”,也可以指代任何可以散步的地方,比如“一个游廊”。
关于“选举”的争执其实不难想象。将这一点与殖民地头几任地方官员中没有当地人的名字联系起来,似乎可以确定新的政治安排以某种方式使本地居民处于不利地位。一些现代学者甚至猜想,本地居民或许被完全排除在了选举之外——尽管也有可能是以不那么极端的方式,这更为合理。至于与“散步”有关的争执到底是指什么,引发了人们的无数猜想。例如,以“ambulatio”一词的“散步”这个含义来理解,这是否意味着庞贝人在城内活动的权利受到了限制?或者某个特定的游廊禁止他们入内,否则便会构成罪行?抑或,西塞罗提到的那个词根本就不是“ambulatio”,而是(如一份该演讲的手抄本所写的那样是)“ambitio”,意为“行贿”或“腐败行为”——这样问题又回到了选举制度上来?
坦白说,这里的谜团还未被解开。但无论答案多么可疑,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虽然麻烦只是暂时的(几十年后,那些原先缺席的奥斯坎人名字又重新出现在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名单中),可在庞贝被完全纳入罗马后的最初岁月里,当地原来的居民的日子肯定都是不太好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