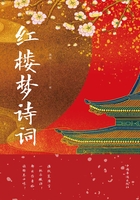
心较比干多一窍·林黛玉
自《红楼梦》成书以来,“林妹妹”那形销骨立的凄绝之美便深入人心,但凡略懂风情的人,想起她,总不免要慨叹唏嘘一番。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林黛玉。于我,每当思及,脑中就泛出一泊冷湖,这湖仿佛独立于凡界之外,微微泛着些波光粼动,偶尔风过,舞起水上薄雾,袅袅如纱,像是有什么正待诉说,然而终究归于寂静无声。
整日里将珠泪抛洒,始终不曾见容于世,徘徊中,凄凄然魂断潇湘。这,便是林黛玉的一生。
从来造化不由人。她不知道,自西边角门被抬进荣国府的那一刻起,命运的掌纹加速蜿蜒,她的一生便要在这里铺展开去;缘起缘灭,爱恨悲欢,她不知道,恩情山海债,唯有泪堪还。与宝玉的一段生死纠缠,三生石上,早已注定。
那夜掷花名签,黛玉那一支上描着芙蓉,上题“风露清愁”,一如她的性情。“莫怨东风当自嗟”的前头,隐去的是宋代文人欧阳修的叹息:“红颜胜人多薄命。”黛玉之薄命,正与她“红颜胜人”相照应,凡见她之人,无不称其风流袅娜、举世无双,究竟是怎样的美,代代有代代的附会。只从贾宝玉的眼里看去:
品读之,黛玉眉宇间的秀气和行止间的优雅自不待言。但若只论美貌,世上佳人何其多哉,她的奇绝,更在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敏感纤弱、细腻多思,在于那“泪光点点”的悲情之美,是以得宝玉赠字曰“颦”。
眉尖若蹙,颦而难舒,正是黛玉愁郁敏警的画像。
幼年丧母,少年殁父,已是大不幸;原为父母掌上明珠,转眼便成他人篱下寄孤,这客居的外祖母家偏还是个皇亲国戚的大家庭。莫说多疑善感的黛玉,便是任何一个小小女子,初来到这“到底是客边”的所在,也必然“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的。
自卑的种子,就此埋下了根,偏还才高自许,孤高更致疏离。在外人看来,黛玉的性子,总是不易亲近的了。她敏感至极,生怕被人看低,那一声声冷笑暗讽,那“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的挖苦,还有那“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的泣诉,都使她看起来如玻璃娃娃一般易碎而不可碰触。
于是,纵然是“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却毕竟冷漠如冰。缺乏耐心的人,表面上虽仍敷衍着,心里却不免与她生出了距离,私底下早给她贴上了“尖酸刻薄”“任性刁钻”的标签。好在她倒也乐得远离众人,只独守着一围修竹,教鹦鹉背诗,或焚香等候燕子归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诗意盎然。
一个人尝浮世轻愁,一个人看细水长流。
品味孤独,倒是一种超然的情怀。“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是美人对尘嚣的绝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天地一人的江湖境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再热闹也掩不住、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哀愁。黛玉所拥有的,也正是这样一份目下无尘、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她领受这孤独,沉醉于它浓酽婉转的美,纵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纵然饱含苦涩凄凉,她仍兀自沉浸其中,不管不顾。
这日,她又是孤身一人。因为前一晚被晴雯拒于怡红院外,她误会宝玉故意与自己疏远。芒种佳节,本该和姊妹们共祭花神,黛玉却“独抱幽芳出闺阁”,兀自立在远离众人的角落——先前与宝玉共同埋葬桃花的花冢前。但见得落英乱阵,便有了一幅这样的葬花图:
值此“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的浓烈凄美,又兼心中郁结难舒,多情如她,怎不泪如雨下?是以“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
想这些花儿“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不正如同自己薄命?临风洒泪,倚锄伤情,半为这飘逝的飞花,半为自己无根的命运。
既然“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是自己与飞花共有的结局,只不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会是与她知心的宝玉吗?昨夜探访,他迎了宝钗进门,自己却不得而入,害得自己“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
原来宝玉也是指望不了的。念及此,一句“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悲叹,惊得暗处里躲着听的宝玉怀里的花瓣撒了一地……
黛玉每落泪,并不需要太多理由,甚至根本不需要理由,她的胸中,随时涌荡缠绵着一种难与人说的抑郁,落红能让她落泪,鸟鸣也令她心惊。闲愁万种的秋夜,“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听到“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唱词便要心动神摇、站立不住之人,此时自然更是难以自持。这便是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这晚,黛玉歪在床上,回想起白日里宝钗来探,惠赠燕窝,彼此说了许多推心置腹的话。原来,身旁姐妹中,最令黛玉担心忌惮,至于素常以“心里藏奸”去揣度的这位宝姐姐,却实在算得是她的一位知音。
世事往往如此,以为最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之人,往往是最了解你的人。
窗外正是夜阴沉黑,雨滴竹梢,黛玉不禁心中有感,吟成一首《代别离·秋窗风雨夕》,拟《春江花月夜》之格,恨那“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值得“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竟又迎来了个“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的无眠之夜。
此回之后,钗黛前嫌尽释、互怜相惜。《琴曲四章》里,黛玉对宝钗“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忧。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的唱和,在看似清淡的铺陈中,已将宝钗与自己的境地连到了一起。同是红尘沦落人,黛玉叹息宝钗“不自由”,又深悲自己“多烦忧”,其实不论孤傲如黛,抑或克己如钗,兜兜转转,终是怎么也走不到幸福的明天。
难道要求她如宝钗般周全起来?那便就没有黛玉了。使她处处隔绝于人的,是生就的天性。没有人能强迫她赢取所有人的欢心——宁愿寂寞,宁愿不容于世,只为自己的心,只为自己而活,这便是与世间大多数人都不同的林黛玉。
如此,便再无指摘黛玉矜持自许的理由。她的孤单、她的伤,说是孤芳自赏也好,顾影自怜也罢,让这一朵注定不能盛放的花,只随着自己的心性舒展吧。不知是否可怜她镜影清减,遂有满树灼灼的桃花纷扬了下来:
这是黛玉《桃花行》中的诗句。因着这首诗,本已萧疏的海棠诗社重又聚拢起来,便是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宝玉读过,“便知出于黛玉,因此滚下泪来”,说:“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
薄命的黛玉,恰似这灼灼桃花,不知不觉间,已如夕阳晚景。桃花谢枝那一瞬,她仿佛阅尽自己一生:
悲身世如风吹落花,题素怨问谁解秋心?工愁工病的林黛玉,流泪不尽的林黛玉,清早起来,揽镜自照,正是“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又是“心病终须心药治,解铃还是系铃人”,可谁才是她的卿?谁是她的解铃人?
是宝玉,那个读《桃花行》而落泪的人。她的幸与不幸,全在乎这个懂她最深也爱她最深的贾宝玉,他是她的命中情缘,也是她的前定劫数。
他曾咬牙做出“你放心”的承诺,也曾雨夜探病而来,还曾逼问黛玉道:“难道你只知道你的心,就不知道我的心不成?”话中并存的温暖与痛苦,令人闻之动容。他对她,是最高的尊重,最纯的挚爱,刻骨铭心的生死不离。
她爱宝玉,却爱得孤独绝望。心内自是涌动着万千情愫,奈何无人做主,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担忧,仿佛深藏了一个汹涌的海洋,流出来,却只有两行泪珠。
她所求的,不过是清静而纯粹的两个人,知心依偎。
然而最难实现的,往往也正是最平淡的幸福。
背负着沉重的心事,对爱情,黛玉始终不曾安心,她急切地一次次称量自己在宝玉心里的分量,以确认自己存在的意义。敏感和猜疑的脾性儿,又使她总处在和宝玉激烈的冲突中,在伤害对方也伤害自己的同时,才能将心稍稍放稳。
分明依依你侬我侬,偏又极少以温暾和平的言辞表达,宝黛的爱情,也因此成了历来读红楼者最怕、最感揪心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