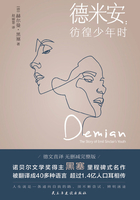
第2章 两个世界
我的故事始于十岁那年,当时我正在镇上的拉丁文学校读书。
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时日既有甜蜜也有忧愁。小镇的巷子或阴暗或通明,两侧遍布各式住宅,远处还有塔楼和钟楼。家中的房间有些华丽、舒适、温暖又令人放松,还有些隐藏着某种秘密。年轻的女仆、弥漫的药材味,以及桌上的果脯,都让我感到既温暖又亲切。
日与夜的交替创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彼此交织在一起。父母的房间自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十分狭小,实际上仅有父母两人生活在其中。我熟悉这个世界的种种,包括父母的慈爱与严厉以及各种规矩与学业要求。这个世界阳光灿烂、明晰、洁净,我们谈话温文尔雅,饭前洗手、衣着整洁,并时刻保持礼貌。每日清晨,我们都会唱赞美诗,也会在圣诞节大加庆祝。未来似乎一片坦然,既有责任、愧疚、忏悔、宽恕、善举,又有仁爱、敬畏以及《圣经》智慧与箴言。一个人若想要明明白白地生活,那么他就应竭尽全力维护这样一个世界。
然而,在这个世界中还重叠着另一个世界,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弥漫着不同的气息。这个世界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做着不同的承诺,并提着不同的要求。女仆与工匠生活在其中,他们时常讲鬼故事并散播流言蜚语。整个世界充斥着惊悚却又神秘的场所和事物,比如屠宰场、监狱、酒鬼、粗鲁的妇人、产犊的母牛、奄奄一息的马匹,以及抢劫、谋杀甚至自杀事件,尽管野蛮、粗鲁且丑恶,但又极具诱惑。它们就在周围,甚至仅在一个巷子、一间房屋之外。随处可见警察、流浪汉以及家暴的醉汉,年轻女工在傍晚时分从工厂中蜂拥而出,甚至会遇见某位老巫婆、藏在树林中的强盗以及被警察押解的纵火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混乱的气息,只有在父母的房间才存有一丝秩序。这其实也是一种幸运,我可以在一个世界中享受平静、整洁、静谧、心安、宽恕、仁爱与规矩的氛围,然而,那个喧嚣、阴暗与暴力的世界也有其存在的意义,一步之遥便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两个世界紧密地重叠在一起,这一点着实令人费解。例如每个傍晚当我们进行晚祷时,女仆乌娜会事先洗手并整理整理围裙,然后坐在客厅门口同我们一起祈祷,这时她便进入了我们所营造的这个光明、正义的世界。但当她回到另一个世界后,在厨房或柴棚,她仿佛变了一个人,会再给我讲“无头的小矮人”这样的鬼故事;同时,她还会与隔壁肉店老板娘讨价还价。这些都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我是我父母的孩子,因此我毫无疑问属于光明、正义的世界。但不论我朝向哪个方向走,都会迈入另一个世界,我在这个世界中属于一个陌生人,时常会感到恐慌与内疚,但我确实也生活在其中。有时候,我甚至想要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因为每当我返回光明的世界,我觉得它似乎过于单调乏味。还有些时候,我十分确定我会沿着父母的道路,过一种质朴、有序而优越的生活。但在那之前,我需要规规矩矩地上学、考试。在这条路上,我需要穿过那个阴暗的世界,稍有不注意,便可能会滞留其中。有段时间,我热衷于阅读一些关于少年误入歧途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最终都迷途知返。尽管我认为结局就应该这样,但我更感兴趣的却是那些邪恶与迷失。说实话,有时候我并不希望看到浪子回头,但甚至没有人敢这样想,更不用说大声说出来了,而仅仅作为一种暗示,掩藏在意识的深处。我能够想象,经过一番伪装或完全没有伪装的魔鬼就在楼下大街、集市或酒吧中,但绝无可能出现在我的家中。
同时,我的姐姐也生活在光明世界中。在我眼中,她们似乎与父母更亲近。她们更加温文尔雅,当然也会偶尔犯个小错,但相比我来说,她们很少犯错,严重程度也轻得多。我更倾向于接触罪恶的事物,似乎离那个阴暗的世界更近;她们像父母一样更受人欢迎。每次我与她们吵架,事后总是自责,认为自己应该寻求原谅。冒犯她们即意味着冒犯父母,因为她们代表着真与善。于是,我有什么秘密宁愿告诉街边的无赖,也不愿意与她们分享。高兴时,我也很乐于与她们玩耍,会像她们一样乖巧,恰似小天使一般。这是我记忆中最和谐的时刻,但仅出现过寥寥几次。通常情况下,玩着玩着我就会耍性子,然后我们便会开始争吵,进而变得歇斯底里,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受不了的事,说出很多难听的话;之后,我会后悔自责好几个小时,踌躇着寻求她们的原谅。最后,对她们的原谅心怀感激,重又变得开心快乐起来。
跟我同班的还有镇长和林务官的儿子,我们之间还算熟悉。他们虽然有些不羁,但总体来说,我们都属于第一个世界中的人。我们这个世界的人通常都看不起公立学校的孩子[1],但我却更愿意与他们接触。我的故事便从一个邻家男孩说起。
我十岁那年,趁着半天假期,我约了两个男孩出门玩。半路上,我们遇到了弗朗兹·克罗默,他是镇上裁缝的儿子,长得十分壮硕,同样在公立学校读书。他的父亲经常酗酒,家庭的名声十分不好。我听说过他,并有些怕他,因此一点都不乐意他加入我们。他当时已有成年男性的特征,模仿工厂工人的言行举止。那天,他领着我们从桥头爬下河堤,然后钻进桥拱中。桥墩与缓慢流淌着的河水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带状区域,上面堆积着一些垃圾、陶瓷碎片和生锈的铁丝等。有时候,可以在这个地方捡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弗朗兹·克罗默让我们翻找这片垃圾堆,并让我们把找到的东西给他过目。有些东西他会装进口袋中,而其他的他会直接扔进河里。他命令我们翻找铅、铜或锡制品,这些东西他都会装走,那天我们还找到了一个旧的牛角梳。在他旁边,我总是觉得惴惴不安。我知道,父亲一定不会同意我跟他来往,我也从心底里怕他。但是,我又十分高兴他能接受我,而不区别对待。尽管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但很自然地听从他的命令,这似乎早已成为老规矩。
翻找了一番之后,我们坐在一旁休息。弗朗兹朝着河水吐唾沫,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个成年人。唾沫从牙缝中吐出,可以准确地命中目标。渐渐地,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开始吹嘘在学校中的英雄事迹和恶作剧。我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但又害怕我的沉默会让他不满。在遇到弗朗兹·克罗默后,我那两个朋友便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我。对他们来说,我仿佛是一个异类,我的行为和穿着与他们格格不入。我的学校、我的出身意味着弗朗兹不可能喜欢我,同时我还敏锐地察觉到,我的两个朋友很快便会与我划清界限。
最终,在这种紧张之下,我编了一个故事。我告诉他们,有一天晚上,我有和一个小伙伴悄悄钻进磨坊旁边的果园中,偷了满满一袋子苹果,都是上好的苹果。我尽量自然地讲这个故事,以期让他们接受我。为了避免冷场,同时避免情况恶化,我又详细描述了一些细节。我告诉他们,当时我们一个放哨,另一个爬上树使劲摇晃树枝。最后,袋子装得太满,我们不得不扔下一半,而半个小时后又返回将剩下的一半带走。
讲完这个故事后,我停了一会,期待着他们的回应。
我希望他们相信我讲的故事。那两个男孩默不作声,等着弗朗兹·克罗默发表意见,他眯着眼看着我,以一种威胁的口吻问道:
“是真的吗”
“是。”我回答。
“你确定?”
“是,我确定。”
我咬死这一点。
“你能发誓吗?”
我开始有些担心,但立即表示可以。
那你照着念:“我以上帝和灵魂的名义发誓。”
“我以上帝和灵魂的名义发誓。”于是我说。
“嗯,相信你了。”他说完便转过头去。
我成功瞒了过去,并很庆幸他很快站起来,打算回家。爬上桥之后,我迟疑地表示想要回家。
“那么着急干什么。”弗朗兹笑着说,“我们顺路,对不对?”
然后,他慢悠悠地走在前面,我却不敢跑开;他确实朝着我家的方向走去。逐渐走近,当我看到门上的大黄铜门环、窗户里透出的光芒以及母亲房间那熟悉的窗帘,我长长舒了一口气。
当我刚迈进门口打算关上门时,弗朗兹·克罗默紧跟着挤了进来。走廊里十分阴冷,只有面向院子的一扇窗户透入一丝阳光。他挨着我,抓着我的胳膊压低声音说道:“别着急走。”
我看着他,有些害怕。他的手像钳子一样夹着我的胳膊。我猜测着他想要说什么,是不是想要伤害我。我纠结是否要大声呼救,应该有人能够及时跑来救我。但最终我决定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有事吗?”我问道,“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只是想问你一点事。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哦,是吗?我没什么能告诉你的。我得上楼了。”
弗朗兹·克罗默轻声问道:“你知道磨坊旁的果园是谁家的吗?”
“磨坊主的吧,或许”。
弗朗兹攀着我的脖子,用恶狠狠的眼神盯着我,笑得不怀好意,表情也十分残酷。
“那么,让我来告诉你那是谁家的。我早知道有人偷了苹果,同时我还知道果园主愿意出两马克[2]悬赏强盗。”
“哎呀,天哪!”我喊道,“你不会告发我吧?”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好心。
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背叛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我的这一感觉十分强烈,他与我们不是一路人。
“不告发你?”他笑了,“小孩,你开玩笑呢?我会造钱吗?我是一个穷鬼,不像你有一个富爸爸。既然有机会赚两马克,那我绝不会放过。或许他还会多给我点。”
突然,他松开了我。那条长长的走廊现在让我感到不安,世界[3]似乎就要崩坏。他会报警!我犯错了。他会告诉我的父亲,警察会来抓我。他在威胁我,我脑子里一团乱麻。我到底偷没偷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况且我已经发过誓。
我一下子委屈地想哭。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买通他,于是拼命地从口袋里翻找些什么。
没有苹果,没有小刀,什么都没有。忽然,我想起我有一块表,那是祖母给我的一块比较旧的银表,已经不走了,我平时带着它只是装装样子。于是我迅速把它摘了下来。
我嘱咐道:“克罗默,只要你不告发我,我就把这块表给你。我也没有其他东西,只有这个。这是银子的,但有点小毛病,需要修一修。”
他咧嘴一笑,抓过了手表。我盯着他的手,正是那只野蛮而怀有敌意的手,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
我迟疑道:“它是银子的。”
“不管是什么的,它就是块破表。”他轻蔑地说,“你还是自己修吧。”
因为担心他扭头就走,我哆嗦着大喊:“弗朗兹!等一下,等一小下。为什么不拿着?这真是银子的,我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冷漠地看着我,带着一丝轻蔑。
“嗯?你知道我现在要上哪吗?或许我应该去警察局,我跟警察很熟的。”
他转过头作势欲走。我一下抓住他的袖子,我不能让他走。我宁愿死也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
我恳求道,声音变得有些嘶哑:“弗朗兹,别去。你是开玩笑的,对不对?”
“对,我是在开玩笑。但你要多付点代价。”
“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他眯着眼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虚伪地说:“别犯傻,你知道我这就可以去赚两马克。我很穷,对我来说那可是一大笔钱。但你家很富呀,你看,你都有一块表。你只要给我两马克,那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明白他想要什么。但那两马克对我来说与十马克、一百马克、一千马克一样,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我甚至连一芬尼[4]都没有。我只有一个存钱罐。每当来亲戚的时候,他们会往里投上五芬尼或十芬尼。除那之外,我没有任何零花钱。
“可我没有钱。”我沮丧道,“一分都没有。但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给你。我有一个锡质的士兵玩偶,还有一个罗盘。你等一下,我这就拿给你。”
克罗默撇撇嘴,露出一抹冷笑,然后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他粗暴地道:“留着你那些破烂吧,还罗盘!别让我发火!听着,我只要钱!”
“但我真的没有呀,我没有办法呀。”
“不管怎样,明天你必须给我两马克。放学后我会在市集附近等着。就这么着吧,要是拿不来,你等着!”
“但我上哪去给你弄两马克呀?”
“你家里多的是呀。至于怎么弄,那是你的事。记得明天放学。别说我没警告你,要是弄不来的话……”他瞪了我一眼,吐了口唾沫,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像个幽灵。
一时间,我连楼梯都爬不上去了。我的生活全毁了。我甚至想要逃离,再也不回来了,或跑到河边跳进去算了,但最后也没能下了决心。夜黑了,我无助地坐在台阶上,抱成一团,不禁悲从中来。最终还是乌娜下楼取木柴时,发现我坐在那抹眼泪。
我求她别告诉父母,随后我跟着她上了楼。看着玻璃门后挂着的礼帽和遮阳伞,我又感觉到了家的舒心与温暖;就像一位浪子回到了熟悉的房间。但现在我却有些迷失,所有这些都属于父母的光明世界。而我已深陷于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不得不面对外来的威胁并承受随之带来的危险、恐慌和耻辱。礼帽、遮阳伞、砂岩地面、橱柜上方的大幅油画,以及客厅传来的姐姐的笑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我珍惜,但从今天开始,我却无法再从中寻求抚慰。父母和姐姐会严厉指责我。这些温馨将不再属于我,我的心已不再平静,不再轻快。我的脚上沾上了泥巴,无法在地垫上擦干净。我给这个家带来了一些阴影,而他们却一无所知。我之前也有不少秘密,也曾有过不少担忧,但相比今天这件事情,所有那些都无足轻重。我变得心神不宁,不幸就在前方,即使母亲也无法保护我,而我绝对不能让她知道。是偷窃还是撒谎(我以上帝的名义发了伪誓,应该也算神圣吧)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与魔鬼做了交易。我为什么要跟他们一块玩?为什么听克罗默的更甚于父亲?为什么要编故事来炫耀?这下好了,让那个浑蛋抓住了把柄。
眼下,我没时间考虑明天会发生什么。我所担忧的是,从今天开始,我将一步步坠入黑暗。我可以预料麻烦将会接踵而至,我需要编织一个个谎言,将实情隐藏在内心深处。
在看到父亲的礼帽时,我心里忽然产生了一丝希望。我可以向父亲坦白、向他忏悔来寻求救赎,他怎么惩罚我都行。类似的忏悔我早已熟门熟路,只要下决心低下头,便可获得宽恕。
一想到这,我便蠢蠢欲动!但这次我估计忏悔起不了作用。我必须保守秘密,独自承担一切后果。我似乎站在了一个岔路口上,迈出这一步便意味着我将转入邪恶阵营,依赖他们、遵从他们并最终变成他们的一员。谁让我瞎吹嘘呢,现在必须承担后果了。
一见到我,父亲最先问的是我怎么把鞋弄脏了。鞋子成功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这让我舒了一口气。我甘心接受责备,以免暴露了什么,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此时,我心里竟然产生了一种奇妙又新鲜的感觉,令我变得无比兴奋:我面对父亲居然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他的无知让我心生鄙视,居然只是责备我弄脏了鞋子。
我站在那,心想:“你知道什么!”就像一个杀人犯仅被指控偷了一片面包。虽然这个念头十分无理,但如此强烈,怎么也挥之不去。我决定隐藏这个秘密。克罗默或许已经去警局揭发我了,暴风雨正压顶而来,而他还是将我当个小孩子。
在我的经历中,这个时刻尤为重要。父亲的光辉形象首次出现了瑕疵,我们之间也首次出现了裂痕。个体要实现自我成长,必须打破父亲的笼罩。我们的命运深处交织着一系列这种无形的经历。这些裂痕会重新得到弥补,通常会被人遗忘,但仍存在于内心最隐秘的角落。
这一想法让我感到十分恐慌,我几乎要跪下寻求宽恕。但即使我这样的小孩子也知道,有些原则性问题难以获得谅解。
我觉得我应该先想想明天该怎么办,却始终没抽出时间。整个晚上,我脑袋里一片混乱。自由的生活正在渐行渐远,我正被拖入另一个阴暗而又陌生的世界。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味道,有些苦,或许是因为死亡意味着新生以及对重新开始的恐惧。
之前,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晚祷,但那天晚上,晚祷对我来说却成了一种折磨。直到躺在床上,我才放松了下来。我无法加入其中,每个音符都在折磨着我。当听到父亲说“上帝与我们同在”,我感觉有某种力量将我与他们隔了开来。上帝将继续施与他们恩宠,而我却再也享受不到。我浑身发冷,耗尽力气逃离了他们。
在床上躺了一会,我才重又感觉到了温暖与安全,但担惊受怕又变成了迷茫,令我十分不安。
母亲像往常一样,过来跟我说了声晚安。我听着她的脚步声在隔壁的房间中响起,门缝中还透着烛光。我想,她肯定察觉到了什么,她肯定会再过来亲亲我问我发生了什么,那么我想我会哭出来,抱住她,这样一切都会解决,我也会得到救赎!直到门缝中的烛光暗了下去,我仍竖起耳朵听着,并坚信她会过来。
不一会,我又想起来即将面临的困境。我能清晰地记得克罗默的面目,一只眼睛眯着,嘴角露出残酷的微笑。盯着盯着,他变得越来越大,面目也越来越丑恶,那只眼睛中透着残忍的目光。直到睡着,我也未能将他的形象从脑海中剔除。但我没有梦到他,也没有梦到白天发生的事。相反,我梦到了父母还有姐姐,我们一家人在船上享受假日的安宁。深夜,我醒了一次,尤能回味梦中的幸福,甚至能看到姐姐的裙子在阳光下闪着光芒。当我意识到那只是个梦时,我又想起了克罗默那凶恶的眼神。
次日清晨,母亲急匆匆打开门,埋怨我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起床。我脸色很差,她问我哪里不舒服时,我一下子吐了出来。
这让我有一丝庆幸,庆幸生病了。这样我就可以继续躺在床上,边喝着菊花茶,边听着母亲在另一个房间中忙碌,同时还可以听到女仆在门廊处讨价还价地买肉。不用去学校的清晨仿若童话般美妙,我可以享受着难得的阳光,因为在学校中,我们通常会拉着窗帘。但这仍让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接下来会有不妙的事情发生。
还不如死了算了!但这次和往常一样,只是稍微有些不舒服,死是死不了的。这让我能逃过上学,但逃不过弗朗兹·克罗默,十一点左右,他会在市集处等我。母亲的关心不仅无法让我感到安慰,反而令我不耐烦。我假装又睡着了,好专心思考下该怎么做,但什么办法都没想到,我必须按时出现在市集。十点到了,我悄悄穿上衣服,告诉母亲我好多了。她的回应像往常一样,要么再休息会,要么下午去上学。我说我打算去上学。我得有个计划。
一分钱没弄到就去见克罗默,这肯定不行。我得把存钱罐弄出来。虽然我知道里面的钱肯定不够,但有总比没有好,起码能暂时让克罗默满意。
我仅穿着长筒袜,偷偷钻进母亲的房间,将存钱罐从梳妆台上拿了下来。我很纠结,但相比昨天却轻得多。我心跳加速,几乎让我窒息。下楼后,我发现情况不妙,存钱罐被锁住了。打开它其实很简单,只需要用力扯断那片薄薄的锡网。但那断口却刺痛着我的心,我这次真的偷东西了。在那之前,我至多偷吃点糖和水果。这一次,性质就严重多了,尽管拿的是我自己的钱。我觉得自己又朝克罗默的世界迈了一步,一点一点走向堕落。事已至此,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提心吊胆地数了数,虽然晃一晃听起来很多,但实际上却寥寥无几,只有六十五芬尼。我藏好存钱罐后,攥着这些钱出了门。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我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我似乎听到楼上有人喊我,但我装作没听到,迅速跑开了。
到十一点还早,我特意绕了路,钻进一条条小巷,连同头顶上的积云,都是我前所未见的。我走过一栋栋房屋,甚至觉得里面的主人投来怀疑的目光。我忽然想到,有一位同学曾在牲畜市场捡到一枚泰勒[5]。于是,我祈求上帝给予我奇迹,让我也捡到一枚。但我已经丧失了祈求的资格,况且存钱罐也修不好了。
弗朗兹·克罗默打老远就发现了我,不慌不忙地走来,装作不认识我。走近了后,他示意我跟上,然后径直朝前走,穿过巷子和小桥,最后在郊外的一栋新盖的房屋前停下了脚步。没有人在施工,围墙尚未粉刷,门窗也还没有安上。克罗默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走了进去,而我默默地跟上他。他站在一堵墙后,朝我伸出了一只手。
“钱带了吗?”他冷冷地道。
我从口袋中掏出那只手,将攥着的钱放入他的手心。还没等到最后一芬尼落下,他已经数完了。
“只有六十五芬尼。”他盯着我。
“嗯,”我紧张地说,“我只有这么多。我知道不够,但再多我没有了。”
“我还以为你比他们聪明一些,”他不紧不慢地说,“你们那类人不都按规矩办事吗。我只要两马克,这点钱你还是拿回去吧。听明白了吗,拿着滚蛋。我去找另一个人,哦,你知道是谁,我想我可以从他那里拿到两马克。”
“但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我的存钱罐里就这些。”
“那是你的事。我也不想过于逼迫你。你现在欠我一马克三十五芬尼,什么时候能给我?”
“我一定会补上的,克罗默。虽然不确定什么时候,但明天或后天,我应该能凑出来。你知道,我绝对不能让我爸爸知道。”
“这我就不管了。我并不想逼迫你。你明白,我很穷,而只要我想,我可以在午饭前拿到那两马克。你的衣服这么贵,食物也丰盛得多。但我不会去告发你,我可以再等一等。后天我会吹口哨提示你,你听过我吹口哨吧?”
他吹了一下,我之前听到过。
“嗯,”我说,“我能听出来。”
他走了,就像没见到过我。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易。
我十分清楚,今天过后,如果突然听到他的口哨声,我一定会吓一大跳。现在,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他的口哨声。那声音简直无孔不入,不论我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都挥之不去。口哨让我成了他的奴隶,这已经注定。我这几天有时会钻进小花园里,享受绚烂的秋日午后时光。我会假装仍然是那个善良、自由、天真的男孩。而每当克罗默的口哨声响起,都会让我心惊,打破我的幻想。我便不得不走出花园,跟着他,告诉他我又得到了多少钱,然后悉数交给他。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周,但对我来说却像是好几年,没完没了。我几乎没有机会弄到钱,最多也就是在莉娜买菜回来后,从厨房里偷拿五芬尼或十芬尼。克罗默每次都责骂我,且越来越难听。比如,他说我一直在骗他,侵犯了他的利益,欠他的钱,让他苦不堪言!我长这么大也没受过这种委屈,从来没像这样感到无助。
我在存钱罐里装上玩具钱币,并将它放回了原处。没有人发现不妥,但我却日夜担心不已。每当母亲朝我走来,我都会想她是不是来问存钱罐的事,这甚至比克罗默的口哨声更令我恐惧。
有几次我两手空空地去见克罗默,他便换着法子折磨我、利用我,而我不得不按他说的办。他父亲会给他安排各种各样的差事,而他又会安排我去做。有时他会命令我单腿跳十分钟,或者向路人身上贴纸屑。在许多个夜晚,我都会梦到这些折磨,并会出一身汗然后惊醒。
有几天我确实病了,呕吐不止且全身打寒战,晚上又会发烧出汗。母亲十分细心地照顾我,但这更让我良心不安,因为我欺骗了她。
有一天晚上,我躺下后,她拿着一块巧克力给我吃。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时光,那时我还很乖巧,每天临睡前我都能够吃到一块巧克力。而这次,我心痛到直摇头。她边问我怎么了,边捋了捋我的头发。我只是不断地说:“不!不要!我不吃!”于是她放下巧克力便离开了。次日清晨,她问我昨天那是怎么了,我假装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她请过一位医生来给我诊治,建议我每天早上洗冷水澡。
那些日子几乎让我抓狂。在有序、祥和的家中,我却痛苦挣扎着,仿若一个幽灵。我表现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时不时会发呆。父亲经常埋怨我,问我到底怎么了,而我却只是沉默不语。
注释:
[1]富裕的上层阶级奉行精英教育,一般安排孩子就读昂贵的私立学校,而普通阶级的孩子通常只能就读公立学校。
[2]德国货币单位。
[3]即静谧、安全的第一世界。
[4]德国辅币单位,一马克的百分之一。
[5]德国的旧银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