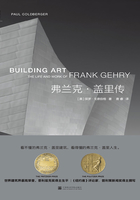
第4章 超级月亮之夜
2011年3月19日的晚上,曼哈顿下城尚未完工的一座七十二层公寓的顶楼豪华套间里,纽约地产商布鲁斯·拉特纳(Bruce Ratner)为了庆祝他这座新地产项目的开幕,正在举办一场派对。对于一场庆祝新项目竣工的派对来说,它的嘉宾名单显得有些非同寻常——歌手、社会活动家Bono[1],艺术家查克·克劳斯(Chuck Close)、克莱斯·奥登伯格[2],演员本·戈扎那(Ben Gazzara)、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著名艺术品经销商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布鲁克林音乐学院(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的老院长哈维·李奇登斯坦(Harvey Lichtenstein),酒店业巨头伊恩·施拉格(Ian Schrager),以及著名记者如莫利·塞弗(Morley Safer)、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等各界名流都赫然在列。举办派对的这座公寓通体被不锈钢板包裹,落成之后,它将成为整个纽约最高的一座住宅。长久以来,关于这座公寓内部套房样式的猜想已经成为纽约街谈巷议的话题。但是,当晚前来这座钢构巨塔的名流们,目的却并不在于对这幢建筑先睹为快,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都不是布鲁斯·拉特纳的朋友。这些名流和其他三百多位普通来宾,都是为了一位身材矮壮,戴着眼镜的银发老者而来。在整场派对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身着黑色T恤衫,外罩黑色西装的老人都站在公寓北侧的窗前,窗外便是曼哈顿壮观的天际线和布鲁克林大桥高耸的两座桥塔。他就是这幢公寓的设计者,当今世上无可争辩的最著名建筑师。
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两个半星期前刚刚度过了他八十二岁的生日,这场派对也是布鲁斯·拉特纳为他举办的生日派对。建筑师的生日派对,拉特纳觉得这是对公寓落成最好的庆祝。同时,举办这次派对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淡忘他与盖里之间的不愉快:就在二十一个月前,他在另一个更大规模的项目“大西洋场”(Atlantic Yards)的规划和建筑单体设计中解雇了盖里。“大西洋场”是拉特纳的森林城集团(Forest City Ratner)投资开发的一个巨型地产项目,计划在位于布鲁克林中心城区的铁路站场原址上完成十七座建筑,其中包括刚刚从新泽西搬到布鲁克林的篮网队(Nets)的新主场。当时,盖里已经完成了项目的总平面、球场以及区域内几座摩天大楼的方案设计,他的参与使得“大西洋场”较之一般的大型商业地产项目显得更为野心勃勃。然而,在使用盖里的总平面为项目获得了前期许可之后,拉特纳却突然用另一家设计机构提供的更简单而经济的设计方案替换了盖里的方案——他炒掉了盖里。盖里对这一决定深感震惊与愤怒,这一变故使得他位于洛杉矶的事务所陷入困境,不得不裁掉了许多在这个项目上工作的建筑师。而让盖里尤为郁闷的是,他还只能在私底下表露自己的不爽。因为此时他仍在继续参与拉特纳在曼哈顿下城的公寓楼项目,这使得他很难和拉特纳公开翻脸。事实上,盖里是那种当事情进展得不如意时,无论自己如何愤怒都很少外露的人。因为他不喜欢冲突,通常情况下他总能通过友善而和气的方式使事情得到解决,而非扮演一个暴躁的艺术家。
盖里的这种处事之道正合拉特纳之意。作为地产商,比起炒掉弗兰克·盖里,他显然更加愿意因向盖里提供了设计纽约最高公寓大楼的机会而被人们记住。在大西洋场项目上解雇了盖里之后,他极尽所能地想用后一种方式把他的名字与盖里联系起来。在他的销售顾问的建议下,拉特纳将曼哈顿下城的公寓项目称为了“盖里的纽约”(New York by Gehry),将弗兰克·盖里的名字也变成了公寓的卖点之一——因为盖里的声望如此之高,他的名字便和开阔的景观,宽敞的衣帽间,漂亮的厨房,宽大的窗户,甚至是房地产开发的终极要素——地段一起,成了这座公寓的绝佳卖点。在纽约,之前从未有过一座由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公寓大楼。事实上,在此之前,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里也找不到一座盖里设计的摩天大楼。一直以来,盖里都是以设计博物馆、音乐厅、小住宅、教育建筑,以及小型商业建筑而知名。他位于洛杉矶的事务所虽然规模颇大——在生日派对那会儿大概有150名雇员,但并不是那种批量生产高层办公楼的事务所。相对而言,他的事务所更像是一个巨型的艺术家工作室,一个以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中心的大型作坊。在完成纽约公寓之前的职业生涯里,盖里的两个代表作: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1997年完成)和洛杉矶的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Walt Disney Concert Hall)(2003年完成),均可跻身于上一时代最杰出建筑作品之列。2010年,《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邀请了90位世界顶尖的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提名“1980年以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五座建筑”,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毫无悬念地以压倒性优势成为赢家,它得到的票数是其他任何建筑的三倍以上。“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3]《名利场》杂志断言,“现年81岁,出生于加拿大的盖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一位建筑师。”
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正式落成的几个月之前,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曾参观了这座建筑。螺旋形的结构、钛合金包裹的表面,都使得博物馆的外形充满视觉张力。约翰逊直言,这座建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盖里创造了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式——灵动、粗野,又具有巴洛克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除了“现代”,人们找不到更为合适的词汇来定义这种非同寻常的建筑形式,但是这种“现代”又断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现代主义”风格——冰冷的玻璃方盒子。
盖里很喜欢用纸来做工作模型,随着折叠、挤压而揉皱的纸的形态,常常成为他设计的起点,他由此获得灵感,进而从中深化和发展出他想要的建筑造型。因为这种工作方式,很多人认为他的设计是偶然而随意的。当然这是一种误读,与五十年前人们对于弗兰兹·克莱恩(Franz Kline)和杰克逊·波拉克(Jackson Pollock)的绘画艺术的误读十分类似。盖里的建筑作品与波拉克的“滴画法”(drip paintings)一样,也是一种偶然性的创造,因此他们的作品也都具有一种相类似的怪诞、新奇、热烈而充满活力的美。
事实上,你也可以参照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对于克莱恩、波拉克以及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等人的经典概括——“行动派画家”(action painters),[4]来把盖里的建筑作品视为是某种“行动派建筑”(action architecture)的代表。然而,虽然盖里的建筑通常也能给人带来同样的动态感受,但无论是其建筑作品的实现过程还是方式,都与行动派绘画全然不同。罗森伯格所提出的“行动绘画”一词,是为了描述绘画过程中画家本人与画布本身的一种激烈的互动方式。而建筑不同于绘画,建筑作品不仅仅需要引发感官体验,同时也必须满足实际的日常使用功能。此外,建筑作品的完成过程也完全不像绘画那样自由:每一个节点和细部都需要事先进行深入而精确的设计,不能异想天开。为了保证设计的可行性与建筑结构的可靠性,与工程师的密切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建筑创作来说,想象力是必须的,但仅有想象力还远远不够,因为天马行空的想象终须落到实处,建筑的形态不能仅仅停留在想象之中,必须是能够被建造出来的。[5] 20世纪50年代,伟大的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t)画家们创作了大量影响深远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现代主义绘画。但相比之下,同时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却并无太多突破,仍旧停留在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在探讨的那些主题之上。在20世纪50年代,一座钢结构的玻璃房子,可能看上去比一座木板墙面的科德角式小住宅(Cape Cod cottage)要先进、前卫许多,但是要论颠覆性的创新,比起房中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德·库宁的画作(如果房主幸运的话),这座玻璃房子可要逊色不少。建造技术和工艺上的种种限制,使得建筑界的新思潮很少能像艺术界一样迅速地产出成果。画家进行创作,只需要在画布上刷刷点点,而建筑师若想将一个复杂形态的流动的空间付诸现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尽管工程师们从未停止追赶时代步伐的努力,但若和当时画家们的作品比起来,即便是可以称之为挑战当时的结构工程极限的作品——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设计的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TWA航站楼(1962年)——看起来也几乎是平淡无奇,无甚亮点。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如弗雷德里克·基斯勒(Frederick Kiesler)等,也曾做出过许多更为大胆的设计,但那都只不过是停留在想象中和纸面上的空中楼阁,根本建不出来。
在艺术界浸淫多年,深受艺术界影响的盖里,是第一批意识到可以利用数字技术的手段追赶艺术家们创作脚步的建筑师之一。虽然他自己并不喜欢操作电脑,但他仍以自己身为一个技术上的创新者,以及前所未见的建筑形式的创造者而自豪。他发现,在建筑师事务所中应用数字技术,除了能使绘图变得更加方便以外,还可以引发更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使得许多从前断然无法建造的极端复杂的建筑造型获得了结构设计与建造的可能性。他意识到,头脑中能够想象出的所有建筑形式,几乎可以通过电脑实现工程设计。这将使建筑师的想象力获得彻底解放。
盖里和他事务所的同事们使用一种原本应用于航空航天工业的先进数字设计软件进行工作,并有针对性地对软件进行了改良,使其能够更适用于建筑设计。这款软件也成为设计类似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这种形态的项目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可以说它就是联系盖里的想象力与实际建成的建筑之间的桥梁。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并不是数字化设计革命的浪潮所孕育出的第一座建筑,但它绝对是这波浪潮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引起公众轰动的建筑,也是第一个向世人清晰展现了这场由计算机引领的建筑设计革命的建筑。借助新技术,盖里得以创造出这种全新的建筑形式——一种沙里宁在几十年前的技术水平下苦苦追寻而不得的建筑形式。
作为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第一个能够在很长时期里对大众文化产生持续影响的作品。由盖里所塑造的大胆的建筑造型,其影响力从建筑界延伸至了整个大众文化领域。在建筑业界,这座建筑是现代以来少数的几个为建筑评论家和史学家所公认的严肃而重要的新建筑作品之一,与此同时,尤为可贵的是,它还能够被公众广泛接受。考虑到公众对于建筑的欣赏水平通常还停留在类似于古典主义的市政大楼或者红砖砌筑的乔治亚式小住宅(Georgian houses)如此这般的建筑上,并且他们通常对任何能跟“前卫”沾点边的东西嗤之以鼻,这座建筑在公众中的大受欢迎,实际上标志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进步。若和其他的艺术领域类比来说,就好比严肃文学的代表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小说竟能比流行作家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的小说更畅销,或者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这样的音乐家竟然在排行榜上击败了流行歌手Lady Gaga。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进步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上,许多平日里对现代建筑不怎么感冒的人慕名而来,流连其中,讲述着他们有多爱这座建筑。这不禁令人想起位于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另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馆。1959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为那座博物馆所设计的螺旋形结构,也曾在公众中引发热烈的轰动和追捧。而自那以来,盖里的这座建筑恐怕还是第一个能够打破建筑与大众文化的边界,令公众如此兴奋的建筑作品。
当然,对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来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仅仅是它众多的地标之一。然而对于毕尔巴鄂,这样一个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Basque)的旧工业城市来说,这样一座建筑所能引发的效应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凭借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巨大吸引力,毕尔巴鄂迅速转型成为了一座火爆的旅游城市。这座建筑不仅仅是艺术与建筑发烧友们的朝圣之地,每天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游客被吸引前来参观游览,源源不断的游客赋予了毕尔巴鄂这座老城以新的活力。一座建筑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推动了整座城市的变革和复兴,人们开始把这种力量称之为——“毕尔巴鄂效应”(the Bilbao effect)。
* * *
多年来,盖里在建筑领域一直为人所熟知,但他真正名声远播,还是要归功于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博物馆于1997年正式落成之后,盖里的声望急剧上升,迅速蹿红成为一个大明星,也成了继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之后最知名的美国建筑师。两个弗兰克(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弗兰克·盖里),为同一个机构,设计出了同样极具开创性,又深受大众喜爱的两座博物馆建筑。二者之间虽然相隔四十年,人们仍不免对他们两人进行对比。然而事实上,虽然他们有着同一个名字,对建筑同样热情投入,同样天赋异禀,能够做出颠覆性的设计,但就像他们风格迥异的设计一样,两人的个性也截然不同。赖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个独裁者,政治上非常保守并且自恋。他绝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的身边有着一群教徒一般忠实于他的崇拜者。赖特的处世态度仿佛是——如果你不喜欢他的建筑,那一定是因为你不懂得欣赏伟大的设计。
盖里则往往显得不那么自信。他渴望人们对他的喜爱和接受,他希望他的建筑能够让人喜欢和满意。有的时候他似乎把别人对于他作品的认可,和对于他本人人格的认可画了等号,视为是同一回事。“对于弗兰克来说,通过认同他的建筑,使他感受到被需要和被爱,是非常重要的,”[6]盖里的老朋友巴布斯·汤普森(Babs Thompson)说,如果你不喜欢他的作品,“那你就是不理解他,不接受他这个人。”
不过,虽然盖里的生活一直被这种焦虑所困扰,他的举止却总是表现得轻松而友善。与赖特的锋芒毕露不同,他把自己钢铁般坚定的意志隐藏在一种随和的外表之下,盖里的老朋友,艺术家彼得·亚历山大(Peter Alexander)称之为“盖里独有的温和而谦逊的处事方式”[7]。赖特从没有被误认为谦逊过,而盖里却经常如此。
* * *
两人如此迥异的性格的成因,可以从成长背景中管窥一二。盖里,原名弗兰克·戈德堡(Frank Goldberg,典型犹太姓),看姓氏便知是个犹太人;赖特则来自一个殷实的威尔士裔家庭。盖里在多伦多(Toronto)和安大略省的矿业小城蒂明斯(Timmins,Ontario)长大,在他的青少年时代,社会上弥漫着反犹太主义,这使得他在内心之中,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外来者——在当时还是一个拮据的外来者。而赖特则成长于19世纪末的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Madison,Wisconsin)和斯普林格林(Spring Green,Wisconsin)乡村,生活在他母亲的家族庄园里。虽然并不能算是出身大富大贵,但这样的童年也给了他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他来自一个庞大且关系紧密的家族,家训是“以真理对抗世界”(Truth Against the World)——盖里绝对会认为这句话极端的矫揉造作且十分自负。赖特信仰土地以及一切土地的象征物。他把他著名的自宅——塔里埃森(Taliesin),建在了斯普林格林他家族的土地上。盖里从小居住在城市里的狭小公寓和城区住宅中,当他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建筑师,像赖特一样,要为自己设计一栋自宅时,他选择了改造加州圣莫尼卡(Santa Monica,California)市郊一个街角处的一栋普通小住宅——离所谓的“祖产”远远的。
但是,盖里与赖特确实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他们的父亲事业都很不成功,以至于父亲这个角色,在经济上,乃至于情感上,对他们的家庭都缺乏支持。但他们又都有着坚强的母亲,是母亲给予了他们父亲身上所缺乏的专注力,并且引导他们接触了艺术、音乐和文学。赖特的父母在他18岁的时候离了婚,他的父亲威廉·赖特(William Wright)此后便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盖里的父亲,欧文·戈德堡(Irving Goldberg),倒是一直没有离开儿子的生活,直到1962年他61岁时死去。不过对于盖里来说,父亲一直是他悲哀和挫折的缘起。尽管盖里努力地想要找到以父亲为荣的理由,因为父亲一直是他渴望去崇拜、敬仰的对象,却经常归于徒劳。欧文有一点设计方面的手艺,他喜欢用木料来制作一些小物件,还曾因为一个橱窗的设计得过奖。但是他几乎所有的商业尝试都失败了,而且,糟糕的健康状况使得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当中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废人。老戈德堡的一生不断地经历着各种挫折和失败,以至于他自己都觉得人生就是在不停地错失机遇中度过的。这使他成为了一个难以相处的,喜怒无常的人,他与儿子的关系中也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和痛苦。他往往习惯性地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亲人身上;不过可贵的一点是,无论他的境遇多么的艰难,他都始终坚守着他的左派自由主义政治信仰。欧文相信世界上总会有比他更困难的人,他认为这些人需要得到帮助。所以,他最终所能留给儿子的遗产,并不是设计方面的一点天赋,而是一种对于包容和社会公正的信念,以及对于社会底层的同情心。
欧文糟糕的健康状况,还意外地为他的儿子提供了另外一笔财富。在1947年的一次心脏病发作后,欧文被医生告知,他的身体状况可能无法再承受多伦多的寒冬了。因此为了逃离严寒,欧文举家搬到了洛杉矶,他18岁的儿子弗兰克便也随之来到了这座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他将度过他的一生,他将作为一名建筑师与这座城市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同克里斯托弗·列恩(Christopher Wren)之于伦敦,抑或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之于纽约一样。盖里的天性似乎更倾向于艺术家,而非建筑师。因此,在他的早年岁月里,他更多的是和洛杉矶的艺术家圈子混在一起,而不是和他的建筑师同行们。这座城市中有着一群充满才华的艺术家,他们选择在洛杉矶生活和创作,远离艺术世界的中心——纽约,这种远离主流的态度与盖里这个艺术圈“局外人”的感受相契合。同这些艺术家在一起时,盖里便成了一个双重的“局外人”——一个混迹于远离纽约的非主流艺术圈子里的非艺术家。
他并不喜欢以艺术家或者雕塑家自居,据他在一次采访中说,一部分原因是“当你将‘艺术’这个词用在一座里面有厕所的建筑上时,有一些艺术家会感到被冒犯”。[8]在更早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是否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他坚定地回答称:“不,我是个建筑师。”这句话后来也几乎成为了他的口头禅。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他确实比大多数建筑师更热衷于创作那种具有高度艺术表现力的建筑,而自从毕尔巴鄂的博物馆落成以后,他的建筑设计也被很多评论认为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造型艺术。尽管有贴标签之嫌,但是盖里的老朋友之一,洛杉矶艺术家托尼·伯兰特(Tony Berlant)仍然说:“我认为弗兰克是全洛杉矶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另一位洛杉矶艺术家比利·阿尔·本斯顿(Billy Al Bengston)则说的更为绝对:“我觉得弗兰克是当今世界上顶级的艺术家。”[9]
* * *
如果说公众对于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欢迎和喜爱给盖里带来了什么挑战的话,那就是如何避免让这座建筑成为盖里建筑创作的“标签”了。对盖里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他要继续像之前一样,充满创造力地进行建筑设计,同时也意味着他要放弃掉许多机会,那些可以把他的著名作品“模式化生产”,让他可以到处复制的机会。“成功往往比失败更难应付。”[10]盖里如是说。在毕尔巴鄂之后,他在其他一些作品上沿用了他那抒情的曲面金属、玻璃或石材造型,因此有的人会认为无论这些新作在造型上多么引人注目,它们都只不过是盖里对自己以往手法的重复而已。听到这类的评论,盖里会觉得非常失落。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对他的误解:那些觉得他之后的作品只是在延续毕尔巴鄂的设计的人,并没有认识到,他所真正致力于创造的,是一种全新的建筑语言,而他在每一座新建筑上运用这种建筑语言进行表达的方式,事实上都有着微妙的不同。
建筑师和批评家大多认同上述评价,而且,盖里在媒体上的形象总体上来说也还不错,至少比他同一时期的其他建筑师都要好。不过,名誉总会有两面性,盖里的盛名也使得一个并不贴切却十分尖锐的词汇——“明星建筑师”(starchitect)被频繁地用作他的称谓。这个词轻巧地把严肃的设计追求与明星的光环混为一谈,所以也难怪盖里会痛恨这个称号。在公众看来,他可能是一个典型的明星建筑师,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称号则完全歪曲了他的创作,好像是在暗示他的建筑除了惹眼而浮夸的造型之外便没有其他的内涵。尽管他曾公开表示不喜欢被人贴上“明星”的标签,他对声名本身却是并不反感的。事实上,他的一些举动甚至看上去像是在刻意地博取名声。他允许他的形象以被讥讽的方式出现在电视剧《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的一集中;他还接受了蒂芙尼公司(Tiffany&Co.)的邀请,为他们设计珠宝首饰和其他产品。他还设计过一款伏特加酒瓶,几款手表,并曾受他最喜欢的运动——冰球的启发而设计过一组家具(从少年时代在加拿大,一直到他七十多岁,他始终坚持打冰球)。此外,在洛杉矶生活了六十多年的盖里,还比一般的建筑师更为懂得如何同娱乐圈的人士合作。他允许他的朋友,导演西德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带着一名摄像师用几个月的时间对他进行跟拍,并制作了一部关于他的充满敬意的纪录片。波拉克把这部纪录片定名为《建筑大师盖里速写》(Sketches of Frank Gehry)。
虽然盖里可能是个典型的“明星建筑师”,但他很擅长于掩饰他“明星”的那一面。2014年,他在伦敦完成的第一个项目落成揭幕——位于巴特西发电站(Battersea Power Station)原址的一座住宅和零售综合体,英国的《建筑师杂志》(Architects’ Journal)借此对他进行了一次视频采访。当被问到为何之前从来没有在伦敦设计过任何项目时,盖里的回答轻描淡写,“没人来找过我。”他说道。他的这种回答让采访者很失望,估计采访者本来还指望着他会借机抱怨伦敦严格的建筑审批流程——在伦敦,想要获得这种大型建筑的建造许可是非常困难的,即便以盖里的盛名亦是如此。相反,他的回答似乎是在表示他会很乐意在伦敦做任何设计,即便是一个小项目也可以,他只是一直在等待着一通邀请的电话。他说,他的事务所里缺少一个负责去四处推销他的市场部门。在这段采访视频中,他看起来十分和蔼可亲,就好像他只是一个勉力维持的小工作室的主创,而不是领导着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事务所的,野心勃勃的明星建筑师。
这是盖里的一种经典的伪装——反明星的建筑师,盖里的公众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与伍迪·艾伦的结合体。事实上,尽管他经常抱怨项目不足,但在接受《建筑师杂志》采访那会儿,他事务所中正在进行的大大小小项目多得数不清。他还经常拒绝客户,一些客户的项目引不起他的兴趣;还有一些客户,在他看来,对他的设计缺乏足够的热诚。虽然他颇为自得于自己灵活的处事方式,但是他只愿意为那些事先明确表示认同他的作品,并且希望得到一个盖里式设计的客户付出时间。当然,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座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式的优雅的白色建筑,或者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式的玻璃幕墙塔楼,抑或是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所设计的那种古典的建筑,那其实你也没有理由来请盖里设计。因此,盖里在筛选客户这方面,也部分地取决于客户的这种自主选择,他与那些认同他的设计,并且愿意任由他以自己的想法进行设计的客户合作起来才是最愉快的。
在盖里职业生涯的早期,他的那些老客户们显得和他一样特立独行: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自洛杉矶和纽约的艺术圈,都热衷于拓展建筑设计的边界,尝试更多的可能性。盖里早期的客户们基本上预算都比较紧张,因此当时的盖里以喜欢使用廉价的日常建材而闻名,如不上漆的胶合板、金属护栏和瓦楞铝板等,这种建筑语言也成为盖里职业生涯初期的标志。那时他也已经有了一些固定的公司客户,大多数规模都比较小,只有一个例外——劳斯公司(the Rouse Company),一家主要做购物中心的开发商,盖里曾为他们设计过一座总部办公楼,以及几座其他的建筑,其中包括盖里唯一的一座购物中心——圣莫尼卡广场(Santa Monica Place)。但是到了1980年,盖里和劳斯公司“和平分手”了,分手并不是因为盖里不愿意继续为劳斯公司设计他们想要的那种更为常规的建筑,更多是因为,无论盖里还是劳斯公司,当时都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盖里事业的发展方向并不在于常规的、传统的建筑设计。“弗兰克,为什么你把你的时间都浪费在了和开发商虚与委蛇之上呢?你的人生有着更重要的使命。”[11]在参观了其时刚刚落成的位于圣莫尼卡的盖里自宅后,马特·德维托(Matt Devito),劳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盖里说道,“为什么你不去做你最擅长做的那种设计?”
盖里确实那样去做了。如德维托所说,盖里所“擅长”的,是设计那种既能引人思考,同时又能够带给人愉悦的建筑,他的设计总是足够与众不同,一些人把它们当作是艺术品,而还有一些人则只觉得他的设计尽是些“奇奇怪怪的建筑”。譬如他在圣莫尼卡的自宅,原本只是一座普通而老旧的荷兰殖民地式住宅(Dutch colonial),盖里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在立面上添建了许多不规则四边形的胶合板和瓦楞金属板。改造后的这座自宅就冒犯到了他的一部分邻居,他们想要把这些乱糟糟的裸露的建材统统拆掉,因为他们觉得这座建筑是对他们那宁静的市郊街区的侮辱。在此后的日子里,盖里的声誉逐渐提升,他开始被委托设计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和教育建筑等公共建筑。与此同时,一些既有钱又大胆的客户开始委托给他一些私人住宅项目,比如保险业的亿万富翁彼得·刘易斯(Peter Lewis),就曾前后用去六年时间,支付了总共超过六百万美元的设计费,请盖里为他的一座总预算为八千二百万美元的豪宅做了许多不同版的设计,不过最终刘易斯选择了放弃这个项目。
随着盖里的愈加成功,他的客户群体也变得越来越有钱,来找他的客户预算都更为宽裕,他们开始期望使用更为奢侈的建筑材料。于是,盖里早期招牌式的胶合板逐渐被炫目的新材料——钛合金板所取代。不过,虽然他的设计逐渐走起了“高端路线”,盖里自身的那种对于社会的敏感和关怀却从未改变——至少他自己希望如此。他的那些大规模的项目,对他而言,一方面是他作为建筑师的骄傲,另一方面也寄托着他对社会的忧思。早期,他以胶合板和金属护栏网扬名于严肃建筑界,一路走来,他渐渐地成为了昂贵设计的代名词,这种转变实际上给他造成了一种长久以来无法完全摆脱的不适应感。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俨然成为了一个“高端定制”建筑师。为那些富有的客户们设计一些造价不菲的高端建筑,已经成了他那时最主要的项目来源。“本质上讲,我是个犹太人,一个左派自由主义者,一个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主义者。[12]所以对我来说,为有钱人设计小住宅这种工作,并不解决社会问题,也根本不具备任何社会效益。”1995年他接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采访时说。
但是,他也并不想让人们对他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古根海姆或者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等几个具有高度表现力的建筑上,尽管他深知这几个作品被认为是他的巅峰之作。有人指责他从来不做穷人买得起的经济住房,他对此非常愤怒,因为他心底里其实从未放弃过年少时的信仰,他坚信建筑会以某种方式造福于社会。只是,任何一个建筑师,即便是弗兰克·盖里,如果没有客户的需求,也建不出任何东西。因此,盖里常常通过义务地为一些慈善性的小项目提供设计服务,来表现他“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的一面。例如,为了纪念他的老朋友,因乳腺癌去世的麦吉·凯斯韦克(Maggie Keswick),他在苏格兰的邓迪(Dundee)和香港各设计了一座癌症治疗中心。还有后来他在柏林为他的朋友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做的一个小音乐厅,他对待这个袖珍的小音乐厅就像对待一个五十层高的建筑一样殚精竭虑。他还设立了一个机构,专门资助加州公立学校的艺术教育,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亲自认命的。此外,他还深入地参与了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主要是通过他的朋友,精神病学专家米尔顿·韦克斯勒(Milton Wexler)的基金会。韦克斯勒的家庭长久以来一直遭受着亨廷顿氏舞蹈病(Huntington's disease)的折磨,为此他建立了这个基金会,以专门资助遗传病学方面的研究。盖里和妻子贝尔塔(Berta)一直把这个基金会当成他们自己的事业来做。自从盖里的女儿莱斯利(Leslie)——他最年长的孩子,在2007年死于子宫癌以后,医学研究就成为了他们夫妇关注的重点。
然而,无论多么的真诚投入,慈善事业终究不是建筑。他有点怀念他生涯早期的那些粗野而低成本的项目了。于是,他开始寻找一种更经济的手段,来实现他所钟爱的那种富有表现力的建筑形式,以使那些预算有限的客户也能够接受。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数字技术上。在通过毕尔巴鄂和迪士尼音乐厅向世界展示了数字技术所能够创造的非凡的、独一无二的建筑造型之后,盖里开始觉得数字技术也一定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帮助他把常规的建筑设计得更有吸引力。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通过计算机辅助造型来实现那些曾经需要手工塑造的异形的建筑形态,那么,那种曾经超出一般商业地产开发商承受能力的、定制化的建筑,也应该能通过计算机辅助的方式更为经济地实现。计算机不仅仅是用来快速复制廉价产品的工具,它完全能够辅助建筑师做出独一无二的设计,盖里越来越热衷于证明这一点。数字技术对于他设计的意义,就如同早期作品中的胶合板和金属护栏网:让他得以在正常的预算下,做出非凡的建筑。
于是,盖里开始为娱乐和互联网大亨巴里·迪勒(Barry Diller)这样的客户工作。迪勒当时正与地产开发商马绍尔·罗斯(Marshall Rose)、亚当·弗拉托(Adam Flatto)和约瑟夫·罗斯(Joseph Rose)合作,准备在曼哈顿的切尔西区(Chelsea)为迪勒的公司IAC开发一处新的总部。起初,迪勒对于选择盖里作为建筑师非常谨慎,他担心盖里会在设计上独断专行,而且会让预算变得难以控制。但盖里还是说服了迪勒,他让迪勒相信他是个理性的人,并且在做设计时会根据合理的预算理性考虑,迪勒最终同意了让他试一试。这个项目并不容易,众所周知,在纽约要盖一座房子又贵又麻烦,这座城市对于那些试图在紧张的预算之下完成项目的建筑师来说并不友好——特别是对于盖里这样一个以那些他自称为是“小气鬼建筑”(cheapskate architecture)的项目起家的,来自洛杉矶的建筑师。但盖里还是于2006年完成了这座建筑,一座十层的塔楼,立面上覆盖着起起伏伏犹如船帆的白色玻璃。为了控制预算,建筑整体采用的是较为常规的结构形式。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完成了盖里的一个夙愿,多年来,他参与了数个位于纽约的项目,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其中包括一座庞大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新馆:一手促成了毕尔巴鄂项目的古根海姆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克伦斯(Thomas Krens),曾经计划在曼哈顿下城的滨水地段再建一座古根海姆。然而,2001年9月11日的那场恐怖袭击让这个计划彻底落空,无论在资金上还是规划上都再也无法获得许可。
盖里在参与巴里·迪勒的项目之前,就已经和布鲁斯·拉特纳在2000年纽约时报新总部大楼的设计竞赛上见过面了。拉特纳的地产公司是纽约时报那次竞赛的合作方,他们邀请了盖里参与竞赛,这是盖里第一次尝试设计摩天大楼。布鲁斯·拉特纳对盖里印象极为深刻。他十分欣赏盖里面对评审委员会的方式。“他走过来然后说:‘我是弗兰克·盖里,我喜欢建筑设计。是的我承认,我之前没有做过高层建筑,不过我认为我有这个能力。’”[13]拉特纳一边回忆着一边说,“他很谦逊,穿着也不是那么的刻意。他没有带模型,汇报也很平实,基本上就是介绍自己然后介绍自己的设计。”
为了打消评委对于他缺乏摩天楼设计经验的顾虑,盖里是与他的老朋友,SOM公司(Skidmore,Owings&Merrill)的合伙人之一大卫·柴尔斯(David Childs)组成团队共同参赛的。但是,就在评委会即将宣布结果之前,盖里却突然决定退出了竞赛——他觉得这个项目不适合他。即便他当时已经是获胜的热门人选,他还是无法消除内心中对于涉足商业建筑的谨慎。评委会最终把这个项目交给了他的竞争者之一,意大利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这已经不是盖里第一次因为自己“不开心”而推掉到手的机会了。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的一种行为模式。在他还是个年轻建筑师的时候,他就曾拒绝过他当时的老板提供给他的一个负责掌管巴黎办公室的机会。后来,他还曾放弃过成为著名而富有的家具设计师的机会——曾经有一间家具公司非常看好他的家具设计,并且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打算把他的作品推向市场。
布鲁斯·拉特纳对盖里的退出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并不习惯被建筑师拒绝。一般的房地产开发商可能会很反感这样的建筑师。但是来自于克利夫兰(Cleveland)庞大犹太房地产家族的拉特纳,反而因此立刻喜欢上了盖里。他欣赏盖里的低调随和,以及隐藏于其下的坚定的追求,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和拉特纳本人的性格有点相似。他们两人相谈甚欢,对于盖里的退出,拉特纳更多的是感到遗憾,而不是愤怒。他特别重视维系与盖里的友好关系,并且决心要找到其他的机会与他进行合作。不久之后,拉特纳就找到盖里,问他是否愿意接手他正在策划中的,位于长岛铁路场站(Long Island Railroad train yard)原址上的巨大项目——大西洋场,以及曼哈顿下城的一座高层公寓。大西洋场项目后来经过漫长的扯皮,最终以一场不快收场,[14]但公寓楼项目则不然。最早,这个项目只是被当作曼哈顿岛上比比皆是的又一座普通高层而已,“纽约最高的公寓楼”这个概念也并不是从开始就有的,而是经过了几年的酝酿和反复的考虑而逐渐发展成熟的,提出这个想法,部分的原因是盖里觉得矮矮胖胖的造型比例不够吸引人。
在这座公寓楼项目上,盖里面对着和IAC总部项目相同的挑战,即必须严格控制客户的建造成本,同时,又必须在视觉上足够的引人注目。这座建筑的外观必须有辨识度,让人一看便知是出自弗兰克·盖里的手笔,但在建筑内部的功能布局上,又必须上下对位地排布足够实用的公寓套房。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降低建造的难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吸引那些在选房时并不太看重建筑艺术的租客们。总而言之,这座建筑必须“很盖里”,但又不能“太盖里”了。
盖里最终给出的设计,是一座被总共10500块不锈钢板材包裹着的纤细塔楼,这10500块板材,几乎每一块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和IAC大楼立面上的玻璃幕墙风格如出一辙。塔楼的北、东、西三个立面布满了螺旋状的起伏不平的肌理,从总共几百英尺高的尺度上看起来,就如同在纺织品上揉出的褶皱一般。这一次,又是借助于计算机程序的辅助,这些形状各异的不锈钢板材才得以被生产出来,而且成本能够被控制在和常规的不锈钢立面差不多的范围之内。这些“褶皱”的肌理在立面上又构成了更为大尺度的造型,比如贯穿数层的巨大螺旋和曲线线条等。但是,在夸张的立面造型之下,整个建筑内部的构造却是相当常规的,不仅结构形式简单可靠,而且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内部房间的规整,避免了出现奇形怪状的房间。整座塔楼总共包含了九百套公寓单元,其中也包括顶层的三套豪华套房。
当布鲁斯·拉特纳决定以一场建筑师的生日会来为他的新公寓楼揭幕的时候,公寓顶楼的豪华套房尚未完工。不过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倒是更便于布置派对场地——整个顶楼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的空间,看起来很像是曼哈顿下城的那些近来被改造成为时尚空间,经常举办产品发布会或者时装秀等活动的旧厂房。但是拉特纳并不希望这场派对给人的感觉是一场商业活动。为了把派对现场布置得更吸引人,他租用了一些富有设计感的现代风格的家具陈设,其中有一些就是出自盖里本人的设计,还有一些则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经典作品。然而这些漂亮的家具布置在1万平方英尺(约合929平方米)的空间里,显得有些零零散散,未粉刷的墙边摆着密斯·凡·德罗那件优雅的皮质巴塞罗那椅(Barcelona chair),整个场景似乎并不太协调。派对的承办者彼得·卡拉汉(Peter Callahan)还设置了吧台和鸡尾酒桌,并把整个空间用鲜花装点了起来。场地里还摆放了一架钢琴,不过很可能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等到派对开始以后,嘈杂的人声就会盖过琴声,根本听不到。
大楼的顶层有着额外的挑高,顶层套房的窗子也因此格外巨大,在这里举办派对,来宾们可以饱览曼哈顿壮丽的夜景。而且,2011年3月19日的派对当晚,还将正巧发生一次不同寻常的天文奇观:近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满月。当月球正好在满月的时候来到公转轨道近地点时,人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就会比平时的满月大14%,亮30%,天文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地球—月球—太阳系统的“近地点朔望”,而大众则称其为“超级月亮”。自1993年以来,超级月亮就没有再出现过,而下一次的出现则又是数年以后了。派对当晚,天空异常晴朗,这也意味着派对上的每个人都能够目睹到一轮巨大的满月升起于布鲁克林大桥之上的盛景。
布鲁斯·拉特纳一直以来为了准备这场派对而焦虑不已,他把这不同寻常的天象看作是一个好兆头。当宾客到齐,开始享用美食、美酒和窗外的美景时,拉特纳把大家叫齐到了建筑的北端,在一个造型好似是由盖里的建筑拼合而成的,巨大的蛋糕前,以窗外盖里最喜爱的曼哈顿中城天际线作为背景,拉特纳发表了他的祝酒词。
“我生命当中的一大幸事,就是能够有机会遇到许多奇妙的人,”[15]拉特纳说道,“其中,弗兰克可能是最奇妙的一个,我很高兴能够与他相识。他是个务实的建筑师,一个正人君子。还有,他是个天才。我由衷地崇敬弗兰克·盖里。生日快乐,弗兰克。”
在众人的掌声中,盖里接过了麦克风。他向拉特纳表示了谢意,并且很有风度地回避了关于大西洋场项目的种种不愉快。不过,他还是提醒了大家,他们所处其中的这座建筑,在建成过程当中经历了多少波折,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它曾险些被大幅度地缩减成一座盖里极力反对的那种矮而敦实的建筑。他赞扬了拉特纳,感谢他在经济上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不懈地推进这个项目直到完成,而随后,他话锋一转。
“这里离我父亲出生的地方不远,”[16]他指着窗外的曼哈顿中城说道,“在这里,我很难不想起他。我真希望……”他的声音开始哽咽起来,片刻之后,他接着说:“我真希望他今天能够在这儿,能够亲眼看看他的儿子在这座他生长的城市里建起了什么。我父亲从来没见过我的作品,他认为我只不过是个梦想家。我想,他会为今天的我感到骄傲的。我多希望他能看看这座建筑。我想让他知道,他的儿子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