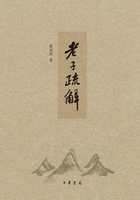
一章
道,可道也,
[非恒道也;
名,可名也,
非]恒名也。①
无名,
万物之始也;
有名,
万物之母也。②
故恒无欲也,
[以观其眇];
恒又(有)欲也,
以观其所噭(曒)。③
两者同出,
异名同胃(谓),
玄之又玄,
众眇之门。④
道,若可晓告,
便不是恒常之道;
名,若可言称,
便不是恒常之名。
道无名可称,
——当它为万物所本;
道勉可命名,
——当它为万物母君。
所以,以其恒常无所欲求,
体察道的幽微杳冥;
以其恒常有所趋就,
观瞩道的呈露有征。
无欲、有欲共其所出,
无名、有名同其所谓,
这意趣玄而又玄呵,
乃是通着那众多奥义的门径。
【校释】
①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帛书乙本“恒名”上残损九字,据甲本当为“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补损阙后,其字句如上。帛书甲本此节文字所存完好,乙本存留之字句与甲本从同。
郭店楚简本未见此章文字。
王弼本此节文字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帛书甲、乙本相勘校,甲、乙本“恒道”、“恒名”,王本作“常道”、“常名”;“常”与“恒”同义,“恒”当为《老子》所用本字,汉以降改“恒”为“常”乃因避汉孝文帝刘恒讳之故。甲、乙本四“也”字王本俱无。
※诸传世本皆同于王弼本;张君相本无首句,由其注“经术政教之道也”可推知此当属抄写之脱漏。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其第一个“道”字为名词,用以喻示人生而天地万物的终极性理趣;《韩非子·解老》所谓“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此“所然”、“所稽”亦即《周易·系辞上》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那种“形而上者”。其第二个“道”字为动词,意为言说,一如《诗·鄘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之“道”,亦如《广雅·释诂》所释“道,说也”。“恒道”,恒常不移之“道”;“道”既然为“形而上者”,便不会像时空中的“形而下”之“器”那样委从于兴衰、生灭之运。“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乃是说“道”不落言诠,一旦诉诸言语,那表之于言说的道就不再是有着恒常不移之品格的“道”了。
“名,可名也,非恒名也”,其第一个“名”字为名词,此“名”指名称或名谓;第二个“名”字为动词,意为命名或称说。“恒名”,恒常不易之“名”;“恒名”相应于“恒道”。“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乃是说与“恒道”相称的“恒名”是无从命名的,倘如命名“形而下”之“器”那样命名“道”,则这由命名而有的名即不再是相应于恒常不移之“道”的恒常不易的“名”了。
②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
帛书乙本字句如上。甲本字句与乙本从同。
王弼本此节文字为:“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帛书甲、乙本“万物之始”王本作“天地之始”,今从帛书本。《史记·日者列传》引此句云“无名者,万物之始也”,王弼注亦云:“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其正可与甲、乙本相印证。此外,甲、乙本“无”(非“無”之简体字)王本作“無”(“无”为六体书中奇字之“無”);甲、乙本“始”下、“母”下并有“也”字,王本俱无。
※诸传世本多同于王弼本,其与王弼本略异者则有:易州景龙碑本、易州开元幢本、遂州龙兴观碑本、敦煌写本之甲本、唐李荣本,二“之”字并无,整节文字为:“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
“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司马光《道德真经论》、王安石《老子注》皆将此句读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衡之《老子》三十二章经文“道恒无名”、“始制有名”,三十七章经文“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四十一章经文“道褒无名”,复衡之以《史记·日者列传》所引古本《老子》语“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可知“无名”、“有名”俱为老子专用术语,不可破而读之。魏源《老子本义》援丁易东所引《老子》三十二章经文即已指出“上二句以‘有’、‘无’为读者,非也”,蒋锡昌《老子校诂》则再度申说“‘有名’、‘无名’为老子特有名词,不容分析”(蒋锡昌:《老子校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第6页)。梁启超《老子哲学》、高亨《老子正诂》蹈司马、王之前辙,依然以“无”、“有”为逗,张松如《老子校读》遂引蒋说又一次予以矫正。
“无名”、“有名”皆喻“道”之称,其相系与相异可由“万物之始”、“万物之母”之“始”与“母”之蕴意辨其大略。“始”,《说文》释其“女之初也”;“母”,《说文》解为“从女,象褱子之形。一曰象乳子也”。“女之初”为处女,“母”则为“褱(怀)子”之女或乳子(以乳哺子)之女;处女与怀子之女或哺子之女原是一女,前者有孕育、生养之潜质而未孕,后者则既已孕乳而使其生之潜质得以显现。以“女之初”(处女)与“褱子”或“乳子”之女——一女而为未母之女、既母之女——隐喻“道”的朴壹与“道”的生生之德的微妙关联,遂就此晓示了“道”由“无名”而“有名”所称举的“无”、“有”两种性状。
③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又(有)欲也,以观其所噭(曒)。
帛书乙本首句“也”后残损四字,据甲本当为“以观其眇”;补损阙后,其字句如上。帛书甲本首句句首残损一字,据乙本当为“故”字。甲、乙本互校,其字句略从同,唯乙本“有”作“又”(“又”为“有”之借字)。
王弼本此节文字为:“故常无(無)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与帛书甲、乙本相勘校,甲、乙本“无”(非“無”之简体字)王本作“無”(“无”同“無”);甲、乙本两“欲”字下并有“也”字,王本俱无;甲、乙本“眇”王本作“妙”,甲、乙本“所噭”王本作“徼”,“噭”当与“眇”相对而言,据此宜从帛书本。
※诸传世本中多有与王弼本略异者,其如:易州景龙碑本、易州开元幢本、遂州龙兴观碑本,无“故”字,两“以”字亦并无,整节文字为:“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敦煌写本之甲本,无“故”字,两“以”字亦并无,“徼”作“曒”,整节文字为:“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曒。”李约本,无“故”字,“徼”作“儌”,整节文字为:“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儌。”黄茂材本,“徼”作“窍”,“以观其徼”为“以观其窍”。邢州开元幢本、易州景福碑本、庆阳景祐幢本、周至至元碑本、楼观台碑本、磻溪大德幢本、北京延祐石刻本、唐李荣本、唐《御注》本、唐《御疏》本、张君相本、杜光庭本、强思齐本、道藏无注本、陈景元本、吕惠卿本、司马光本、苏辙本、陈象古本、宋《御解》本、邵若愚本、李霖本、彭耜本、董思靖本、宋李荣本、林希逸本、文如海本、无名氏本、吕知常本、赵志坚本、寇才质本、赵秉文本、时雍本、邓锜本、杜道坚本、吴澄本、张嗣成本、明《御注》本、《永乐大典》本,无“故”字,“故常无欲”为“常无欲”。
河上公、王弼诸家之注皆以“常无欲”、“常有欲”为句,宋人司马光、王安石、苏辙、范应元、林希逸、明人释德清等则断句于“常无”、“常有”;近人马叙伦、劳健、高亨、朱谦之等亦步武上述宋、明人,而陶绍学、束世澂、蒋锡昌等却又上追河上公、王弼,遂于此处颇有争讼。马叙伦《老子校诂》指出:“详此二句,王弼、孙盛之徒,并以‘无欲’、‘有欲’为句;司马光、王安石、范应元诸家,则并以‘无’字、‘有’字为句。近有陶绍学依本书后文曰‘常无欲可名于小’,谓‘无欲’、‘有欲’仍应连读。易顺鼎则依《庄子·天下篇》曰‘建之以常无有’,谓《庄子》已以‘无’字、‘有’字为句。伦校二说,窃从易也。”(见中华书局“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老子》,1998,第1587页)蒋锡昌《老子校诂》却认为:“此文‘无欲’、‘有欲’皆老子特有名词,不可分割。三章‘常使民无知无欲’、三十七章‘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五十七章‘我无欲而民自朴’,皆其证也。束世澂曰:‘《老子》中“以”字作介词用者,有后置之例……此处“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文例正同,犹云“常以无欲观其妙,常以有欲观其徼”也。于“无”、“有”读,失其旨矣。’(《国立东南大学校刊》第十三号《老子研究法》)束氏以文例来定‘无欲’、‘有欲’为读,亦极精确。又以文谊而论,此文‘无欲’、‘有欲’正分承上文‘无名’、‘有名’而言。三十七章‘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以‘无欲’紧接‘无名’之下,可知二者有密切之关系也。安可以‘无’、‘有’为读乎?”(蒋锡昌:《老子校诂》,第7-8页)两相校雠,显然以“常无欲”、“常有欲”为逗更契于句脉,但最后之定论尚须勘验于帛书《老子》。无论是帛书甲本,还是帛书乙本,其“无欲”、“有欲”后皆有一“也”字,此汉初古本足可印证河上公、王弼至束世澂、蒋锡昌等之判断不误。
“欲”有多种涵义,此处意为愿望、欲求;“无欲”当指无所欲求,“有欲”则为有所趋就。“妙”,依帛书甲、乙本,当为“眇”。清人黄生所撰《义府》云:“篆文妙作窊,本训精微之意。《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老子》‘常无欲以观其妙’,又‘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正得本训。后遂以妙为美好之称,故隶字变而从女。”(《义府》卷下《隶释》)又云:“(要妙)本字当作幺窊……自汉以来,又借为美好之称,因改其字从女作妙,其实古无此字。《老子》之妙,必后人所改也。”(《义府》卷下《幼眇》)据此可知,先秦无“妙”字,《老子》“观其妙”之“妙”乃汉人用隶书后由“眇”所改。“眇”之本义在于微小、微茫、眇默,此处以“眇”形容“道”之微茫、眇默,正与《老子》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之意味相通。从“恒无欲”、“恒有欲”之对举,可知“观其眇”之“眇”与“观其徼”之“徼”的对举;“眇”为眇茫、眇默之意,则“徼”(jiào)或当作“曒”(jiǎo)。敦煌本即作“曒”,校之以帛书甲、乙本“以观其所噭”之“噭”(jiào),“曒”较之河上公、王弼以下诸本之“徼”更合老子本义。“徼”、“曒”、“噭”以至李约本“常有欲以观其儌”之“儌”(jiāo)、《老子》十四章河上公、王弼诸本“其上不皦”之“皦”(jiǎo),皆本之于“敫”(jiǎo)而由“敫”孳乳以生。《说文》释“敫”:“光景流也。”段玉裁注云:“谓光景(影)流行,煜燿昭著。”“敫”之“光景流”所喻示的昭著、显著、彰显之意,无不隐含于“曒”、“噭”、“皦”、“儌”、“徼”之中。“曒”,光明之谓,寓昭著、彰显之意于其中;“噭”,声音响亮之谓,亦寓昭著、彰显之意于其中;“皦”,光亮洁白之谓,仍寓昭著、彰显之意于其中;至于“徼”、“儌”皆边界、边际之谓,其对界限、畛域的指示亦未尝不寓有“昭著”、“彰显”之意。不过,与“眇”对举,在诸多由“敫”孳乳的字中,“曒”显然更相宜些。于是,所谓“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曒)”,便应作如是理解:以其恒常无所欲求,体察道的幽微与眇默;以其恒常有所趋就,观览道的运作与呈现。
④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
帛书乙本字句如上。甲本下一“之”下残损一字,据乙本当为“门”。乙本“又”甲本作“有”(“有”为“又”之借字);除此外,甲、乙本字句从同。
王弼本此节文字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与帛书甲、乙本相勘校,王本于“两者”上多一“此”字,于“出”字下多一“而”字,于“同谓”下多“之玄”二字,“眇”则作“妙”;甲、乙本“谓”作“胃”(“胃”为“谓”之借字),甲本“又”作“有”(“有”为“又”之借字)。王本此节文字与帛书甲、乙本文义略从同,然上半节文字之句脉有异。
※诸传世本俱同于王弼本。
“两者”,其所指者何,历来争议颇多。凡对上句以“常(恒)无”、“常(恒)有”为读者,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辙、范应元以至梁启超、马叙伦、朱谦之、高亨等,必以“两者”为“无”与“有”或“常(恒)无”与“常(恒)有”;凡以“常(恒)无欲”、“常(恒)有欲”为读者,则或如河上公所谓“两者,谓‘有欲’、‘无欲’也”,或如王弼所谓“两者,‘始’与‘母’也”,或如吴澄所谓“此两者,谓‘道’与‘德’也”,不一而足。其实,细审全章,“恒无欲”、“恒有欲”何尝不通于“无名”、“有名”,“恒无欲”而“无名”、“恒有欲”而“有名”又何尝不可以“无”、“有”概而言之,诚然,这既不必将“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读为“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不必将“恒无欲,以观其眇;恒有欲,以观其所噭(曒)”读为“恒无,欲以观其眇;恒有,欲以观其所噭(曒)”。
与“两者”的歧说纷纭相应,“同出”亦有不同诠注。自大端而言,河上公注、王弼注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说法。河上公注:“同出者,同出人心也。”王弼注:“同出者,同出于玄也。”前者以“无欲”、“有欲”之“欲”为人之“欲”,所以称其“同出”于“人心”;后者以“无名”(“始”)、“有名”(“母”)喻示“道”,所以称其“同出”于“玄”。依王弼之见,“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弥伦而不可极也;‘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然则,‘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然弥伦无极,不可名细;微妙无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王弼:《老子指略》)。这即是说,在王弼这里,尽管“道”、“玄”、“深”、“大”、“微”、“远”皆是对“常道”(“恒道”)的各取一端而“未尽其极”的形容,但比勘而言,“道”与“玄”是用于此一形容的最相宜的术语。亦即是说,“道”、“玄”之所指原只是同一“惚恍”之“状”(“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十四章),因此,“同出”于“玄”正可谓“同出”于“道”。不过,真正说来,“无欲”、“有欲”可对人而言,却也未始不可对“道”而言;谓“道”之“无欲”、“有欲”,乃是拟人以言道。如此,“两者”既可以说是“无名”(“始”)、“有名”(“母”),也可以说是“恒无欲”、“恒有欲”,因而,“同出”既可以说“无名”、“有名”同出于“道”,也可以说“恒无欲”、“恒有欲”同出于“道”。“无名”与“恒无欲”相贯,“有名”与“恒有欲”相贯,全章主旨乃在于“道”(“恒道”)的标示,而其一以贯之的致思线索则在于“无”(“无名”而“恒无欲”)、“有”(“有名”而“恒有欲”)两者相即不离而同一于“道”(“恒道”)。
这“无”(“无名”而“恒无欲”)、“有”(“有名”而“恒有欲”)相即不离而同一于“道”(“恒道”)的理致是玄微而又玄微的,懂得了如此玄微而又玄微的理致,也就找到了领悟“道”(“恒道”)的诸多奥趣的门径。此之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
【疏解】
此章乃是老子“道”论的总纲,亦可视为整部《道德经》的眼目。“道”(“恒道”)由此而导,“名”(“恒名”)由此而明;老子之属意,于此可窥其大略,五千言的致思脉络亦就此敷演而出。
“道”是老子运思的至极范畴,它由通常所谓“道路”(导路)之“道”升华而来,至老子时它已有了“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那种“形而上”的品格。甲骨文未见“道”字,但已有“道”之异构字“杦”( )出现。“杦”亦见于周之石鼓文,宋明金石学家薛尚功、杨升庵等已将“杦”训作“道”。郭店楚简本《老子》中三处“道”字写作“杦”,这印证了甲骨文、石鼓文中的“杦”字即“道”字之异构。比“杦”晚出,“道”在西周金文中写作“
)出现。“杦”亦见于周之石鼓文,宋明金石学家薛尚功、杨升庵等已将“杦”训作“道”。郭店楚简本《老子》中三处“道”字写作“杦”,这印证了甲骨文、石鼓文中的“杦”字即“道”字之异构。比“杦”晚出,“道”在西周金文中写作“ ”。“杦”字从行(甲骨文“行”字写作“
”。“杦”字从行(甲骨文“行”字写作“ ”)从人(甲骨文“人”字写作“
”)从人(甲骨文“人”字写作“ ”),“道”字从行从首(甲骨文“首”字写作“
”),“道”字从行从首(甲骨文“首”字写作“ ”),而“首”指代“人”,因此“杦”与“道”同为一字。就初始之意而言,甲骨文“杦”、金文“道”皆为人于十字路口寻路或辨路而行。寻或辨涉及所行方向的选择,其在于对所行方向的辨而导之,而这正可印证于唐人陆德明“‘道’本或作‘导’”(《经典释文·尔雅音义》)之说。
”),而“首”指代“人”,因此“杦”与“道”同为一字。就初始之意而言,甲骨文“杦”、金文“道”皆为人于十字路口寻路或辨路而行。寻或辨涉及所行方向的选择,其在于对所行方向的辨而导之,而这正可印证于唐人陆德明“‘道’本或作‘导’”(《经典释文·尔雅音义》)之说。
老子遭逢春秋末季,周代“郁郁乎文”(《论语·八佾》)数百年后这时已日见“文敝”(《史记·高祖本纪》)——“文胜质则史(饰)”(《论语·雍也》)——而“礼坏乐崩”。“文敝”的现实逼使敏感于此的老子从终极处反省人为之“文”对于人生而天地万物的意义,其“恒道”意味上的“道”的提出乃在于导示世人弃“文”复“朴”以返回生命之自然。在老子看来,朴浑而自然是人生与万物本始之常态,而任何“文”——相对于自然它涵括了所有措意为之的人为——的出现都会打破这种常态的浑全或纯备。人的言说是人为之“文”的一种,为“道”之所导的那种浑化之自然一旦诉诸言说即可能为言说所析离。所以,从根本上说,言喻这一人为之“文”与朴壹的自然之“道”终究是不相应的,此所谓“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名”字的出现早于“道”字,其在甲骨文中写作“ ”。一如后来篆体、隶体的“名”字,甲骨文的“
”。一如后来篆体、隶体的“名”字,甲骨文的“ ”亦“从口从夕”,只是《说文》对其所作“名,自命也”、“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的解释,尚难以从既经发现的甲骨卜辞中得到印证。但酝酿并初成篇章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其“名”已具有“自命”之“命”意(命名、称呼、告诉)而与“明”相通:“名,明也,名实使分明也。”(刘熙:《释名·释言语》)命名使浑沌中的世界得以依类判物,而为人所分辨,然而,先前浑沌中的那种圆备也因着如此的察识而被打破。因此,通常所谓“名”是对万物中的此一(种)物或彼一(种)物的命名,其“名”是可称说的(“可名”);但这样的“名”不是那种可喻示或可称述恒常之“道”的恒常之“名”(“恒名”)。此所谓“名,可名也,非恒名也”。“道”作为“万物之始”,其浑朴而一任自然,因而无可名状或无从描摹(“无名”);“道”作为“万物之母”,其所成全的森然万象可予名状、可予描摹,所以其对可予名状或描摹的万物的成全本身遂亦勉可予以名状或描摹(“有名”)。此所谓“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
”亦“从口从夕”,只是《说文》对其所作“名,自命也”、“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的解释,尚难以从既经发现的甲骨卜辞中得到印证。但酝酿并初成篇章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其“名”已具有“自命”之“命”意(命名、称呼、告诉)而与“明”相通:“名,明也,名实使分明也。”(刘熙:《释名·释言语》)命名使浑沌中的世界得以依类判物,而为人所分辨,然而,先前浑沌中的那种圆备也因着如此的察识而被打破。因此,通常所谓“名”是对万物中的此一(种)物或彼一(种)物的命名,其“名”是可称说的(“可名”);但这样的“名”不是那种可喻示或可称述恒常之“道”的恒常之“名”(“恒名”)。此所谓“名,可名也,非恒名也”。“道”作为“万物之始”,其浑朴而一任自然,因而无可名状或无从描摹(“无名”);“道”作为“万物之母”,其所成全的森然万象可予名状、可予描摹,所以其对可予名状或描摹的万物的成全本身遂亦勉可予以名状或描摹(“有名”)。此所谓“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
与“道”的无可名状、无从描摹相应的是“道”的恒常无所欲求(“恒无欲”),与“道”因着成全可名状的万物而自身遂亦勉可名状、勉可描摹相应的是“道”的恒常有所趋就(“恒有欲”)。“道”的恒常有所趋就(“恒有欲”)唯在于对万物的“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老子》五十一章),但“道”的这种有所趋就本身即体现了“道”在究竟处的无所欲求,亦即其“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同上)。“道”在对万物的成全中恒常显现,而“道”之显现的深眇终在于其“弗有”、“弗恃”、“弗宰”的“恒无欲”,此即所谓“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曒)”。
老子之“道”不像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 )那样把一种势所必至的“命运”——所谓“不可挽回的必然”(伊壁鸠鲁)——强加于宇宙万物和人,它没有那种一匡天下的咄咄逼人的霸气,它对于万物和人并不意味着一种强制性的他律(人和万物之外或之上的某种律令)。“道”也决非黑格尔以思辨所悬设的那种“绝对理念”(absolute Idee);作为精神实体的“绝对理念”利用人类的“热情”(利欲、权势欲等)对人施以“理性的狡计”,从而在一种“正、反、合”的逻辑节奏中为自己的既定目标开辟道路,“道”则决无预谋,亦决不把人与万物用作达到自己某种目的——真正说来“目的”之谓对于它全然不相应——的资具。“道”不是实体,既非不同于诸物态实体(“万物”)的另一物态实体,也非“逻各斯”、“绝对理念”那样的精神实体。它只意味着一种对“文”之所“敝”消而除之的引导,一种对摈绝一切造作以使人与万物归于自然而然的开示。“道”之所“导”无所谋取,无所执着,这诚可谓其始终无所欲求(“恒无欲”)而无可标示(“无名”),但既然其确有所“导”而从不间断,则又不可不谓之始终有所趋就(“恒有欲”)而未始不可称述(“有名”)。“无”(“无名”而“恒无欲”)与“有”(“有名”而“恒有欲”)同出于“道”之所导,名虽相异却相即于一,这“异名”而“同谓”的玄眇趣致乃在于:其形而上境地的持存同其对形而下俗世导引的相因相成,与其说是对“道”的臼机的最后吐露,不如说是对领悟“道”的诸多奥义之门径(“众眇之门”)的深切喻示。
)那样把一种势所必至的“命运”——所谓“不可挽回的必然”(伊壁鸠鲁)——强加于宇宙万物和人,它没有那种一匡天下的咄咄逼人的霸气,它对于万物和人并不意味着一种强制性的他律(人和万物之外或之上的某种律令)。“道”也决非黑格尔以思辨所悬设的那种“绝对理念”(absolute Idee);作为精神实体的“绝对理念”利用人类的“热情”(利欲、权势欲等)对人施以“理性的狡计”,从而在一种“正、反、合”的逻辑节奏中为自己的既定目标开辟道路,“道”则决无预谋,亦决不把人与万物用作达到自己某种目的——真正说来“目的”之谓对于它全然不相应——的资具。“道”不是实体,既非不同于诸物态实体(“万物”)的另一物态实体,也非“逻各斯”、“绝对理念”那样的精神实体。它只意味着一种对“文”之所“敝”消而除之的引导,一种对摈绝一切造作以使人与万物归于自然而然的开示。“道”之所“导”无所谋取,无所执着,这诚可谓其始终无所欲求(“恒无欲”)而无可标示(“无名”),但既然其确有所“导”而从不间断,则又不可不谓之始终有所趋就(“恒有欲”)而未始不可称述(“有名”)。“无”(“无名”而“恒无欲”)与“有”(“有名”而“恒有欲”)同出于“道”之所导,名虽相异却相即于一,这“异名”而“同谓”的玄眇趣致乃在于:其形而上境地的持存同其对形而下俗世导引的相因相成,与其说是对“道”的臼机的最后吐露,不如说是对领悟“道”的诸多奥义之门径(“众眇之门”)的深切喻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