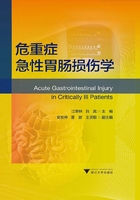
第五节 胃肠的微生态
一、胃肠微生态
微生态系统是由正常微生物群与其宿主的微环境(组织、细胞、代谢产物)两类成分组成。研究人体正常微生物群的结构、功能及其与宿主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关系的科学称为微生态学。肠道微生态系统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人体营养吸收、代谢,肠道和免疫系统的发育等重要生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人体最重要的微生态系统。它主要包括了三大类肠道菌群:①与机体共生的生理性菌群;②与宿主共栖的条件致病菌;③侵入性病原菌群。肠道微生态系统功能多样,不仅能调节肠黏膜免疫,维持肠道稳态,还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一)胃肠道微生态组成
成人胃肠道黏膜表面积约为300m2,是机体与外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最大器官。据估计,人体胃肠道内细菌数量超过成年人体细胞总和(见图2-1)。从基因组角度来看,一个健康成年人肠道微生物的全部基因组远超人类自身基因组的总和,其总基因组的大小估计是人类基因组的100倍。

图2-1 胃肠道菌群数量分布
(引自:Biedermann L, Rogler G.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it's role in health and disease[J].Eur J Pediatr, 2015,174:151-167.)
胃肠道内微生物自宿主出生后就开始定植(见图2-2),并伴随宿主的生长而逐渐成熟,属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婴儿的肠道微环境与母体有密切关系,一岁左右,肠道微生物发展至成熟状态,菌群结构接近成人。胃内微生物可分为腔菌群和膜菌群两大类,健康成人胃液具有杀灭细菌的功能,因此,胃液细菌总量极少,通常在101~105/mL,绝大多数为死亡菌。宿主的不同的生理状态如胃液的pH、胃黏膜的病理改变、机体免疫状态、胃动力失常、胃手术以及抗生素的应用等,均可影响胃内微生物种类及数量,其中胃pH的变化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人类肠道宏基因组计划组”(Metagenomies of the Human Intestinal Tract, MetaHIT)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人肠道菌群的宏基因组研究,结果显示,肠道中的细菌基因组是控制人体健康的“人类第二基因组”。肠道菌群与宿主营养、免疫、行为发育等方面的关系十分密切。只有当人体自身基因组、人体共生微生物基因组及所处环境三者之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状态时,才能保持人体的健康状态。

图2-2 胃肠道菌群类型分布
(引自:秦环龙.临床疾病的肠道微生态改变与微生态制剂的应用[A].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2009全国肠外肠内营养学学术会议论文集[C];2009.)
1.胃微生态构成
胃腔菌群主要来源于口腔及咽部菌群,随进餐或唾液吞咽进入胃腔。因此,腔菌群的构成与口咽部菌群构成类似,主要有链球菌、乳酸杆菌、微球菌、葡萄球菌、韦荣氏菌属及口腔类杆菌等。当胃液pH<4时,绝大多数细菌被杀死,因此,胃腔菌群被认为并非常驻菌群。
当胃液pH>5时,多种复杂菌群则迅速增殖,引起严重的微生态失衡。如果胃液pH每天下降至4以下1~2h,则足以阻止腔菌群的定植和过度增殖。胃黏膜菌群除幽门螺杆菌外,其他胃黏膜菌群的研究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表明,健康成人胃黏膜可分离出需氧的链球菌、微球菌、葡萄球菌和厌氧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以及白色念珠菌和类酵母菌等。但绝大多数菌数量较少,检出比例低。其原因是胃酸具有杀菌作用,大部分外籍菌群都将被杀死而难以在胃黏膜上定植。
2.肠道微生态构成
肠道微生物菌群可分为如下三大类。
(1)人体肠道正常菌群或原籍菌群:是肠道菌群的主要构成者,为专性厌氧菌,如双歧杆菌、乳杆菌、类杆菌等。其种类和数量在人体处于健康状态时,保持相对稳定和平衡,被称为正常菌群或原籍菌群(Normal bacteria flora),它们是机体内环境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多数与人体形成了共生关系。一方面,人体选择性地让某些微生物定植于肠道,并为其提供适宜的栖息环境;另一方面,肠道微生物群产生的代谢产物又会随着血液与营养分子一起运送到各个细胞组织中,每个细胞的生理活动都会受到肠道菌群代谢物的影响,它参与人体的多种代谢,与肠道屏障功能的完善密切相关。人体肠道内有益菌的种类和数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人体的健康状态。
(2)与宿主共栖的条件致病菌:肠道非优势菌群,以兼性需氧菌为主,如肠球菌、肠杆菌、拟杆菌等,正常情况下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过度生长或发生易位时就会引起微生态失调。
(3)侵入性病原菌群:较典型的有害菌包括铜绿假单胞菌、葡萄球菌、艰难梭菌等,可与宿主竞争养分,与潜在病原体产生细菌协同作用,在宿主体内产生毒素或致癌物,甚至导致内源性疾病或机会性感染。
肠道微环境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可因不同个体和年龄段、饮食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是优势菌群相对固定,且肠道菌群的生物功能大致相同(见图2-3)。

图2-3 胃肠道菌群种类随年龄变化分布
(引自:Power S E, O'Toole P W, Stanton C, et al.Intestinal microbiota, diet and health[J].Brit J Nutr,2014,111:387-402.)
(二)人体肠道正常菌群的种类和数量
人的胃肠道栖息的共生细菌大约重1.5kg,种类大约30个属,达800~1000多种。肠道菌群主要由厌氧菌、兼性厌氧菌和需氧菌组成,其中专性厌氧菌占97%以上,而仅类杆菌及双歧杆菌就占细菌总数的90%以上。由于胃酸、胆汁作用及小肠液流量大、蠕动快,因而胃、十二指肠、空肠细菌的种类及数量极少,主要为革兰阳性需氧菌,如链球菌、葡萄球菌和乳酸杆菌。回肠末端由于肠液流量少、蠕动减慢,导致细菌数逐渐增加,主要含乳酸杆菌、大肠埃希菌、类杆菌和梭状芽孢杆菌等;至结肠处,细菌数明显增加,主要含双歧杆菌、类杆菌和乳酸杆菌等,且大多为厌氧菌。
随着宏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来自欧洲的人类肠道宏基因组计划(MetaHIT)和美国的人类微生物组计划(HMP)更加全面、精确地分析了人类正常肠道微生物的构成。人体肠道中具有1~3种基本的菌群形态,形成各自的肠道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控制和调节着人体基本的新陈代谢,其中优势菌群主要为:以乳杆菌、支原体、芽孢杆菌、梭菌和链球菌为代表的厚壁菌门,以拟杆菌为主的拟杆菌门、变形菌门、放线菌门、梭菌门等。
二、肠道正常菌群的生理功能
(一)肠道细菌对肠黏膜屏障的影响
肠黏膜屏障由机械屏障、生物屏障、化学屏障以及免疫屏障等组成,为宿主提供了一个可有效抵抗外界病原菌入侵的屏障。肠道细菌的机体保护机能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肠道细菌能够抑制其他外源性微生物在肠道内的定植或增殖,与致病菌竞争消化道上皮的附着位点;另一方面,与致病菌竞争营养物质;最后,肠道细菌也能通过产生一些抗微生物的物质(细菌素)来抑制微生物竞争者的生长繁殖。
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对于维持肠道乃至机体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肠道菌群参与了肠黏膜屏障的构成,也促进了免疫系统的发育和成熟。
1.肠道微生物影响肠道机械屏障
肠黏膜机械屏障由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细胞间紧密连接、菌膜和黏液层等构成,肠道微生物对肠黏膜机械屏障的结构及功能有直接影响。菌膜能有效阻止条件致病菌与肠上皮直接结合,肠道上皮细胞通过机械屏障隔离肠道病原菌群与免疫系统,提供第一道防线。
2.肠道微生物的生物屏障作用
肠道正常菌群对于外源性致病原菌的入侵可以起到生物屏障作用。黏膜上皮表面存在的栖息微生物群,在肠道黏膜表面形成密集的菌膜,与肠黏膜紧密结合构成肠道的生物屏障,能通过占位效应、营养竞争及其所分泌的各种代谢产物和细菌素等抑制条件致病菌的过度生长以及外来致病菌的入侵,同病原微生物竞争细胞上的结合部位,阻止病原微生物的黏附感染,从而维持肠道的微生态平衡,起到生物屏障作用。正常肠道菌群可在肠道局部产生一些抑菌物质,如大肠埃希菌产生的大肠菌素,乳酸菌产生的乳酸链球菌肽等,从而抑制外源性病原菌的增殖。不同的益生菌黏附方式不同。如加氏乳酸杆菌(L.gasseri)通过糖类和糖蛋白来实现黏附,且其黏附力最强;嗜酸性乳杆菌依靠糖类、二价钙离子来实现黏附;双歧杆菌通过磷壁酸黏附于肠上皮细胞表面,构成一层菌膜屏障,并产生细胞外糖苷酶,对上皮细胞上作为致病菌及其内毒素结合受体的复杂多糖进行降解,竞争性抑制肠道内源性(主要是肠杆菌科细菌)及外源性潜在致病菌(Potentially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PPMOs)对肠上皮细胞的黏附、定植,从而起到定植拮抗作用。肠道内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有益菌的酸性代谢产物(乙酸、乳酸、丁酸、短链脂肪酸等)能降低肠道局部pH和产生细菌素、过氧化氢等具有广谱抗菌作用的物质,抑制肠道致病菌及条件致病菌的生长,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并降低内毒素。
3.肠道微生物影响肠道免疫屏障
肠道不仅具有消化、吸收功能,还具有重要的免疫功能。肠道黏膜免疫屏障由大量弥散性分布在肠上皮内和固有层的免疫细胞、免疫分子以及派尔集合淋巴结(PP)和肠系膜淋巴结(mesenteric lymphoid node, MLN)等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ALT)组成。存在于肠道黏膜表面的益生菌作为一种活的有机体对肠道黏膜具有多重的保护作用,它们可以活化肠黏膜内的相关淋巴组织,使S-IgA合成增加,从而提高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见图2-4)。S-IgA是机体内分泌量最大的免疫球蛋白,能中和病毒、毒素和酶等生物活性抗原,具有广泛的保护作用。另外,正常的肠道菌群大量繁殖可以竞争性地消耗外源性致病菌生长繁殖所必需的营养物质,特别是铁离子,从而使得外部入侵的致病菌由于载铁量低而无法与正常菌群竞争。

图2-4 肠道微生态免疫屏障作用
(引自:Aidy S, van den Bogert B, Kleerebezem M.The small intestine microbiota, nutritional modulation and relevance for health[J].Curr Opin Biotech,2015,32:14-20.)
黏膜栖息微生物的存在对黏膜和全身淋巴样组织的发育和功能的发挥起着重要作用。大量的研究显示,无菌动物缺乏生发中心,黏膜浆细胞量极少,对肠道致病菌的易感性更高,对抗原的应答显著减弱。正常肠道菌群能活化肠道黏膜内的相关淋巴组织,诱导T、B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细胞因子,通过淋巴细胞再循环而活化全身免疫系统,增强机体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黏膜栖息微生物可以通过与上皮细胞相互介导作用来产生黏膜固有免疫,维护上皮组织的屏障作用。肠道菌群与宿主免疫细胞间不断的相互作用,刺激了黏膜免疫系统的成熟,阻止了病原菌在宿主肠道内定植,保证了黏膜屏障的完整性。
另外,益生菌还有抗肿瘤作用,如双歧杆菌细胞壁的肽聚糖、磷壁酸和多糖等。其主要机制是通过增强宿主的免疫功能,如激活巨噬细胞、NK细胞和B淋巴细胞,促使这些细胞释放免疫活性物质,如TNF、IFN、IL-1、IL-6等细胞因子,从而发挥抑制肿瘤的作用。
4.肠道微生物的营养作用
肠道菌群可利用本身所特有的某些酶类(如半乳糖苷酶等)补充宿主在消化酶上的不足,帮助分解上消化道未被充分水解吸收的营养物质,有利于宿主进一步吸收、利用各种营养物质,包括增加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如维生素B、维生素K)、氨基酸、微量元素、某些无机盐类(如钙、磷、铁等)的吸收和利用。双歧杆菌能将胆固醇转化成类胆固醇,可降低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改善脂质代谢紊乱。双歧杆菌、乳杆菌、大肠埃希菌等可以合成多种蛋白质和维生素,被人体利用。益生菌还可在营养物质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其优势生长来竞争性地消耗致病菌的营养素。当完整的小肠上皮细胞被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细菌占据时,可形成防止病原微生物侵入以及肠腔中有害物质被吸收的屏障。
肠道微生态系统与肠黏膜屏障共同组成完善的肠道防御机制,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共同抵御致病菌的侵袭。直接方式为肠道共生菌群与致病菌竞争性地消耗营养物质,抑制致病菌的增殖;间接方式为肠道共生菌群通过分解代谢糖类以获得短链脂肪酸,主要是乙酸、丙酸、丁酸等,从而抑制毒素在肠道内的移位。同时,肠黏膜在肠道共生菌群的刺激下增加黏液的分泌,加强肠道的屏障作用。
5.肠道菌群的抗衰老作用
肠道菌群可因不同个体、各年龄段和食物变化而有所不同,随着年龄增长,肠道菌群的平衡状态也会发生变化。机体衰老时自由基过剩,肠道pH升高,魏氏梭菌(Clostridum welchii)及大肠埃希菌增多而双歧杆菌减少,大肠埃希菌等腐败细菌增多,引起肠功能紊乱,发生便秘、腹泻和肠道解毒功能减退,以及肝功能受损。腐败产物中的氨、胺类、硫化氢、酚类、吲哚、粪臭素和内毒素等有毒物质产生增多,这些物质被吸收进入血流,侵蚀全身各组织器官,会加速机体衰老、使免疫力降低,引发老年病如胆固醇增高、动脉硬化、癌症等。
(二)肠道微生态平衡的影响因素
健康人的肠道微环境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人体肠道菌群结构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平衡。宿主饮食习惯、年龄、性别以及健康状况均会对菌群结构造成影响。
1.饮食因素
饮食对肠道微生态组成有较大影响,尤其是纤维成分及其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乙酸、丙酸、丁酸等)对宿主和肠道微生物双方均有利;细菌成分如多糖A和肽糖等也对微生态平衡有积极的贡献。不良饮食习惯或精神压力可破坏肠道菌群平衡。
2.年龄、性别因素
人体肠道菌群状况是随年龄而变化的,婴儿肠道几乎全是双歧杆菌,随年龄增大,双歧杆菌减少而腐败菌增加,超过60岁后变化更为明显,30%的老人肠道中几乎不存在双歧杆菌。肠道中的有害细菌梭状芽孢杆菌在年轻人中检出率仅为50%,而在老年人中检出率可达80%。
3.疾病因素
手术、外伤、感染、肿瘤、化学物品及疾病时对肠道菌群也有影响,特别是危重症患者,有时可丧失整个乳酸菌群。同位素、激素、放射治疗和化疗均可在治疗疾病的同时降低机体免疫力,也破坏了肠道菌群的平衡。此外,长期大量使用广谱抗生素后,可使大多数敏感菌和正常菌群被抑制或杀死,而耐药菌则由于抗生素的选择作用得以大量繁殖,因此,长期大量使用广谱抗生素是引发菌群失调的常见原因。
肠道微生态失调是指正常菌群和宿主两方面的失调,主要表现形式为肠道菌群种属和数量的改变及肠道菌群/内毒素易位(Bacterial translocation, BT)等。前者主要指小肠细菌过度生长(Enteric bacterial overgrowth syndrome, EBOS),多见于胃酸、胃肠液分泌下降,以及营养不良、炎症性肠病、糖尿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硬皮病、贾第鞭毛虫等寄生虫感染患者;后者主要指肠道细菌或毒素向肠系膜淋巴结及血管的迁移,大多伴有肠黏膜通透性增加、肠道运动功能减弱、细菌过度生长以及肠道免疫功能的紊乱,是肠道屏障功能不全的严重后果。若大肠菌群上移,则可致小肠污染;若细菌外移,则可致腹腔感染、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甚至多器官功能衰竭。常见易位细菌有大肠杆菌(占48%)、奇异变形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肠杆菌、粪杆菌、拟杆菌等。
三、肠道正常菌群的检测方法
(一)传统检测方法
传统细菌培养法一般采用各种培养基培养细菌,将各种细菌分离并根据革兰染色、生化反应及血清学实验等方法对细菌进行鉴定。同时可进行倍比稀释和菌落计数来测定活菌数量。肠道微生物菌群复杂,粪便样品中很多微生物难以培养,若采用常规技术,则自然界中90%~99%的微生物用传统方法是无法培养出来的,因为对微生物菌群进行传统微生物技术培养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菌株的富集或衰减,这就人为改变了原始菌群的微生态构成,对研究结果造成较大偏差。该方法只能对部分的菌群进行分析,而且耗时,对于种类、数量如此巨大的肠道微生态系统而言,只对部分菌群进行分析不够全面,也不能反映整个微生态系统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分析的结果与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检测方法
目前用于肠道菌群研究的分子技术有rRNA/DNA序列分析、随机扩增多态性分析(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analysis,RAPD)、温度梯度凝胶电泳(Temperature gradient gel electrophoresis,TGGE)、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enaturing gradient gel electrophoresis,DGGE)等。其中DGGE是近年国内外应用比较广泛的技术。它是由Fisher发明用于检测DNA突变的技术,Muyzer首次将其用于分析土壤的微生物区系,成为检测微生物多样性的一种有效方法。该方法为首先提取欲分析样品的细菌总DNA,然后根据16SrRNA基因中比较保守的碱基序列设计通用引物,用来扩增微生物群落基因组总DNA之后,对扩增混合的PCR产物进行变性梯度凝胶电泳。由于核酸序列不同,因此,相同大小、不同序列的DNA片段将停留在凝胶的不同位置,以达到分离混合PCR产物的目的。电泳条带的数目和密度可分别反映细菌种类的多少和细菌的相对构成比例。如想鉴定细菌,可将其单一条带切下回收,克隆测序,然后将所得序列提交到核酸序列数据库,并与数据库中的公开序列进行对比分析。DGGE技术在揭示复杂微生物区系的遗传多样性和种群差异方面具有独特的优越性,目前已成为分析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动态变化的有力工具。但无论什么方法均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因此,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
人类肠道宏基因组计划组(MetaHIT)集中研究了人类消化道、口腔、阴道、皮肤和鼻腔五大组织器官内的微生物元基因组。元基因组指自然环境中全部微生物基因组的总和。元基因组学是一种以环境样品中的微生物群体基因组为研究对象,以功能基因筛选和测序分析为研究手段,研究微生物多样性、种群结构、进化关系、功能活性、相互协作关系及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新的微生物研究方法。元基因组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微生物群落,无须分离单个细菌,可以研究那些不能被实验室分离培养的微生物,使人们摆脱物种界限,扩大对胃肠道菌群基因的认识,可揭示更高、更复杂层次的生命运动规律,有助于认识和诊断疾病、开发新药物和防治方法。
四、肠道微生态与人类疾病
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着人体的健康程度。这里的基因,不仅指人体自身的基因,还包括大量与人体共生微生物的基因。只有当人体自身基因组、人体共生微生物基因组及所处环境三者之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状态时,才能保持人体的健康状态。
肠道菌群按一定的种属比例组合,各菌属间相互制约、互相依存,在质和量上形成一种生态平衡。肠道微生物不仅帮助宿主消化食物,为宿主提供能量和营养物质,更为宿主提供一个可有效抵抗外界病原菌入侵的屏障,肠道菌群的成熟也促进了免疫系统的发育和成熟。宿主与肠道微生物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平衡稳定的肠道菌群对宿主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若肠道平衡被打破,则会引起肠道炎症细胞因子、炎症介质、蛋白酶类和氧自由基的释放,除了会加重肠道黏膜机械屏障损伤外,也可以造成细菌易位和消化道免疫调节的激活,触发疾病的发生进展乃至恶化。
(一)肠道细菌与内分泌系统疾病
肠道细菌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宿主代谢,包括如下几方面。①促进多糖发酵:厚壁菌门、拟杆菌门等既是肠道中的优势菌群,又是发酵多糖的主力军。微生物组能编码一些人类自身所没有的,参与多糖分解的酶。人体10%~15%的能量来源于肠道微生物菌群酵解碳水化合物而获得。②小分子营养物质的吸收:如肠道中最常见的多形拟杆菌(B.thetaiotaomicron)可以参与一系列营养物质吸收相关基因的调控,刺激宿主对葡萄糖、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 SCFA)等小分子营养物质的吸收。③影响与脂肪贮存相关基因的表达:肠道细菌能够抑制禁食诱导脂肪因子(Fasting-induced adipose factor, Fiaf)在肠道上皮细胞中的表达,阻止它控制脂蛋白脂肪酶(Lipoprotein lipase, LPL),从而提高LPL活性。LPL活性提高后,可以增加脂肪细胞中脂肪酸和甘油三酯的沉积。因此,肠道细菌与肥胖、糖尿病等内分泌系统疾病密切相关。
研究者将从肥胖者的肠道内获得的厚壁菌门菌和从消瘦者的肠道内获得的拟杆菌门菌分别移植到无菌小鼠肠道内,结果发现,移植了厚壁菌门菌的小鼠与移植了拟杆菌门菌的小鼠相比,长得更胖。Turnbaugh等在后续研究中,选择了肥胖和消瘦的双胞胎进行研究,发现肥胖和消瘦的双胞胎各自拥有不同的核心微生物基因组。肥胖会引起肠道细菌菌群发生“门”水平的变化,降低菌群多样性,并改变菌群的代谢通路。
肠道细菌可通过影响宿主自身免疫系统发育来影响宿主Ⅰ型糖尿病的发生率。Fei等将肥胖患者肠道内的一种产内毒素菌(Enterobacter cloacaeB29)接种给无菌小鼠后,小鼠出现了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同时,该研究组让患者服用全谷物、中药、益生元所组成的食物23周后,患者体内Enterobacter cloacaeB29的数量很快下降到检测不出的水平,同时体重由最初的174.8kg下降到了51.4kg,高血糖、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等也恢复正常。这一研究提示我们,采用以肠道菌群作为靶点的饮食干预,可能成为人类慢性病治疗的新途径。Qin等采用宏基因组关联分析的策略,对345位中国人的肠道细菌DNA进行了研究,发现Ⅱ型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中度失调,主要是产丁酸菌丰度降低,机会致病菌数量上升。在菌群功能方面,硫酸盐的还原功能和氧化应激抵抗能力增强。
(二)肠道细菌与消化系统疾病
1.炎症性肠病
目前普遍认为,免疫系统对肠道微生物的过度反应是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相关研究证实,回肠黏膜上皮侵袭性大肠埃希菌、副结核分枝杆菌与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的发生关系密切。研究显示,IBD患者肠道微生态的种属与健康对照者明显不同,细菌种类的改变会调节T淋巴细胞的自发性增殖及激活,引起肠道炎症,而肠道炎症又会加重肠道微生态失衡。Morgan等证实了CD患者肠道微生物中厚壁菌门和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的丰度会随着病情发展、治疗进程和个体状态的改变而发生改变。通过16SrRNA探针技术分析比较了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CD患者与其各自对照组肠道菌群的组成,发现UC和CD患者肠道益生菌群数量下降而致病菌群数量上升。其中,急性期UC患者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数量下降而小梭菌、肠球菌数量上升;急性期CD患者亦出现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数量减少,同时酵母菌、肠杆菌数量上升。
2.肠易激综合征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一种免疫-炎症模式的胃肠道疾病,肠道细菌所引起的宿主肠道局部持续性、低级别的炎症反应状态是该病发生的病理生理学基础。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肠道细菌过度繁殖可导致胃肠道动力失调及内脏神经敏感性改变,最终导致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生。IBS患者肠道微生态系统的组成与正常人相比差异显著,主要表现为:①肠道菌群种类减少;②肠道优势菌群数量下降;③肠道益生菌群数量下降。食物经肠道菌群代谢的产物如丙酸、醋酸等有机酸以及甲烷(CH4)等气体产物,也可影响肠道动力及肠道敏感性。Saulnier等通过对22位IBS患儿的粪便进行16SrDNA测序分析发现,与健康儿童相比,IBS患儿γ变形菌门含量显著增高;IBS患儿疼痛发作频率随另枝菌属(Alistipes)细菌丰度的增加而增加。分析IBS患者肠道菌群的组成,发现产短链脂肪酸的乳酸杆菌和韦荣球菌数量增多且肠内丙酸、醋酸的含量与IBS症状严重程度成正相关。
3.肝脏类疾病
肝代谢异常、慢性肝炎等肝脏类疾病也与肠道细菌有关。肝脏与胃肠道通过门静脉相互关联,门静脉中有来自肠道的细菌产物、食物抗原及环境毒素,肝功能受损时,肠道微生态及免疫可发生显著变化。Henao-Mejia等对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的研究显示,肠道细菌调节了由NAFLD引起的一系列代谢综合征。Chen比较了肝硬化患者和健康人的粪便菌群,发现肝硬化患者粪便内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数量显著降低,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和梭杆菌门(Fusobacteria)数量较多;在“科”水平上,肝硬化患者的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韦荣球菌科(Veillonellaceae)和链球菌科(Streptococcaceae)等潜在的诱发肝脏疾病的致病菌数量显著高于健康人群,但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等有益菌含量降低,这些变化也对肝硬化患者的病程产生影响。
4.结直肠肿瘤
肠道细菌被认为与人类宿主发生癌变有直接关系。最新的研究显示,微生物能够通过调节宿主发生的肠道炎症、影响宿主细胞基因组的稳定性以及产生特定的微生物代谢产物等方式参与到宿主发生癌变的过程中。在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方面,如丁酸、甲烷等可能在抑制结直肠肿瘤发展中发挥着有益的作用。其中,肠道细菌主要的代谢产物丁酸,可通过组蛋白超乙酰化来抑制肿瘤生长和诱导细胞凋亡。Wang等比较了结直肠癌患者与健康人群的肠道细菌发现,肠球菌(Enterococcus)、埃希菌/志贺菌(Escherichia/Shigella)、克雷伯菌(Klebsiella)、链球菌(Streptococcus)和消化链球菌(Peptostreptococcus)等属的细菌在结直肠癌患者体内较多,而罗氏菌属(Roseburia)和其他毛罗菌科的产丁酸菌较健康人群少。
肠道细菌可以使肠道黏膜促炎症反应的信号传导机制发生异常,从而加剧宿主肠道黏膜上皮损伤修复过程;某些肠道细菌群落会对宿主肠道黏膜上皮细胞产生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或通过旁观者效应对这些细胞发挥毒性作用;某些肠道细菌参与了宿主营养物质代谢过程,其代谢产物对宿主肠道上皮细胞会产生毒性作用。
(三)肠道细菌与心血管系统疾病
肠道细菌可通过激活Toll样受体信号传导通路,或生成代谢产物,如胆碱、氧化三甲胺和甜菜碱来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天然免疫系统具有抵抗病原菌进攻的炎症应答能力,这可能也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率升高的信号。基于这样的假说,研究者采用了益生菌对心血管疾病患者进行治疗。Bukowska等让患有胆固醇血症的患者服用乳酸菌(Lactobacillus)进行治疗后,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和纤维蛋白原水平显著降低。
(四)肠道细菌与神经系统疾病
肠道细菌可影响宿主行为和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已有研究证实,致病菌感染与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等常见神经发育障碍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一些研究显示,肠道细菌可以调节小鼠大脑发育和行为。Diaz等发现无菌小鼠与具有正常肠道细菌的SPF级小鼠相比,更具活力且焦虑行为减少,认为是肠道细菌定植启动了相关神经环路的信号机制。Bercik等发现肠道细菌能够影响宿主大脑的自律神经系统和肠道特异神经传导物质,认为肠道细菌微生态失调可能是患有肠道疾病的精神病患者精神失常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洪南,湛先保.肠道微生态系统与肠黏膜免疫关系研究进展[J].医学研究生学报,2014,27(4):444-446.
[2]刘玉兰.整合肝肠病学——肝肠对话[M].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3]王春敏,李立秋.人体肠道正常菌群的研究进展[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2010,22(8):760-762.
[4]胡旭,王涛,王沥,等.肠道共生微生物与健康和疾病[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2012,24(12):1134-1139.
[5]尚婧晔,余倩.肠道菌群代谢作用与人体健康关系的研究进展[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2012,24(12):87-89.
[6]Ley R E, Peterson D A, Gordon J I.Ec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forces shaping microbial diversity in the human intestine[J].Cell,2006,124(4):837-848.
[7]Hooper L V, Gordon J I.Commensal host-bacteria relationships in the gut.Science,2001,292(4):1115-1118.
[8]Power S E, O'Toole P W, Stanton C, et al.Intestinal microbiota, diet and health[J].Brit J Nutr,2014, 111:387-402.
[9]Kamao M, Tsugawa N, Nakagawa K, et al.Absorption of calcium, magnesium, phosphorus, iron and zinc in growing male rats fed diets containing either phytate-free soybean protein or soybean protein isolate or casein[J].J Nutr Sci Vitaminol,2000,46(1):34-41.
[10]Aidy S, van den Bogert B, Kleerebezem M.The small intestine microbiota, nutritional modulation and relevance for health[J].Curr Opin Biotech,2015,32:14-20.
[11]Akyol S, Mas M R, Comert B, et al.The effect of antibiotic and probiotic combination therapy on secondary pancreatic infections and oxidative stress parameters in experimental acute necrotizing pancreatitis[J].Pancreas,2003,26(4):363-367.
[12]Wiest R, Rath H C.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of the critically ill:bacterial translocation in the gut[J]. Best Pract Res C Ga,2003,17(3):397-425.
[13]Ley R E, Turnbaugh PJ, Klein S, et al.Microbial ecology:human gut microbes associated with obes-i ty[J].Nature,2006,444(7122):1022-1023.
[14]Turnbaugh P J, Ley R E, Mahowald MA, et al.An obesity-associated gut microbiome with increased capacity for energy harvest[J].Nature,2006,444(7122):1027-1031.
[15]Turnbaugh P J, Hamady M, Yatsunenko T, et al.A core gut microbiome in obese and lean twins[J]. Nature,2009,457(7228):480-484.
[16]Fei N, Zhao L.An opportunistic pathogen isolated from the gut of an obese human causes obesity in germfree mice[J].ISME J,2013,7(4):880-884.
[17]Wu H J, Wu E.The role of gut microbiota in immune homeostasis and autoimmunity[J].Gut M-i crobes,2012,3(1):4-14.
[18]Wen L, Ley R E, Volchkov P Y, et al.Innate immunity and intestinal microbiot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ype 1 diabetes[J].Nature,2008,455(7216):1109-1113.
[19]Qin J, Li Y, Cai Z, et al.A meta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gut microbiota in type 2 diabets[J]. Nature,2012,490(7418):55-60.
[20]Abraham C, Cho J H.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J].N Engl J Med,2009,361(21):2066-2078.
[21]Thibault R, Blachier F, Darcy-Vrillon B, et al.Butyrate utilization by the colonic mucosa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a transport deficiency[J].Inflamm Bowel Dis,2010,16(4):684-695.
[22]Morgan X C, Tickle T L, Sokol H, et al.Dysfunction of the intestinal microbiome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treatment[J].Genome Biol,2012,13(9):79.
[23]Henao-Mejia J, Elinav E, Jin C, et al.Inflammasome-mediated dysbiosis regulates progression of NAFLD and obesity[J].Nature,2012,482(7384):179-185.
[24]Chen Y, Yang F, Lu H, et al.Characterization of fecal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J].Hepatology,2011,54(2):562-572.
[25]Greer J B, O'Keefe S J.Microbial induction of immunity, inflammation, and cancer[J].Front Physiol, 2011,1:168.
[26]Bultman S J.Emerging roles of the microbiome in cancer[J].Carcinogenesis[J],2014,35(2):249-255.
[27]Grahn N, Hman-i Aifa M, Fransen K, et al.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of Helicobacter DNA present in human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s by 16S rDNA PCR amplification and pyrosequencing analysis[J].J Med Microbiol,2005,54(11):1031-1035.
[28]Wang T, Cai G, Qiu Y, et al.Structural segregation of gut microbiota betwee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nd healthy volunteers[J].ISME J,2012,6(2):320-329.
[29]O'Keefe S J, Ou J, Aufreiter S, et al.Products of the colonic microbiota mediate the effects of diet on colon cancer risk[J].J Nutr,2009,139(11):2044-2048.
[30]Saulnier D M, Riehle K, Mistretta T A, et al.Gastrointestinal microbiome signatures of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irritable bowel syndome[J].Gastroenterology,2011,141(5):1782-1791.
[31]Kiechl S, Lorenz E, Reindl M, et al.Toll-like receptor 4 polymorphisms and atherogenesis[J].N Engl J Med,2002,347(3):185-192.
[32]Bukowska H, Pieczul-Mroz J, Jastrzebska M, et al.Decrease in fibrinogen and LDL-cholesterol levels upon supplementation of diet with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in subjects with moderately elevated cholesterol[J].Atherosclerosis,1998,137(2):437-438.
[33]Diaz H R, Wang S, Anuar F, et al.Normal gut microbiota modulates brai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J].P Natl Acad Sci USA,2011,108(7):3047-3052.
[34]Bercik P, Denou E, Collins J, et al.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affect central levels of brain-derived neurotropic factor and behavior in mice[J].Gastroenterology,2011,141(2):599-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