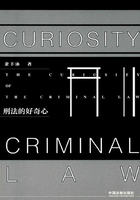
通奸的罪与罚
1
有这样一些罪名,平日只是待在刑法条文里,几乎没有检察官或法官来光临拜访,但一旦要让它们挪位,请它们离开,则又要引起轩然大波,通奸罪即是其中一位。
从晚清立法开始,几乎每一次的刑律修订,都会在此处引发一番论争。
清末修律,《大清新刑律》是新法中的重要一部,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部。礼法两派针对新刑律草案闹得不可开交。跟修律大臣沈家本站在一边的杨度、汪荣庭等人,都是到东洋喝过洋墨水的,更有日本人田朝太郎等人助阵。那厢的礼教派则是赫赫有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劳乃宣等人,亦非等闲之辈。虽然礼教派步步退让,但关于无夫奸(身份限定于在室子女、寡妇甚至尼姑)和子孙违犯教令两项,则始终坚守,并获最终的表决支持。这一次论争中有夫之妇通奸则不在讨论之列,第一回合,毫无疑问,是保留通奸入罪派胜。
然而新刑律还没实施,清政府就倒了,匆忙打响的辛亥革命,场面自然也是一团糟,民国的立法者们也就无暇坐下来再论争一番,因此革命后的《暂行新刑律》基本就抄袭了末代王朝的成果,关于通奸罪规定如下:“和奸有夫之姓者,处四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相奸者,亦同。”
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出台,这一回废除通奸派又站出来了,据理力争,争论的结果是:“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罪名仍然存在,但处罚减去了一半,也算是半个胜利吧。
1936修订的《中华民国刑法》通奸罪名不变,只是悄悄地将有夫之妇改作了有配偶,“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相奸者,亦同”。最起码在法律条款上做到了男女平等,而且在处罚上又轻了不少,最高刑期又减去了一半。
到了1949年,众所周知,国民党败走台湾,也带走了《中华民国刑法》,通奸罪也就沿用至今。而在大陆这边,包括这部刑法在内的《六法全书》全部被废止停用,新中国的刑法则干脆地废除了通奸罪。
2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甚至还有些吊诡。集体主义道德观念关照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通奸除罪化了,但追求个人自由崇尚享乐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台湾地区却保留了通奸罪。是不是台湾社会要比海峡对面的大陆更加保守呢,虽然如何判断一个社会风气的开发程度并不容易,不过仅从两岸综艺节目的尺度来看,海峡对岸显然更为开放,所以,结论应该相反才是。
还不止如此,在台湾地区,对于通奸罪不仅有刑法约束,还有配套的民法措施。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986条规定:因奸经判决离婚或受刑之宣告者,不得与相奸者结婚。(这与1943年《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第9条基本相同,不过是将相奸者改为相好者)第993条规定:结婚违反第986条之规定者,前配偶得向法院请求撤销之。法律对奸夫淫妇的痛恨,真是令人想不到和忍俊不禁。虽然这条法律现已删除,但那也已经是20世纪末的时候了。更有甚者,可参考我国元代的法律,其中有一关于“杀奸权”的奇葩规定:“诸妻妾与人奸,本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并不坐。但若于奸所杀其奸夫而妻妾获免,杀其妻妾而奸夫获免者,杖一百七。”
如今台湾游正热,不过在我看来,游台湾不纯是为了自然景色或海岸风光而去,这些景致,疆域辽阔的祖国大陆并不缺乏,而且往往更胜一筹。台湾与大陆同宗,它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经由60多年来的政治隔阂,为我们展示了另一条道路的风景,无论是繁体字、竖排版的书籍和文化,还是不同政治体制下的治理风格。
法律的变化总体上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但社会变迁是一个宏大叙事,将其充当理论解释的万金油,对于智识的帮助不大。我们大致上认可,社会变迁总体上是缓慢而平稳的,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来看的确如此,但若截取社会变迁中的某些片段,往往会发现,这种变迁并不是缓慢地自主演化着,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而可能是一个或数个突出的因素搅乱或主导了变迁的方向。
这些因素包括但不仅仅包括执政者的更替或社会制度的革新。实际上,政治革新或朝代更新对于法律的变革效用不容忽视,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每次朝代的更新换代,都会颁布新的法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法律往往成为一种引导社会变革的工具,不是按部就班地将现有的习惯、惯例上升为法律,或者经过社会生活的长期发酵来制定和完善法律,而是由立法引导社会变革,期待法律的革新给予民众启蒙。由此来看通奸罪在两岸刑法中的不同境遇,反而是政局上的原因更加不可忽视。社会风气开放程度、道德和法律的剥离程度、人们对于不同性行为的认识及宽容程度,并非当然地成为通奸罪存废的主要原因,虽然从直觉看来,它们与通奸罪的存废有着更强的关联度。
一个小插曲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今昔对比。曾经是中国卓越法律人士的集散地,东吴大学以其英美法的研究著称,它之所以衰落并非后继乏人,或者地理位置不在北上广,而是因为1949年之后整个政法制度的倒转。对于法律这样的学科而言,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但它的地域范围实质上是政治统治的边界,政治体制层面的变化,无疑立刻使得曾经的那一套知识体系不仅不受重视了,而且也没有了用武之地。所以,那一批曾经叱咤风云的法律精英,等到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时候,几乎已是耄耋之年,他们最后的心愿也只能是关于一部英美法系法律词典的编撰了。
3
回到前文中所述的通奸罪条文,通奸罪的流变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男女有别,法律一直以来都是明显偏袒男性,直到晚近时期,大概由于妇女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女权主义者的觉醒,才逐渐在处罚程度上达到男女平等。这种差别,不单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中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刑法也无法脱离这个窠臼,比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中就有规定:妻通奸罪处三月以上两年以下徒刑,夫于家里容宿姘妇者处一百至两千法郎罚金。
这种男女有别,特别是对女性要求严苛,很久以来一直被看作专制社会对于女性的压制,反映了男权社会的特点,因此不只被女权主义者所诟病,也为社会各界所不能忍受。如今这个社会,女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以往男性才能从事的职业中,“女人早已能顶半边天”,看看国际政治就知道了,女总统、女总理现身政坛仍然令人振奋,却早已不再鲜见。尽管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为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我们仍然不可忽视的是,男女毕竟有别。波斯纳就在《性与理性》里对通奸罪的这个处罚差别做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见解,他认为男女通奸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关键在于女人通奸是有产出的,容易出现非婚生子女。在一个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还没有诸如DNA之类的亲子鉴定,只要是在婚后出生的子女,就很难断定这个孩子是否与其母亲名义上的丈夫有血缘关系,因此,她的合法丈夫很可能要为不是他所生的孩子担负起抚养教育的责任来。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落后的时代,人们最多只能怀疑,而不能确证孩子到底是不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而男性则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相反的是,如果他在通奸中使得女方怀孕,反而不用他自己就有另一个男人替他担负起这个责任,从生物的本能来讲,雄性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嗣越多越好,以便自己的基因能够得到继承和延续。
纯粹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很多事物都是具有生物学上的动机,通奸的差别对待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婚姻家庭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与此类似,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有点惊愕却难以否定的解读。苏力在法理学课堂上解读过为什么婆媳关系总是难以处理好,而翁婿之间则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后者还有一句俗语帮衬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抛开其他因素不言,生物学上的这两种关系其实是很不同的,对于婆家来说,媳妇的孩子肯定是媳妇的,但有可能不属于自己家的血脉,而对于娘家来说,不管女婿是谁,女儿的孩子总是自己家的。这个解答似乎太赤裸裸了一点,但与自私的基因的策略是吻合的。
从这个角度,基于经济学甚至是生物学的层面,而不是道德评判来看待通奸罪的处罚不公,我们能够获得另一种新的认识,反而加深了对法律深处的理解,尽管不一定全对,但毕竟有道理。“若是我们发现一种制度不能满足人某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并不必姑息它,或隐讳它,但是要了解它所以然的苦衷。”(费孝通语)比如,在另一个男女有别的继承权上,对于农耕社会来说,实际上单系继承是更便于实施和节约成本的,如果双系继承则要带来很大的麻烦。假如一个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父母将家里的一块地分给两人,而女儿终究是要嫁人的,但地却不能带走,管理田地就成了一个问题,况且土地的分割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即使她没有得到自己父母的财产,但她却得到了她的丈夫的姐妹的份额,这样从整个社会来看,这种继承方式大体上仍是公平的。
还可以沿着波斯纳的视角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大都认可女人更重视情感大于性爱,男性则相反,如果这个前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对于女性来说,把情感和性分开来,要相对困难一些,也就是说女性更容易在婚外性活动中投入真情实感,这种投入会分担她们原本用在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身上的关注和照看,她们也许对丈夫、孩子和家庭都不怎么用心了,相比较男性而言,女性通奸更容易消耗掉家庭资源,不仅是物质上的,更主要的是情感上和精神上的。其实这个思路,仍然是经济学角度的,情感投入也是一种成本,甚至它并不纯粹是精神上的,也会带来间接的物质消耗。这很容易明白,一个小伙子向心仪的女孩表达爱慕,总不能光靠甜言蜜语,而玫瑰花却是要花钱买的。
不同的是,如今科学技术要比过去发达多了,血缘关系很容易通过科技手段做出判断。因此,女性通奸的额外产出就不再那么隐蔽了,废除这种差别实质上与社会现实的改变是相吻合的,尽管这种吻合,很容易被争取妇女权利运动或女权主义者揽去了功劳。
4
尽管通奸罪在两岸的境遇不同,也尽管通奸罪在某些国家仍然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对通奸罪的处罚大不如前了,有时候它仅仅是写在法条上的具文而已了。一方面,是个人权利事业的兴起,人们对私人权利更加看重,通常通奸行为中的男女双方都是自愿的,尽管道德上受到谴责,但法律却不能再插手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法律控制的范围,表面上受制于大众的道德伦理,但背后是隐含着经济学上的道理的。
如今人类的生活已经迥异于以往的任何时候,人际交往中的陌生化、通信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都使得单就通奸行为,比以往更加隐蔽,更加难以被发现,或者说发现的成本大大增加了。我们不再生活在一家一户的小村落里了,而是城市化的陌生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甚至私会都不需要面对面或者书信往来,借助移动电话和网络,这种交流上的便捷和即时不言而喻。通奸行为的隐蔽性使得司法机关的侦查成本无限地增加了,在一个司法资源总是有限因此不能力往多处使的情形下,司法放松或放弃了对这种行为的追究,就不会令人难以理解了。而且,法律控制放弃的地方,并非等于也不受其他力量的控制。对于通奸行为来说,最好的监控者仍然是作为个体的配偶,也只有朝夕相处的夫妻才能敏感地从对方身上的不同味道或一根头发中发现到蛛丝马迹。
古代就大相径庭了,即使是西门庆这样的大官人,要与潘金莲私会,每次还得通过王干娘搭个桥,以至于街坊四邻谁人不晓呢,就连卖梨的郓哥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一个小范围的熟人社会中,发现通奸相对要容易得多,几乎很难有偷腥不被发现的,不被发现的也只有武大郎这样的局内人了,而旁人早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对于通奸行为以及其他涉及私权利的类似行为,通常都有法律无权干涉人们的私生活这样的道德话语的包装,但道德话语常常是一种伪装。借助于简短有力的语句、直接的思维方式,使得道德话语的表达和传播变得迅捷,它最容易让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这是它所具有的优势。但正是这种优势,减弱了对逻辑上的要求,虽然裹挟着民意,但很多时候,并不必定代表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