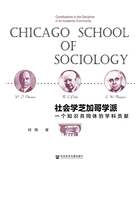
第1节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中国缘分及其再续
一 断裂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中国缘分
按理说,芝加哥学派与中国社会学界的渊源极深:其一,巅峰时期学派的灵魂人物帕克应吴文藻先生的邀请曾于1932年秋在燕京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带领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学生们实地考察中国社会。费老在《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中明确指出,帕克先生的中国之行对包括费老在内的年轻学生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费孝通,2001: 206~337)。实际上,早在1925~1926年,帕克就曾在考察环太平洋沿岸各国的旅途中来到过南京,这是他研究环太平洋沿岸亚裔美国人(主要是日本人)社会适应项目的一个部分。燕京之行应该算得上是帕克先生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其二,另一个为学者们熟知,但是又常常在社会学领域中失声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亦曾来到中国讲学。要知道,在20世纪初期,杜威可是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首席教授,其倡导的实用主义哲学直接塑造了芝加哥学派面向社会现实的学术品格。无论是帕克还是杜威,这些和芝加哥学派存在密切关系的学术大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或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社会学产生影响。在笔者看来,人们之所以并未把杜威、芝加哥学派和中国社会学联系起来,一方面是由于杜威的身份是哲学家;另一方面杜威是在1919年年初来到中国的,其时中国社会学仅仅是初现端倪,尚未形成气候,学术界对社会学缺乏明确的认识。正是这双重因素导致了国内社会学基本上没有看到杜威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间接影响。其三,巅峰时期的芝加哥大学曾为中国培养出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即吴景超先生。吴先生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具有典型的芝加哥学派特质(吴景超,1991)。但是,遗憾的是,吴先生这样一个芝加哥学派直接的中国传人并未能扩大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原因极为复杂,在笔者看来,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吴先生本人的原因。回国之后,吴先生提出了“第四种国家”的想法,以此探索中国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这无疑体现了吴先生作为学者的时代使命感,但是,这也使得吴先生把精力集中于政治论争而无法像芝加哥学派的前辈那样把精力投入到具体的问题研究之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费先生,投身于乡村研究的他写出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著述《江村经济》和《生育制度》(费孝通,2001),不仅深刻地探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及其转型特征,而且也为后来者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与方法论借鉴。另一方面是当时社会学界人才结构客观状况上的原因。作为移植过来的西方学科,主要是欧美大学培养了中国社会学界的第一批人才。尽管吴景超先生是正牌芝加哥学派传人,但是,在国内还属于独苗,相反,在民国时期,影响中国社会学风格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传统,如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博士朱友渔191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此外,孙本文(1894~1979)、李景汉(1894~1986)、陈达(1896~1975, 1923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潘光旦(1899~1967)、吴文藻(1901~1967, 192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等都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其中孙本文先生是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社会学专业的部颁教授,主编的教材是教育部在全国推荐的标准社会学教材(阎明,2004: 27~33)。 其四,民国时期求学于美国的社会学大家大都通过不同方式接受过芝加哥学派的间接影响。除了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吉丁斯(季廷史)的影响之外,孙本文还受到法里斯(发利斯)、帕克(派克)、托马斯的影响;言心哲(1898~1975)在芝加哥大学毕业生鲍格达斯(鲍格度斯)门下接受社会学训练(阎明,2004: 27~33)。芝加哥学派对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产生间接影响的典型代表是吴泽霖(1898~1990),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他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具有典型的芝加哥学派风格。除了研究主题是芝加哥学派的经典研究领域——种族歧视与移民美国化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该研究引用大量芝加哥学派学者,如沃斯(韦斯)、伯纳德、帕克、伯吉斯、鲍格达斯(博加德斯)、约翰逊、弗雷泽、托马斯等的研究著作,尤其是频繁引用弗雷泽、约翰逊的黑人研究著作。此外,在全书的总结部分——第6~8章更是直接应用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距离、族群歧视、种族隔离等概念作为分析框架(吴泽霖,1992)。可以看出,无论从哪个层面看,芝加哥学派都是中国社会学传统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源头,但是,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芝加哥学派并未得到中国社会学界的积极响应。
其四,民国时期求学于美国的社会学大家大都通过不同方式接受过芝加哥学派的间接影响。除了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吉丁斯(季廷史)的影响之外,孙本文还受到法里斯(发利斯)、帕克(派克)、托马斯的影响;言心哲(1898~1975)在芝加哥大学毕业生鲍格达斯(鲍格度斯)门下接受社会学训练(阎明,2004: 27~33)。芝加哥学派对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产生间接影响的典型代表是吴泽霖(1898~1990),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他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具有典型的芝加哥学派风格。除了研究主题是芝加哥学派的经典研究领域——种族歧视与移民美国化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该研究引用大量芝加哥学派学者,如沃斯(韦斯)、伯纳德、帕克、伯吉斯、鲍格达斯(博加德斯)、约翰逊、弗雷泽、托马斯等的研究著作,尤其是频繁引用弗雷泽、约翰逊的黑人研究著作。此外,在全书的总结部分——第6~8章更是直接应用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距离、族群歧视、种族隔离等概念作为分析框架(吴泽霖,1992)。可以看出,无论从哪个层面看,芝加哥学派都是中国社会学传统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源头,但是,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芝加哥学派并未得到中国社会学界的积极响应。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走上了重建之路。在学科发展遭受近30年中断的背景下,社会学再次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但是,受制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对西方社会学的学习主要是借鉴其研究方法与基础性社会理论,缺乏对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深入认识。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西方社会学标准教科书中的各种理论,但是,并没有洞悉各个理论流派之间的关联与分歧。尤为重要的是,人们并不知道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道路在哪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费孝通提出了社会学的“补课”任务,身体力行地向人们讲述他理解的芝加哥学派及其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具有的借鉴意义与价值。当然,费先生对芝加哥学派的介绍也较为简单,主要集中于学派的灵魂人物帕克身上。遗憾的是,费先生的呼吁并未得到人们的广泛响应。时至今日,国内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除了费先生的若干文章之外,就是他的学生于长江撰写的芝加哥学派方面的专门性论著,即《从理想到实证:芝加哥学派的心路历程》(于长江,2006)。另外,周晓虹亦曾发表过若干篇芝加哥学派文章,以及他的博士生胡翼青在2006年出版的《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胡翼青,2007)。
影响美国与西方社会学现代走向、塑造社会学经验品质的芝加哥学派一直引发人们的浓厚兴趣,也不断激发人们的研究热情,成为后发国家与地区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典范。但是,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是在改革之后,芝加哥学派都没有在中国获得应有的重视与深度的研究。时至今日,在标准的中文版社会学教科书或者社会学史教材中,人们对芝加哥学派的介绍或者极为简明或者语焉不详,如无论是刘玉安主编的《西方社会学史》还是刘豪兴主编的《国外社会学综览》都没有介绍芝加哥学派,仅提及了斯莫尔、托马斯和帕克等人,而王康主编的《社会学史》仅仅对芝加哥学派做了简要的介绍,贾春增的《外国社会学史》在论述美国社会学本土化时扼要地提及了芝加哥学派。此外,无论是谢立中主编的《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还是文军新近主编的《西方社会学经典命题》等西方社会学通识读物,基本上都对芝加哥学派采取了无视态度(刘玉安,1993;刘豪兴,1993;王康,1992;贾春增,2000;谢立中,2007;文军,2008)。总体来说,目前社会学教科书或者把芝加哥学派扔进了历史故纸堆中,或者提供一些同质性、碎片化的简介。就碎片化而言,不仅体现在对学派主要人物完整性思想的割裂上,而且表现为社会学子领域各取所需,仅仅把芝加哥学派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内容做简要的陈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芝加哥学派,如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社会心理学芝加哥学派、犯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等。此外,一个常见的谬误是一提及芝加哥学派,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托马斯或者帕克,也许会想到伯吉斯,不过,基本上不会想到博士生。尽管托马斯、帕克和伯吉斯搭建了芝加哥学派的基础性骨架,但是,赋予学派以具体血肉、鲜活生命的正是一届又一届的博士生,他们开展的实地研究把教师们抽象的、睿智的思想转化为具象的、可感知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托马斯、帕克和伯吉斯的学术洞见与无私奉献,那么就不会有芝加哥学派的参天大树;同样,如果没有众多杰出博士生身体力行地付诸行动,那么芝加哥学派之树也不会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芝加哥学派不仅是教师和学生精诚合作的产物,而且也是他们心智交流的结晶。虽然人们可以根据研究主题把芝加哥学派划分为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城市犯罪学,等等。但是,无论是研究城市,还是研究人的行为,抑或研究社会病理现象,这些研究主题都共享着相同的价值取向、研究方法、理论架构,或者说,学派的不同子研究领域都有一个共同的“元叙事”,这是那些割裂了芝加哥学派内在统一性与整体性联系的人所看不到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本书拟在历史演变和理论贡献两个层面向人们描绘出芝加哥学派的内在关联及其主要贡献。“历史演变”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厘清芝加哥学派形成、繁荣与由盛而衰的连续性历程;“理论贡献”的基本任务是要澄清芝加哥学派在不同领域中的主要贡献,进而指出串联起芝加哥学派不同领域的精神内核。
二 再续学派前缘:努力及其意义
为什么要研究芝加哥学派?如何研究芝加哥学派?研究芝加哥学派的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在研究芝加哥学派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之所以研究芝加哥学派,既是出于理论发展连续性方面的考量,又是出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现实。周晓虹教授曾引用一则笑话来说明社会科学发展史的重要性。踌躇满志的自然科学家不屑一顾地对社会科学家说:“看,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已经将宇宙飞船送上了天,而你们却在谈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此,社会科学家回应道:“这不更说明我们的话题是亘古常新的吗?”(周晓虹,2002:序1)这则笑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科学发展的独特性:与通过否弃前辈理论及其假设而催生新的学科“范式”以推动学科发展的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必须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继承与发扬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求而发展。罗伯特·默顿曾引用两个人的话来表达对这一问题的辩证看法:一个是英国社会科学家艾尔弗雷德·怀特海的名言——“一门科学,如果不能果断地忘掉其创立者的话,就会迷失方向”;另一个是挪威数学天才尼尔斯·阿贝尔的名言——“我认为,一个人要想在数学上有所成就,他就应该向大师学习,而不是向学生学习”(刘易斯·科塞,2007:序4)。在这里,如果脱离上下文就会对怀特海的话产生误解,即容易认为沉醉于思想史研究的他居然把思想史知识视为一文不值。事实上,怀特海是在向人们发出警告:如果我们一味地赞美创建者,而不试图通过持久的努力来发展他们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墨守成规,无法增进知识的积累。由此,为了正确对待前人的成果或许应该通过重温歌德的告诫:“你必须把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赚过来,才能占有它。”(刘易斯·科塞,2007:序4)人们不仅要重温前人的知识遗产,而且要设法将之化为己有。这也是研究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意义所在,即研究芝加哥学派、考察学派思想家的心路历程可以让我们真正地融入社会学学科活生生的生命历程中。
除了理论上的考量外,研究芝加哥学派也是顺应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趋势使然。中国社会学学科的缘起受到了芝加哥学派的直接影响。1932年,应吴文藻先生的邀请,帕克先生来到北京进行讲学和开展研究活动,标志着芝加哥学派正式传入中国。尽管费孝通先生尚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但是,在听了帕克的课程之后也深受震动,甚至在晚年进行社会学“补课”时还重温帕克的著作。帕克的中国之行直接影响了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对此,费老曾说过:“吴文藻和帕克这两位老师是我一生从事社会学的源头。”(费孝通,2001: 210)1985年,费老的社会学入门教师吴文藻先生在去世之前,曾对家人说要将自己的一部分藏书送给得意门生费孝通先生,具体的书目由费老挑选,结果费老就挑出了帕克的《社会学科学导论》和《城市》两本著作。在费老看来,之所以挑出这两本书,原因在于,“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我一生从事社会学的源头,留此实物作为纪念,永志不忘。没有预料到今天这两本书竟是老师留下的为我当前 ‘补课’的入门。”(费孝通,2001: 210)当然,费老在晚年之所以不惜浓墨重笔向国内学者介绍帕克,根本原因在于帕克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深远影响(孙平,2005)。当年燕京大学学生在编辑《派克社会学论文集》的序言中曾对帕克做出如是评价:“先生在此短促的时间中,传给我们的绝非书本的死知识,而是一种大生命的鼓舞;听讲者受其陶冶诱导,无不油然沛然,尽发其蓄积的潜力,以从事于学问的探讨。我们今日之所以起始追求学问的意义和本象,可以说完全是先生所启发的。”(费孝通,1999: 21)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渊源之一,芝加哥学派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学思想宝库的一部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学。”(费孝通,1999: 21)芝加哥学派通过三种途径或层面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其一,通过帕克对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如费孝通、吴景超、吴泽霖等人影响中国社会学。其二,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学科关切领域。临别中国时,应燕京大学学生的要求,帕克撰写《论中国》一文。文中认为,城市是西方的社会实验室,而乡村则是东方的社会实验室;现代西方的社会问题是城市问题,而东方的社会问题则是乡村问题(派克,2002: 18~19)。可以说,延续至今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强乡村、弱城市”传统的历史根源或许就在这里。其三,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品质。帕克提出了实现“社会学 ‘中国化’的具体方法”,即开展社区研究。在吴文藻先生的支持下,源自芝加哥学派的实地研究方法成为下一代中国社会学家研究中国社区的主要研究方法。帕克在燕京大学的讲课历时3个月——从9月到12月,主要开设了“集合行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两门课程。费孝通先生晚年回忆说,帕克的讲课内容对中国学生的触动尤大,“社会学研究方法”是最令学生们兴奋的课程。“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课堂上说的第一句话:‘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教你们怎样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这句话打动了我的想象力,开了我们的心窍。”(费孝通,2001: 213)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帕克还时常带领学生在现实中体验理论,不仅到民间的贫民窟、“八大胡同”中去,而且还带领学生参观监狱。由此,帕克把芝加哥学派的质化研究传统移植到了中国。
在塑造“社会学中国学派”的过程中,早期的社会学先驱们表现出了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特别关注,其原因就在于芝加哥学派表现出来的理论特质与研究关怀切中了中国社会的客观现状。时至今日,我们之所以重新回顾芝加哥学派,亦是因为与之共享相同的或相似的社会文化环境。自1978年始,中国社会学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这也恰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30多年。在民族复兴的恢宏历史进程中,中国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不断遭遇新的困难、面临新的问题,为社会学学科提供了大有可为的时代舞台。不过,虽然30多年间中国社会学学科已经由重建之初的蹒跚学步发展到时至今日的初具雏形,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学与恢复重建后的社会学存在发展脉络与历史使命上的重大断层,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表现出非连续性、断裂性特征,社会学学科发展缺乏足够的历史底蕴与知识积累,因此,重温与中国社会学学科存在直接关联、对中国社会学学科产生重大影响的芝加哥学派,不仅可以为未来社会学学科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而且还可以为人们重新认识学派这一知识共同体在学科发展中的意义提供新的启迪。
从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学科与学派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学派是学科的直接推手。美国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社会学界长期独占鳌头,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为社会学学科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流派,如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哥伦比亚学派、符号互动论者、冲突论者,等等,生生不息、延绵不绝。反观今日中国社会学界之现状,对照是醒目而刺眼的:在重建30多年之后,尽管中国社会学呈现出勃勃生机,但是,尚无一个获得学界同人共同认可的、能够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流派。更为糟糕的是,在中国学者从事社会学研究更像是一种“个体户”行为,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埋头苦干。但是,学术是一项知识分子的共同事业,无论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功能主义的哈佛学派,等等,这些对社会学学科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派都不是一个人的成就,相反,都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集体事业。只有在知识共同体的集体努力之下,才能催生社会学学科深入发展的强大动力,才能增进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历史底蕴,也才能为学科的后来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基于此,回溯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的芝加哥学派,对于反思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个体化” “碎片化” “巴尔干化”,彼此隔离的现状是不无裨益的;也希望由此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呈现流派纷呈、思想争鸣的新格局,不仅具备进行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而且还能对民族再兴的时代使命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