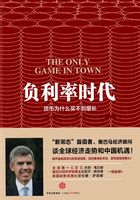
第二章 当今世界唯一的主导力量
有时候正是那些最意想不到的人,能做出最超乎想象的事。
——电影《想象力游戏》——
近几年来,货币政策一直是第一世界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甚至常常是唯一的支持工具。
——《经济学人》——
巴黎,11月里令人心情舒畅的一天,受人尊敬的法国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安·诺亚(Christian Noyer)参加了法兰西银行的国际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央行:前进的方向?”,央行界的精英们云集于此。虽然法兰西银行的会议室更加富丽堂皇,但由于正在装修翻新,2014年度的这届盛会选择在威斯汀酒店举行。
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央行行长们促膝而坐。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和其他分行总裁们聚在一起。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印度央行行长拉格拉姆·拉扬(Raghuram Rajan),以及非洲、亚太地区、拉丁美洲、中东的央行行长们也出席了研讨会。
许多重要学者、思想领袖、货币政策的评论家们也参加了这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聚会。来自主要金融机构的私营部门的代表们作为媒体成员也出席了会议(场地有限,他们大部分人只好坐在阳台,眺望着已经人满为患的房间)。
会上,诺亚行长阐述了现代央行的优劣势,在承认“央行已经被看成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主导力量”的同时,他想知道是否“被寄予厚望的央行在将来(有可能)会让人们大跌眼镜”。1
与会者们当然无法知道,仅仅在几周之后,央行世界将会发生动荡,这个动荡并不是由大型机构的行为引发的,而是由小机构出人意料的突发行为引起的。这些小机构的品牌和声誉多年以来——至少在央行动荡之前——都被小心呵护着,它们就是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代名词。
几周之后,瑞士央行突然宣布准备取消其汇率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这个做法后来被证明对市场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新加坡改变了汇率体系,丹麦宣布控制政府债券的发放规模。
之后的几周,这些人见证了国债市场收益率的暴跌,比如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0.05%;他们还看到了投资者们同意不要利息甚至甘愿接受负利,就为了急于从一些欧洲国家直接购买新发行的国债;他们也见识了大型银行积极地劝说储户们不要存钱的做法。
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情况发生。长期以来,瑞士法郎被视为坚挺的货币,就在瑞士央行努力遏制瑞士法郎上涨的同时,瑞士的负利率结构超越了德国。甚至像意大利和西班牙这种欧洲国家,他们发行的那些利率“风险”更大的政府债券,利率也降到了历史超低水平。然而希腊,这个“欧洲外围”国家,面临的将是经济崩溃以及无力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上少数几个优先债权人之一——的贷款的风险(最后希腊确实在短期内拖延了还款)。
再来说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连瑞典银行也步丹麦和瑞士的后尘,执行负的政府利率。那么公众对此又是如何评论的呢?一位观察家指出,这种做法“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参考”,“就像学习倒着开车一样,绝非易事”。2
现代央行和全球金融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受人为因素影响更大,更加畸形扭曲。这个发展方式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令人既着迷又困扰。
回想一下我这些年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专业工作经验以及对经济学的研究,我对央行及其对社会经济福利的贡献深感敬佩。它们在所有运转良好的经济生态系统,特别是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这些神秘的机构维持着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却常常被世人曲解,这些年来,我对它们的感触颇多。在价格管理和货币数量控制、遏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以及避免金融风险方面,央行发挥着关键作用,那些才华横溢的技术官员把心血都投入到了这么重要的工作当中,我对他们无比尊重(然而他们的付出常常被低估)。
央行承担的政策负担日益沉重,我对此越来越觉得焦虑,这势必会对央行未来的信誉、影响力和声誉造成影响,它们的经营前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央行就一直在努力抑制市场波动,并且推出了“流动性辅助增长”的操作模式——这指的是由于特殊的流动性注入而带来的金融市场的繁荣最终导致的经济增长。然而,央行的这种不懈努力却无法足够迅速地过渡到真正的增长和有序的政策正常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政客也在寻求控制央行经营自主权的方法——这个自主权对央行的影响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央行受形势所迫走上了冒险之路,甚至更深入地探索自己不熟悉的、复杂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领域。它们把利率压至最低,大力干预市场运作,通过买入证券这种大规模的项目来排挤其他银行;更有甚者,有的央行还以咄咄逼人之势,试图操纵投资者的预期和投资组合决策。
因为这一切太背离常态,因此无论是央行还是其他银行,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都没有现成的测试用例的脚本可参考,也没有历史经验可借鉴。这不仅是当下一段时间内的一种大胆的政策实验,更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有鉴于这一切,我很快意识到,在这个巴黎的房间里,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焦虑的人。迫于压力的央行将会如何运作?对此,我们当中很多人内心都感到不安,都想弄清未来前景如何。
研讨会的组织者在当天会议主题的最后划上的那个问号,也将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表露无遗:“央行:一路向前?”在全球经济、市场以及政策管理的最重要的盛会上,会议组织者们发出了正确的不确定性信号,房间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和金融领域。受其影响的还有相应的制度、政治、地缘政治和社会问题。
央行总是有一种肩负着“道德与道义”的使命感,因此不得不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它们所面对的问题,都是其他决策机构无力且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尽管这些机构的政策“武器库”中的工具才更适合解决目前的各种问题。不知何故,现在的世界完全依赖于央行的机构设置,而央行手中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却又极为有限。
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终于发现,它们不得不承担起比预期更多且持续时间更长的工作。理智告诉它们要立刻停止这种“实验”,开始进行政策规范化,但心却在敦促它们别停啊、继续做下去啊,并且还时不时地在“锦囊”中寻找些新玩意儿。
据我所知,尚无人能精准预测出这个政策困境的范围和影响究竟有多大。
从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一天起,人们就寄希望于英勇无畏、反应迅速的央行,盼着央行能成功地把接力棒传递给高增长的经济、强劲的就业增长、稳定的价格以及稳健的金融体系——无论这种传递是直接的,抑或更有可能是通过争取足够的时间让私营部门恢复元气、让其决策部门有能力帮助当权者加强经济管理责任感。随着经济繁荣和就业率回升,世界就能够在中期内摆脱债务问题的困扰,避免对无序去杠杆化、毁灭性紧缩以及债务违约的需求。
值得赞扬的是,央行早已认识到这种做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2010年8月,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镇举行了一次年度会议,世界各地的央行家和他们的贵宾们云集于此。会上,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这次演讲标志着美国货币政策的支点的确立——从以金融市场的标准化为目标到央行要承担起主要和重要的责任,以提供经济的高增长、就业、稳定的低通货膨胀和整体金融的稳定性。他观察到,运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带来的不只是“收益”,更有“成本和风险”。3这种政策执行的时间越久,带来的成本和风险就越有可能超出收益。
人们的关注点已经远远超出了非常规政策提供的预期政策结果失败的可能性,包括被称为“经济腾飞”或者“逃逸速度”的那些东西。人们对于这些事情之外的问题忧心忡忡,这些忧虑有的有用,有的是瞎操心。
央行会延长实验期吗?它们会打算进一步行动吗?它们的这些做法会成为执政者和决策机构的负面刺激而让他们齐心协力团结起来吗?金融资产的人工定价行为多次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推动——毕竟,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央行是市场最好的朋友,但这会导致过度冒险和大规模资源分配不均,最终损害增长和稳定吗?一波猛烈的通货膨胀即将到来了吗?央行会迫于压力不得不卸载掉资产负债表,以致对企业价值和金融市场造成损害吗?受抑制的波动性最终会让步于“波动的波动性”吗?4
这些问题还在不断地涌现出来,但说到底还是下面这个根本问题:在从一个解决方案的主要部分向一个问题的重要部分过渡的过程中,央行的风险应该控制在什么程度?也就是说,与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循序渐进地推进去杠杆化的做法相比,央行最后还是会选择造成额外债务积累的结局,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加乏力,再加上经常性的金融不稳定,还会破坏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福利,包括管理良好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的忧虑不仅限于经济和金融方面,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
房间中的欧洲人都很清楚,欧洲国家经济不景气是如何加剧政治极端主义和非传统政党(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出现的,都不用从经历过早些年茶党运动的美国人那里道听途说,他们会亲身体验到反对当局的候选人的卷土重来,他们也会很乐意告诉那些候选人,破坏两党合作和在相应政策上做出妥协的后果有多可怕。
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的人很清楚非国家行为体——无论是在伊拉克、叙利亚还是尼日利亚等——所扮演的暴力及引发社会混乱的角色,而某些西方国家又太软弱,没办法协调出合适的应对办法,更别指望会有个和平的结果。难民潮的到来近在咫尺。
房间中的所有人都很清楚,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在以一个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着。在不断蔓延的贫困和不可思议的财富对比状况持续加剧的大背景下,这样发展下去最终会将中产阶级掏空。
巴黎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央行在政策制定上所扮演的关键的、独特的、实验性的角色。这个角色,不只决定着社会各种机构的运行,更影响着现在和未来的几代人。这个问题无先例可循,央行的现时境况与其说是精心安排的结果,不如说是误打误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