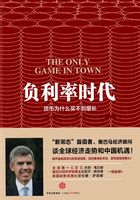
第七章 央行的复苏
持久的还是回光返照?
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创造未来。
——艾伦·凯——
在过去的3年中,央行别无选择,只能不可持续地去维持不可持续发展,直到其他部门为了恢复可持续发展而进行可持续发展。
——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
面对眼前的混乱局面以及可能到来的更严重的后果,央行的监管从自由放任的模式转变为“不惜一切代价”高度干预模式。这是一个十分戏剧化的转变。
央行和财政机构配合起来共同工作,人们都激动地期待着伯南克主席和保尔森部长共同出访美国国会山的领导——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来稳定极不正常的金融系统。
印钞机开始超速运转,无数应急资金窗口打开,大量现金从四面八方注入金融系统;主权借贷和信用担保全面开放,直接公共资金被发放给美国主要银行和无数小银行。
这就像拼命往墙上扔东西一样,有什么扔什么,并希望总有什么可以粘在上面。在经历了一个危险阶段之后,作用终于开始显现了。
对于流动性的空前部署和让市场直接参与进来的措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对市场体系幕后的操控力量重新恢复了信任。从支付结算系统的恢复开始,功能失调的源头也慢慢被修复了。信贷额度逐渐恢复,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重新开始使用,整个系统开始向着正常化的方向愈合,虽然这个过程十分缓慢。接着,不断下降的经济活动开始触底反弹,尽管增长速度十分缓慢。所以,在因为对不负责任的银行系统监管不力而备受指责之后,央行的地位和声誉开始慢慢恢复。毕竟,是它们把世界从一场骇人的大灾难中拯救了出来。
央行也为政客们联合起来统一行动争取到了时间。在巨大利害关系的驱使下,2009年4月,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伦敦20国集团峰会。我敢说,这次会议将被作为全球政策高效协调的极好范例而载入史册。在20国集团峰会上,领导人们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加强财政措施和扩大多边资金以支持央行政策。
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大衰退危机被化解,全球经济进入了复苏期,而主导这一切的是重要新兴经济体,这种模式前所未见。对新兴世界来说,西方国家经济的崩塌并没有将它们也带离轨道。人们常说,西方世界一感冒,新兴经济体也早晚进医院,但当有的西方国家进入重症监护室时,新兴经济体却站出来引领发展方向了。尽管过度杠杆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也给新兴经济带来了结构性的伤害,但它们仍然成为牵引全球经济前进的强有力的火车头,这也让许多人跌破眼镜。
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的黑暗数月中,央行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行动,而不是坐等让经济和金融停滞不前、给社会造成破坏。之后在2012年7月,它们还再次部署了一个战略,用来规避欧元区——欧洲历史性区域一体化项目的核心组成部分——的崩溃危机。
这一次,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宣布,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1为了彻底打消公众对他所承诺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怀疑,他还特别强调说:“相信我,这就够了。”
或许是因为金融市场领悟了美联储“不惜一切代价”的含义,总之,德拉吉行长的话发挥了神奇的魔力。央行凭借一己之力,把欧元区经济从混乱边缘和代价高昂的分裂状态边缘拉了回来,秩序得以恢复。在这个过程中,央行没有部署任何资金,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市场挑起了重担。
这个“魔术般的”作用,不仅使即将分崩离析的欧元区货币联盟金融市场恢复平静,保证了欧洲的历史性区域一体化项目得以顺利进行;同时还调整了欧元区的权力等级,把欧洲央行推上了领导地位。事实上,正如两位受人尊敬的《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杰克·尤因和本雅明·阿佩尔鲍姆指出的那样,“通过一些措施,德拉吉先生登上了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他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承诺,让欧元区成功避险并且稳定了市场,他挥舞着道德权威大棒,对欧洲央行管辖范围的扩大进行监管”。2
毫无疑问,央行对自己的定位是有效的危机管理者。此外,伦敦峰会结束后,随着危机最极端部分的化解,政客们似乎失去了关注的焦点,央行的存在不仅是有效的,更是唯一的决策实体,就像诺亚行长指出的那样,它们是“唯一玩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唯一玩家”的说法与其说是为保证经济高枕无忧,倒不如说这个优势政策成为人们去关注它们的原因。
临时干预政策持续的时间之长超出了包括央行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设想。经济复苏进度持续低于预期,人们这时担忧的不仅是有效性,也包括最终的退出过程本身,如市场预期管理、大型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持久性,以及如何与其他政府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合作。3
国际清算银行(央行中的央行)在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对这种忧虑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总结,其中提到,当央行发现“平滑的标准化非常难以实现”时“颠簸退出”的前景如何。4就在几个月之后,即2015年1月,为了降低瑞士在欧元区危机中的风险,瑞士央行宣布退出钉住汇率制,再次确认了这种担忧。
与其说欧元区经济从金融正常化转变为了全面复苏,倒不如说欧元区一直停滞在1%的地带——1%的低经济增长率,1%的“低通胀率”,还有个更广泛的问题,就是发达国家最顶层的1%的人口拥有着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和收入。
对于那些认识到严重的金融碎片化和经济崩溃问题已经步步逼近的人来说,这1%的地区情况好像并没有那么糟糕。然而,欧洲经济停滞不前的时间越长,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也就越严重,结构性失业、通货紧缩、政治极端主义和社会结构风险也就越大。
由于其他决策实体持续性的反应迟缓,欧洲央行不得不选择风险更大的实验性策略。2014年6月,欧洲央行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举动——之前从没有央行施行过的,而且处于重大金融危机时期之外的举动——将银行利率下调至负数。2015年1月,欧洲央行更是进一步大规模购买市场证券,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大至1万亿欧元。
2015年1月23日的《华尔街日报》头版标题赫然写着《新时代》(见图5),欧洲央行已经开始着手实施大规模且相对开放的量化宽松政策,它重新肯定了将资产渠道的使用作为对抗通缩预期和低增长的手段。为了强调其严重性,德拉吉行长在欧洲央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央行已经准备好购买负收益的债权(没错,负收益)。

图5 《华尔街日报》头版上的文章《新时代》
这个声明的不同之处在于,纵观央行之前的发展历程,它从不愿意冒险,从没做过哪怕只是远离正统一英寸的事情,它负责决策的理事会还需要在争取以保守闻名的德国人支持的同时,争取艰难的政治妥协。5
在这期间,市场对于央行的持续性参与的反应十分兴奋,机构成了投资者最好的朋友。这种情形曾多次出现在当时《金融时报》的记者特雷西·阿洛韦(Tracy Alloway)笔下《对央行的崇拜》的文章中。6
由于反复调节,当资产价格遭遇大气流冲击或经济情况重新又开始波动时,投资者开始变得期待央行干预。因此,即使合理的市场价格调整被人为限制了的时候,由于有了央行的支持,投资者都应该逢低买进以保证获利。
央行是因为其重复性而显得可靠的(至少在大多数投资者眼中),其积极的行动再次点燃了市场上两个最强大的术语——“金发姑娘”和“大缓和”。长期的极低利率有力推动了这两个词的出现,以至于在2014年12月的《华尔街日报》CEO理事会上,德高望重的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菲舍尔(Stanley Fischer)说:“我们几乎已经习惯性地认为零利率是正常的,但那已是过眼云烟了。”
市场也开始习惯了异常低波动的长期周期,美国经济逐渐改善,央行宣布它有足够的“耐心”——这些都预示着经济金融将保持一段相对长时间的平静,无论其中是否有人为因素作祟。这种市场环境很自然地去鼓励投资者冒更大风险,包括利用借贷和杠杆去增加市场投资机会。
有了这种一再重复的“和你做朋友的趋势”,加上资产价格极其压抑的波动,“搭市场的便车”变得诱惑性十足。毕竟,央行已经确保它所做出的所有调整都是小范围的、暂时的、迅速可逆的。人们接受了“理性泡沫”理论,通过评估债券的绝对和相对表现来进行更短期的投资,这样一来,如果最终投资者们不愿意调整他们的预期回报值,资本也能够得以快速流动。
对一些人来说,金融市场的表现再次显示了它对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重要见解缺乏重视。明斯基最出名的理论是他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7,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稳定时期会导致随后的巨大的金融不稳定时期。
潜在的道德风险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2014年10月,适度市场波动的收益导致一些尊重市场参与者要求美联储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QE4)政策——另一个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目的是抑制市场波动性和人为的再次推高资产价格,这让当时的我困惑不已。
必须说清楚的是,这个时期的美国经济正在缓慢回升,而且对于高收入群体的倾向性减少,每月提供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其发展势头令人印象深刻。消费者信心回升,美联储处于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QE3)政策的最后阶段。然而,所有这些都是由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引发的波动,它们请求美联储推出另一个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
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最直接目标——国债收益率、新增抵押贷款以及住房再融资——已经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这让整个情况变得更加荒谬。8银行现金充裕、美联储持有大量超额准备金。没有迹象表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能够改善政府功能失调的现状,并提供一个有美联储参与的全面应对政策。不管怎样,绝大多数美国公司和家庭都开始从国际油价大幅下降中受益。
虽然很多人都在鼓吹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但潜在的行为制约是很多央行都面对的一个让人头疼的现实问题。央行之前曾几次尝试退出实验性货币政策,但都以越陷越深而告终。现在央行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市场平静期,央行中的一些人曾对市场未来的波动性提出过警告,其中就包括在2015年1月举办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提出:“市场和政策制定者预期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对金融系统波动带来巨大影响。”9
实验性策略实施的时间越久,我就越担心央行会逐渐从问题的解决方变成问题的一部分,尽管它们才是整个解决方案中唯一能起真正作用的重要参与者。
令人失望的经济结果和对不平等的高度关注,再加上不断飙升的金融市场已经完全脱离了反应迟缓的普通民众——第三部分我们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发展——自然而然地加剧了民众对金融部门和监管机构的不满情绪。
我们在这里说的远远不止“救助疲劳”那么简单,还包括(仍然包括)根深蒂固的愤怒情绪和触目惊心的信任赤字——不仅是针对央行对不负责任冒险行为的纵容,还包括将数万亿美元的救市资金注入到各行业领域,以及它们一手安排的这场盛大的金融复苏,但从中受益的是华尔街而不是普通百姓。
针对这个危机,在秘书长蒂姆·盖特纳的书中有这么一段很有用的评论,却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总统知道,如果金融系统不牢固,他就无法修复更广泛的经济形势。银行就像经济的循环系统,在经济日常运行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离开金融系统,什么经济都玩不转。”10
但是,当银行系统“稳定”下来之后,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仍然停滞不前。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我们将分成10个可诉性问题来讨论这些经济萎靡不振的主要地区,以及会对当代和后代福利带来重要影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