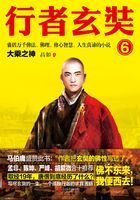
第4章 经筵擂台
戒贤尊者坐在同玄奘第一次见面时的法堂里,他的面前放着玄奘所著的三千颂的《会宗论》。
“真是新奇的理论……”他闭着眼睛想。
经过无著、世亲二位菩萨的推进,戒贤所宗的瑜伽行派渐渐隆盛起来。其后,世亲的弟子陈那作《观所缘缘论》《入瑜伽》等论著以宣传瑜伽行派之思想,复以《因明正理门论》而定因明论式;后有亲胜、火辩二位论师注释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论颂》,发挥三性之旨,提倡观行万法唯识之理,以悟真如之性。
而就在瑜伽行派发展的同时,大乘中观学派也开始崛起,空有二宗的矛盾和争执愈演愈烈,大有水火不容之势。
从开始住持那烂陀寺的那一天起,戒贤就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大乘佛法,对于空有二宗的矛盾则采取搁置的态度。原因很简单,近百年来各种外道的兴起直接影响到佛教的地位,而佛教内部大小乘的较量也是越来越激烈。相比较而言,空有二宗的争执还算温和,仅仅是在学术辩论的范畴之内,只要自己稍加控制,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但近些年来,他却感到有些控制不住了,就拿这次来说吧,师子光长老突然发难,不仅在讲筵上对瑜伽行派和他本人大肆批判,甚至连护法菩萨也在批驳之列,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着实令他有些措手不及!
那几天他一直坐观,希望能想出一个较为完美的解决办法,既可以维护瑜伽行派的声誉,又不至于激怒对方,毕竟那烂陀寺良好的学术氛围得之不易。然而几天过去,始终未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正值莫可奈何、进退无据之际,玄奘却突然站了出来,仅以正常的征诘酬答,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或许是我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戒贤尊者叹息着想,“玄奘的解决方式不能说是太合适,甚至更加扩大了矛盾,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比什么都不做要强得多。”
师子光长老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自然十分恼怒,这几日讲经时的语言更加激烈,这是可以预见的。幸运的是,这种激烈的语言总算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的结果令戒贤心下稍安,同时他又想,玄奘这个时候写出《会宗论》,是为了安抚这位长老吗?
他摇了摇头,否决了自己的这一想法。一部三千颂的论著可不算短,无论怎么看都不会是一部安抚之作。难道这位求法僧真的认为“唯识”与“中观”这二者可以融会贯通?
睁开眼睛,戒贤的目光又落在面前的《会宗论》上——现在,这部著述已经成为那烂陀寺藏书的一部分,很多学僧不顾天气炎热,纷纷云集于三大宝阁中,竞相抄习,这一事实反倒令他心中不安。
空有之争已持续了百年之久,虽然龙树与护法都曾提出过“中道”之说,但与眼下玄奘所提的“会宗”理论完全不同。历代大德要么站在“中观”的立场上批“瑜伽”,要么站在“瑜伽”的立场上驳“中观”,还从未有人想过要会通此二者,在戒贤看来,这种会通实在与捣糨糊无异。
戒贤知道玄奘的学问不光得自于那烂陀寺,他能不远万里来此求法,自是早已具备了极高的佛学修养。单就自己所知,玄奘进入印度境内之后,就已经师从了十几位大德,涉猎之广,可谓令人瞠目。
即便是在那烂陀寺,他也不光自己一个老师,九大长老包括师子光在内,谁的讲座他没听过呢?更不要说他每日与各位高僧学者参学讲道,在三座宝阁内抄学各种或热门或冷门的经典……
“这孩子,”尊者喃喃自语,“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了这种奇怪的想法呢?”
他虽不同意玄奘的观点,却也不能轻易予以否定。这倒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外国弟子帮了自己和那烂陀寺一个大忙,更在于其对佛法与俗书的涉猎如此之广,自己在他面前已经越来越感觉到吃力。这一次,就算他提出的理论与众不同,也难说没有“圣言量”做支撑……
“师尊,玄奘法师到了。”觉贤长老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
“快快有请。”尊者将思绪收了回来。
师徒二人面对面坐定,戒贤尊者开口说道:“法师的《会宗论》,老僧已命人大字抄写,悬于三座宝阁之中了。”
“弟子愚作,怎可与历代圣贤相伴?师尊太过抬爱了。”玄奘不安地说道。
“法师不必过谦。”尊者微微笑了一下道,“如今寺中很多弟子都在抄习这部新论,法师今日没去宝海阁吗?那里已经快被挤得透不过气来了。”
玄奘暗暗松了一口气,心中颇为欣然。如此说来,人们是同意将这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大乘佛教少几句争论,便会少一些内耗,这真是太好了!
可他又觉得奇怪,为什么师尊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中并无半分欢喜之意呢?难道他不同意我的观点?
“大乘佛教的分裂,乃是由婆毗呔伽而起。”戒贤尊者缓缓说道,“他曾著《中观心论释思择焰论》,指名道姓地批驳瑜伽行派之宗义。这之后,清辨一系与瑜伽弟子就争端不断。”
“师尊,弟子有一事不解。”玄奘终于将他心中的疑问和盘托出,“那烂陀寺自建寺以来,空有二宗便争执不断,如今少说也有数百年了,就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融通,协调两派之间的矛盾吗?”
“是啊。”戒贤道,“这种奇怪的想法,之前从未有人起过。”
奇怪的想法?玄奘心中很是不解,世间万法,有分裂就会有融通,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难道师尊觉得,中观和瑜伽有什么本质上的分别吗?”他问。
“法师觉得没有分别吗?”戒贤反问,“你的《会宗论》上说,中观的真空与瑜伽的妙有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佛法进行阐释,它们都是双破‘我执’和‘法执’的,这话没错。但是,这两种体系对世界的观察方式是不一样的。瑜伽讲究次第修行,转识成智;而中观讲究的却是无为、不二、无分别观和整体观,与瑜伽行派有很大的不同。”
“弟子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同啊。”玄奘道,“中观的这四种观不就是瑜伽行派的‘转识成智’吗?无为是成所作智;不二是平等性智;无分别观是妙观察智;整体观是大圆镜智。这两种思想看似不同,其实是不二的。”
戒贤尊者沉默了,他不能不承认,玄奘说的有一定道理。
玄奘接着说道:“瑜伽宗里其实包含了中观思想,中观宗里也包含了瑜伽思想。它们都告诉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认识自心,以及心与外境之间的关系。只不过瑜伽更注重现象,从现象入本质;而中观更注重本体,从无限的可能性直接观照宇宙万法的本质。两者阐释的重点不同罢了。”
戒贤尊者点头道:“所以在中观学者看来,瑜伽宗是不了义的;而在瑜伽学者看来,中观宗更像是搭建了一座空中楼阁,只想着一步登天,倘若不小心一脚踩空,是要摔得粉身碎骨的。”
玄奘笑着摇头:“也不能这么说,弟子以为,瑜伽与中观都是了义的,只不过一个是由近及远,一个是由远及近,角度不同罢了。佛陀当年讲经时,经常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种观点进行反复的阐释,由此产生不同的佛法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平行和平等的,不能简单地说谁是了义、谁是不了义。至于修行,更是法无大小,应机为上了。”
“法师的这个想法,是由来已久呢,还是最近才产生的?”戒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是由来已久的。”玄奘答道,“弟子很久以来就有一个想法,调和大乘佛教空有二宗,进而调和大小二乘,让佛门弟子从此不再面对经典而无所适从。”
戒贤尊者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在你们国家,人们都喜欢调和融通一切吗?”
“是的,师尊。”玄奘答道,“在我的国家,持不同意见的人可以在一起很好地相处,并努力追求各种思维方式和文化的相互融合……”
尊者的眼中流露出向往之意:“这是圣贤的国度啊……”
当然。玄奘想,古老的中原一向是圣贤辈出的,那里同样有各种思想和文化的碰撞,却远远没有印度这般残酷。那里的人们大都心地纯良,懂得求同存异,也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那是个美丽的地方,如果圣教传不过去,该是多么可惜!我西行求法,正是希望能将佛陀的慧光甘露洒在那片土地上,以利益那里的每一个人,这也是我西行的目的之所在……
“老僧却认为,这世上有些东西是没有必要调和的。”戒贤尊者缓缓道出自己的想法,“法师你也说了,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这个世界。那么,就让它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共存于世,不是也不坏吗?”
“弟子当然希望这样。”玄奘说道,“弟子主张会宗,就是希望它们能够共存于世。因为在有些学者的眼中,这些东西是不能共存于世的。”
“法师指的是什么?”戒贤问。
“争论。”玄奘道,“弟子原本以为,在真理的世界里,完全没有争的必要。真理是无我无人、无彼无此、无高无下、无圣无凡的,所谓一相平等,无住真空之理,一切事物均可共存于世,而不会发生无谓的争论。”
说到这里,他又想起师子光那怨怼的眼神,他已坚信自己上次看到的是真的,那种眼神让他的心里很不舒服,仿佛又坐到了那个可怕的火山口上。
戒贤尊者摇了摇头:“所谓共存于世是要保留住自己的东西,哪怕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妥协与夹杂。在五印度,辩论是人们探求真理的一种传统方式,你之所以把它当成是争论,是因为它有时很惨烈。但事实上,它也是极其神圣的。因为,印度的传统文化与哲学思辨就是在这种自由的论辩氛围中不断发扬光大的。”
玄奘没有想到师尊竟然赞成这种辩论方式,心中颇觉意外:“能够通过辩论的方式找到真理,并将其发扬光大,这当然很好。可是到了割舌、献首级的地步,难道也与佛法相应吗?”
“割舌、献首级乃是传统辩论的规矩,早在佛陀降世之前就有了。”
“难道佛教内部的辩论不应该改一改这个规矩吗?”
“为什么要改呢?”尊者的慈目温和地看着他,“辩论也是一场战争,为寻求真理而进行的战争。失败者原本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这也是随顺众生的一种方式。”
“可是弟子不明白,我们都是佛的弟子,佛陀才是我们共同的导师。至于不同的学派和修行方式,真的事关真理吗?当年佛陀针对不同根器的众生,讲说不同的佛法,这既是一种智慧,也是出于慈悲。佛法如药,对治众生八万四千病,每一种都有存在下来的理由。可是在印度,只因辩论失败,许多学派的理论荡然无存。这是后世众生的损失,与真正的佛法根本就是相背离的!”
“法师过虑了。”戒贤坚定地说道,“这是大浪淘沙,真正的黄金是不会消失的!”
玄奘静静地坐着,看着自己最尊敬的导师,心中涌起一种无力的感觉:“师尊真的以为,失败者就一定是泥沙吗?”
“难道法师认为,胜利者才是泥沙?”
玄奘摇了摇头:“弟子认为,谁都不是泥沙。当年部派佛教刚刚形成时,曾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一根金手杖,掉在地上摔成十八段,每一段都是纯金的。弟子以为,不管什么学派,所修所学都是真正的佛法,都是那根金手杖的一部分,应该彼此和睦,取长补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在辩法和讲经中,冒着生命和荣誉是否尚存的风险!”
听了这话,戒贤尊者长叹一声:“法师不仅博学多闻,且兼宅心仁厚,令人起敬。可是如今的佛法早已不是当年的那根金手杖了,它被一代一代的修行人掺入了太多的杂质,重新熔铸,这中间是有泥沙的。法师主张会宗,只怕会使真正的黄金渗入更多的泥沙。”
玄奘明亮的目光直视着自己的导师,声音显得有些沉凝:“师尊心里其实并不同意玄奘的‘会宗’观点,是吗?”
戒贤尊者默然点头:“老僧一直对中观、瑜伽这两派的对峙深感不安,但若说将它们融合,却又觉得不是什么好主意,两派行者怕是都不能同意。”
“可是师尊却在法会上对玄奘的《会宗论》大加赞叹。”
“因为法师写得确实好啊。”尊者的眼睛里放射出温暖的光,“那烂陀寺已经很久没出过一部论述如此精微、说理如此透彻的新论了,这难道不值得赞叹吗?老僧虽然不同意法师的观点,却也无法在逻辑上驳倒法师。更何况老僧又非圣贤,怎么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众生头上?”
可敬的长者!玄奘心中涌起一种深深的感动,他知道,正是这份可敬的真诚与宽厚,才使得身为寺主的戒贤尊者,在师子光向他发出诘难时,依然能够坦然面对,让这位与自己作对的长老继续留在那烂陀寺讲经,继续对自己的批评和指责……
但与此同时,他又从尊者平淡的语气中听出了几分萧索之意——那烂陀寺有如此多的大德,却已经多年未出过一部像样的论述,也难怪他会感到遗憾。
尊者说他不同意融合二宗,却又将《会宗论》大字抄录贴出,这固然是对学问的尊重,但是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希望寺中长老和学僧们能在抄学的同时提出不同意见,哪怕由此展开你死我活的辩论。尊者相信,真理就像黄金,是可以在激烈的论辩中展示出来的。
然而玄奘心中依然感到不安——辩论,残酷到以项上人头和整个学派的生死存亡为赌注的辩论,真的就是找到真理的最佳方式吗?如果一个学派的人都不善辩,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所学的不是真理了呢?
佛教在印度传播的过程中,有高峰期也有低谷期。高峰期,大德如满天星斗,层出不穷;而低谷期,可能很长时间也出不来一个真正的人才。“道靠人弘”,一旦出现人才短缺,就面临宗派难续的尴尬。当年波咤厘子城的佛教徒因为与异道辩论失败,被逼十二年不得敲击犍槌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玄奘抬起头,正要说出这些想法,突然发现戒贤身子一抖,满头大汗地歪倒在一边。
他赶紧上前扶持:“师尊,你怎么了?是痹痛又发作了吗?”
“是……是啊……”戒贤嘴唇颤抖着说道,“多亏了你,近两年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原本以为好了,想不到它依然还在。”
玄奘从袖里取出针盒打开,先用短针扎破尊者的双耳放了一点血,又拈出三根三寸长的银针,分别深扎在足三里、关元、命门这三大强穴之中,手指在针尾轻轻捻动,过了一会儿,戒贤的眉头便渐渐舒展了开来。
玄奘松了一口气,五年前,他到那烂陀寺学习《瑜伽师地论》不久,戒贤的恶疾便再度复发,一时痛不欲生。当时恰好玄奘就在身边,立即伸手替他切了脉,发现师尊所患恶疾其实是一种风湿痹症,中原医家称之为“风痹”,主要累及各个关节,以及周围骨骼、肌肉、肌腱、韧带等部位,以疼痛为主要症状,严重时各关节处红、肿、热、痛,缠绵难愈。
戒贤称自己这病是业力所致,一开始拒绝让玄奘施治。玄奘劝说道:“世间既有医道,它便是因果的一种。当年佛陀也曾示疾,并且接受了名医耆域的诊治。焉知师尊遇到了玄奘,不是菩萨要我来解除你的病苦吗?”
听了这话,戒贤也觉有理,况且这病疼痛起来确实要命,连脑壳都跟着痛了起来,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只好答应让玄奘试试。
再次给师尊切了脉后,玄奘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于是使用三寸银针进行深刺,几针下去,镇痛效果显著,戒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着玄奘手中的银针发愣。
可惜他得的毕竟是顽疾,要治愈几乎没有可能。因此这五年时间,玄奘除了学习经论,便是想方设法为尊者治疗。除用针外,还辅以草药。虽然这个过程缓慢无比,但总算是减轻了不少症状,最近更是连续数月也难得发作一回,以至于戒贤还以为自己的病好了。
“菩萨慈悲,让我遇见了你。都说你的银针包治百病,我还不信。谁能想到,竟然真的能减轻我的痛苦呢!”戒贤由衷地赞叹道。
玄奘笑了:“我这银针绝非包治百病。只不过,治疗您这种痛症却是相当对症。虽然无法根治,镇痛解苦还是可以的。可惜这里没有艾绒,否则用火炙上一炙,效果更佳。”
“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戒贤重新坐正了身体道,“根治是绝对不敢指望的。菩萨说我当年做国王时,曾做下过许多恶事。我想我原本应当去地狱受报的,幸好今生学了佛,才能够重罪轻报。如今又遇见了你,让我减轻病苦。老僧唯有精进修行,以报佛恩,哪里还敢有什么不知足的?”
玄奘道:“那么弟子先行告退了,师尊身子不安,早点歇息吧。”
“不忙。”戒贤摆手道,“老僧这次请法师来,是希望法师能够帮助那烂陀寺,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请师尊吩咐。”
“热季将过,很快便又到雨安居了。”尊者淡淡地说着,将目光转向窗外,“每年的这段日子,都是那烂陀寺人最多的时候,可惜今年寺中讲席不盛。老僧恭请法师设立讲筵,为众僧开讲《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万望法师不要推辞。”
玄奘愣了一下,那个露形外道的卜卦还真准!难道戒贤长老将自己的打算提前透露给了他?
“师尊如此盛情,玄奘不敢不遵。但玄奘只是一介学僧,学法未成,恐怕难以胜任。”
“法师太过谦逊了。”戒贤叹道,“法师在那烂陀寺已历五载,早已完成了学业,且又正当盛年,主持寺中讲席最合适不过了。”
玄奘摇了摇头:“弟子愚钝,虽居寺中五载,却未真正完成学业。宝阁内所藏经典还有很多未学,学过的经典中也有很多未能贯通。”
“经典是学不完的。”戒贤尊者道,“法师年纪轻轻,学问已超过这寺中的许多长老,跻身十大德之列,寺中诸德无不敬重法师的人品和才华。法师开设讲筵、弘法利生,这是件功德无量之事,你就不必推辞了。”
见玄奘仍在犹豫,戒贤又道:“学习佛法不仅要自我精研完善,更须传道授业,让更多的人得闻佛法,这才是菩萨道行者。法师这般推辞,莫非是怕以后没有时间习经了吗?”
“不。”玄奘道,“弟子只是担心,眼下师子光长老正在寺中开讲《中百论》,师尊要弟子讲的《唯识抉择论》,不仅在佛学本源及研究的重点上与《中百论》有所不同,而且恰恰是师子光长老所指摘的,会不会……”
“原来如此。”戒贤尊者微笑道,“法师不必担心,到安居日的时候,师子光长老的《中百论》就该讲完了。”
“弟子听说,长老准备在安居期内再从头讲一遍。”
“嗯……”戒贤略微沉吟了一下,点了点头,“法师不是想要融合空有二宗吗?这正是一个机会。可以同各部派论师以及中观学者正面切磋,辩论双方互补短长,不仅可以传播佛法,还可获得更多的心得体会,这不是很好吗?”
玄奘对此有些迟疑,心中隐隐觉得,师尊此举倒像是为自己设下了一座佛学擂台,单等不同派别的高手前来打擂。
老实说,他不喜欢这种太过激烈的方式,但师尊所说的“传道授业”的话打动了他,使他再次想到了回归故国——
是啊,人生苦短,不能一味追求知识而放弃弘扬佛法的机会。
他自幼深受佛儒两家思想的熏陶,心中常怀感恩之念,也知道一旦踏上归国之路,从此便是山水迢遥,此生再想回到那烂陀寺便是千难万难。因此上路之前,他必须先报答那烂陀寺和恩师这些年来的传道授业之恩。
而接受恩师的盛情,在寺中设筵讲经,与不同派别的论师、学者们辩论切磋,弘法度生,确实是目前最好的报恩方式了。
“师尊所言甚是。”他恭敬合掌道,“玄奘恭听师尊安排。”
戒贤尊者欣慰地点了点头,满怀慈爱地看着这个外国弟子,对于这座他亲手设立的佛学擂台,他有着充足的信心。
玄奘本就辩才无碍,在进入那烂陀寺之前就已经如此,何况又有了这五年的潜心学习。尊者相信,凭着玄奘的阅历、他的明悟、他读过的经书,以及他与印度各派名僧学者的交流,整个那烂陀寺已没有人能够难得住他!
另外,戒贤尊者也希望能借此事告诉玄奘,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融通的,也不是所有的矛盾都可以协调,佛学擂台也是擂台,只有智者和勇者方可取得最终的胜利!
贞观十一年(公元638年)五月的一个清晨,那烂陀广场巨大的讲坛前,人潮涌动,从各地赶来安居的僧侣俗众齐聚此地,准备聆听两位大德讲经。
师子光长老被弟子扶持着下了青象,他面前的台阶湿漉漉的,讲坛顶上,巨大的华盖还在往下滴着水,显然,昨天夜里这里刚刚下过一场透雨。
“今年的雨季到得有点早啊。”长老淡淡地说道。
他的心情同这天气一样阴郁,十天前,他的《中百论》讲座结束,为了让新来的学僧和那些临时到此结夏的僧侣居士了解大乘中观学说,他决定再次从头开讲,并将讲筵地点设在那烂陀寺中心最大的广场上,以便届时有更多的人前来谛听。
然而弟子布隆陀耶却告诉他,广场上已经有一个讲筵了。
“是谁啊?”他问。
“玄奘法师,今日就要开讲了。”
“那个东土来的客僧吗?”师子光不屑地问道,“他还只是个学僧,凭什么开设讲筵?”
“师尊有所不知,玄奘法师如今已经不是学僧了,正法藏亲自任命他做那烂陀寺的讲经师,在广场上开设讲筵。听说他这次讲的内容是《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
“法相唯识,瑜伽行派的理论基础。”师子光难得地笑了笑,“你知道正法藏此举是什么意思吗?”
布隆陀耶摇了摇头:“弟子不知。”
师子光哼了一声:“这是正法藏在借东土客僧之口,向我发起挑战!我若不应战,岂非不给正法藏面子?”
布隆陀耶依然不解:“师父的意思是……”
“这东土客僧上次平白羞辱于我,我还未找他算账,如今他又在我之先设立讲筵,宣扬瑜伽行派,这分明是在挑衅!既然如此,我们的讲筵就设在他的对面好了。”
布隆陀耶有些迟疑:“师父,这合适吗?”
“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师子光冷冷地说道,“而且,这不也是正法藏的意思吗?”
他的这一决定使得两场经筵都异常火爆,每天天不亮,广场上就已经热闹非凡,两座经棚前聚满了人。对于来此学习的僧侣居士们来说,这可是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学术胜景——两位大乘论师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宣讲两部立论完全不同的经论,宣扬两种完全相反的学说,如此壮观景象大约也只有在那烂陀寺可以见到了。
可师子光的心情却如那棚檐上积聚的雨水,越来越沉重。他原本以为,这场擂台自己是赢定了的,因为开讲筵毕竟不同于辩论征诘,是需要一些威望和人脉的。玄奘是一个外国来的求法僧,一无弟子,二无根基,凭什么敢在那烂陀寺开设讲筵?
然而事实却令他大惑不解,虽然前来听他讲经的人数要比热季时多得多,但是很明显,去玄奘那边听经的数倍于自己这边。
“布隆陀耶,你去东土客僧那里看看,是什么人在听他讲经。”一日,他终于忍不住,吩咐弟子道。
布隆陀耶恭敬领命,很快便来到玄奘的法筵前。
没有人注意他,来此听经的太多了,除了那烂陀本寺的,还有很多是来自别的寺院,甚至其他国家的。僧人、婆罗门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都有,他可以很自然地夹在人群中谛听。
法坛上那位面貌清秀的东方法师说着一口纯正流利的梵语,与本地高僧一般无二。这令布隆陀耶感到十分意外。他曾跟随师尊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各式各样的外国人,他们穿着各种古里古怪的衣饰,说着各种古里古怪的语言,即使有学梵文的,也是腔调各异,交流起来极为困难。眼前这位法师却是一口完美的中印度梵音,无论是用词还是语音,都相当地熟练和正规。
布隆陀耶心中暗暗纳罕,他想:“若是未见其面,只闻其声,根本就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外国法师在说法啊。”
这么一想,心中便油然生出几分钦佩之意,听起来也就格外认真。
东土法师的口才确实好得出奇,他的用词简单而到位,只需一两句话,就可以把一个看似复杂的问题说得准确而又透彻。他语音轻缓,态度温润,讲经说法直入核心,将一些被人们忽略的道理娓娓道来,让人听着很舒服,丝毫没有感觉到逻辑论证的烦琐和无力。
听惯了师尊按部就班的说教,布隆陀耶感到听这样的演说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他不知不觉听了进去,常因为某一句话而陷入短暂的思考之中,几乎忘了师尊要他来做什么了。
直到一段讲完,中间休息时,布隆陀耶才终于想起师尊的吩咐,立即同旁边的僧人攀谈起来——
“师兄不像是本寺的人,从哪来的?”
“我们都是附近寺院里的。”那僧侣兴奋地说道,“早听说了东土法师的名字,一直希望能亲耳聆听法音,如今总算达成了这个心愿!”
“我是从东印度来的。”旁边一位白衣婆罗门说道,“我们远近各国的僧侣居士都听说,那烂陀寺出了位神奇的东方法师,心里都好奇得很。这次他讲学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就有一大批同修慕名前来听讲。”
“我五年前就来了,从波罗奈国一直追到了摩揭陀,只为能亲眼看到东土法师。只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法师已进入那烂陀寺,一待就是五年。我正恨自己无缘,就听到法师再次升座说经的消息。你知道我和我的同修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是多么地欢喜吗?光我们寺院就来了一百多人!”
“原来都不是那烂陀寺的……”布隆陀耶喃喃说道。
“谁说的?”旁边有人喊道,“我们就是那烂陀寺的!法师的论述如此精微,这寺中长老怕是无人能及呢!”
“师兄说得极是。”布隆陀耶心中钦佩,忍不住附和道,“我只道这位东土法师是远道而来取经求法的,却想不到他竟有如此才华和智慧,也难怪本寺及外寺的僧人都爱听他的讲座。”
“也不全是来听经的。”一个身披黄衣的中年僧侣在一旁说道,“沙门是北印度来的上座部论师,来此的目的,就是慕名来找东土法师辩经论法的。”
“真的?那你先跟我辩论吧。”最前面那位年轻僧侣笑道,“我叫室利般摩,来此的目的就是要做东土法师的弟子,你先辩赢了弟子,再去辩师父如何?”
“不必了。”这位上座部论师笑道,“现在沙门已经知道,玄奘法师比我想象的还要了不起!”
“大师可以读读我师父写的《会宗论》三千颂。”室利般摩俨然已将自己当成了玄奘的弟子,兴之所至,朗声诵道,“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惑者不能会通,谓为乖反;此乃失在传人,岂关于法也?”
旁边的人不禁赞叹道:“室利般摩,你真是厉害,这么快就将法师的新论背了下来!”
布隆陀耶终于明白,作为新任讲经师,玄奘的声望其实早已超过师子光长老。这场经筵擂台,师尊怕是有输无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