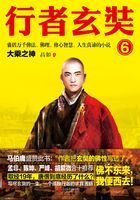
第3章 圣人立教,各随一意
这番精彩的对论,台下诸僧莫不听得如痴如醉。特别是如此热天,人们都身着薄衫,满脸油光闪烁,师子光长老更是大汗淋漓,而玄奘的身上竟是一滴汗也没有,更让人觉得这位东土僧侣不是凡人。
然而玄奘心中却是忧虑更甚,他知道自己虽然取胜,毕竟靠的是学识和辩才,无法真正说服师子光长老,更不可能移除长老心中对瑜伽行派的偏见和非难。
其实不只师子光长老,寺内诸僧中拥有这种你死我活思维方式的不在少数。一些中观学者始终支持师子光,如今见长老发怒离场,都不禁摇头叹息。
卢达罗耶却很兴奋,回去的路上嘴巴就没闲着,一个劲儿地说个不停。
“这个师子光长老,口中一向不留德,就连正法藏都不放在眼里,法师你早该来批驳他了!再说了,你看他执着的都是些什么呀?一切皆空,生死是空,涅槃是空,烦恼是空,菩提是空,总之就是空空空,一空到底!那还修个什么劲儿啊?”
“另外,他们还不承认有阿赖耶识。没有‘我’,没有阿赖耶识,那到底是谁去轮回呢?要是没有轮回,那和顺世外道的‘人死如灯灭’又有什么分别?要是有轮回,靠什么去轮回?法师你看,我都能去和他辩论了!”
他越说越得意,越讲越兴奋,玄奘忍不住回了一句:“般若中观是承认有轮回的,虽然没有‘我’,但所造的业不会消失。另外,唯识宗也是讲无‘我’的。”
“但是咱们有阿赖耶识啊。”卢达罗耶道,“这不就是轮回的主体吗?有了它,造业、受果、受报、生死相续,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了。我听过正法藏讲经,他说阿赖耶识能贮藏一切善恶种子,种子生现行,造了业之后,现行又反过来熏习种子,藏在阿赖耶识里。这多好理解啊!可是师子光长老却说什么‘惑、业、苦’,因为惑,然后就造业;因为业,然后就产生苦果;在受苦果的过程中,又起惑、又造业、又招感苦果。轮回就是‘惑、业、苦’。可是他又不承认有一个轮回的主体,那么这其中到底是谁在受‘惑、业、苦’呢?还是没有人。”
玄奘道:“其实师子光长老讲得也没错,是你自己没有理解罢了。如果你把缘起法学好了,理解起来就不会有问题了。”
卢达罗耶顿时愣住了:“您说师子光长老是对的,那不就是说,您和正法藏是错的吗?那您为何还要同他辩论?”
玄奘奇道:“为什么他是对的,我就一定是错的?这个世界不是非此即彼的,佛门弟子最忌讳的就是以分别心说此是、说彼非了。师子光长老演说的佛法本身没有错,但他对龙树菩萨的真空的理解有问题,对瑜伽宗的批驳更有问题,他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空,甚至没有试图去理解,就依照自己的想法下了结论,毫不客气地去批驳和遣除他宗。这是他的分别心所决定的,而我针对的也是这个。”
“可是法师啊,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卢达罗耶道,“每个人都有分别心,每个人都在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这样才有了辩论。再说中观与瑜伽在表述上的确是有矛盾的嘛。”
玄奘道:“我没有看出哪里有矛盾,只知道这些宗门教派的问题中带有很深的法执。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太狭窄,以致不能融会贯通,误解了佛陀的本意。佛经中有时说有,有时说无,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维度上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出现矛盾呢?中观二谛是从凡夫的角度讲的,唯识三性是从圣者的角度讲的。就好比几只蚂蚁要爬到树上去,一个从前面上,一个从后面上,一个转圈儿上,路径不同,目标却都一样。要说这里面有矛盾,只能怪我们自己太愚痴了。”
“也许不是愚痴,是故意的。”卢达罗耶笑道,“总想让别人认为只有自己理解的才是正确的,别人说的都是错误的。”
“那就更愚痴了。”玄奘道,“这是‘我执’在作怪。”
说到这里,他心中暗暗思忖:“辩论毕竟是争论,惹人烦恼不说,在话赶话的过程中搞不好还会说错话,徒造口业。如果我将这番理论变成文字,或许可以说服他们。”
写一部论著,以融合大乘中观和瑜伽学派,这其实是他这段日子以来的心愿,只不过由于一直忙于习经抄经,有些顾不上罢了。本想等到自己将寺中佛法抄学得差不多了再做这件事,但同师子光的这场辩论使他明白,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他必须及早完成这部新论。
玄奘选择宝海阁作为自己完成新论的场所,这里空旷而又宁静,四周环绕着贝叶经和木椟经函的淡淡香气,不必担心有人打扰,只这一条就比戒日王院的僧舍强太多了。
夜已经很深,灯台上的光影开始变得飘飘摇摇,玄奘放下手中的笔,从旁边的油罐里抽出一把小小的银匙,轻轻舀出一勺桐油,依次添在白铜铸就的灯匙里。火苗快乐地跳动着,他的眼际立即变得明亮起来。
随着灯匙里的桐油逐一添满,里面光明开始一层一层地向四周蔓延……
玄奘放下添油的银匙,重新提起了铁笔,在那张黄白色的坚韧的贝多罗叶上刻写下自己对佛法的感悟。灯匙中那些倒伏着的火绒鼓胀起来,火苗整齐地跳跃着,将他整个人包裹在一片柔和的光明之中。他只感觉到身心舒畅无比,仿佛有一池莲花正在身旁静静地开放……
两名守经人走了过来,各自抱着厚厚的一摞木椟经典,放在玄奘案前。
“这是法师白天要的。”
“多谢二位。”玄奘将这些木椟拿过来,细细观看。
“法师真是幸运,能再看到这些经典!”看着玄奘专注的面容,一个守经人突然感叹起来。
“怎么?”玄奘抬起头,奇怪地问道。
那守经人解释道:“这些经典在被收入那烂陀寺之前,几乎每天都在遗失。法师你看,这些木椟既结实又耐用,摩揭陀国的居民们都喜欢用它们来拼成卧室的地板,赤着脚在上面来回地行走……”
玄奘心中一阵伤感,佛陀时代的经典,不知有多少是这样遗失的,实在令人既痛心又遗憾。
可悲的是,一些重要的经典还不准抄录备份。
“不光是在摩揭陀国,很多国家的人都有这种习惯。他们说,经典如果没有人读,那便是无用之物了,用来铺地,倒还有些用处。”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玄奘淡然笑道,“但眼下无人读不代表永远无人读。他们不明白,经典一旦遗失,后世的人就看不到了。那烂陀寺将这些珍贵的经典收入到三座宝阁之中珍藏,实在是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法师现在做的也是功德无量之事。”守经人殷勤地说道。
“沙门的功德只是空中之华,水中之泡。”玄奘自嘲地摇头,突然问道,“现在这三座宝阁里的藏书已经不全了吧?”
“法师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守经人奇怪地问。
“上次你们不是说,修持火光三昧的外道将宝海阁、宝彩阁的部分经典烧掉了吗?”
“是这样啊。”守经人释然一笑道,“法师不用担心,那件事情过后,经过历代僧众的补充,现在藏经阁所藏的三藏经典的数量比那时还要多得多,为历年之最!”
“原来如此,这真是佛陀庇佑啊……”玄奘感慨地说道。
历尽劫波的佛法,其典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这至少说明了佛教旺盛的生命力。一念及此,足以令人备感欣慰。
玄奘的《会宗论》很快完成,此论是以瑜伽“三性”理论为基础,糅合了护法论师的“中道”思想。用玄奘的话说,此为“融会瑜伽、中论之微旨,以静大乘之纠纷”。说到底还是为了调和大乘“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的论争。
对那烂陀寺和戒贤尊者来说,察究一部新论,主要是看它是否符合“三法印”、是否有违圣论、是否立论准确、是否推理严明,以及是否能够在逻辑上自洽。至于此论本身是否是真理,却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可以下定论的,因而戒贤尊者从不追求自身的认同。
事实上,戒贤本人并不认为“瑜伽”和“中观”这两种学派可以调和,就如同他不认为“五种姓”可以调和一样,在这方面,他甚至同师子光的想法一样,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调和。他不明白身为瑜伽行者的玄奘为什么会想到要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予以会通,在他看来,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想法。
但玄奘那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却令他感受到一股清新之气,他由衷地喜爱这个给那烂陀寺越来越僵化的思想领域注入新鲜血液的异族青年。
经过详细审阅后,戒贤发现自己确实找不出此论的逻辑问题,这令他心中隐隐涌起一股不安。他又将《会宗论》交给寺中其他几名大德传阅,这其中,虽然师子光长老借故回避,其余七名大德阅后,相继认可,依次打上印信,交回戒贤尊者的手中。
于是戒贤尊者当众宣谕:“新著《会宗论》,系摩诃至那国比丘玄奘所造,这是经由那烂陀寺长老们共同认可的佛法经典!”
众人一起高宣佛号,撒花致礼,共同庆贺一部新经典的诞生。
随后,戒贤命人将此论大字抄录悬示幢顶,供寺中学僧们抄习。
法会结束时,已经接近正午,玄奘骑象返回戒日王院,般若羯罗与他同行。
“师兄是怎么想起来要贯通空有二宗的呢?”路上,般若羯罗不解地问道,“便是要贯通,也该由师子光长老提出才是。”
“这是为何?”玄奘觉得奇怪。
般若羯罗道:“师兄前段日子应对师子光长老的征诘,不是将那长老驳得无言以对,狼狈不堪吗?此事阖寺上下无人不知啊!”
“所以才应该由我来贯通。”玄奘道,“空有二宗同属大乘佛法,对佛陀之说各有发挥,正可谓殊途同归,并无向背,完全没必要辩驳的。”
“师兄差矣,越是看上去差不多的,就越有必要辩个清楚明白。你们大乘就这两个门派,加上‘如来藏’也才三个,彼此排斥,水火不容,不辩个清楚怎么行?”[1]
般若羯罗一向对傲慢的师子光很不感冒,说这话显然是希望辩才无碍的玄奘能经常性地挫挫他的傲气。
玄奘哪里不知这位师兄的想法?但他认为,教派之间的争端说到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如何能蔓延到佛法之中?因此摇头道:“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从无相互违妨之处。只因人们为内心无明所惑,不能贯通,这才出语征诘,谓为乖反。此乃失在传人,又岂关佛法?”
般若羯罗道:“怎么不关法?你们唯识论师讲有,中观论师谈空,这不就是截然对立的吗?”
玄奘道:“空和有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空宗并不是专门谈空,有宗也不是专门谈有。”
“这倒奇了。”般若羯罗笑道,“既然空宗也谈有,有宗也谈空,那为什么还要有空宗和有宗的分别呢?”
玄奘道:“龙树中观的最大特征是强调‘缘起性空’,缘起是咱们佛门的共同理论。不管是大乘还是声闻,空宗还是有宗,每个宗派都讲缘起。但中观除了讲‘缘起’外,更强调了‘性空’,也就是无自性。”
“师兄你学过部派佛教,应该知道,自性这个概念,最早出自萨婆多部,他们认为‘三世恒有,法体恒有’,也就是说,不论心法还是色法,不论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都是恒常实有的。所以此部又被人称作‘说一切有部’。”
“龙树菩萨的中观思想就是针对有部的自性观点提出了反驳,认为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比如《中论》中有一首偈子:‘未尝有一法,不从因缘生。’说的就是缘起和自性的关系,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因而都是空的,无自性的。”
般若羯罗恍然大悟:“也就是说,龙树菩萨的学说主要是针对有部自性实有的思想提出来的?”
“正是。”玄奘道,“所以中观的论著中谈得最多的就是‘空’和‘无自性’,正因为它重点揭示了‘空’的内涵,所以才被称为‘空宗’。”
般若羯罗想了想,道:“可是,缘起和自性的概念在有部中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同时存在,诸法都有自性,所以诸法才是缘起的。”
“你说得对。”玄奘道,“但这两个概念在中观的思想中就形同水火,难以相容了。这其实也不是龙树菩萨的本意。龙树的空只是‘空性’,并没有否定‘缘起有’。可有些人对他的思想不能正确理解,以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不仅世俗谛是空的,就连胜义谛的真理也是空的,这样就生生把龙树菩萨的‘自性空’给弄成了‘恶取空’,落入断见之中。于是无著菩萨就以‘三性’来破空,但其实呢,他破的是人们的‘恶取空’,而不是龙树菩萨的‘性空’。”
听到这里,般若羯罗若有所悟:“也就是说,中观的空其实就是瑜伽的有,它们之间并无本质上的矛盾?”
“师兄果然通透!”玄奘忍不住赞赏道,“一般人总以为‘空’和‘有’是一对矛盾,其实不然。同一事物中,既有空的一面,又有有的一面,这就叫作‘真空妙有’。师兄没读过大乘经,都能够看出这一点来,可叹一些大乘学人却执迷其中。”
“他们之所以执迷,是因为中观和唯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般若羯罗笑道,“抛开空有不谈,你们唯识学者处处讲自性,而中观论师却处处讲无自性,这就是区别了。”
玄奘道:“但是师兄你要知道,此自性非彼自性。中观所否定的自性,也是唯识所要破斥的。比如世亲菩萨在《唯识三十论》中就说:‘次无自然性’,自然性不是缘起的自性,而是中观论师所破斥的独存不变的自性。至于唯识论师所讲的自性,是指事物自身的体性,比如水以湿为性、火以暖为性、地以坚为性。这种性是缘起的,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说,中观和唯识关于自性的概念就不一样,他们其实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宇宙人生的真理,最终都是殊途同归。”
听了这话,般若羯罗不禁有些泄气:“既然如此,师兄又何必去和他辩论?”
玄奘的脸色有些黯淡:“我本不喜欢辩论,之所以前去应对长老的征诘,实是因为高看了自己。中观、唯识,包括师兄方才所说的如来藏,皆是出于同宗,彼此毫无乖反矛盾之处,实在没必要弄得你死我活。何况眼下大乘佛法正处于忧患之中,经不起内耗。如果玄奘能当面说服师子光长老,也就不用写什么《会宗论》了。唉,我本以为可以当面说服他的。”
说到这里,他长长叹了口气。
般若羯罗笑道:“世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即使辩不赢对方,也未必肯接受对方的主张。再说师兄这些年来钻研诸部,遍阅经藏,本就该有所著述。否则整日枯坐,与那苦行头陀有何区别?羯罗观师兄的新论,当真是文采斐然,逻辑清晰,义理顺畅。正法藏命人将它抄录贴出,看到的人无不啧啧称赞。只是很多人都同羯罗一般心思,觉得师兄的新论在辩驳力度上稍显纤弱了些。”
玄奘苦笑:“师兄太客气了,什么稍显纤弱?其实玄奘根本就没有辩驳,只是希望此论能将大乘的唯识、中观二宗融会贯通。”
“可是师兄啊,羯罗从未听说这两宗可以融通的。”
“这正是玄奘所不解的。”东土法师有些困惑地问道,“正法藏乃是护法菩萨的嫡传弟子,师子光大师则是中观学派婆毗呔伽一系的传人,他们所持的见解看似不同,仔细想来却是一体之两面,完全可以融会贯通。玄奘不明白,为什么从前的那烂陀寺无人做这件事情?”
“因为别人的想法都没师兄这么古怪。”般若羯罗忍不住说道,“论师之间彼此有分歧,不管是损毁也好,质疑也罢,只管拿到台上辩论就是了。若是都融通了,岂不是再也没有思辨了吗?”
玄奘怔了一下,他早已听出般若羯罗不赞成融通,初时还只当是对师子光长老的不满,现在看来并不全在于此。他隐隐觉得这位上座部同修的说法中似有什么东西,在他脑中灵光一闪,就隐去了……
他抬起头,希望这位师兄再说些什么,好让他重新抓住这点灵光,却突然看到不远处一座高塔外走过来一头青象,象背上的人朝这边望了一眼,只一瞬,就又将脸转了过去。
虽然只是一刹那间,玄奘还是看到了一双很熟悉但却充满怨恨的眼睛……
“师子光长老……”他喃喃自语,一时竟突然有了一种坐在火山口上的感觉。
“师兄你在说什么?”般若羯罗奇怪地问道,“师子光长老?他不是称病告假了吗?怎么,师兄你刚才看到他了?”
“没,没什么……”玄奘随口应着,心想,或许刚才只是眼花了。
“师兄方才说,一旦融通,就再无思辨了,玄奘有些不明白。”他又将话题转了回来。
“那不过是羯罗自己的想法罢了。”般若羯罗谦逊地笑笑,“师兄的想法一向与众不同,羯罗是知道的。再说,既然正法藏都欣赏和赞叹师兄的会宗理论,羯罗又能说什么呢?羯罗今日与师兄同路,一来叙旧,二来辞行。”
“你要走?”玄奘心中顿感诧异。
“是啊,大王已经派特使来了,昨天下午到的。”般若羯罗略有几分不舍地说道,“想想也是,羯罗已经在那烂陀寺学习了五年,虽然不能将所有上座部经典阅尽,但生命有限,不能总在这里逗留,因此还是回去的好。特使说了,大王希望羯罗能在雨季前赶回磔灿国,这样便能赶上国内的雨安居了……”
后面的话,玄奘完全没有听清,他只是喃喃自语:“是啊,人命如露,弘法的事情总是要做的……”
心中不可遏制地想到了自己的故乡——日月如梭,自从离开长安之后,十年时光已如流水般过去,不知何时我方能回归故里,将佛陀的法露遍洒神州?
“两位骑着好大的蜗牛啊,都这会儿了才爬过来!”
这个刺耳的声音出自一个浑身赤裸的家伙,他年纪不大,容貌却是沧桑丑陋,令人生畏。此刻他正站在戒日王院门前,看到刚刚骑象过来的两位僧侣,便张开四肢,夸张地做了几下爬行的动作,样子十分滑稽古怪。正值正午时分,烈日高悬,将他全身上下晒得黝黑发亮,他却浑不在乎。
“伐阇罗,又是你啊。”般若羯罗很随便地打着招呼,“这么大的太阳,你也不找个遮荫的地方,就这么肉干似的烤着……咦,你又抓蚂蚁去了?”
玄奘也注意到了,伐阇罗干瘦的手中举着一根树枝,上面密密麻麻的满是被晒成干的白蚁。
“天热,味道正好。”伐阇罗咧嘴笑着,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黑色牙齿,“晒晒太阳不好吗?太阳神不仅带给我们光明,同时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烹调大师呢!”
说罢伸出舌头,在树枝上舔了一口,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
那烂陀寺刚刚成立时有着严格的录取规定:相貌猥琐的不招,出身低贱的不招,品行差的也不招。但是现在,录取条件放宽了许多,只要有心学习并能通过考试的,皆有机会进入。
所以像伐阇罗这样的,也能成为那烂陀寺的一员。
玄奘有些看不下去了,说道:“玄奘那里还有些瞻步罗果和供大人米,居士尽可以拿去吃。”
“谢谢。”伐阇罗仍在津津有味地舔着树枝上的白蚁,“我的肠胃对那些大德吃的东西不感兴趣,它更喜欢白蚁,我猜我的前世一定是只食蚁兽。”
“所以把业力带到今世来了。”般若羯罗笑道,“这样的天气,苍蝇蚊虫什么的都被热死了,这小小生灵居然还能存活下来,真是奇迹!”
“蚂蚁的生存能力是你们想象不到的。”伐阇罗不屑地说道,“它们住的地方可凉爽了!我的树枝伸进去,又拔出来,就可以感觉到这种清凉。你们知道它们出来觅食的时候,是怎么保证不被热成干的?”
玄奘道:“我在沙漠里曾见过一种蚂蚁,它们多数时候都藏在很深的沙地里,早晚出来觅食。它们爬得飞快,听一些沙漠居民说,如果它们不能及时回洞,头就会被晒昏而迷失道路。”
“哪里是晒昏的事,是脑浆子会被烧开!”伐阇罗咧着嘴笑道,“这里的蚂蚁不同,它们就像一群黄色的麦粒,总是随着最强的阳光出现。看到它们,你就会发现无知的好处。想想看,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外面待得久了,脑浆子会开锅,你还会出门吗?”
“阿弥陀佛。”般若羯罗合掌诵了一声佛号,“生存如此不易,居士还要吃它们。”
“那是,我不度它们谁度它们?”伐阇罗咂着嘴说。
玄奘无奈摇头,伐阇罗是个露形外道,但他不属于耆那教的天衣派,后者是修苦行的,绝对不可能杀生。
也幸好类似伐阇罗这一派有不良嗜好的露形道人数量稀少,否则这些有着出众建筑天才的白蚁早就该绝种了。
上楼的时候,玄奘还在想,那个骑青象的人是不是师子光长老呢?
“你们知不知道,食蚁兽具备很强的预卜能力。”伐阇罗不知何时已跟随他们进到院内,边上楼边喋喋不休地说道,“这种能力,今世的我依然具备,怎么样,要不要我为你们卜上一卦?”
“正要请教。”般若羯罗道,“我最近准备回磔灿国,仁者给看看行程顺不顺利?”
“太遗憾了。”伐阇罗摇晃着脑袋,“为什么好朋友一定要分开呢?”
我们也算是好朋友吗?般若羯罗觉得好笑,但他还是解释道:“爱别离乃是人生八苦之一,每个人都要经历,仁者有什么好遗憾的?”
“那是你们佛家的说法,我就喜欢跟谈得来的朋友长相厮守。”
“你还是多交些天衣教的朋友吧。”般若羯罗笑道,“对了,叫你来替我占卜,看看行程,说这些做什么?”
“我已经占好了。”伐阇罗捏着手印,摇头晃脑,“堂堂国师,哪有不顺的道理?我预测你们的国王一定会派人率象队沿途迎候你的,你会安全抵达你的国家!”
这种便宜预测却让般若羯罗很是欢喜受用:“谢你吉言了,对了,你给奘师也卜上一卦?”
“谢谢,我不需要。”玄奘边说边将他们让进房间。
“我预测你一定需要。”伐阇罗顺手拾起玄奘刚刚脱下的草鞋,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用香茅草做成的精致的编织品,“真是奇怪!你怎么有心思和时间去做这么精巧的玩意儿!”
“这也算不得精巧吧?”玄奘道,“做这个不需要多长时间,我读经累了,闲暇的时候就可以做。”
伐阇罗不解地摇了摇头:“我真是搞不明白,好端端的,在脚上套这么个东西,不难受吗?”
玄奘心说,像你们这样,光脚踩在滚烫的路面上,才难受吧?
不过他没把这话说出来,各人习惯不同,这种事情没必要反驳。
因而只是笑着回答:“难受不难受,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情啊。”
“说得也是。”伐阇罗道,“我是永远也搞不懂你们这些穿衣服的家伙了。而你比别人更极端,连脚都要穿上衣服。别说,你编得还真漂亮,这些打弯的地方居然和人的脚一模一样,真有心思!你们国家的人都穿这么漂亮的鞋子吗?”
玄奘苦笑:“这是草鞋,是最简陋不过的了。我的国家的人穿的鞋子,种类之多,制作之精,是你想象不到的。”
“为什么?”伐阇罗茫然问道,“头和身子很高贵,因此衣帽做得精致漂亮些可以理解。脚那么下贱的东西,为何也要照顾它们?”
这下轮到玄奘不理解了:“你自己身上的部位也分高低贵贱吗?”
“这是梵天分的,关我什么事?”伐阇罗振振有词地说道,“难道脚不是长在最下面吗?有眼睛的都能看得见吧?”
玄奘道:“它是长在下面,但这并不表示它就低贱。如果脚伤了,不能走路了,头和身体估计也高贵不到哪里去吧?”
“怎么不能?”伐阇罗瞪着眼道,“如果我有高贵的头脑和身体,即使没有脚,也可以让别人抬着我走,让其他人做我的脚。但是如果我的头脑和身体是低贱的,即使有一双好脚,也是替别人奔波的奴隶!”
这个回答还真是正确无比,其中蕴含着的“强大”逻辑令玄奘彻底无语了。
他只能说:“玄奘和你的想法不同。对我来说,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出了问题,都会令我很不舒服。所以我会平等地照顾它们。”
“你还是更照顾你的法身吧?”一直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说话的般若羯罗突然插了一句嘴,“听卢达罗耶说,你每天都睡得很少,多数时间埋头于经典之中,这是平等照顾自己身体的行为吗?”
玄奘有些无奈,这位师兄怎么选择这个时候跟他顶牛?
伐阇罗哈哈大笑:“就是这样,咱们两个联合起来,把玄奘法师辩赢!”
“你们已经赢了。”玄奘无奈地说道,“我认输。”
“别呀!”伐阇罗道,“你还没跟我说,为什么你的国家的人都把脚上的鞋子做得那么精致呢!”
这位的好奇心怎么这么强?玄奘只得解释道:“我的国家有一个季节,天气非常地冷,若不穿鞋,脚指头会被冻掉的。”
“我知道啊,那些大雪山上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以他们会用毛皮把脚包起来。但是这里的天气不冷啊,你为什么还要拿这扎人的东西把脚包起来呢?”
玄奘道:“习惯而已。”
伐阇罗不是第一个对他的草鞋感兴趣的印度人,自从进入这个半岛,包括佛教徒和婆罗门教徒在内的很多人都把他的鞋子当艺术品。其实印度人也不是完全没见过鞋子,佛陀在《大智度论》中就曾经提出过这么个问题:一个人要走远路时,为保护两足,是把道路上铺满皮革呢,还是只要在两足包上皮革呢?佛陀教人的方法自然是在脚上包上皮革。
但这仅仅是一种说法,佛陀自己在印度各地弘法都是赤足的,普通印度人自然也没有穿鞋的习惯。只有北方地区那些雪山脚下的人,才会用毡布包住双脚来过冬,因此他们看到玄奘脚上的鞋子还是颇有新鲜感的。其实别说鞋子了,多数印度人连衣服都不裁剪,只将布料用各种固定的方式搭系在身上,何曾见过把鞋做成分左右脚的模样?
玄奘懒得多做解释,伐阇罗也决定暂时放过这个话题了:“现在,正法藏要我来请法师,你不想知道有什么事情吗?”
正法藏请我?玄奘不由得回过身来,这个伐阇罗!东拉西扯了一大堆,直到现在才说到正题!
“我想,一定是为了《会宗论》的事。”般若羯罗猜测道。
“不不不。”伐阇罗摇头道,“我的预测是,正法藏是要请玄奘法师做长老,设筵讲经。你想啊,奘师现在有这么大的名气和修为,总听别人讲经不是太浪费了吗?”
听了这话,般若羯罗顿时面呈喜色:“那羯罗要先恭喜师兄了,能在那烂陀寺开讲筵的都是真正的大德!可惜羯罗即将回国,听不到师兄讲经,真是太遗憾了。”
“阿弥陀佛。”伐阇罗竟念了一声佛号,“原来你也有遗憾的时候。”
玄奘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这两位,居然把预测当真了!特别是伐阇罗,光着身子念佛,真是闻所未闻。这样的人也有预测能力?
再说了,那烂陀寺的讲席可不是谁都能开的,只有精通经律论的高僧大德才有资格获此殊荣,自己毕竟是来此学习的外国求法僧,设的哪门子经筵啊?
相比之下,倒是那个并不懂得预测的般若羯罗,说出的话还比较靠谱,正法藏这个时候请他,十有八九是为了《会宗论》的事。
伐阇罗已经扯了大半天,也不知正法藏等多久了,我可不能再在这里跟你们闲聊了。
想到这里,玄奘一把夺过伐阇罗手上的草鞋,一边穿在脚上一边说:“多谢居士,请居士在此稍坐,回头玄奘还要请教。”
“你去吧。”伐阇罗微笑着挥了挥树枝,“我正好在此品尝一下那些只有大德才能吃到的美食,看看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注释:
[1]所谓“如来藏”,就是“性宗”,传入中国后称“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