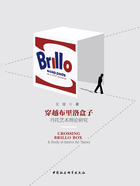
一 艺术的定义问题
丹托在艺术界的名声缘于1964年的《艺术世界》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丹托提出了“艺术世界”的观点,认为艺术制度和艺术理论知识对艺术品具有重要的作用。
艺术的定义问题始终是丹托艺术哲学的中心问题,本书也将从丹托的艺术定义的发展及艺术的内涵两方面加以研究。
首先,丹托提出的“艺术世界”(the artworld)[25]来自所谓的“杜尚之谜”,即艺术的身份确认问题。“艺术世界”的作用在于,用“艺术理论”确定艺术范围,即艺术理论造就艺术身份,从而为“艺术定义”提供一个必要的条件。在构建“艺术世界”的过程中,丹托将“叙述句子”引入定义,从而使得历史和时间成为艺术阐释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艺术世界》中,丹托首次提及波普艺术,并将之视为其理论的现实实现。如此,一方面,波普艺术成为丹托艺术理论产生的现实来源;另一方面,波普艺术也成为日后丹托艺术理论的实践支撑。正如丹托自己所说,通过波普艺术提出了自身真正的哲学问题,并转化了生活中对人们最有意义的东西,将它们提升到高级艺术主题的地位之上。由于波普把人人知道的东西转化成了艺术,所以是当前历史时刻集体思想的表现。由此,波普不仅成为丹托哲学中“现在时刻”的一个重要的论证,而且也预示了未来的艺术发展方向。
当“艺术世界”完成对艺术理论的确认后,丹托开始致力于“艺术定义”工程。这一任务在《寻常事物的变容》中全面展开,基本上确定了“艺术”的系列要素。随着丹托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丹托在1997年的《艺术的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界限》中,给出了“极简主义”的艺术定义,在第二章我们会重点展开谈论。对于研究丹托的学者来说,这个定义的问题在于,它搁置了丹托早期艺术哲学的“不可辨识”问题,无法形成对艺术理论和历史叙事的观照,进而把丹托置于一个思考普遍定义的困境中。因此,丹托后期艺术哲学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满足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普遍艺术定义;二是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关系。对第一个问题,丹托在强调艺术品的意义的同时,以“一切皆可”的艺术形式做出回答;第二个问题,他则认为艺术哲学一直在等待着艺术史,艺术史因为艺术本质的到来而终结。
尽管卡罗尔批判丹托放弃了早期对艺术理论的关注,不过,这也是丹托哲学的必然发展结果。在早期的哲学中,丹托批判实质的历史哲学,它的错误在于能假定我们能在事件发生之前书写事件的历史,因而溢出了现世知识的范畴。虽然丹托赞同布克哈特的看法,认为“历史哲学”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但他自己的历史哲学依旧呈现相似的矛盾。一方面,丹托的旧定义用艺术理论和氛围来限定,不仅使得现实同艺术实践之间产生矛盾,而且也让很多东西被排除在艺术之外;另一方面,丹托的新定义似乎呈现出无时间性、无历史叙事、无历史背景限定等无限开放的状态。所以,丹托的困境在于,无法圆满地解决艺术定义在历史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的矛盾。不过,笔者认为,丹托后期越来越偏向意义,因而,他事实上更加重视语境,靠近历史主义。
从分析美学内部来看,丹托的“艺术世界”始于反对比尔兹利用“审美”标准定义艺术,进而为以审美为基础的传统艺术定义画上了句号。丹托“艺术世界”的观点也直接影响到迪基提出“艺术惯例论”,他们二人被视为从“空间维度”来界定艺术,即都倾向于从社会约定俗成的空间氛围来框定艺术。[26]基于这种原因,丹托的“艺术世界”与迪基的“艺术圈”常常被等同。所以,全面了解丹托的艺术定义的内涵,有助于区分他与迪基的本质不同。从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丹托也强调艺术氛围,然而他主要从艺术的本体存在来谈论这个问题,即他在给艺术品划定范围之后,重点围绕艺术品与单纯的真实客体在本质上的区分来讨论艺术定义。相反,迪基提出的“惯例”更像是一种内在的、约定俗成的习俗,尽管它不同于一种外在的团体或者机构,然而,它具有决定某物是否为艺术品的能力。因而,迪基的艺术定义呈现出一种外部“授权”的行动特点,对艺术品的认识就不属于本体论上的认识。因此,即使后来戴维斯(Steven Davies)把他们的定义都归为“程序主义”,但二人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第二章第三节我们将具体讨论。
总之,艺术定义作为丹托艺术哲学的中心问题,一开始就同波普艺术这一艺术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促使他把艺术与美学区分开来。此外,艺术定义的不断修正不仅指向丹托哲学重心的偏移,而且也使得丹托的艺术理论呈现从内到外的转变。因而“艺术的定义”既是解读丹托艺术理论的起点,也是一个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