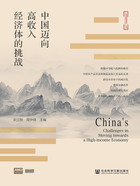
一 在发展阶梯上的动态变化
过去40多年来,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是改革开放与人口结构良好结合的结果(Lin,2013a;Cai et al.,2018)。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基本模式时,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强大激励效应与中国在高增长时期的充足的劳动力供应表现得非常匹配,尽管这些劳动力供应最初是低技能的,但在发展的后期逐步转向了高技能(Li et al.,2012)。我们可以从这一经验中获得一些关键的发展启示。
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制造业发展为中心,尽管近年来制造业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有所减少,但制造业仍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见图1.1)。工业投资创造了就业,空前地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建立了综合性制造业基地,并先后通过深化国际一体化和专业化,遵循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东亚制造业增长模式和深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逐步将中国转变为一个国际性的工业强国(Kojima,2000;Lin,2013b)。正如卡尔多增长定律所阐释的那样,制造业的发展具有正向外部性,也就是说,制造业产出增长与GDP增长、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制造业以外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之间,均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Thirlwall,2015)。一项使用中国省际数据所做的经验研究验证了这种增长规律(Thirlwall,2011:111)。

图1.1 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1996~2020年)
数据来源:作者使用CEIC数据库的数据计算。
第二,中国工业部门的发展并没有使农业部门的发展显得落后太多。事实上,中国农业部门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刷新着生产力增长的纪录,也实现了自身的转型(Sheng & Song,2019)。大量农民工不断向城市流动,同时随着农村家庭收入的稳步提高,农村已经成为工业品需求的重要来源。农村改革和城市化实现了工业部们和农业部门的相互支持,使得两个部门的收入迅速增长,并缩小了差距。2005年,中国的农业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取消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Heerink et al.,2006)。当然,为了深化农村改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土地流转和农村宅基地改革等(Liu,2018)。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些国家,通过实施偏向城市的政策(Pugh,1996),工业部门的增长往往以牺牲农村部门的发展为代价。这种发展模式最终拖累了整体经济发展(Lipton,2007)。
第三,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成功。政府和私人部门通过对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高铁、大型水利工程、电力和天然气设施等的大量投资,为国内外投资铺平了道路,并在加快市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商品、生产要素和思想更自由的内部交流(Qin,2016;Song & van Geenhuizen,2014;Yu et al.,2012)。新地理经济学文献表明,市场扩大带来了市场竞争加强和可竞争性增强的好处,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知识和技术的进一步传播(Canning & Bennathan,2000)。正如Canning和Bennathan(2000:2)所说的那样: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腾飞依赖于一场高度协调的投资运动,那么通过公共协调的方式提供具有投资风险的大型基础设施,就有可能激发私人部门投资,并由此脱离贫困陷阱。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支持了这一点。如今中国正在开展“新基建”,以加强对数字经济的投入(Meinhardt,2020)。
第四,以1995年从关贸总协定(GATT)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与全球化进程的实施期和再实施期高度重合。在世界贸易组织主持下,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加快,中国已经成为这一进程的重要参与者。2021年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周年。此前20年中,中国通过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和按照入世时所做的承诺进行国内改革,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国(Drysdale & Hardwick,2018)。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21)的数据,截至2020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而当时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下降了42%。不仅如此,中国还成为海外市场的重要投资者。2019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18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大国。尽管相比201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峰值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2019年同比增速达到11.7%)。为了完全满足入世要求,中国在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市场、深化国内改革和解决诸如知识产权、国家补贴、市场竞争和国有企业等一系列的改革问题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Yu,2018;Zhou et al.,2019)。
第五,在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础上,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在创新和技术革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研发支出同比增长10.3%,达到2.4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780亿美元(NBS,2021)。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20年,研发支出占中国GDP的2.4%[见图1、2(a)]。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共有52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350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运转;2020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了大约457000个项目,产生了360万项专利——相比2019年增长了40%。这些发展使得中国在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几个关键领域均实现了技术能力跨越,并使中国在从技术模仿到创新的过渡过程中,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Zhou,2014)。根据全球创新指数中的全球131个国家和经济体创新绩效的详细指标,中国的创新绩效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十四。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WIPO)报告显示,其中国办事处在2018年共收到了创纪录的154万件专利申请,领先于其驻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的办事机构。2018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美国和日本的专利申请数略有下降。2019年,全世界超过84.7%的专利申请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专利局(EPO)的知识产权(IP)办公室。中国的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量的40%以上(见图1.3)。

图1.2 各经济体的研发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密集度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计算。

图1.3 2019年主要国家专利申请数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数据库。
在提升技术能力方面,中国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更加紧密地合作,从而在新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和5G网络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例如,截至2020年,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5G网络,5G基站占全球总数的70%以上,并在关键5G技术的专利注册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高度重视“5G+工业互联网”战略,并且这一战略已经连续四年在中央政府主要工作报告中得到了强调。根据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的数据,中国在建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100项,涵盖了水泥、汽车、石化、钢铁、采矿和石油等22个行业(新华社,2021b)。
根据工信部的一份报告,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19.1%(新华社,2021a)。可以预期,这些前沿技术特别是与经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技术,将促进整个经济体生产力的提高。这种转变将在新的工业化模式、新的贸易和跨境技术转让模式以及新的消费模式等方面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第六,这种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环境的恶化。中国长达几十年工业主导增长模式的特点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的快速增长,工业制成品和消耗的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的增加(Roberts et al.,2016;Zheng et al.,2020)。中国的碳排放及其在全球碳排放中所占的份额从1970年代开始持续增长,尤其是在2002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加快,碳排放增长明显加快,在2007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鉴于自身工业化的规模、速度和轨迹,中国在碳减排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然,考虑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代价,转向低碳增长显然符合国家整体利益。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采取了包括技术变革和创新、市场价格机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消费模式转变等在内的一系列大的举措,以实现低碳增长(Jiang et al.,2013),这符合国家整体利益。
第七,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Kharas,2017),消除了绝对贫困(Guo et al.,2019);全民医疗覆盖了93%的人口,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62%。凭借大量的教育投资,中国通过义务教育和庞大的培训体系显著提升了国民的识字率。中国的大学也开始进入全球顶尖大学排行榜(Fraumeni et al.,2019;Li et al.,2014)。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见图1.4)。

图1.4 1990~2020年中国各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CEIC数据库数据数据计算。
由于死亡率持续下降且生育率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人口老龄化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趋势,而非只是发生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Zhao,2011:296)。
总体而言,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经济转型有三个重要的机会窗口。中国已经成功地应对了前两个挑战,但尚待时日证明其在第三个挑战中的成功。第一个机会窗口是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机遇,中国果断地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拥抱开放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创造财富,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第二个机会窗口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承认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从而让中国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市场化体制,并实现与世界其他国家高度相互依存。从那时起,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为改善全球福利水平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因巨大的调整成本给其贸易伙伴带来了强烈的竞争压力。第三个机会窗口是关于中国在新冠疫情出现后的世界中,如何拥抱数字技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并应对结构变迁、去全球化、人口老龄化、收入不平等、公共部门债务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挑战。成功应对所有这些重要挑战,是中国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关键。
与此同时,中国长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如资源配置不当、效率低下、高碳排放强度、收入不平等以及缺乏市场相容的制度等。在中国已经实现部分变革的体制背景下,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广泛的供给侧改革、制度建设和社会变革来解决,以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生产成本上升导致无法提高生产力和实现技术进步,因而无法生产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最终导致收入增长的停滞、社会失去增长和发展的动能。因此,建立与市场兼容的体制是确保长期增长与发展的关键。
如何避免“未富先老”,是中国需要回答的紧迫问题(Dollar et al.,2020)。中国迈向老龄化社会的步伐凸显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涉及生育政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改革。考虑到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在减速,这种担忧不无道理,部分原因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下降,出生率持续下降,总人口预计将从2025年开始下降(Bai & Lei,2020)。经济增速的下降部分也是因为近年来生产率水平的下降。对此,中国的“十四五”规划提出从2021年开始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旨在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建立更加成熟的市场体系,继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应对气候变化和收入不平等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