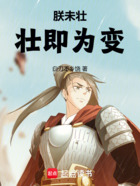
第69章 长安将成,诸王将朝(求追读~)
吕太后言辞恳切,搞得旁观于侧的刘恭心中,都不免生出阵阵嫉羡。
——就这教导方式,不说是身体力行的手把手教,也起码是把道理揉开嚼碎,再嘴对嘴喂给刘长了。
刘长接下来的反应,也未让吕太后失望。
没有硬着头皮继续犟,也没有从善如流的拱手称是。
而是微皱着眉,略带疑惑间,终开口发了问。
“儿臣,难道错了吗?”
“——身为人子,得知母后受辱,儿臣难道不应该悲愤?”
“难道儿臣应该故作不知,对母亲受到折辱——对嫡母太后受辱视而不见?”
闻言,吕太后自又一阵摇头失笑,望向刘长的目光中,却更多了几分怜爱。
刘长仍一脸困惑,吕太后也不再开口,而是朝刘恭稍一昂头,将话头递了出去。
便见刘恭沉吟片刻、思考一番,而后,才明显刻意的迟疑道:“嗯…侄儿倒是认为,王叔这怒,似是怒错了地方。”
“——母亲受人折辱,做儿子的,似是更该为母亲撑腰才对?”
“母亲本就受了折辱,再被儿子指责‘没有强硬反击’,只怕非但不能受到抚慰,反而还会更伤心些……”
话说一半,刘恭更是演技爆发,煞有其事的皱眉思考起来。
似是真的思考许久,方面带犹豫道:“王叔,似乎真的错了。”
“皇祖母为匈奴单于冒顿所辱,王叔应该对冒顿发怒,而不是对皇祖母。”
“王叔应该说:冒顿安敢辱我母?!”
“我与冒顿不共戴天!”
“而不是说:我母受辱,乃我母软弱好欺之故;我母如此作态,当真气煞我也。”
言罢,刘恭还不忘‘忐忑不安’的望向吕太后,似是在问:不知孙儿说的可对?
而御榻之上,吕太后也是应声作落寞之态,似是真被刘长伤透了心。
见此状况,刘长先是狐疑不定的侧身看向刘恭:当真如此?
而后又望向御榻之上,见吕太后一脸受伤,更是不由急躁起来。
“母、母后!”
“儿臣!”
“儿臣……”
一副快急哭了的架势,也是让吕太后顿生不忍。
没等刘长真急哭,便见吕太后温尔一笑,旋即语重心长的说道起来。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只要能让阿长,明白这世间的道理,朕,便别无他求。”
言罢,吕太后又向刘恭一挑眉,嘴上却仍是在说教刘长。
“且太子方才所言,只是为人子者,对待母亲的道理。”
“——阿长,不单是朕的儿,也同样是我汉家的王。”
“——淮南王。”
“遇到类似的事,阿长不能只想着:我母如何如何,作为儿子,我当如何如何。”
“而是也要想,甚至应该首先想:太后如何如何,作为淮南王,寡人,又当如何。”
…
“等什么时候,阿长逢人遇事,能首先想起自己是淮南王,而非朕与先帝的皇七子,朕,便也就能忍痛,送阿长离京就藩了。”
话音落下,吕太后仍目光灼灼望向刘长,眉宇间,却一片说不尽的柔情。
而吕太后目光所至,淮南王刘长则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思虑良久,方似有所悟般,起身拱手一礼。
“儿臣,明白了!”
“母后今日之教诲,儿臣谨记于心!”
“等儿臣就藩,北蛮匈奴再敢来犯,儿臣必尽发淮南国兵,引军北上,以血母后受辱之耻!”
刘长话音落下,御榻上的吕太后,以及落座于刘长次席的太子刘恭祖孙,皆是忍俊不禁的摇头苦笑起来。
“匈奴人,不是阿长该关心的。”
“阿长该留意的,是南边。”
呵笑之余,吕太后又下意识道出一语,不等刘长反应过来,便含笑低下头。
抓过一卷未处理的奏疏,于面前摊开。
笔尖蘸墨,再提笔半悬空中,嘴上也终是下了‘逐客令’。
“即是要去探望鲁元,便早去早回。”
“夕食到长信共餐。”
“朕叫尚食备了炙牛。”
听到有牛肉吃,刘长当即咧嘴一笑,方才种种也都被刘长抛到脑后。
下意识要告退,余光扫见刘恭仍坐在次席,又呵笑着再道:“母后。”
“让阿恭陪儿臣同去吧。”
却见吕太后微一皱眉,头也不抬道:“自去。”
“朕还有话要问太子。”
请求被驳回,刘长却也不多纠缠。
只稍有落寞的看了刘恭一眼,便脚步轻快的退出殿去。
临走时,还不忘压低声线,朝刘恭轻声嘀咕一声:“阿恭莫忧。”
“若母后不留阿恭,那炙牛肉,寡人便给阿恭留一块!”
看着刘长无忧无虑,满心欢喜的离去,刘恭自又是一阵失笑摇头。
待殿内再度安静下来,刘恭才缓缓站起身,拾御阶而上,于吕太后所在的御榻旁站定。
“安国侯,可曾为难太子?”
刘长离去才不过三五息,吕太后方才还温情满满的语气,便再度恢复到平日里,那近乎融入灵魂的本能淡漠。
听闻此问,刘恭也只稍一躬腰:“不曾。”
言罢,又似是怕吕太后不信般,苦着脸补了一句:“呃…也算不得为难。”
“只老师脾性率直,孙儿,还需适应一些时日……”
便见吕太后微一颔首,轻‘嗯’了一声。
专注于手中政务,故而沉默良久,方冷不丁再道:“长安城,将告建成。”
“岁末九月,诸宗亲藩王,皆当朝长安以为贺。”
“——代王今岁本就当朝,出发的早些,昨夜便到了新丰,至多再两日便到长安。”
“指望皇帝亲迎,想来是痴人说梦。”
“若不迎,又恐其余诸王,怨皇帝不亲手足。”
…
“劳太子假节,代父出城相迎。”
“顺带替朕探探代王。”
说到此处,吕太后终是抬起头,面无表情的望向刘恭。
“先帝皇五子:赵王刘友,后宫不宁,治国不勤。”
“朕,欲使代王移封赵地。”
“太子替朕探探,看代王是否愿意移封,又能否肩负起赵国的重担。”
…
“太子如何问、代王如何答——又代王言谈口吻、举止神态如何,皆记下回奏于朕。”
“再留意一下代王与王后之间,究竟是真的举案齐眉,还是于外人面前惺惺作态。”
“——这,也算是对太子的一道考验。”
“识人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