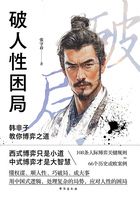
第7章 扬权:把持住要害点
1 圣人执“腰”
原文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无害。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行之不已,是谓履理也。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因而任之,使自事之。正与处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谨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为圣人。
作者智解
那些香甜美味,厚酒肥肉,虽然嘴上好吃,但是对健康不利;皓齿美女,虽然能够娱情,但是损害精力,所以要去掉过分的、奢侈的,身体方才无害。
(这是讲人应该寡欲,控制自己的欲望。关于这个,可以讲一下蛇的案例。有一种虫叫作虺,它一条身子两个嘴,互相争着咬,最后把自己咬死了。这个故事想说明,人必须控制欲望,如果听凭欲望发展,就会搞内讧,自相残杀,最终没有赢家,就像蛇自己吞吃了自己。)
权力不应该被暴露出来,要表现得朴素、无为。事情都在四方发生和运作,但关键的“腰”就要握在中央。(腰,通要,就是要点、关键点,要抓住的)圣人执这种“腰”,四方都来效命。虚而待之,对方会自然成形。顺着走下去,这就叫“履理”。
(意思是,领导者只需要抓住关键要点。如果面面俱到,就是过度,领导者是无法跟下属竞赛的。把握住“腰”,也就是关键处,然后虚而等待,事情即能自己走下去。)
事物都有它适宜的方面,材料都有适合施用的地方,让它们各处其宜,这样上下就都可以省力气。叫鸡去报晓,叫狸去抓老鼠(当时还没有猫),都是用它们的特长,这样上面的人也就清闲无事了。如果上面人有擅长的东西,偏去耍弄,这样下面的人就办不成事。上面的领导自矜某方面能力,就会被下面的人趁机欺骗。所以,圣人执一而静,因着下属的特性而任使之,使他自己去做事。因缘着他的特点而给了他机会,他会自己做起来。正确地把他安处好,使他自己建立事功。上面的人根据名声来举用某人,不知道他的名声是否可靠,就再考察他的形。形名相符,这才成功。
谨慎地做自己的事,以等待天命,不要失去其“腰”,才能成为圣人。
延伸论据:管仲——让君主给自己授权
以上其实还是讲君臣分工。君主执“腰”,抓住关键,顺着下属的自然特点,听凭下属把事情做好,这是本节的主要意思。
领导自己做得少,而让下属做得多,这是领导之术。一次,有司去向齐桓公请示一件事。齐桓公说:“去跟仲父说去。”(仲父就是管仲。)有司又来请事,齐桓公说:“告诉仲父去。”如是者三。旁边的近臣说:“一说是找仲父,再说是找仲父,当国君真容易啊!”
齐桓公说:“我没有得到仲父的时候,很难,得到仲父之后,为何不变得容易呢?”
这就是君主执“腰”,臣子任事。君主腾出精力思考国家的方向以及大的决策,授权之后,叫臣子自己提出目标,然后再去考核臣子。
这就是韩非子说的,领导者应该执“腰”,只抓要点,其他进行授权。
2 上位者为什么要保持虚静
原文
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国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虚以静后,未尝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万民一从。
……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凡听之道,以其所出,反以为之入。故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听言之道,溶若甚醉。唇乎齿乎,吾不为始乎;齿乎唇乎,愈惛惛乎。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根干不革,则动泄不失矣。动之溶之,无为而攻之。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主上不神,下将有因;其事不当,下考其常。
作者智解
圣人之道,就在于去掉智和巧。不去掉智和巧,难以有恒常的治理之法。普通人用智和巧,自己就会遭殃;君主用智和巧,也会亡国。要顺天之道,回到事物的理,进行督查检验,这样以终为始。要虚和静,然后得到结论,不要用自己的主观判断。凡君主的错误,就是在对立的观点中,认同其中一端的观点。要真诚地对待,不要只赞同其一端,这样万民才能统一跟从。
(这里反对智巧,其词义跟当今不完全相同。在韩非子乃至老子的语境中,智巧是人为,是人的私智。你以为是智和巧的,其实可能是偏见,是一端。在韩非子的语境中,运用客观的法,而不是主观的智和巧,就是他反对私智和巧的意思。上级和君主,就要虚和静,不自以为是,先入为主,不把自己固定在一端上,这样才能得到万民,否则会失去一半。
如果你固定在一点上,就会被人迎合,那么,即便你执的一端是好的,比如要俭朴,也因为迎合而变得荒唐,上文举过这样的例子。好的工具,一旦变成了目标,就会闹出弊病,所以圣人弃掉智巧,保持空虚。韩非子在这里,一定程度上受老子的思想影响。以上说的是君道。)
君和臣的道是不一样的。臣以名来提出申请,提出自己想做的事;国君抓住结果进行检验,看臣下是否名实相符,这样就上下和调了。(循名责实,形就是实。)
听下属汇报的办法是:根据下属说出的东西,检查他实际做成的东西。也就是审名以定位,确定他的类别。听下属说话的时候,自己好像喝醉了。我不要抢着先说话,而是让下属说,我保持昏沉沉的,让他评价和分析自己说的话,我因之而明白其正误。如果树根不动,那怎么摇晃树梢也没事,所以我要保持虚静、闲暇、无为。
如果相反,我表现出喜欢什么东西,他就会多事,多提要求;我表现出厌恶什么东西,他就会生怨,所以要去掉这些,让心空下来,来听。
主上不神秘莫测,下面的人就会顺着来利用。主上对事情的决策不当,下属就会把这当作常例沿用下来(从而作为借口)。
延伸论据:田子方和宫他——会盘问才不会被蒙蔽
主上不神秘莫测,下面的人就会顺着来。关于这一点,可以看这个案例:
田子方问唐易鞠:“射鸟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方答说:“鸟用数百只眼睛看着你,你用两只眼睛看对方,所以你一定谨慎,小心保护住自己的粮仓(射鸟就是为了保护粮仓的)。”田子方说:“善。这个道理也可以用于保住自己的国家。”别人用那么多眼睛盯着你,你只有做到虚无,才能什么都不表露出来,这样才能守住自己的国或权位,否则,你表露出聪明或者愚蠢,下面的人都会进行利用,从而欺瞒你。
所以,领导就要高深莫测,令人无法揣测、迎合、防备或者利用。即便表现出自己在某些方面很聪明、明察,也不行,因为对方会藏匿自己相应的问题,进行防备。不要表露出自己善于明察,也不要表露出不善于明察,不要表露出自己的聪明,也不要表露出自己的傻,对于别人的试探,不要表露出自己的欲望。
下属在跟主上讲话的时候,是藏着许多心眼的,所以这时候君主应该少说,让他自己充分展现,从而发现他话中的矛盾,探索他语言中的实情。我们举一个臣子与国君沟通的案例。
周趮对宫他说:“我要对齐王讲:‘请让我在齐国做大官,掌握齐国,我就能以齐国的威势,使得魏国来服从和侍奉大王。’”
宫他说:“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表示你还没有拥有魏国,需要齐国帮着加重你的分量,你才能掌握魏国,齐王肯定不干这傻事。齐王听你这么说了,就不会答应你了。你应该改说成:‘我能满足大王的所欲,我能让魏国来听从、服从大王您。’齐王就会觉得你已经拥有(掌握)魏国了,一定会答应你。这样你就能在齐国当大官,有了齐国,凭齐国之威,就有了魏国。”
宫他讲得比较绕。大致意思就类似于向领导介绍外面一个项目时,说我已经有了这个项目,而不是我拿着你的资源,才能做来这个项目。虽然实际并非如此。宫他教周趮,就是故意含糊和扭曲某些事实,这就是言辞的虚实。
那么,领导怎么避免被忽悠呢?办法就是韩非子说的,“我不要抢着先说话,而是让下属说,我保持昏沉沉的。让他评价和分析自己说的话,我因之而明白其正误。”也就是说,我保持半信半疑的状态,保持沉默,让他充分交代更深入的信息。当他说得多了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相矛盾,露出马脚。
3 小腿比大腿粗,不能快走
原文
欲治其内,置而勿亲;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门,唯恐多人。……毋富人而贷焉,毋贵人而逼焉,毋专信一人而失其都国焉。腓大于股,难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随其后。
作者智解
要治理内朝事务,就设置一个官,但不要对他太亲近(太亲近就无威)。要治理外朝,就每官设一个人,不要叫他们随心所欲,这样也就不会出现一个人同时有两个职权,或干预别人的岗位。大臣的家门,不能有很多人来登门(跑来追附结党)。不要使人富贵起来,那样他就能够来逼迫君主。不能专信一人而失去自己的国(专信一人,不如使用平衡术)。如果人的小腿比大腿还粗,那人就走不快了,所以臣子不能比领导还有势力。主上失去了自己的神秘莫测,虎就会跟在后面(指臣子就势力发展)。
延伸论据:李乾祐——不怕业绩差,就怕拉帮结派
以上说的,就是对于某个官职,不能给他过度的权力,不许他和别人交结、结党。信息也是权力的重要构件,所以也不能允许臣子之间分享信息和机密。所以,如果臣子和国君商量什么,臣子又把这信息透露给别人知道,君主都会严厉处置这种行为。
比如,唐朝的时候,有个官员叫李乾祐,他向皇帝推荐,想把崔擢提拔担任尚书郎。皇帝还没有完全批准这件事,李乾祐却把相关情况告诉了崔擢,这件事情后来被皇帝知道了。大臣把跟皇帝讨论事情的情形泄漏出去属于严重违规,“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于是皇帝就罢免了李乾祐,之后李乾祐很快就死了。
这里,皇帝之所以这么忌讳,就是厌恶臣子间横向联系,分享信息。如果臣子间互相通气,彼此商量,那就跟结党差不多了,皇帝的权力就会逐渐被侵蚀掉。所以,皇帝要求臣子和自己一对一地沟通,每个臣子互相都是孤单、独立的。
权力的来源之一,就是人际网络,人与人的网络联盟的力量是很大的。臣子以信息分享结成人际网,这个网的枢纽人物,就会拥有权力。企业员工中的无形的领导,就是这样的人际网的枢纽人物。他没有被任命,但一样拥有权力。在古代,这种人际网络,在君主的角度就被贬称为朋党。所以下一节,韩非子又抨击了朋党。
4 上下级一日百战
原文
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欲为其地,必适其赐;不适其赐,乱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将用之以伐我。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
故上失扶寸,下得寻常。有国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贵其家。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备危恐殆,急置太子,祸乃无从起。内索出圉,必身自执其度量。厚者亏之,薄者靡之。亏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亏之若月,靡之若热。
作者智解
想治理好国家,一定要伐掉那些聚居的大户或势力(指贵族、望族)。当给人封地、地盘时,给的多少一定要适当。给多了,这个人就会要得更多。他要我就给,这是把斧子借给仇人(对方势力会更大),这样,对方就会拿着斧子来砍我了。黄帝说过:“上下一日百战。”臣下藏匿自己的私心打算,来试探自己的上级,上级就应该使用度量(衡量),来切割下级(类似于木匠拿尺子绳墨,削平弯曲之处)。党友,是臣子的宝贝。臣子之所以不敢弑君,是因为党友不够。
上边的人失去一寸(把一点权力失给下属),下面的人就得了一丈。君主不要把臣子的封邑设得很大(这样臣下会据之反叛),君主不要使臣子过于尊贵(贵在古代指当官,富指有钱,贵和富还不一样),使他又贵又富,他就要取代你了。防备危害的办法是尽快定下太子,这样祸乱就不会起来了。
要自己拿着度量(类似绳墨、尺子,也就是法)。下属势力太强的,就给他削弱,势力弱的就给他壮大。弄多弄少,有量的要求,以不使他们联合一起欺负上级为标准。把他削弱,要逐渐地来,好像月亮逐渐亏下去;把他壮大,也要逐渐地,好像慢慢加热一样。
延伸论据:唐玄宗——更早的“杯酒释兵权”
这是讲,不能叫臣子发展成大家族,不能有大的封邑。如果臣子势力强了,要把他削弱。而下属中势力弱的,要适当扶植,使他可以制衡其他势力强的。比如,提拔一些新的、弱的,制衡老的、强的。
以汉朝初年为例,刘邦先是封了七大异姓诸侯,到了次年,就把其中的楚王韩信废掉。然后,刘邦把韩信的楚国,一分为二,淮东地区五十二城,封给将军刘贾为荆王,定都苏州;皇上的弟弟(刘老四)刘交,封为楚王,王淮北三十六城,定都彭城(离韩信从前的都城下邳不远)。
接着,刘邦又把自己的外室所生的长子刘肥,封到齐国,是为齐王,有七十余城。这个齐国,曾经也是韩信的封国。这就是削树枝,但也是一步步地,先削掉韩信这一根树枝,随后又用上“掺沙子”策略。
再以唐朝为例,在唐玄宗以前,每一代的皇太子,按理说都应该顺利继位,结果没有一个能继位,都被弟弟们杀死了,由弟弟乃至侄子通过政变夺得皇位。
弟弟总是夺皇太子权。当然,弟弟本人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正是贵族的力量大,帮助他做到了这一点。如果贵族弱,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比如明朝),而且贵族们也分成帮派,支持不同的皇子。于是,唐玄宗继位后,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辅助下开始限制皇室贵族的权力,包括这些举措:
第一,将有政治号召力的李姓亲王(亲王即贵族)都遣往地方担任刺史,而且并不负责具体管理,只挂虚名。为了防止诸王跟地方形成过分紧密的联系,诸王还需经常更换辖州。
第二,削减亲王、公主的僚佐系统。在唐朝前期,诸王都有王府,李世民能发动政变,靠的就是王府里的文官武将。唐玄宗上台以后,对此严加限制,从而堵住了秦王和他的僚属结成集团之路。这就类似于韩非子说的,不能让臣子有党友。亲王府里的官员,不能由亲王自己任命,而是要朝廷统一任命,这就是限制臣子党友的办法。
就这样,历任皇帝积累下来的叔叔、大伯、侄子等远近亲戚贵族亲王的人脉,势力就变弱了。他们弱了,就没有能力跟皇子联系,也就没有可能去扶植某个皇子搞政变,威胁皇帝或皇太子了。
相应地,贵族权力削弱后,由科举制产生的官僚和宦官开始增强,后者更容易管控。
这种博弈的特点是顺应和过渡,也采用了韩非子本篇说的,对官职权力的分割、对党友的伐断等技术。削减其权力,“要逐渐地来,好像月亮逐渐亏下去”。
作为中国式博弈,原则就是在因循中逐渐过渡,不用过激手段。具体方式有下面两条:
一是除去亲王府的官员任命权,这也就是下一节比喻的“削树枝”。
二是逐渐引入科举制人才,这就是“掺沙子”策略。
一推一拉,有推有拉,彼此制衡,这就是中国式博弈的策略。
5 一根竹竿上不能站两只公鸡
原文
一栖两雄,其斗㘖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将塞公闾,私门将实,公庭将虚,主将壅圉。数披其木,无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将逼主处。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公子既众,宗室忧吟。止之之道,数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数披,党与乃离。……探其怀,夺之威。主上用之,若电若雷。
作者智解
一根竹竿上不能站两只公鸡。一栖两雄(雄鸡),它们就会互相斗(指不要让身边的人发生猜疑分裂,像太子和后妻那样互相争,这不利于君主)。有豺狼在羊圈里,羊就不会繁殖(指有权臣)。一家有两个贵人,事情就做不成功。夫妻都执政,儿子就无所适从。作为人君,要经常削掉树枝中的一部分,使它稀疏。如果树枝太茂密,就把你家的大门堵上了(比喻臣下势力太大)。私家不断充实,国君家就会逐渐虚掉,所以要经常披其枝,不要叫它的枝子横伸出来。横伸出来,就会逼上面的主子了。枝叶太大,就会不胜春风,一吹就断了,危害到树干(指枝叶太大,风一吹,就折了,把树干弄折了,比喻害到君主。臣子是树枝,君主是树干)。要经常把树枝削疏,他的党友才疏离。探其怀,夺掉下属的威,这样君主才可以若电若雷。
(以上说的,总体来讲还是对于某个具体的臣子,要限制他的权力和势力,不能让他过于尊贵、过于富贵。一根竹竿上站两只公鸡,意思就是卧榻之侧不能容别人酣眠。)